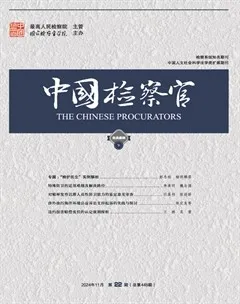网络直播销售假货类犯罪的认定思路
摘 要:网络直播销售假货类犯罪的打击,以刑罚的必要性和效益性为先,分层分类把握不同岗位人员的罪与罚,重点打击经营者、管理层及主播,对底层雇佣人员一般不作为犯罪论。以直播平台涉案账户电子数据证据固定、运用为中心,甄别有效订单,筛选出非法经营数额。假货销售价明显低于正品市场进货价或销售价的,犯罪金额不宜以正品价为参照值用市场价格比较法作价定罪,应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以同种品牌同种型号假货实际销售单价审计出非法经营数额。查扣库存货值可以同种品牌、同种型号网售假货单价计算出未遂部分犯罪金额。对电商企业或团伙型组织犯罪,每个主播团队之间如系独立带货分成,且不参与共同管理的,可单独计算销售金额。对一般违法的其他辅助人员,可以检察意见等形式监督职能部门对其行政处罚。
关键词:网络直播 销售假货 侵犯注册商标 行刑双向衔接
一、基本案情及办案过程
2021年12月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蔡思某作为奇航百货公司经营人,在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租赁一处仓储式库房,组建互联网直播团队卖货,团队成员有主播雷某、张某某,跟播蔡某某和冯某,另雇佣20余人从事整货、打包、客服等劳务性工作。该团伙销售商品有真有假,在“快手”直播间获取客户订单后,每天由快递员上门取件寄给顾客。经审计,共销售阿迪达斯、耐克、安踏等17种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金额146625.69元,其中衣服95031.94元,鞋子51593.75元(包含蔡思某、张某某合伙从上线党某某处购进阿迪达斯、耐克两种假鞋货值3万余元,已销售部分净获利13734.65元)。警方在库房起获待售假货货值922179.1元,其中衣服863196.24元、鞋子58982.86元。
2022年6月29日,蔡思某等人被立案侦查。2022年9月2日,警方以蔡思某等19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请检察机关审查逮捕。9月9日,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蔡思某、雷某,对张某某等17人以证据不足为由不批准逮捕。
2023年1月18日,检察机关以被告人蔡思某、雷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退回补充侦查期间,警方查明张某某单独与蔡思某协商卖假鞋,其使用自己的快手账号直播销售金额34515.3元,并给雷某提供部分假鞋的货源,雷某已销售金额17078.45元,累加上雷某的销售额后张某某的销售假鞋金额51593.75元。而蔡某某为主播雷某服务,和蔡思某、雷某夫妇构成共犯。2023年3月9日,检察机关依法追诉张某某、蔡某某。
2023年6月9日,法院认定被告人蔡思某等4人均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4年不等,并处罚金。被告人蔡思某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被告人雷某以自愿认罪认罚但法院未采纳检察机关缓刑量刑建议为由提出上诉。
2023年8月22日,二审法院对被告人蔡思某维持原判,对雷某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23年10月26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认定雷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改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8万元。雷某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2024年1月31日,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检察意见,对假鞋供货商党某某给予行政罚款3.5万元。[1]
二、网络直播销售假货案件办理难点及解决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的“销售金额”修改为“违法所得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司法机关在办理网上直播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时,如何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与违法所得、其他严重情节入罪标准的区分、不同岗位人员、上下游侵权产业链上异地管辖、涉案不同主体犯罪圈边界的把握、刑事打击还是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分歧。
(一)以固定电子数据为突破口,锁定犯罪嫌疑人
蔡思某案发系直播噪音扰民引起群众举报,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执法时当事人已藏匿,且账簿、电脑、直播设备等关键证据被销毁,警方只起获了库存假货和一些外贸尾货。蔡思某等人到案后拒不配合,上下游销售商不明,警方将侦查的重点放在搜集假货订单,以便计算销售金额,但侦查中发现网售的鞋服真假掺杂,以数以万计的消费者为中心来反推涉案金额难以做到,案件侦查一度陷入停滞。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确立以电子数据取证为重心,从“快手”后台订单数据中倒查销售额,与商品照片、上架代号及快递单等证据相互比对得出有效订单后,再鉴定实售假货的经营额。先是引导警方对雷某手机中的数据进行恢复,调取了聊天记录、微信及支付宝流水账单,并登陆其快手直播账号截取视频录屏36个,固定了该团伙犯罪的初步证据。同时提示民警奔赴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调取了涉案4个快手账号的大部分电子数据,获取主播雷某、张某某快手账号(粉丝15万+)200余万条销售数据。经比对梳理,删除退货、退款、退库、刷单等原因交易失败数据后,获取了真实有效交易订单信息,经蔡思某等人结合物流发货数据进行辨认,近200种商品中有17种假冒他人品牌的商品、共计40款型号的假鞋服被上架至快手平台销售。主播卖货时是以阿拉伯数字代替货物,检察机关经筛选比对后确定销售金额146625.69元,其中雷某销售衣服金额92068元、鞋类金额17833.38元,张某某独自用其快手账号销售假鞋金额34574.7元。另据快手后台获取的同种品牌、同种型号假货的销售单价,计算出库存货值922179.1元。在销售金额达不到15万元立案标准情况下,检察机关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的库存货值金额锁定蔡思某、雷某,并对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张某某、蔡某某提出继续侦查意见,核实两人是否跟蔡思某夫妇构成共犯。
(二)网络售假商品的非法经营额不宜以市场价格比较法作价推定
假货价值有厂商“鉴定”价、商品标牌价、实际销售价、市场平均价四种不同处理意见。但蔡思某案库存假货经品牌商“鉴定”高达2000余万元,商品标牌价是正品行货价,前两种价格明显失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分歧点在于是否采信物价部门按市场法的作价。检察机关认为,蔡思某从福建莆田等多地进货时,是以一包麻袋的重量计价,商品发货清单、进货票据即时销毁,仅剩转账记录,每种侵权商品的进货价、违法所得不明。假货品牌、种类、型号不一,已部分无实物,如以正品价为参照按市场法作价得出非法经营额,则远远高于其实际销售额,于法有据却又显失公允,争议较大,应以“快手”订单中每类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论。查扣部分的货值,仅以能匹对上、且查明订单中的同种品牌、同种型号单价计算出总额,对型号相同但不同期间销售价存在上下浮动的,以最低价计。据此由警方委托第三方机构作司法审计,即以侵权商品实际销售单价得出销售金额和库存货值。因每个主播之间是在独立的直播间工作,跟播蔡某某只辅助主播雷某工作,只系雷某的共犯,不应累加主播张某某的犯罪金额。
(三)宽严相济,分层打击,对一般劳务人员不以犯罪论处
警方对在库房“上班”的所有人员列为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审慎甄别加以分层处理:一是对组织者从严打击。蔡思某系经营者、负责进货、雇佣工人、收付款等日常运营管理,应对全部犯罪事实负责。二是对主播雷某、张某某,鉴于二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特别是雷某,检察机关在走访中了解到其是听从丈夫蔡思某吩咐直播带货,有自首情节、借钱主动退缴查明的鞋子部分的违法所得13734.65元,其系单亲家庭,母亲、婆婆身患重疾、女儿正读小学,夫妻俩被羁押后家庭陷入困境。检察机关委托社会调查,接到司法局同意将雷某纳入社区矫正意见后,对蔡思某和雷某宽严有别,对雷某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三是对跟播蔡某某、冯某区别打击。蔡某某系主犯蔡思某表弟,深度参与作案,月工资7000多元,并有小号直播闪电购,其到案后虽辩称不知情但检察机关根据证据依法追诉。而冯某是通过社会应聘而来,帮助张某某在直播时上架商品链接,修改商品信息,月工资1920元,不直接接触假鞋,其作用等同劳务岗,检察机关对其没有批准逮捕,后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是对底层打工者不批准逮捕。从事劳务岗位的15名妇女为附近村民应聘而来,工作时间不长、按件(打包一件快递赚1角钱)或按日计酬、多不清楚经营者是直播卖假货,不宜扩大犯罪的打击圈,均未批准逮捕,后警方作撤案处理。
(四)对主播、跟播及上游供货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一是补证主播张某某的犯罪金额。张某某使用自己的快手账号直播卖假鞋的销售金额为34515.3元,其中从党某某处购进的阿迪达斯、耐克两种假鞋的获利金额9841.07元。在库房查扣蔡思某跟张某某合伙购进的假鞋货值58982.86元。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标准有三:销售金额5万以上;尚未销售的是货值金额15万以上;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但已销售金额与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合计15万元以上。[2]张某某销售假鞋金额和尚未销售金额、违法所得均不够刑事立案标准。雷某售鞋金额17078.45元,但缺少货源等方面能关联上张某某的证据。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张某某后,引导民警补证蔡思某、党某某等人的证言、转账记录后,发现张某某为2021年年底新加入,跟蔡思某协商合作只卖鞋子,按三、七比例投资和分成,并为雷某提供货源,因此雷某“快手”账号销售的假鞋应当累加到张某某的销售额中,即张某某的销售金额为51593.75元。二是推定跟播蔡某某主观方面明知。蔡某某辩称不知道是假货,只是跟表哥蔡思某打工的,妄图以普通员工身份逃避刑罚。检察机关经反复审查直播录像发现,雷某在对商品进行展示,介绍商品的特征、面料、款式、价格时,蔡某某在现场帮助上架商品链接、修改商品价格,互动、烘托气氛来招揽顾客,他的淘宝订单也佐证其经常比对并购买过同种正品商品,而雷某直播间商品价是正品的一至两折,可以推定雷某主观应当明知雷某在直播卖假货,而其仍然参与且分赃,构成共犯。三是追缴部分违法所得。检察机关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顺藤摸瓜,找到外县鞋行老板党某某,查明了蔡思某从其处购买假阿迪达斯、耐克鞋子的进货价,通过销售价减去进货价,查明两种假货的违法所得13734.65元,并予以收缴国库。四是对“闪电购”订单未认定。蔡思某控制的两个快手账号销售的“闪电购”商品,有真有假,无法确定哪一种为侵权商品,且因网络拥堵等因素消费者账号后台订单查找不到,也没能从快手公司调取到完整的交易数据,销售金额不明,对该部分销售金额警方是以部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推算,理据不足,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检察机关起诉时未予认定。
(五)行刑双向衔接,全链条打击侵权违法犯罪
检察机关对销售假鞋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鞋店经销商党某某,根据我国《商标法》第60条第2款、《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2款等规定,认为党某某知假进假、转售给蔡思某、张某某两种假鞋销售额3万余元,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扰乱正常市场秩序,导致大量假冒名牌运动鞋流向不特定消费者,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应当对其进行行政处罚,2023年12月19日依法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2024年1月31日,市场监管部门对党某某给予罚款3.5万元,并根据检察意见会同属地检察院对辖区鞋市开展执法检查。
(六)规范快递行业经营,斩断电商直播售假发货通道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邮政、圆通分公司与蔡思某口头达成寄件协议,约定电商客户收件之后不再对包裹里的物品拆封检查。寄件方式是由两家企业为蔡思某提供空白的快递单子,蔡思某雇佣的库房打工者将待邮寄的衣服、鞋子和日用品打包好贴上快递单,每天下午快递员揽件后直接将包裹装车拉到营业部统一发出。蔡思某每天发货1200余件,隔日通过扫快递公司微信收款码或用支付宝转钱结账。蔡思某之所以能够利用“互联网+寄递”实施犯罪,反映出快递企业在收寄电商渠道大客户订单时,不执行开箱验视寄递安全规范,违规寄递侵权假货。检察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75条之规定,向邮政部门提出检察建议:一是对涉案快递企业处罚。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及《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把好禁止寄递关口。二是开展对快递企业电商平台渠道业务专项执法检查。对落实《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32条情况进行检查,快递企业对电商客户群,签订安全保障协议后应向邮政管理部门备案。三是加强寄递安全行刑衔接。落实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突出收寄源头安全管控,增加电商渠道邮寄假货违法成本。涉案企业据此整改后,当地寄递渠道售假发案率呈下降趋势。
三、线上直播售假类案办理思路
鞋服虽小,关乎民生。当前互联网电商平台已成为群众消费的主战场,网络直播平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是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打击的重点。围绕检察机关正在开展的“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聚焦网络直播带货产品质量安全,遵循“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路径,震慑网络平台侵权假冒行为,加强注册商标权人保护,以精准履职净化市场秩序,解决消费者急难愁盼,将直播带货新业态纳入法治轨道。
(一)以网络销售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锁定犯罪金额
网络直播具有移动性、互动性和即时性,“闪电购”更是一键下单快速完成交易。网络主播可以不受时间、地域限制,随时随地直播售假,反侦查手段类似“纸飞机”等密聊软件“阅后即焚”,并不断在智能化迭代升级,传统监管、侦查手段滞后且多失效。对线上销售假货类犯罪,去快手、抖音、快递等平台公司总部调证,按图索骥成为侦查常态。检察机关在介入此类案件后,应引导警方及时、全面调取电子数据,包括直播账号、直播平台、微信、支付宝、快递等数据,防止人为或因保存时效性问题灭失。对海量电子数据检察机关应杜绝拿来主义,要结合银行账户、送货单、快递记录、收货单、言词等证据搜集、锁定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3]一是对于完全售假型直播犯罪,应剔除失败订单、退货、退款、退库、为走量有订单但未实际发货等原因未交易成功、未真实销售、自买自卖的销售记录,甄选出有真实买家的有效订单数据;对于商品有真有假的,还应剔除真货部分数据;二是对于商品真假难辨型直播犯罪,证据不充分的应不予认定。三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违法所得数额可理解为获利数额。对有进货价的,以非法经营数额或销售金额定罪的同时,应扣减进货成本后得出获利金额,获利金额即是违法所得,起诉书中应指控并建议法院予以追缴。四是对查扣部分假货的货值,同品牌同型号的以对应的销售单价计算。对于因商品号码、批次、出售日期不一样存在不同销售单价的,以犯罪期间该型号商品的最低单价论,不宜按平均价核算。五是对于“闪电购”等电子数据不全、无法辨别商品真假型号只有销售金额的,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笼统计入犯罪金额。六是此类犯罪金额的认定,物价部门无法作价的,可由检察机关向警方提出审计思路,交由司法会计鉴定机构出具报告,通常不宜办案人员自行“估算”认定。
(二)统一司法裁判标准,谨防随意扩大犯罪打击圈
互联网电商“直播带货”分为团队型和个人型,销售商品一般真假掺杂,严控泛化犯罪圈。对团队型有组织犯罪,其运行模式一般为经营者、主播、跟播、其余人员多为商品售后的配货、打包、第三方物流等辅助人员。司法机关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枉不纵,精准把握,区别对待,对涉案不同岗位人员分类分层处理:一是重点惩处组织者、领导者和管理人员,包括团队的核心层、管理层和主播,以及其他发挥主要作用的骨干人员。二是对跟播的范围应作限制性解释。以直播过程中接触到产品与否为区分点,对协助主播活跃直播间气氛,配合主播介绍产品,引导直播氛围,宣传假货,完成促单的跟播,一般可以从犯论。对虽是名义上的“跟播”,但同从事一般性劳务勤杂人员所起作用相当,如美妆、设备调试、场景布置、商品整理等直播服务人员,该类人员在团队型直播售假案中,人数众多,未直接参与售假,多有钟点工,不属于实质的帮助犯,应谨慎入罪,极个别确有处罚必要的,可以相对不起诉等形式从宽处罚。三是对于不接触制售假领导层、无犯罪共谋的临时聘用人员,如上货、包装、客服、财务、售后、物流等底层普通劳务员工,一般不作为直接责任人员或从犯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其主观明知是假货,一般情况下亦可以“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检察机关更不宜出于案外等因素考虑折中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作相对或存疑不起诉,因一旦入罪标准泛化,反而不利于行业的综合治理。对普通员工,可视为证人,其正常合理的工资性收入,不能因是从犯罪的经营者处获取的酬劳既认为是违法所得进行追缴,即使有证据佐证工资报酬来源于售假赃款。四是对查获的假货认定为未遂。行为人为了网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实施的购买行为,不是犯罪预备,因为进货、定价、寻找买主等行为均视为销售行为的组成部分,是犯罪的环节。[4]
(三)分层分类监督,使违法者罚当其责
“直播带货”团队的商业价值uXTdiHQuerRP5sAEEMn56Q==除商品质量外,主播的影响力直接关联货品的销量。因此,“直播带货”型犯罪如公安机关只对经营者、幕后老板刑事立案的,原则上检察机关应当对主播、跟播等销售一线的直接实施者、参与者履行追捕、追诉监督职责。对非共同犯罪的低层级普通员工刑事立案的,应作羁押必要性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以监督公安机关撤案,如有违法行为且有处罚必要的,可以建议公安、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对其治安或行政处罚。另外,检察机关可以对电商平台经营者及上下游企业违规违法行为,向监管部门提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负面评价意见[5],以行业自律引领电商平台守法经营风向标。
(四)行刑双向衔接,高质效办好侵权案件
净化直播带货市场,需要消费者、企业、司法行政机关多方共享共治。检察机关秉持“三个善于”,开展“检护民生”专项活动,“治罪”与“治理”兼顾,以消费领域公益诉讼维护消费者权益,支持注册商标权人(或授权使用商家)以民事诉讼等形式打假维权,对于有赔偿意愿的侵权人、犯罪嫌疑人,自身联系被侵权企业(或国内外知识产权人)有困难的,检察机关可以搭建沟通桥梁,促成双方达成民事赔偿。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与知识产权等行政执法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特约检察官助理调查协作等工作机制加强配合,督促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日常执法稽查,对违法线索同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对不构成犯罪、情节轻微作相对不起诉的制假售假违法行为人,以检察意见等形式推动行政机关依法给予售假者以行政处罚。检府联动,提升电商行业知识产权保护质效,让“直播带货”人员有法律畏惧感,斩断其违法利益链条,让注册商标权人合法权益有保障,让消费者有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有力维护我国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