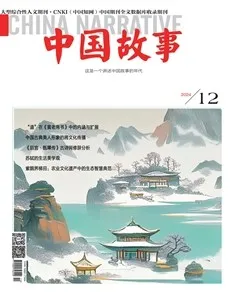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礼法合一
【导读】礼与法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两种手段,并且礼法交织,直至唐代实现礼法合一。礼法合一既体现在《唐律疏议》的立法制定上,也体现在《唐律疏议》的内容中。
一、“礼”指导《唐律疏议》制定
《唐律疏议》在制定之初就旁征博引儒家的思想观点,并从儒家经典中吸取了道德教化的思想。特别是在《唐律疏议·名例》中,提到十恶、八议、五刑等法律制度及其原则时,其引证更加频繁,其理论依据都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唐代的律学家在编撰法典之初就采用了两条立法原则:
(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儒家先贤推崇以道德教化来引导民众,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标。儒家学者推崇的伦理教化在《唐律疏议》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不论是《唐律疏议》的制定原则,还是其适用的臣民范围,甚至是定罪量刑的依据,都体现了儒家伦理教化的色彩。
在《唐律疏议·名例》中即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的说法。律学家将“德礼”与“刑罚”,也就是“礼”与“法”之间的关系阐释得很明确。两者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治理国家不可分离的重要手段与方式。但是两者的关系却不是平行的,而是“主”与“辅”、“本”与“用”的关系。《唐律疏议》中的许多条文都是在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尤其是维护三纲五常,这是《唐律疏议》的一大特点。在《唐律疏议》的制定及立法原则上,最能够体现“德礼”的,莫过于“名例”中有关十恶、八议和五刑的记载。《唐律疏议》在对十恶重罪进行评价时,直接采用了儒家经典《春秋》与《左传》的说法。无论是法典编纂者的身份,还是法典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乃至对十恶重罪的评判标准,都与儒家经义密不可分。种种迹象表明,《唐律疏议》旨在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并将其纳入国家法律。
《疏议》曰:“《周礼》云:‘八辟丽邦法。’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唐律疏议》在解释“八议”时,从久远的历史中找寻踪迹,认为周代的“八辟”是唐代“八议”的滥觞。《唐律疏议》将“八议”明确规定为: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八种,此八种身份的民众在犯了除谋反死罪的其他罪时,对其需多加宽赦,经皇帝批准后方可定罪量刑。八议中的“议宾”是对先代贵族的一种尊重和优待,以彰显唐朝的大国风范。《唐律疏议》将“议宾”归为“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为解释何为“先代之后”,还引用了《诗经》中的“有客有客,亦白其马”之句。诗歌当中的这位客人,可能指的就是殷商旧臣微子启。周朝建立后大肆分封诸侯,其中就分封了纣王的兄弟微子于宋,统帅殷商的遗民,并以宾客的礼仪待之。最能直接阐释“议宾”含义的,莫过于《疏议》言:“昔武王克商,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氏之后于宋,若今周后介公、隋后酅公,并为国宾者。”不仅从久远的历史中寻找有关“议宾”的诗句,还将周后介公、隋后酅公同样视为“国宾者”,给予先代贵族浓浓的优待,以存其后。
笞、杖、徒、流、死统称为五刑,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严酷刑法。五刑依据违法的不同程度施以不同的处罚,而关于五刑的刑种、刑罚等级的制定都与儒家经义有关。儒家认为圣人制定五刑以威慑百姓、维护统治,使民众知道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
(二)“于礼以为出入”
《唐律疏议》的另外一条制定原则就是“于礼以为出入”。唐代律学家在编撰《唐律疏议》时,通过解释儒家经典和律条来阐明律例,将古代宗族观念、儒家传统思想充分融入法典条文中,使儒家经义贯穿《唐律疏议》制定、实行的整个过程。儒家传统经典中关于道德的基本论述,成为《唐律疏议》的思想基础。
二、礼典、礼文入法
《唐律疏议》在编撰之初,就有儒学大家参与其中,将唐代的经学、礼学思想融入法典,一些律文甚至是从儒家经典中直接摘用而来,未作增减。比如“八议”一词直接来源于《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中的“八辟”,律学家们依其照抄改编而来。《周礼》云:“八辟丽邦法。”也就是说,唐代法律中有关八议的相关规定是从《周礼》照搬过来的。
同时,在《唐律疏议·户婚》中,我们可以看见有关“妻无七出”的相关问答:
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
早在东周时期,社会上就已经有了“七去”的说法,但在礼制和法律上都并未形成完整的规定,因而对当时的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影响有限,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汉代时,“七出”“七去”虽然名称不一,但两者在内容上却是一致的。“七出”在汉代已正式成为社会层面所认同的“礼”,影响着百姓的婚嫁。直至唐代,“七出”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不仅得到社会的全面认可,而且还被纳入法典之中,并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唐律疏议》里的“七出”“三不去”与《大戴礼记·本命》中的论述大致相同,都是儒家经义的体现。
《唐律疏议》中除了有从“礼”中改编而来的律文,还有直接照搬儒家经典的律文。诸如《唐律疏议·名例》中关于“矜老小及疾”的法律条文,直接来源于儒家经典《礼记》。具体规定如下:
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
显而易见,这是从《周礼》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和《礼记》“悼耄不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衍变而来的。《周礼》三赦之法与《礼记》“悼耄不刑”,都是针对老幼之人以及智力障碍之人而设,对弱势群体在法律上予以优待,这不仅与儒家矜幼、怜悯的思想保持一致,更体现出儒家思想对法典的影响力。《唐律疏议》中有关不孝罪的规定为:
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
汉代法律虽然也有对不孝罪的相关规定,但《唐律疏议》对不孝罪,甚至是不孝的行为都给出了详细的定罪规定。除了不得与祖父母别籍异财、不得违反祖父母教令外,辱骂、殴打祖父母更是不孝重罪,要受到严厉惩处。《唐律疏议》对不孝罪的规定较之汉代更加明确,与儒家提倡的长幼尊卑之说完全契合。因而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对《唐律疏议》影响深远,后继王朝也遵从《唐律疏议》的相关法律规定,未作出大规模修改。
三、定罪量刑以礼为准则
儒家提倡百姓有尊卑贵贱之分,恰如《礼记·乐记》所言:“礼义立,则贵贱等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这是传统礼仪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所在。而这一点同时也是《唐律疏议》立法和施行的重要依据。
唐朝时期以“礼”别贵贱,以“礼”定尊卑。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统帅民众,《唐律疏议》将民众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的权利与义务都与其身份息息相关,其在法律上的地位也不同。最尊贵的莫过于皇帝,是天然的第一等级,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律的权威由皇帝赋予,因而可以说,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只是统治的工具。第二个等级是贵族和官吏,两者属于王朝的上层集团,他们“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对皇帝负责。贵族和官吏又因不同的身份地位,细分为四个不同的层级,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最高者为皇室宗族、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称为“议贵”;其次为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职事官,二品以下、五品以上的散官和一品以下、五品以上的侯爵,称为“通贵”;再次为五品以下、七品以上之官,以及七品以下、九品以上之官。
他们在身份地位上天差地别,在法律地位上也有明确的高低贵贱之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唐律疏议》中关于五刑二十等的规定。《唐律疏议》依据不同的社会身份,有差别地对案件进行定罪量刑,即同罪异罚。按照唐代的社会等级,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对臣民进行生杀予夺,因而皇帝无罪可罚。对其他的三个阶层,除谋反、谋逆无可赦之外,其余诸罪皆可依据身份地位进行相应的减刑或免刑。身份越高之人,减刑的程度越高,甚至能够免于刑罚。在有官与无官犯罪的问题上,有官之人可以利用官位进行“官当”,以此减免刑罚,而无官之人则严格执行《唐律疏议》中的相关规定,依法论处。《唐律疏议》在这一点上进行了详细规定,体现出强烈的等级思想。
在《唐律疏议》中,有官犯罪依据官位大小而接受不同的刑罚。例如《唐律疏议·名例》中关于官员私家犯罪的处罚规定:“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这里对官位卑贱的九品以上、五品以下官员的处罚较轻;而官位重的五品官员及以上,则加重处罚力度。
可以说,《唐律疏议》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法律的适用范围和定罪量刑上,都是以儒家的“礼”作为核心。凡是违礼之罪,无论有官与否都要加重处罚。法律又会因其不同的身份地位而减免刑罚,十恶重罪不在减免之列。
四、结语
中国古代礼法合一的历史起源较早,经历了汉朝引经注律的发展,直至唐代《唐律疏议》颁布,标志着礼法合一的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唐律疏议》影响深远,是后继王朝法典编撰的范本。
参考文献
[1]岳纯之.唐律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丁佳.论德主刑辅在唐律中的体现[J].法制与社会,2011.
[3]徐华.儒家思想对《唐律疏议》影响之管见[J].宜宾学院学报,2009(2).
[4]张晋藩.唐律中的礼法关系[J].人民法治,2019(13).
[5]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5).
——基于主人公“五品” 流汗表现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