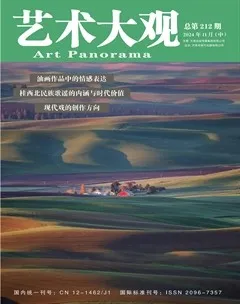艺术·真理·事件
摘要: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以现象学的方法,通过对作品的直接描述,认为艺术就是真理的自行置入。而真理在这里是放在存在论上而言的,它是无蔽的真理观。真理作为“无蔽—遮蔽”的解蔽过程,具有事件发生的含义,这一事件被在作品中发生的“世界”与“大地”的争执所争得和保存。基于此,可以说艺术就是作为真理发生的事件。对艺术与真理之关系的重思,是在反思如何回应艺术作品中存在的真理问题。
关键词:艺术作品的本源;艺术;真理;事件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艺术与美相提并论似乎不成问题,甚至在一段时间里,美学不言自明地成为研究艺术的科学。当然,这里面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艺术作品总是与审美、感性相连,真理问题却总是与抽象、普遍相关,是偏理性逻辑而非感性体验,艺术与真理相提并论倒是有些令人惊讶。但事实上,自荷马时代起,艺术与真理就被放在一起讨论,虽然那时往往是从真理方面去否定艺术。同样,到了黑格尔这里,虽然他认为“艺术是绝对真理在感性领域中的一个自我展开过程[1]”。艺术可以说是真理阐发的事业,但最后也会被更加高级的辩证反思和概念逻辑所扬弃掉。难道艺术果真达不到真理的水平?还是说艺术与真理有着另一种可能的关系?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重思了这个问题,打开了一条新的反思艺术与真理之关系的道路。
一、《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艺术与真理的关系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以“物与作品”“作品与真理”“真理与艺术”三个部分推进他的艺术之思,其中在“物与作品”最后一段中他写道:“艺术就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2]”如果我们去发问艺术是什么,这便是我们能从这篇文章中得到的回答。仅从字面上来看,艺术很明显地就与真理有了联系。虽然在这里直接给出了海德格尔对艺术的看法,但仅是单纯记住这个结论对我们进一步去思考艺术是没有太大帮助的,真正重要的应该是去追溯海德格尔的思路,看他是如何道出这句话的。
《艺术作品的本源》开篇就解释了“本源”(Ursprung)一词的含义:“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2]”也就是某个东西的本质之源。追问艺术作品的本源,就是追问艺术作品的本质之源。但这样就带出了一个循环:艺术作品、艺术家与艺术,三者互为本源。若以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会陷入循环论证的死胡同里。如何走出这个循环,关键在于所用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这样说明现象学:“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2]”直接描述作品,悬置理论前见,这是现象学的方式,以此出发,海德格尔首先对梵高的作品《农鞋》进行了一段描述,并且认为在这幅作品中就有真理的置入。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农鞋是器具,器具就有“有用性”(Dienlichkeit),这似乎对我们来说是自明的看法,但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地追问了有用性又是基于何处呢?他认为,有用性植根于“可靠性”(Verläßlichkeit),即说,在器物对我们有用之前,它首先得是可以被依托的,“只有在可靠性之中,我们才能发现器具实际上是什么。[2]”而对器具可靠性的发现,不是通过对器具的理论考察,而是通过《农鞋》这幅作品所看出来的。
“通过这个作品,也只有在这个作品中,器具的器具存在才专门显露出来了。[2]”每一天我们都在与各种各样的物打交道,和它们在一起:大地的坚实、鲜花的芬芳、阳光的和煦……我们觉得它们是可依托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它们都是日用而不知的,这就是我们自然生活中的样子。但艺术家却将这种日常生活中我们难以言说的朴实、充实、厚重的可依托感保存了下来,并且向我们开显出来。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通过一幅绘画作品看到了一个存在者实际是什么,这个存在者进入了它的存在之无蔽(άλήθεια)中,海德格尔称其为真理的发生,这恰好是在作品中完成的。于是,在艺术作品揭示了存在者的存在性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对艺术下了一个定义:“艺术就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2]”
梵高所画的“农鞋”并不是在模仿某种关于农鞋的理念,《农鞋》道出的器具存在也并非通常我们所停留在的关于器具的有用性的观念中。作品所道出的不是某种超验观念,毋宁说在其中展现的是发生的真理和真理的发生。海德格尔对艺术的追问给出了艺术的某种宏大叙事,这是真理的视野。到了这里,似乎我们能体会到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革命下的真理观是不同于以往将真理视为永恒理念,或者某种基于正确性的相符合。那么海德格尔的真理观是什么呢?
二、无蔽真理观——真理与事件之关系
在海德格尔看来,希腊人将我们认为的真理命名为无蔽,也即“无—遮蔽”,就是不再遮蔽的东西。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褫夺式的词语——没有遮蔽,就是对遮蔽的褫夺。不再有遮蔽,即从遮蔽到无蔽,就是一个解蔽的过程。“‘真理’乃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状态才得以呈现其本质。[3]”
这种真理观是由一种否定得以贯彻的,这种“无蔽—遮蔽”之间的否定关系被海德格尔称为“源始争执”。争执体现着无蔽真理的动态属性,它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状态,相反,它一直处于遮蔽与无蔽之间的交替过程中,所以它是生发性的。于是,“真理的开启不能看作某种稳定的结构,而毋宁说它总是作为(一个)事件[4]”。
真理被理解为事件在于它的生发性质,就是说得把真理理解为某种不断被解释、被重新书写或被改造的东西,而不是理解为被赋予了某种稳定性和永恒性的客体存在。无蔽的真理从来不是现成的某种东西,存在者的无蔽是需要不断地去解蔽,这本身就是一个进程,“每一种真理都拥有自己的时间[2]”。
所以当每一个解蔽阶段完成之后,不允许我们将此阶段得到的解释当作完成了的并保留下来,而只能被算作处在过渡的范围内,这就能说明无蔽真理的事件属性,即它的不断发生和生发,它不断地处在过渡中。所以我们对“事件”的理解不能陷入一个误区,即把事件当作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东西,比如伽达默尔评海德格尔所作的《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演讲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哲学事件”,这里的“事件”就是指1935—1936年间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的事实,强调说明那件“事”,这与我们所理解的“真理事件”相异。“真理事件”乃是一个处在源源不断的涌现过程中,是生成性的。
为了能更加形象地描述无蔽真理的这种动态的事件属性,我们以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引用的瑞士诗人迈耶尔的诗《罗马喷泉》为例:
罗马喷泉
水柱升腾又倾注
盈盈充满大理石圆盘,
渐渐消隐又流溢
落入第二盘圆盘;
第二层充盈而给予,
更有第三层拂扬涌流,
层层圆盘,同时接纳又奉献
激流不止又泰然伫息[2]。
海德格尔认为,这首诗中已经有了真理的置入。结合之前我们关于无蔽之真理的描述,我们再来体会一下真理作为事件与真理作为流俗意义上所理解的正确性的符合的不同之处。很明显,这首诗没有临摹喷泉实际的样貌,根据这首诗我们并不能指认出这描绘的是哪个喷泉,因此就这方面来说,这首诗里面并没有关于内容与对象的符合。但我们能感受到其中充满了某种流溢之感:水柱升腾又倾注、渐渐消隐又流溢、层层下落……“真理”也是这样充满着流溢流动之感,也是有层次或层级的,是动态发生的,它就像诗中体现出的那种层层展开、层层流溢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将真理理解为事件时,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它是一个生成性的发生,真理同样也是一个不断打开、展开的过程。我们把作为无蔽的真理理解为一种事件,更准确地说,是事件的发生和发生性的事件。
三、艺术与事件之关系
通过将艺术与真理相连,艺术中有着真理的置入,并且这种真理是无蔽的真理观,即它是一种遮蔽和无蔽的争执事件,于是我们可以说,在作品中呈现着真理事件的发生。但是否就能直接将艺术与事件相联系却还要打个问号,因为如果不再继续追问这个“如何呈现”的问题,即在艺术作品中到底发生着什么,从而能让我们将艺术与真理事件建立联系?海德格尔说,作品中发生着“世界”(Welt)与“大地”(Erde)的争执。
作品是一件制作品,它开启并建立一个世界,海德格尔称这个世界为历史性民族的世界。但这样的世界不是某种对象性的存在,世界并不是摆在我们面前可供我们打量和计算的,它是指在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命运中,某种本质性的决断之路的敞开,也就是说在此世界中,我们通过作品能看到属于对我们自身世界的一种以源初方式展开的解释,某个历史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艺术作品中认识到自身的身份意义并且得到强化,作品揭示出了所有历史纪元的真理。那么在作品中,这个世界的建立是如何可能的呢?靠制造大地。
德文中“大地”dieErde对应英语的earth,通常我们译为地球或土地。但这个术语所表达的与一个行星的概念或那种质料的堆积相去甚远,它是指被古希腊意义上的自然,即“涌现”(Φύσις)所照亮的东西,它自身也是一种涌现,涌现着一切返身隐匿的东西,“在涌现者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dasBergende)[2]”。
我们说世界是建立在大地之上的,那么作品中的大地因素是什么呢?大地是涌现着的庇护,是世界返身的置回之所。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作品中的大地不能被看作作品材料,毋宁说它是作为作品之为作品的在场,即它的具体显露是作为某种唤起注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地就是作品的此时此地,是每一次世界的开启都要返回的地方。
世界是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它不允许任何的锁闭,世界总在试图超升于大地之上,因为世界在作品中的呈现往往会成为一种观念问题,比如最常见的一类句式“这幅作品表达了……”。当我们更多关注于表达的内容时,世界就越发挥它观念的一面,似乎不再需要大地了,它就是它自己本身。与世界的敞开相对,大地作为庇护者是自行锁闭的,它总想将世界扣留于自身内。于是,作品中发生着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在这一争执中,无蔽之真理就被争得了:“真理唯独作为在世界和大地的对抗中的澄明与遮蔽之间的争执而现身。[2]”
作品将制造出的大地与建立起的世界之间的争执保持在自身内,作品本身就发生着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事件,而这个事件所争得的是更加原始的事件发生,也就是真理的事件。艺术是真理的自行置入,一个真理事件通过作品中的另一个事件发生——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被带出,那么我们可以说,艺术被理解为事件,而且是真理发生的事件。
从非本源意义上讲,一个作品的诞生本来也就是一个事件的发生,它进入历史中,与我们在生活中相遇。但不仅如此,作品自身还为一种更加本源的事件提供发生的场所。基于此,我们对作品的欣赏也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也即我们不再是单单面对一个客体,而是参与进此真理事件的发生中;我们接受着作品,这也就要求我们需要对作品所带出的真理事件作出决断和筹划,作品因而改变着我们的言说。
四、结束语
把艺术理解为事件,首先,从源初意义上来讲,这是对“本源”一词的回归,作品中的真理事件作为一种发生,作为一种存在事件的爆发,这比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更加原始;其次,在现存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成果十分富饶的当下,以往“能否对艺术下定义”的发问早已变成“是否应该对艺术下定义”的问题,甚至在当代诠释学的背景下,任何解释和理解都有其正当存在的权利,所以若将“艺术作为事件”看作某种定义性的东西,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在妄想成为定义的那一刻就已经失败了。
于是本文的核心观点,“艺术作为事件”,它并不意指对艺术下定义,但也并不意味着这个观点是描述性的,因为关于描述性的观点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潜藏着对艺术评价的放弃。所以,关于“艺术作为事件”更适合的发问应是:当这种观点被提及时,它想表达什么?仅就本文论点来说,这样的回答指向着真理问题。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后记中告诉我们,对艺术之谜的思考并不是为了解开它,而是在于去认识它。就像美国当代艺术批评家特里·巴雷特的著作《为什么那是艺术?》(WhyisThatArt?)的书名一样,对艺术的思考已不再是思“艺术是什么”,而应更多关注“为什么是”以及“如何是”,更多地去思考和反思这样一种情形:当我们谈及或创作艺术作品时,我们在想什么,我们面对着怎样的处境,以及我们如何去回应艺术中所发生和带出的真理事件。
参考文献:
[1]王德峰.艺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2]马丁·海德格尔.依于本源而居——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M].孙周兴,编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
[3]马丁·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詹尼·瓦蒂莫.现代性的终结[M].李建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基金项目:2023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项目“艺术与真理、事件之关系研究——以海德格尔《艺术品的本源》为例”(项目编号:23C01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若宇(1995-),女,四川成都人,硕士,从事哲学、西方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