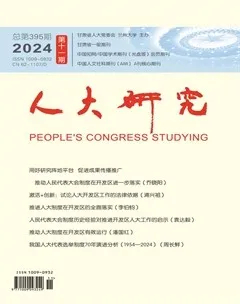激活+创新:试论人大开发区工作的法律依据
一、“开发区人大工作”还是“人大开发区工作”
先讨论一下有关概念的问题。除了本节节题上两个概念外,尚有“开发区人大工委”还是“人大开发区工委”?笔者觉得,上面提到的两组概念中,各自的后者均不会被误读。很明确,意即:某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开发区的工作,以及某级人大常委会在开发区设立的工委。而各自的前者均容易被误读成好像开发区也设立了一级人大。
显然,在我国,凡需要设立一级政府的行政区域,都必须先设立一级人大,由人大产生与监督政府。凡不需要设立一级政府的行政区域,均不设立一级人大,这是宪法的规定,也是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决定的。
比如,街道不设立一级政府,只设立某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办事处),因此,街道就不可能设立一级人大。2015年修改地方组织法后新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大常委会可以在街道设立“工作机构”(非一级人大)。那么,是“街道人大工委”,还是“人大街道工委”呢?与前同理。
有观点认为,现在的浦东新区人大与政府,既是作为上海市市辖区的浦东新区的一级人大与政府,也是浦东新区开发区的一级人大与政府——以此说明:开发区也可设立一级人大与政府。
这是一种误读。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浦东新区人大与政府”,结束了原有浦东地区由多个市辖区(县)政府分治的状况。新建立的“浦东新区人大与政府”,只是作为上海市市辖区的浦东新区的一级人大与政府,而不是浦东新区开发区的一级人大与政府。
还有,上海市所辖的“浦东新区人大与政府”建立后,浦东新区开发区原有的管委会就不复存在(被撤销),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原有管委会“升级”成了“浦东新区开发区的一级政府”。
二、激活与用足人大开发区工作的现成法律依据
近年来,我们讨论较多的是人大要不要在开发区设立工作机构(如工委),以及如何创新这方面的法律依据?这当然很重要(后面将讨论)。我们是否也应当讨论一下:如何“激活”与“用足”那些早已存在却长期“休眠”着的法律依据,以此来推动人大的开发区工作?
例如,监督法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有关的人大常委会应当去“激活”与“用足”这一法律依据,选择本行政区域内开发区的总体工作或者某一方面的工作(预决算、民生实事等),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政府和“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至于如何有效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监督法还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笔者一直希望能够“当真用足”人大制度的“制度空间”。其实,可以“激活”与“用足”的现成法律依据还有不少。比如:人大常委会的地方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以及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等。
如果我们不去“激活”与“用足”那些早已存在的法律依据,而让它们继续“休眠”下去,成为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提醒要避免的“装饰品”“摆设”,那么,再好的法律和制度、再多的规定和依据,也不能转化为实际的效能。为此,笔者建议,既要重视从无到有的“创新”,也要重视“激活”“用足”。
实践表明,“激活”“用足”的过程中也往往包含着“创新”。比如,无锡市有效“激活”了地方组织法规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大“可以设立……其他专门委员会”中的“其他”二字,以及市辖区人大“可以设立……等专门委员会”中的“等”字,便创新了全国首个人大开发区(专门)委员会,进而还创新了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县(市)两级人大开发区(专门)委员会的体制,而且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能。
三、探索与创新人大常委会开发区工委的法律依据
随着开发区的区域成倍扩大、人口迅猛增长、功能走向综合、权力明显膨胀,从事或熟悉开发区工作的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人大常委会应在开发区设立工作机构!事实上,不少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已经在开发区设立了工委等工作机构。
这些机构发挥的功能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协助有关人大常委会(包括人大开发区专委会)开展有关开发区的工作,提供来自开发区的民意和其他信息;二是联络开发区内的属于不同层级的人大代表,组织和服务代表开展学习、培训、视察、联系选民等活动;三是召集代表联席会议,向本开发区的党工委、管委会反映民意、提出代表的意见建议,对管委会开展柔性监督等;四是负责办理人大常委会所交办的监督、选举以及其他工作。多地人大常委会在开发区设立工作机构的实践表明,设置此类机构是必要的。
问题是,设立此类工作机构是否缺乏法律依据?有人认为,地方组织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这个“等”字,就是我们需要的法律依据。其实不然。
应当注意到,他们所引用的“设立……等工作机构”,其立法本意是指在常委会内部设立协助常委会履职的工作机构,而不包括在常委会之外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何以见得?这可从该条的第二、三两款中得到印证。
假如从第一款中真能引申出“可以在常委会之外设立类似工作机构”的依据,那么,立法机关为何还要先后增加第二款和第三款(关于在地区、街道设工作机构)的规定呢?在笔者看来,该条的第一款绝不包括设置在人大常委会之外的工作机构。因此,此条款就不能作为人大常委会在开发区设立工作机构的法律依据。
这就需要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地方组织法,允许有关的人大常委会在开发区设立工作机构——类似人大常委会设在街道的工作机构。然而,立法不是由立法者拍脑袋即可完成的,需要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为前提。实践者期盼立法者提供法律依据,立法者则期待实践者提供实践依据、研究者提供理论依据。
实践依据方面,如江苏无锡、四川成都、浙江平湖等地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里有一个难点需要请教各位:为了坚持依法治国,我们确立了一条原则,即“重大改革举措应于法有据”。难点在于:要修改法律,需要实践依据;实践依据又需要来自于实践探索;为修法而开展的实践探索本身必然于法无据。这该如何办?有人说,我们的原则仅限定于“重大”改革举措。笔者以为,越重大,恐怕越难解上面的难点,此其一。其二,如何区分“重大”与“非重大”?
是否可以认为凡涉及修法的均属“重大”?或者,修法所涉及的事项也可分出“重大”与否。那么,人大常委会在开发区设立工作机构之事是否属重大?笔者注意到,全国人大创新“专题询问”时,于法无据。是否说明此事不属“重大”?另外,人大在街道设工作机构,在修改法律之前,多个地方在“于法无据”情况下,已建立起人大街道工作机构的试点。说明此事也不属于“重大”。目前,人大开发区工作机构的试点,也呈现当年人大街道工作机构试点的状况。本人几年前提出“相邻参照”思路。但有一位知名宪法学者不赞成此思路。
理论依据方面,全国开发区人大研究会举办过十次理论研讨会,取得了一批探索性的理论成果。《人大研究》杂志也刊登过多篇研究人大开发区工作机构的论文。研究会黄会长2023年出版的新著《我国人大制度视域下开发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研究》,获得了乔晓阳主任的赞扬。他说,这部著作“对于我们研究、制定和完善开发区人大工作有关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弥足珍贵”。
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各级各类开发区数量众多、情况复杂、差异很大,必须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总结各地实践探索经验和理论探索成果,厘清若干关系,把握发展目标,形成修法思路。总之,各方还须继续努力,为促进人大开发区工作机构的立法条件日臻成熟作出贡献。
作者简介:浦兴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上海市人大原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政治学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