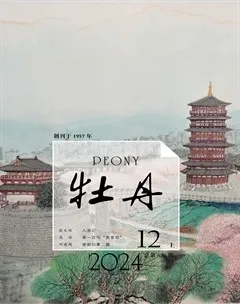在写作中取悦自己
《彼岸花》即将付梓之时,夜深人静,看着案头凝聚着我巨大心血的书稿,我突然从焦虑、疑惑中走出来了,放下了。内心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对文学、对人生的敬畏。这种情感的真实和强大,甚至超过了我对作品的期望。
我在想,是从什么时候,我开始牵手于文字,又是从什么时候,文学走进了我的人生乃至灵魂,以至自己在负重劳顿的中年,依然能醉心于此,痴情不改。
一
我想,文学之于我,已经不是一条成功的途径,而是谨严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憩息的精神家园。从少年到中年,文学熏陶了我,引领了我,丰富了我,因为文学,我的人生多了一份充实和快乐,也增添了一抹令人陶醉的色彩。
依稀记得,八十年代初,那时我上初一。
一天中午放学,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因狭窄的大门被拥堵在校园,忽然几个不认识的学生对我指指点点。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迅速拉展自己的衣服,还下意识摸摸头和脸,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被人注意的啊!
下午是作文课,老师先读范文,题目是《记一个熟悉的同学》。老师分析说,别的同学如果写一个同学,大都会写某某同学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双明亮的眼睛,穿的什么衣服等等。而作者写的是到同学家小院后,看见同学背对着门蹲在地上干活,他便悄悄地走过去蒙上同学的眼,同学用手摸摸他的手,又摸摸他的鞋,然后叫出他的名字。老师说作者这个角度选得好,虽然没有直接说两个人如何熟悉,如何关系好,但通过动作细节让读者分明感到二人的熟悉程度不一般。
老师说这篇作文他特别赏识,上午已经给毕业班念过了。
老师对着大家说,你们猜,作者是谁呢?
大家互相瞅,一时判断不出。老师冲我笑笑大声宣布:韦忠民。
那一刻带来的惊喜、骄傲,让我至今难忘。
上了高中,很多次,老师让我用钢笔或毛笔把作文抄写好,或张贴学校大门口,或在校园白杨树间用绳子穿起来让大家观摩。看着自己的文字在白杨树间飞扬,我感受到的是对文学最初的敬意。
对于写作,我情有独钟,因为老师的表扬,源于老师的欣赏,更得益于喜欢读书和思考。
写作,逐渐成为习惯,融入我的生活。
二
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是那篇《我家的“小耗子”》,写的是我家儿子的趣事。在《洛宁报》刊登后,编辑对我说,也可以向洛阳日报或晚报投稿。很快,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走在洛宁街头,开始有人喊我“小作家”了。第一次用电子形式投稿题目叫《芝麻与西瓜》,也是在《洛阳日报》,那时我刚开始学打字,也刚刚注册了一个电子邮箱,投稿两天后就见报,几乎没怎么改动,很快还寄来了六十元稿费呢。
之后,有那么几年cQ7hfNDPgPGLdzjVmRDdSw==,我发表的更多的是论文,大概有四五十篇之多,写来也算得心应手,皆源于写作的基础了。
2003年,我开始创作诗词,那时候是思如泉涌,见什么写什么,一挥而就,虽然没有什么意境,平仄也不讲究,确实浅薄得很,但我兴致勃勃,一发而不可收。很快我被吸收为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2011年1月,我的诗集《兰溪子杂吟》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为我加入省级作协积累了重要条件,2013年,我被批准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没想到,诗集很受欢迎,2015年 1月出版社再次印刷 5000册。
其间,我笔耕不辍,一直坚持写作。渐渐地,有人约我写序、写评,我成了教师中的“文人”,校长中的“作家”,亦算小有名气。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总要有一项爱好,只有这样,在业余时间,尤其是退休后生活才能丰富多彩、充实丰盈,才不会觉得无聊和无趣。我的骨灰级“爱好”就是写作。写作带来的快乐、甚至烦恼,令我的生活拥有更长久的满足。这种满足是物质远远不能代替的。
三
在钢筋水泥筑起的城市里,到处一片喧嚣、热闹,我借写作排遣孤独,享受那份独有的寂寞,以及由此衍生的痛苦和烦恼,当然更多的是恬然和开心,一种奋斗感和成就感。
古人有句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在别人觥筹交错之时,在别人灯红酒绿之时,在别人萦回梦乡之时,在别人逛街休闲之时,我独坐电脑前,孤独却津津有味地敲打着键盘,输入着枯燥却有无限灵性的文字,这样的时光对于我来说,如神仙一般逍遥。从王维的清幽里走出来的我,一个人和文字这个“情人”真诚相约,饱含深情的“爬格子”做苦行僧。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我在给自己导演一场戏,同时,自己又是戏里的演员。尽管导演不专业,演员不专业,只知道自己导得认真,演得投入。我想这就够了。所谓尽吾志,可以无悔矣。
我很享受这种方式,也常常沉浸在它带来的幸福之中。正如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曾说起的一句话:“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也是感受的一个过程。”
四
《彼岸花》本来是一本文集,包含小说和随笔两部分,后来听朋友建议,便改为小说集和随笔集。
随笔是我平时即兴所写,内容涉及童年往事、旅程回眸、家乡美食、亲情友情、生活情调、感事抒怀、笔耕偶拾以及文学评论等,多是随性而为的琐碎小事,颇显芜杂。遑论主题、意义和体裁,常常得鱼忘筌,得意妄言。不讲文采和技巧,或许写实有余而空灵不足,更不敢奢谈什么深厚的意蕴,一如我自己率直有余而含蓄不足的性格。文因乘兴而起,所以我称作随笔,而不敢妄称散文。
所谓小说,因为是处女作,所以敝帚自珍,自行结集收录 ,是源于一份对文字的痴恋。
豆腐块写多了,我就想尝试其他体裁的创作。小小说,牛刀小试,一投稿就被正式刊物采用发表,这让我很兴奋,产生自信,也激起我更高的创作热情。
创作中篇小说,这也是想法已久的事,妻子听后却将信将疑。当我把初稿递给她,她不禁愣了一下,颇为吃惊。
于是,妻子成了小说的第一读者、第一编辑,为《彼岸花》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从文通到字顺乃至标点符号,再到前后细节连贯、情节衔接、文句严谨等等。
仅就小说中用的医闹案例来说,她就觉得说服力不强,便帮我上网查找,后来仍然不满意,竟然跑到医院三番五次寻上卫校同学找到符合情景的案例才罢休。因为改稿而废寝忘食,对妻子来说,也是常事。《彼岸花》的顺利出版,得益于妻子的莫大支持与帮助。
《彼岸花》是我的第一个中篇,没有完整的时间去潜心写作,只能忙里偷闲,边写边拜师,虚心求教,创作历时两年半。
五
彼岸花是一个神奇的传说,充满着彼此相爱但又不能相见的悲剧色彩。
借助这个神话传说,我一点一线拆开,让它贯穿在整篇小说里,每次不经意的出现,都围绕小说主题,为主人公的悲剧一步步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受章回小说启发,在创作时,我想融进些诗词,让小说更典雅,有些“文化味儿”,但水平有限,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创作起初并没有这个婚外恋情节,结尾是钟思扬在山西与人合伙开的煤矿赚了大钱,事业如日中天,终成正果,如愿以偿,是传统的皆大欢喜结局,小说篇幅也不长。初稿完成后,总感觉薄弱,心里并不满意。偶然一个机会,从一个朋友的“曼殊沙华”网名受到启发,突然有加入“爱情”之想法,便开始“捯饬”,打破原有结构,重新布局谋篇。继而拉大了框架,拓宽了篇幅,由短篇变成了中篇,结尾变为悲剧。这也是我追求完美使然,我总想另辟蹊径,有点不寻常才好。算是对自己的挑战。
爱情,永远是生活亘古不变的主题,更是文学创作的不竭之源泉,或许从心底,我也有一种“戏不够,爱情凑”的潜意识。于是便借小说演绎一番,演绎效果如何,任由读者赏析评判了。
六
第一次创作小说,随着篇幅的拉大,人物、场景、情节、心理活动等等都很难驾驭,甚至人物起个什么名字也是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尤其是前后呼应,贯穿始终,对于我难度更大,许多时候简直有写不下去的感觉。坚持吧,道阻且长,放弃吧,不甘心。看电视,读报纸,坐公交,饭桌上听人说话,所有场合我都会留意,期望多多少少受到启发或者用得上而能够成为小说中的素材。有时为了写好一个情节、设置一个场景,常常茶不思,饭不想,觉难眠。投入其中,累并快乐着。由此也体会到古人写作“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苦乐。同为性僻耽佳句,但终难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境界。
七
写作如十月怀胎,喜悦与顾虑同时萦绕心头而五味杂陈。怀疑自己写作水平,犹如女人产前抑郁一样。
出书费神。
每次校对后感觉可以了,谁知随后放上几天再看还是能发现问题;跑印刷厂无数次,麻烦工作人员重新修改排版 N次,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内文版式、封面装帧、握口设计、纸张挑选、字号大小等等涉及内容,我都会不自觉地操心,这些平时根本不留意、不懂的事儿,这时一直在心头萦绕。为此跑书店,翻看别人的书,成了文集定稿后的又一任务,期望奔波忙碌中受到启发,看别人小说临时抱佛脚恶补,希冀得到参考和借鉴,期待正式出版的书能够让自己称心如意、读者赏心悦目。印刷厂先后打印用于修改的文稿,若摞起来,足有等身之高。
为改稿而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也习以为常。我又有诗曰:废纸三千张,推敲费思量。笔端万千事,一字夜未央。
出书如女人生孩子,既兴奋,又紧张,更充满期待。
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自己读书太少,练手太少。这时,发自内心钦佩那些影视剧的编剧、作家、导演,感觉他们都真的很了不起。
许多人对我坚持写作赞赏不已,我则惴惴不安。确如贤弟所言:创作对于作者而言,是寂寞而甜蜜的事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于我而言,那就是苦乐自知。
八
我,并不祈求或者奢望成为一名知名作家,只为不忘初心,让写作习惯保持下去,用心记录生活中的点滴,表达瞬间看到、听到、想到而萌发的那份情感。
与写作为伴,我的生活丰富、充实,尽管劳神费力,但一直快乐着!
是的,为取悦自己,我一直寂寞地坚守着。正如夜来香选择在夜晚开放,并不是为了讨好谁,是它的自然属性。假如拙作能如那悄然吐蕊夜晚开放的夜来香,有人能枕着它的芳香入梦,我就满足了,欣慰了。
人至中年,对文学,我仍有一颗天真的心,一颗景仰的心。
韦忠民,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小说和散文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