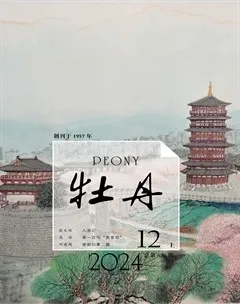最忆是《牡丹》
彭忠彦,河南汝州人,1961年生,汝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长篇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报告文学集等15部,主编文化专著10多部,并有小说和散文获奖,散文《瓷乡听瓷》被《散文选刊》选载。
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最值得我珍视和回忆的当属洛阳市的《牡丹》。结缘《牡丹》,从青春到花甲,一路牵手同行,倍感“牡丹”人亲,《牡丹》情深,《牡丹》香醇,《牡丹》育人;《牡丹》铸魂。
《牡丹》杂志的原主编张文欣老师是我走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家乡的一所小学任民办教师,张文欣老师在洛阳地区主办的《洛神》杂志当编辑。我在教书之余热恋文学,锲而不舍地向《洛神》投稿,换回的是张老师一封封温馨的退稿信。退稿信中那一行行娟秀的毛笔字,一字字透彻的把脉,一句句饱含深情的激励,温暖着我的心房。1982年,小说处女作经张老师编辑在《洛神》发表。1986年机构改革,张老师调往《牡丹》杂志社,及时写信告诉我新的联系地址。虽然飞鸿传信,但彼此并不曾谋面。
1989年秋天一个周末的傍晚,我从九峰山下的家乡赶回单位,灰头土脸的我正在洗漱,门被轻轻地叩响了。一个戴眼镜的儒雅中年人站在门前自报家门:“不速之客——张文欣”。我的大脑在短暂的空白后,方才明白是恩师驾到。原来,张老师回乡探亲,车出故障坏在了化肥厂附近,才跑到劳动人事局找我。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张老师和我同乡。
同乡情义浓,文友真情重。从此,每去洛阳必到《牡丹》编辑部小坐。经张老师引荐,我认识了文质彬彬的梅艺辛、幽默诙谐的乔仁卯、寡言内向的任剑等编辑老师。此时,我虽然还暗恋着文学,但繁重枯燥的公文撰写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又怕被扣上“不务正业”的帽子,只好和文学忍痛割爱。好在被公文挤压的日子里,还有《牡丹》陪伴,吮吸美文的芬芳,似回到温馨的《牡丹》家园,文学的灵光在脑海闪烁,希望的星光在远方召唤,灰暗的心情爽朗打开,精神气儿饱满起来。
1996年春,我从许多人羡慕的“管人”“管官”的劳动人事部门脱身而出,转调清贫冷落的文联当“爬格匠”,重续文学梦。翌年,我发动文友征订30多册《牡丹》,每期全部寄到文联,然后我再一一送到文友的手里。此后,汝州市文联、作协与《牡丹》互动不断,我们邀请《牡丹》编辑部老师来汝州讲学、游览、采风,也接受《牡丹》杂志社应邀,来洛阳赏牡丹、游龙门、开笔会。一朝结友,终生互动。2011年10月29日至30日,洛阳市文联原主席、作家协会原主席、《牡丹》原主编张文欣,和《牡丹》老编辑乔仁卯等一干人,应汝州市作家协会之邀,赴汝州九峰山采风。其时,九峰山尚待闺中,是一处保持着原始风情的处女地。此行,张老师创作了《九峰山杂吟》五章。其中的《楚长城》和《山村》最为精彩。“垒石为墙三千年,依山据隘界牌关。故国明月今犹在,楚声悄然汇中原。”(《楚长城》)。“枝头甜柿点点红,村边秋圃香满垄。饮茶啖果浑如归,一席家常品乡情。”(《山村》)。乔仁卯编辑宝刀犹健,诗风朗润,一首《九峰山记忆》自由诗,写尽九峰山的风骨风情,流露出诗人的怜悯之情,也寄托了诗人期盼宝山开发造福山民的情怀。我记得采风的第一天中午,在我同学家吃红薯面包白面皮时,不见了乔仁卯编辑。原来他溜进了一户农家,喝山楂大碗茶,品面疙瘩汤,和躺在病床上的大哥聊天,听主妇大嫂倾诉。别时,收下大嫂送的柿子,并把票子偷偷地压到茶碗下。张老师、乔老师等九峰山采风的诗,2013年收入我主编的《神韵厚土寄料镇》一书。
岁月流逝,真情绵延。2020年,洛阳市作协申报中国作协年度定点深入生活扶持写作项目——“天青梦”成功。《牡丹》编辑杨亚丽是该项目的主创人。这个项目是写我家乡的汝瓷,定点深入生活的“点”就是我的家乡汝州。作为文友,我自告奋勇担当杨老师采访的向导。也是这样的缘故,我们的接触和交往多了起来。送她来汝州报到的是洛阳市作协副主席、《牡丹》主编王小朋,一个清瘦干练、英气勃发的青年,文采飞扬,为人随和。杨老师汝州深入生活期间,王小朋主编多次来汝州查看项目进度,每次来就到汝瓷企业调研,听取项目进度情况,解决采访中遇到的困难,吃地摊——生活简朴,作风务实,给汝瓷专家和汝州文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鱼沉水底。杨老师天天“泡”在瓷厂,深入一线采访,收获颇丰。一天,我正陪同杨亚丽老师采访“大国工匠”朱文理先生,电话响了,是张文欣老师打来的。他说回家乡了,要和亚丽见个面,看她在家乡深入生活是否习惯,收集资料和采访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其实,我已从朋友、中医名家宋兆普口里得知,张老师患了病,身体虚弱,正在接受治疗。是夜,张老师邀请他高中时的同学、原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厂的厂长李聚万等人,为杨老师采访提供方便。席间,我看见张老师比过去消瘦了许多,吃得少,滴酒不沾。我望着这位硕德达尊的长者,心潮翻涌,不胜热泪盈盈。记得是2000年夏末一天,《牡丹》张文欣带着著名作家阎连科回汝州讲课。阎老师穿着朴素,相貌憨厚,脸上写满真诚。阎老师授课结束后,又为我们的内部刊物《沧桑》题词——“沧桑即文学”。一直忙到傍晚,张老师才挤出时间回家看望九旬老母。张老师才华横溢,本应成为一个当红的大作家,可是他却甘为他人作嫁衣,把精力都放在扶持和奖掖文学新人,从事文学艺术事业组织、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上,以奉献为乐,以牺牲为荣。
杨亚丽不负众望,定点深入汝州生活3年,中国作协扶持写作项目圆满结项,9万多字的《天青梦》由《大地文学》62卷头题刊出。《天青梦》以严谨的构架,质朴的文风,灵动的语言,形象地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汝瓷人前赴后继,奋力拼搏,使断代800多年的汝瓷天青釉釉重放异彩,盛世圆梦,华章璀璨,反响良好。作为《天青梦》诞生的见证人,我也引以为荣。
最忆是《牡丹》,圆我作家梦。1998年《牡丹》3期,在“河洛方阵”栏目发表我的短篇小说《故乡人物》;2001年1期,发表短篇小说《黑蝴蝶》;2002年4期发表短篇小说《戏匪》;2004年6期发表短篇小说《叫响我的名字》。这几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都是韩国平老师。韩老师为人真诚,处事低调,老成持重,作风严谨,对编辑工作精益求精。小说《戏匪》《叫响我的名字》的题目不但在封面展示,而且分别都在“本期导读”栏目中做了介绍。“本期导读”是这样推介《叫响我的名字》这篇小说的:“黑社会头目致死人命,送喜礼的县长牵扯其中。为帮县长度过政治危机,县长家族齐动员,一干老人等演绎出一系列荒诞闹剧——本家兄弟‘随官生’冒县长之名四处招摇,企图为县长消灾祛难,然而天网恢恢……这个荒诞故事,让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反腐主题”。编辑老师的肯定鼓励,再度唤起了我的创作激情,坚定了我的创作自信。从2019年到2022年,我先后在《牡丹》发表散文《东坡的三足洗》《东坡兄弟的梅瓶》《我那亲亲的谷子哟》,以及短篇小说《大爷的单方》等。
人生匆匆,转眼已逾花甲。回首流年岁月,展望黄昏,面对浮躁社会,笑看功利红尘,把一颗纯净的心灵放入《牡丹》,把真情的倾诉交给“牡丹人”,灵魂共振,愉悦人生。
责任编辑 李知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