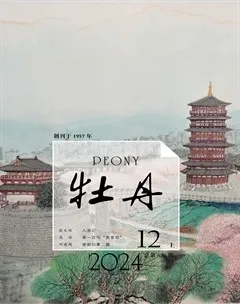大伾山的秋天
许光宇,现居洛阳,作品见于《洛阳日报》等报刊。
1498年春天,阳光明媚。在三月的春闱上,浙江余姚举子王守仁(字阳明)终于走到了八股取士的巅峰。三试及第,名列二甲第八名。
说是浙江余姚人,实际上王阳明少年时代便随父王华迁居北京。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释褐即为翰林院修撰。他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王阳明也自幼勤奋好学,文武兼修。考中进士后,明帝国给王阳明的第一个职位是工部观政,相当于建设部的实习生。万丈高楼平地起,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文科教材的他转入了一个榫卯链接、开山磨石的理工新领域。按时上班,照点下班。一个未来的帝国政治明星、军事奇才开启了充满理想与挣扎的宦海沉浮。28岁的守仁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在扫地端水倒茶、誊卷公文的平凡工部俗务之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放家国情怀实现梦想的平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一年,王阳明非常敬重的名臣王越去世了。王越同样是科举立身,文官提兵,在西北边疆沙场屡建战功,扬名立万,最终病死于甘肃张掖任上,享年七十三岁。王越一生数战,三次大捷。从红盐池大捷、居宁海大捷到贺兰山大捷,与元蒙部落瓦剌、鞑靼部落死磕。在垂暮之年,他仍然在大漠戈壁,追击鞑靼部落,取得了贺兰山大捷。他死后,明孝宗也念其忠勇,辍朝一日,并且委派工部最得力的人才负责王越的安葬事务。
这个人就是王阳明。
也许,王越早就预感到这一天了。叶落归根,在大名府浚县县城大伾山山麓西北向的祖地里,王尚书为自己预留了百年安眠的吉壤。
逐梦仕途,征战沙场,扬名立万。从一介书生到监察御史到大同巡抚到三边总兵、经略哈密,期间屡屡而被人弹劾,湖北安陆流放,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宦海的风浪,他完成了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使命。王越终于能在一个听不见战马嘶鸣、浮言善佞、互相攻讦的地方安安静静地睡上一觉了。
在前方传来消息的时候,家乡也在为他的到来做最后一次的准备。
君子之风,山高水长。王阳明对于王越充满了崇敬。
离京赴浚县,为王尚书的身后事督造坟茔,这是王阳明的第一次钦差外放。彼时,少年得志、睥睨天下。像十五岁时单枪匹马、出居庸关、胡地巡边一样,进浚县县城。乘船进入浚县县境后,王阳明从城北屯子境善化山脚下的卫河码头上岸,沿途考察风土人情,骑马到县署报到。一个南方的温情士子以疾风的节奏进入了工作状态,一介书生以武官的气质登场大明官场舞台。文官武行,这也许暗合了的王阳明以后的人生起伏。
“中秋朔”,也就是阴历八月初三的日子,尚书坟茔顺利开工,王阳明终于得以闲暇,一登青坛山了。
说是山,确实矮了点儿,海拔一百多米,相对高差七八十米,但的确是山,而且是石质的山。黄河在北宋之后已经在山脚下向东改道至山东菏泽,早已经是阡陌纵横、乡野鸡鸣,旷野里,山上的寺钟声时而悠远的飘来, 太行余脉,伏地百里,在此,终于龙脉一收了。
他在《登大伾山诗》中写到此山景象:
晓披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
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
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
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
那一天,他们清晨出发,远望烟雾缥缈,隐约听闻远处缥缈的钟声,仿若遁世而出。王阳明忍不住感怀历史,沧海桑田,风吹水湍,河流终成良田。
远处看山不似山,近处观山山是山。时隐时现的龙洞喷烟吐雾,镇河大佛峰头阳光普照。岁月的变迁,时光的流转,在这一刻变得抽象而具体。
作为一名新科进士,政治表态还是必不可少的。诗句沿袭了殿试八股的颂圣结构,在尾联点题:登山北望,似又看见金銮殿之上的天下英主忙碌而威严的身影,此差一定不负皇恩,保证工程质量好、进度快。让京城放心,让家属满意。
也许,读书人的家国情怀、人生抱负,就是从小处着眼,从组织一个规模不大但是众人瞩目的小工程开始的。
工程进展顺利。南方人的精细、读书人的严谨还是靠得住的。科学组织,工期合理,质量可靠。要诀是,把干活儿的工匠队伍按照军队编成,按边关守卫应急打仗的思路进行时间管理,事半功倍。顺带还把兵家阵法、攻防守退、器械运用、后勤保障演练了一遍。缺点是工作节奏快,工匠们有些累。谁能想到,除了凿石封土之外,还得配合这位精力充沛的新科进士演练兵法阵法呢。所以,当王阳明离开的时候对知县说,这些工匠拉到边关可以直接当正规军、特种兵使用了。
转眼已是深秋,工程也临近扫尾。王阳明在浚县公干期间也交了不少读书的朋友,给大家讲了几次公开课,讲历史、讲圣学。如何应考答题,顺利敲开登科取士的大门,也许是青年学子们问这位新科进士最多的一个问题吧。
九月初四,王尚书入土为安。王阳明得以闲暇,应几个读书人之约,带上两瓶好酒,二次上山论道。
这一次是九月初九,王阳明登高之余,感怀历史变迁,写下了《大伾山赋》。全文文字书写工整、端庄清秀。这篇赋后人补录进入了王阳明的著作集注,后学、老乡两次刊刻石碑,原文原书传续,立于大伾山顶怀禹寺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块碑还是让人给忽略了。毕竟,彼时它仅仅是一位工部观政、新科进士的青涩之作而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五百年后,仍然可以通过这篇习作揣摩这位有明以来、仅有的三位进士出身之一、以军功封伯的鸿儒大家的哲学之思,其心胸之广、格局之大,可容山海,可视古今、可追先贤、可励后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浚县,王阳明登临了一个海拔不高的龙尾之山,留了两篇传之后世的佳作。这一年初冬,王越的后事办理完毕,王家非常满意,执意要将王越生前所用佩剑赠给王阳明。王阳明盛情难却,只得带着宝剑,乘舟返京。
不经意间,浙江余姚的王阳明,这个弘治年间的新科进士,又给这个多有摩崖石刻、文人风骨的青坛山增添了一抹旷达的绚丽色彩。五百年后,一代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文人风骨在这个历史文化名城、龙尾小城得以继续诗意传承。这座山,这座城,又印证了一句话:山不在高,贤过留名;城不在阔,有儒则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