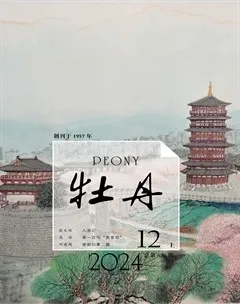入洛记
张文欣,1948年生,河南汝州人,现居洛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洛阳市文联主席、洛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牡丹》文学杂志主编。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发表和结集出版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文学评论300多万字。作品曾获《人民文学》《莽原》和洛阳市“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等多种奖项,被多次转载、选载,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和韩文。
我原籍汝州,原来叫临汝县,虽然当时也在洛阳地区行政区划之内,但家居农村的我,一直到十八岁高中毕业的1966年,还没有到过洛阳。
家中的叔父曾在洛阳上过学,也有到过洛阳的亲戚,但似乎对洛阳的话题也不多,农村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土地村舍和县城的生活模式,节假日从来没有奢望到洛阳走走看看。那时候也藏着梦想,上大学还想去更大的城市呢。
高二的时候,空军要在高中学生中招收飞行员,我们班一位同学一路过关,参加了在洛阳的体检,尽管最后还是被刷了下来,但他毕竟是到过洛阳的,于是体检的经历还有洛阳的见闻就成了他骄傲的谈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洛阳的大街上也是砖铺地哩!”
1966年夏,高中毕业那年,突然,大学考不成了。同学们那时似乎也并不怎么沮丧,反倒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这一年9月初的一天,奇迹发生,我们全班同学竟然乘汽车直奔以前总觉得遥不可及的洛阳。过程不必细述,似乎荒诞,似乎不合逻辑,但却是真实的:车是县委办公室安排的,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刚拉过煤,但并不影响一群激情燃烧的年轻人一路欢笑高歌。
这是我第一次进洛阳,但洛阳并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卡车一直开到洛阳火车站前的广场,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又踏上了从成都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因为太突然,也太仓促,也许还有紧张和激动,我竟然对洛阳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我第二次来到洛阳,是在1968年夏天。当时已是我们高三学生在高中的第5个年头,但仍没有正式毕业。根据学校革委会的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出差外调,先后到了开封、郑州等地,这一天夜里坐火车到达洛阳。人生地不熟,我们一路摸索来到了市中心百货大楼附近的国际旅社。登记住宿的时候却发现价格高得吓人,已经后半夜了,却还是要收一天的费用,这不是太不划算了吗?两人一商量,干脆就躺在外面花坛的水泥台子上凑合。夜深露浓,凉意渐侵,迷糊了一会儿就感到浑身不舒服,于是就又坐起来。我们面对的就是中州路,洛阳最繁华的街道,此时却寂无人影,偶尔有汽车驶过,车灯明晃晃地照过来,又照过去。
突然想起了曾经听说过的一件趣事:说是我们县里几个干部来洛阳开会,商量到一个大饭店撮一顿,吃喝之后结账,却发现价格之高远超他们原来的预料,几个人掏空了衣袋也没凑够。尴尬之余,连忙推选一个能干的出去想办法借钱,最后总算交了饭钱狼狈而出。这是县城里流传甚广的笑谈,有名有姓,想来也不会是瞎编胡侃。他们是干部,在洛阳城里还免不了出洋相,何况我们两个穷学生?露宿街头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天刚蒙蒙亮,我们就直奔长途汽车站而去。
后来又先后来过几次洛阳,但都是来去匆匆,没有停留,印象较深的一次是1970年夏天,在洛阳竟连续住了五六天。
高中毕业离校之后,短短二年,角色却已经变换多次,此时的身份是修焦枝铁路的民工,或者说是民兵。因为当时焦枝铁路是三线建设,战备工程,代号叫4050。参加修路者,都是按军队编制,一个县一个团,一个公社一个营,然后还有连、排、班。洛阳地区的叫二师,师部就在洛阳。我只是我们临汝团骑岭营的一名民兵,至多算是营里的文书之类。50万大军,奋战8个月,焦枝铁路竟已经铺轨通车,我也算这个奇迹的参与者、见证者。
虽说已经铺轨通车,但还有许多收尾工程没有完成,为了便于来往的运输,二师调用了洛阳铁路分局的一辆轨道车。轨道车实际上就是装上了铁轮子的客运汽车,可以坐人也可以拉货。车上有两个师傅,却只管开车,师里决定往车上派驻一个联络员,负责车上和沿线各民兵团、营之间的联络。我突然就成了这个联络员,是营教导员,也就是我们公社的一位领导直接给我分配了任务。我们营建了伊川的白银坡车站,轨道车有时就停在这里,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上车当联络员的原因。
轨道车编号是287,于是我也就成了287车上一个编外的乘员,经常在新修成的焦枝铁路上来往奔驰,往北到过黄河大桥北,往南到过襄樊,沿线的车站差不多都有过短暂的停留。在洛阳这一次是因为要加油,还要修理水泵轴,车就停在东站货场外边的一条支线上。
两位师傅干完活都回家了,我就留守在车上。这里离老城近,抽空就去老城的街上转悠。二师的师部也在附近,师里曾办一份铅印的小报,叫《焦魏战报》,当年4月我还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笔名“文兵”,曾有过去报社看看的念头,后来又被自己掐灭了。那几天就住在车上,地处城东一隅,偏僻荒凉,四周空寂无人,心中免不了有些惆怅:已经22岁了,却仍然没有正式工作,像一棵风中的蓬草,四处飘荡。写了几首诗,却依然是豪情满怀的样子,比如写过黄河铁桥,是“风催樯帆动,旗卷大河红。光武应惊嗟:铁龙伏黄龙!”写“游隆中四首”时,其中一首多少隐喻了一点自己的心境:“躬耕陇亩意不躬,身隐隆中不隆中。若谓饱食无用心,陈情表策何日功?”
一年以后,我终于结束了“生世如转蓬”的状态,被招工到观音堂煤矿子弟学校当了教师。观音堂煤矿地处三门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回家探亲,坐火车先经陇海线,再转焦枝线,洛阳是必经的中转站。那些年,虽无数次经过洛阳,但只是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尝尽了旅途的酸甜苦辣。洛阳也渐渐有了几个熟悉的朋友和同学,有时候,也会去探望一下。有一次,乘候车的空隙,跑到洛阳军分区找到老朋友渠世忠,他那时是宣传科的干事。我们也算文字之交,他爱写诗,听说我去了煤矿,特意找出一本孙友田写煤矿生活的诗集《石炭歌》送给我。情谊殷殷,令人感动,这本诗集我珍藏至今。
1978年来了,这一年我已经30岁。这一年的两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或者说使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一件是国家的大事,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至今仍认为这次会议对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件事关涉我个人,这一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我作为“老三届”成为洛阳师专中文系的学生。
我又一次来到洛阳,来到地处洛阳郊区安乐窝的洛阳师专校园。洛阳在我的心目中渐渐丰厚起来,除了古典诗词文章中的洛阳,还有耳闻目睹的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的微笑,王城公园牡丹花的艳丽,弥漫着古色古香气息的老城,都使我一步步走近洛阳,融入洛阳。还有那种温暖蓬勃的、向前向上的时代气息也在时时鼓舞着我。在校学习期间,也发表了几篇作品,其中一首诗歌就发表在洛阳地区的内部刊物《豫西文艺》上。
1981年春,洛阳地区文联成立,文学刊物《洛神》创刊,人员紧张,来到学校物色适合当编辑的学生。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鹏老师推荐了我。他们让我写了自我介绍的文字材料,后来不久就反馈说,回去已经做了汇报,并上报宣传部,没有异议。我当时很高兴,因为当文学刊物的编辑和我的志趣相符,况且又是在洛阳。但临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洛阳地区文联的领导遗憾地告诉我,他们原以为报到宣传部就可以了,却没有报到人事局,因此这次没有文联的名额指标。
临门一脚,球却踢飞了,心情当然沮丧。但文联的领导安慰我说,你只要争取分到地直单位就可以了,其余的事我们来办。
我又一次出走洛阳,一路向西,来到崤山余脉马头山下的豫西师范学校,当了一名教《文选和写作》课的老师。豫西师范,正是洛阳地区直辖的学校。
在豫西师范,也是我很有意味的一段人生经历,从最初的“被冷淡”,到后来的“被重视”,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我的个人境遇经历了戏剧性转折。这令我欣慰,也常令我深思。其实,我遵循的还是自己的原则:人生不管到了何种境地,都要靠自己的勤奋努力,用实绩证明自己,这才是正道。这一段经历,我曾在另外的文章中叙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1982年6月,我在豫西师范的“观摩课”教学讲评刚刚结束,也收获了许多赞誉褒奖之词。恰在这时,地区文联的赵团欣受领导委派来到学校,向学校领导递交了地委宣传部要求我到《洛神》编辑部工作的函件。随即,我于当年的7月正式来到地区文联报到上班。后来我才知道,地区文联的领导为了我的调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先后三次到豫西师范协商,其中就有时任地区文联副主席的仝杏轩老师。
地区文联和《洛神》编辑部当时就在地委北边的大院里,一幢三层小楼上。这个大院面积很大,有行政机关,也有家属楼,还有许多荒芜的空地。刚创刊的《洛神》势头很好,创刊号上就有一篇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我被分配当小说编辑,和我搭档的就是赵团欣,有人开玩笑,说有你们二位,我们的杂志一定能欣欣向荣。但是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一道难题:给张宇谈退稿意见。当时张宇还在洛宁县,已经是有名气的作者了。他有一部中篇,领导们很重视,但讨论后还是决定退稿,却让我这个新人来谈。不过也有道理,当时分工是把来稿按区域划分,洛宁在我的分工范围。有趣的是,两年以后,张宇被提拔到地区文联当了主席,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宿舍是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吃饭在地委机关食堂,第一次在洛阳有了固定的工作之所,食宿之地,应该很满足了。但是,人性中却总是藏着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家还不在洛阳呢。
家是什么?结婚之前,家是父母,结婚之后,家就和老婆孩子联系在一起,不然为什么说结婚是“成家”呢?那时候在地委食堂吃饭的,大多是所谓“一头沉”的干部,有的是因为家属是农村户口,也有的是因为工作夫妻分居两地。在机关吃大锅饭也有好处,有时和有些部长、局长也能凑在一个桌上,和他们说事儿就方便容易许多,记得张宇还写过一篇小说,标题就是《饭友》。
一年多后,1984年春,由于组织和领导的关心帮助,我们全家迁来洛阳,妻子调到地直机关工作,儿子转到地直中学上学,我们家的户口也在王城路派出所入了户籍,成了名副其实的洛阳人了。这里离王城公园很近,每天早上,我还可以到公园去跑步锻炼。当时心中高兴,还想写一篇散文,拟题为“家在王城”,可惜后来一直没有成文。
有意思的是,当时编辑部的成员,全部来自农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编辑部主任许桂声老师,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来自偃师;编小说的赵团欣和编散文评论的杨炳彦,来自宜阳;资格最老的编诗歌的李清联老师,原是拖拉机厂的工人诗人,他最初也来自孟州农村;而文联副主席仝杏轩老师,则来自新安县。他们来洛的路径大多也是曲曲折折,各不相同,但背景都涂有明显的时代色彩。机缘巧合,我们共同踏进了《洛神》这座“命运之门”。
1986年春,河南全省实施行政区划调整,实行市带县的体制,洛阳地委和地区行署撤销,三门峡市升格为地级市,原洛阳地区所辖的15个县市分别划入洛阳市和三门峡市(只有我的老家临汝县划归平顶山市)。原洛阳地区的干部要分流,大部分西去三门峡,留在洛阳市的对口安排,《洛神》已明确也要西迁。
是去,还是留,我又一次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地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去三门峡,并说将拟任我为文联副主席。当时我已任《洛神》编辑部副主任,负责集稿和二审,老实说我对《洛神》是有感情的,但我对洛阳同样也有很深的感情。洛阳深厚的文化底蕴,壮美的山水和城市风光,还有那种特有的融汇四方的胸怀和气度,都深深吸引着我。就个人的性格或气质而言,我总觉得我并不适合做行政领导,也没有“当官”的欲望,我更喜欢具体的业务工作,能在洛阳这样的城市从事文学事业、编辑工作,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
我最终选择留在洛阳。尽管过程也很复杂和艰难,但组织部的领导最后也对我的选择表示了理解。
1986年5月,《洛神》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当年第1、2期合刊完成了编辑和印刷,我站完了最后一班岗。6月,我正式到洛阳市文联报到上班,第一项工作,就是以洛阳市文协(市作协的前身)的名义,在解放军外语学院组织文学报告会,请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和马云鹏做报告。
我的“入洛”之路漫长而曲折,从初入到最后的确定整整二十年。但想一想,开始也并没有定下明确的目标,每一次机遇,每一步转折都带着时代的印迹。
古人大约也是这样吧,陆机入洛,噪起才名,那是遇到了需要他的环境和时代。同样有才华的梁鸿却因为到洛阳写了《五噫歌》而遭到皇帝的追捕。白居易、欧阳修在洛阳的行迹声名,也与他们在洛阳的任职和时势相关。
洛阳厚重的历史自不待言,新的时代更使这座城市增添了魅力和光彩,也给一代又一代来自四面八方的“入洛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们进入洛阳的背景不同,路径各异,但都能够迅速融入,生根开花,他们在这里生活、成长,建设、创造,共同打造着洛阳城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 李知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