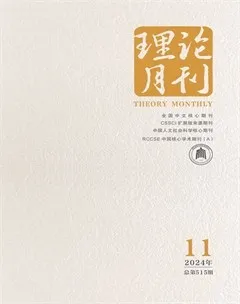胡塞尔陷入唯我论了吗?
[摘 要] 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历来被指责为唯我论。虽然在“第五沉思”中他声称已经揭示了唯我论的假象,但这依然没有阻止之后的研究者对其现象学提出唯我论批评。其中一些批评者认为,即便同感问题得到澄清,胡塞尔哲学中的唯我论问题依然存在。其理由在于: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始终未被动摇;在胡塞尔那里缺少与超越论自我真正同等源初的他人。这些理由显然不够充分,可从三个方面反驳这一批评:其一,重新解释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强调其认识论特征;其二,揭示超越论自我与交互主体性经验的区别;其三,说明他人作为与“我”同等源初的构造主体的可能性。
[关键词] 胡塞尔;现象学;交互主体性;他人;唯我论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11.016
[中图分类号] B51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11-0148-11
作者简介:胡文迪(1992—),女,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现象学研究者大都会同意胡塞尔对同感和交互主体性的讨论旨在说明世界的客观性。不过在相关著作和手稿中,他更明确提到的是现象学所面临的唯我论指责。对此,无论是在早年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10/1911秋季学期讲课稿)中,还是在较晚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中,人们都可以找到相关说明。在这些文本中,胡塞尔也明确宣称,借助对同感的现象学分析,唯我论假象已经得到揭示。因此,现象学,尤其是超越论还原之后的现象学,不应该再被指责为唯我论。
在批评者眼中,胡塞尔自我辩解的力量是微弱的,超越论现象学依然被认为是唯我论。这些批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在以《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为首的文本中,胡塞尔对同感的分析并不成功,“结对”“相似性统觉”等概念并不足以解释我们对他人的经验。但仍能在胡塞尔现象学内部对胡塞尔澄清同感的方式作出修正,以说明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黑尔德(K. Held)。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胡塞尔在有限程度上澄清了同感,克服了笛卡尔意义上的唯我论,但由于现象学的主体性特征,他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超越论的唯我论。因此,超越论现象学必须接受唯我论的标签。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托尼森(M. Theunissen)、瓦尔登费尔斯(B. Waldenfels)、孙小玲等。
胡塞尔对同感的现象学分析尽管存在瑕疵,但通过在其内部进行一些修正和解释,完全可以证明:胡塞尔在其现象学体系内成功澄清了同感,并揭示了唯我论假象。这大致符合第一种批评的立场。然而,由于胡塞尔没有充分解释超越论交互主体性及其与超越论自我的关系,第二种批评也显得十分合理。但如果人们从胡塞尔的角度理解超越论自我的作用、作为超越论主体的他人,以及超越论自我同他人及交互主体性的关系,这一批评便会不攻自破。因此,本文着重考察以托尼森等学者为代表的批评,在澄清超越论主体、交互主体性及其关系等问题的基础上,对这种批评作出回应。
一、胡塞尔现象学面临的唯我论指责
在讨论交互主体性之初,胡塞尔就预料到了对其现象学的唯我论批评,他也对这种批评作出了回应。这里不再重复这类批评,而主要关注澄清同感之后他再一次面临的唯我论指责。在“第五沉思”中,在借助结对和相似性统觉说明了对另一个自我的经验,也就是陌生经验(或同感)之后,胡塞尔说出了下面这些易受批评的文字:
(1)在超越论的具体中,与这个共同体相对应的是一个相应敞开的单子共同体——我们称之为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我们几乎无须说,单子共同体纯粹是在我这个沉思着的自我中,纯粹来源于我的意向性而为我地(für mich)被构造出来的,然而是作为这样的共同体,它在每一个在“他人”这种变式中被构造出来的对象那里被构造为同一个,只是在另一种主体显现方式中被构造,并被构造为其自身必然带有的这同一个客观世界。
(2)唯我论的假象被消解了,尽管这句话保持了基本有效性:所有为我而存在的东西,最终都从我自身、从我的意识领域得到了其存在意义。1
在通常的解读中,这两段文字都表明他人和单子共同体是“我”的同感的意向相关项,两者在“我”的意向性中被构造为“为我”的存在。尽管共同体也在其他自我中被构造,但总的来看,共同体和其他自我最终依然是超越论自我的意向相关项,仿佛是没有独立性的附属物。第二段文字似乎更是包含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以至于澄清同感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似乎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因为,超越论自我依然是唯一的、绝对的主体,他人作为“为我的存在”,最终是“从我的意识领域得到了其存在的意义”。而胡塞尔后来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中对超越论自我的“孤独性”的说明,似乎也与前面的说法相互印证,再次加强了自我的绝对性和他人的依附性:
(3)……是我实行了悬搁,即使这里有好些人,他们甚至现实地与我一起实行悬搁,但是对于我来说,在我的悬搁中,所有其他的人连同他们的整个活动—生活也都包含到世界—现象之中,而这种世界—现象在我的悬搁中只是我的世界—现象。悬搁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哲学上的孤独状态,这种孤独状态是真正彻底的哲学在方法上的根本要求,在这种孤独状态中,我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它由于某种甚至得到理论上辩护的固执……使自己从人类社会中隔绝开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知道自己属于人类社会。我并不是那个总是具有自然有效性中的他的你和他的我们,以及他的由别的主体构成的总的共同体中的一个我。2
以上三段文字常常是批评者们指责胡塞尔现象学没有真正克服唯我论的基本依据。对于上述第二段文字,从批评者的角度看,人们甚至可以说:与胡塞尔的看法恰好相反,如果“所有为我而存在的东西,最终都从我自身、从我的意识领域得到了其存在意义”这句话的有效性没有被取消,唯我论假象就不可能被揭示。例如孙小玲就认为,尽管胡塞尔克服了笛卡尔式的唯我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超越论自我的地位始终未被动摇,甚至共同体“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只能从‘我’之中获得其意义与有效性”1,因此现象学没能真正摆脱超越论层面的唯我论。孙小玲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托尼森。根据托尼森的看法,“第五沉思”看似揭示了超越论唯我论假象,实际上又重新把超越论现象学带入了唯我论,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的澄清只是其超越论现象学的完成2。不过,他们眼里的这种“完成”,并非耿宁所说的是对超越论主体性作为交互主体性的进一步“阐明”3,而只是超越论自我的“自我解释”。也就是说,“在对自己作为最终的构造者的肯定之中,我重新回到了自身的孤独之中,这种不仅是起点处的而且也是终点处的孤独标志着先验主体共同体的不可能性,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胡塞尔的主体际性论的最终界限”4。显然,他们的批评矛头最终都指向了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构造作用。
尽管托尼森承认,在胡塞尔那里,除了自我对他人的构造,也存在他人构造自我的说法;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有一个隐含前提,即只有当他人在自我之中被构造为超越论主体后,他人才能成为构造自我(客体)的主体。与此同时,托尼森还认为,被他人构造为客体的自我成为单子共同体中的一员,由此也就丧失了其“源初主体”(ursprüngliche Subjektivität)的地位。因为“将由他人构造的自我贬低为我本身的一种脱源样态,并对其宣称我作为源初自我的地位,就已经是对他人的贬低”5。而另一位批评者瓦尔登费尔斯尽管肯定超越论自我在现象学中的作用与价值,却认为在胡塞尔那里自我的优先性始终没被动摇。虽然胡塞尔一再提高他人的价值,但是当他人作为“原自我”(Ur-Ich)而出场时,自我也就成为“原真的原自我”。当他人作为“另一个唯一者”而出场时,自我就是设定“另一个唯一者”的唯一者,纵使这个他人也被设定为另一个超越论自我。总之,如果自我的优先地位始终未被颠覆,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就必然无法免于唯我论的指责6。就如托尼森所认为的那样,自我的这种绝对优先性带来的问题是,他人可以从源初的自我这里汲取存在意义,“而我却不必从在那里的他人处汲取我源初的存在意义”7。因此,瓦尔登费尔斯也认为,在胡塞尔那里缺乏真正的与自我同源的他人。
总而言之,在批评者看来,胡塞尔现象学作为唯我论有以下两个应被指责的特征:第一,超越论自我是原自我,他人和交互主体性的意义来源和有效性基础就在于这个自我。由此,他人是自我的意向相关项,以意向性的方式被包含在自我中。在意向性关系中,超越论自我是绝对的,而他人是相对的。第二,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抹杀了他异性,因此与自我同样绝对、同等源初的另一个自我是不可能的⑧。
二、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
针对第一个特征,本文将在这一节和下一节分别从超越论自我的作用,以及超越论自我同交互主体性经验的区分这两个角度作出回应。这一节的分析旨在解除对“他人和交互主体性被意向性地包含在自我之中”“从我的意向性中获得其存在意义”“现象学还原使超越论自我处于一种绝对孤独中”等说法的误解,从而反驳将超越论自我看作唯我论标记的主张。
先从对意向性的说明开始。对于现象学研究者而言,“意向性”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指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与之相应,某物也总是被某种意识行为所意指的某物。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同感。在胡塞尔这里,同感的基本含义是对他人(陌生自我)的经验,他人在同感这种意识行为中被意指。“被意指”意味着,他人从我的意向性中获得其存在意义,我对他人存在与否的设定有经验依据而非凭空杜撰,据此我对他人的设定才是合法的1。“意义”在这里则指的是意向对象2,也就是意向相关项(Noema),它是我形成“他人”这个对象之经验的核心。意义核本身的被给予也与意向行为不可分割3,例如观察他人的行为动作、听到他人的走路声音等等,自我将所有这些不同的经验在同感行为中综合成关于他人的经验,从而在同感意向中指向他人。
当胡塞尔谈及他人和交互主体性从自我中汲取意义时,一方面,他强调的是这种经验的属我性。也就是说,是我对他人的经验,而被我经验到的他人则是对我而言的他人。另一方面,他强调的是关于他人的经验离不开相应的意识行为(同感),通过意向性行为及与之相关联的诸意义核心的综合,作为对象的他人才能真正被我经验到。因此,“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纯粹地在我之中”这句话指的就是: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以意指的方式,而非作为实项Rce9ee2rlQ42fWBV7L7WLqD71DUmWRDu+wIevl5L4tA=或实项部分被包含在我之中。同样,在谈到同感时,胡塞尔所言的他人在我之中,并非指他人被把握为自我的一部分,而是指他人被我意识到,或我具有关于他人的经验。总之,他人和单子共同体都以意向性的方式被包含在我之中,而不是像我在内知觉中直接经验到其自身那样被经验到。因此,他人和共同体没有消融于超越论自我中。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胡塞尔在对同感的论述和相关术语的使用方面有着强烈的认识论色彩。事实上,在同感的问题上,他首先关注的就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即我对他人的经验以及他人存在与否的设定是如何可理解的。这些讨论非但不会加强超越论自我的绝对主体性,反而会因其对他人的不可通达性的承认1而强化他人的主体性。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澄清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确切含义。在胡塞尔对同感的解释中,连批评者们也一定会同意的是:不能从时间先后的角度去理解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在瓦尔登费尔斯看来,胡塞尔的意向性有三个特征:(1)具有对面物(Gegenüberhaben),(2)合目标的意指(zielgerechtes Meinen),(3)视域意向性2。对于同感来说,这三个特征分别意味着:(1)排除了相互性,(2)意指行为只是从自我单方面地发出,因而(3)他人在世界总视域中是被排除的。意向性的这三个特征共同形成了自我相对于他人的优先地位。此外,在意向性中,处于主动的、优先地位的自我是一个绝对主体。这体现在托尼森指出的胡塞尔现象学中自我的三个特征上:“不涉世”(Unweltlichkeit)、“向来我属(Jemeinigkeit)”和“绝然独立”(Absolutheit)3,这三个特征都指向绝对的、唯一的自我。
同时,我们还应清楚,在胡塞尔那里,超越论自我是通过悬搁和超越论还原获得的。但它并不是还原超越物后的直接剩余物,而是作为“内在的超越”的不可被还原之物。关于这个自我,胡塞尔指出,它“属于每一来而复去的体验,它的‘目光’‘通过’每一个现实的我思而朝向对象”,它是“原则上的必然之物,在体验的所有真实的和可能的变化中,它作为绝对的同一之物,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看作诸体验本身的实项部分或要素”4。
超越论还原与胡塞尔使用的所有现象学还原方法一样,一个最基本的目的是审查“某些观点的合法性”,这关涉的是一种“权利/合法性,一种设定通过在它之中被设定之物的直观被给予性而获得了这种权利/合法性”5。简言之,现象学还原的目的就是对设定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进行检验。无论是超越论自我,还是“第五沉思”中的原真自我,都首先在这一目的之下被理解。尽管自我在胡塞尔那里的含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同感中,自我及其直接经验主要被理解为设定他人的依据或基础。
正如瓦尔登费尔斯所说,对胡塞尔而言重要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的自身负责和自身合理化”。与这种彻底主义相联系的是“对绝对确定性的寻找”,而能够保证绝对确定性的只有“意识的绝对”。胡塞尔的这些目标“一方面指向进行奠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指向意识”6。确实,在阐明现象学还原时,胡塞尔常常以笛卡尔“我思”的绝然明见性为参照点,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地位也在这一背景下不断得到凸显。胡塞尔对同感和交互主体性的讨论也循着这条线索展开——相较于我对他人的经验,“我思”以及我的直接经验内容更具明见性。
显然,在意向性和现象学还原中得到强调的自我的优先地位及绝对性,与胡塞尔在现象学中关心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认识的可能性问题1。因此,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也应该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绝对性意味着绝对不可被怀疑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没有任何预设,绝对无疑之物恰好是超越论还原之后的剩余物。作为贯穿这些剩余物的不可被还原者,超越论自我也具有绝对性。而优先性指的是超越论自我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所获得的经验具有奠基作用,它是最确定的和最不可被怀疑的认识,其他的认识都在这个牢靠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
瓦尔登费尔斯尽管看到意识(或“我思”)及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的含义及重要作用,但仍然批评这种绝对性和优先性会导致自我与他人的不对等,或者如托尼森所说的,他人与超越论自我不具有同等源初性。在他看来,他人在我之中被构造,也就意味着通过我对他人的经验而得到设定,这类似于“我允许了陌生的要求,我才会回应”这种做法。只有当“他人的请求先于我的主动性”,这种不平等的限制才可能被打破2。
事实上,无论是瓦尔登费尔斯,还是其他类似的批评者,从一开始就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放入了预先想要讨论的对话关系之中,也就是在存在论和实践哲学中来理解自我相对于他人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在这一背景下,他们提出的替代方案便是“我—你”的社会关系的优先性。这是一个“更高阶的问题域”3,它在胡塞尔那里以超越论现象学为基础。但这种替代方案则相反,是把“我—你”的社会关系当作超越论现象学的前提。他们从存在论和社会哲学的立场批评胡塞尔,其实已经超出了胡塞尔讨论同感的问题范围。他们在胡塞尔那里寻找他根本就没有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势必会失望。而且对于瓦尔登费尔斯的例子,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驳:只有当我听到了或意识到了他人的请求,我才能加以回应。其中或许依然不存在瓦尔登费尔斯所说的平等,但也并未排除他人与自我具有同等的主动性和相互独立性的可能。
在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我们确实无法找出瓦尔登费尔斯所要求的那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严格的平等性。因为自我经验总是具有相对于他人而言的确定性,在自我权能性的辐射范围内,距离我的直观经验越远的认识,越不具有明见性和确定性。但通过对意向性和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塞尔对超越论自我的强调至多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学,而与存在论上的唯我论无涉。
三、超越论自我的交互主体性经验
超越论自我首先是超越论还原之后剩余下来的特殊“超越物”,它也可以在反思中被给予,与这种自我有关的科学被胡塞尔称为“现象学的自我学(Egologie)”4。在其中,人们可以谈论超越论自我的经验。对于唯我论指责,这里要反驳的第二点在于:虽然胡塞尔现象学是主体性哲学,超越论自我在其中有独特地位,但是我的经验并非唯我论式的经验,而是交互主体性的经验或共同经验。
唯我论式的经验可以被理解为“私人经验”,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私人感觉”。在私人经验中没有同感的可能,因为这种经验只能为此主体所知,而不能通过同感被其他自我经验到5。但超越论自我的经验显然不能被理解为私人经验,他人的经验也可以通过同感间接地被给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由第一人称“我”表达出来的共同经验。这意味着,超越论自我的经验尽管使用了第一人称,由此被看作我的经验,但它也可以是交互主体式的经验。通过同感获得的他人经验并不直接就是我自己当下的经验,而是在被我同感到的意义上被看作我的经验,或被我经验到的他人的经验。而在另一些情况中,我与他人共享相同或相似的经验,虽然这种经验也属于我,却并非我所独有,而是一种共同经验。
在目前对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研究中,超越论自我的经验不是唯我论式的经验而是交互主体性的经验这一特征还未受到充分重视,但这一点在胡塞尔1910—1911年的《现象学基本问题》的讲课稿中就已初见端倪。胡塞尔在其中提到对超越论经验范围的扩大,超越论经验并非只限制在知觉经验上,还包括回忆、期待和同感等意识活动所获得的经验1。与此同时,自然不只是单个自我的意识行为的相关项,而且“是关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按一定秩序进行的过程之标志,这个过程包括一切借助同感相互处于经验联系中的意识流”2。由作为指引的自然追溯相关意识经验便会发现,这种意识经验不是只属于单个自我的经验,而是通过同感被关联起来的共同经验。这类想法在之后的思考手稿中也多次被提及,如胡塞尔在《共主观性现象学》第2卷的文稿17中指出:
但是人们现在会说,如果世界只不过就是所谓的客观经验之内在的意向性之极的系统,也就是对于我而言是内在的——尽管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即处于我的内在性中,在一致的证实中可无限地视为同一的——那么我就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
对此的回答是:世界是我的诸经验之统一,但不仅是我的经验(当然是诸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统一,而且按照其固有的意义,也是交互主体性的统一。3
尽管胡塞尔也时常谈及完全排除了陌生经验的原真领域,但它与这一节的讨论并不冲突。超越论自我的经验是一种共同体经验,“包含我的原本的经验和被施以同感的,并作为被现实指示的陌己的经验,而且包含对自己的经验和被指示的陌己的经验视为同一的综合之诸可能性”4。也就是说,超越论自我的经验其实可以区分出两层:第一层是原真自我的经验,也即原真领域,人们也可以将这个领域称为“私人经验”领域,这个领域具有唯我论色彩;第二层是交互主体性经验,其复杂之处在于,它既是他人的经验,也是我的经验,它们借助同感被关联起来。第一层经验与第二层经验一起由同一个自我所统一,被归于“我”这个第一人称之下。但归根结底,超越论自我的经验并不只是我的经验,而是交互主体性的,故上述两层次的区分以及原真还原都只能是一种人为的、抽象的区分和还原。同样,尽管在这里我们只是谈论自我,但实际上这种交互主体性的经验也是他人的经验,也可以由他人的自我所统一,形成对其而言的经验统一、其他的自我对陌生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经验。
至此,我们已在消极意义上表明,尽管胡塞尔侧重于说明超越论自我的构造作用,但这不会导致批评者所说的唯我论。接下来,我们还应在积极意义上指明他人作为另一个超越论自我的独立性和他的构造作用,以及在这个意义上与我的自我同等源初的可能。
四、另一个超越论自我及其构造功能
如上所述,如果人们试图在存在论或实践哲学的意义上寻找一个与自我同等源初的陌生自我,那么这一尝试在胡塞尔那里无疑会落空。但从超越论角度看,自我和他人作为超越论主体,本质上是等值的。因此,这里的反驳主要针对唯我论批评的这一看法:在超越论态度中另一个自我与我的自我不具有同等源初性,故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仍是唯我论的。下面从两个方面展开说明:其一,他人的自我不能被我直接经验到,其主体性不是我的直接的构造成就;其二,他人的自我作为另一个超越论自我,和我的超越论自我一样是进行构造的主体,但无论是我对他人的构造还是他人对我的构造,既不会造成对我的自我的贬低,也不会造成对他人的自我的贬低。
(一)他人的自我不能直接被经验到
胡塞尔在“第五沉思”中提出:他人不能像我自己那样原本地被给予我,我对他人的经验也无法像原真领域中的其他知觉经验一样得到真正的充实;相反,能够不断得到证实的只是一个指示出他人的线索1。
首先,从空间关系上来说,另一个自我的躯体所在的空间位置“这里”不能同时是我和我的身体所处的“这里”。“我亲身存在于这里,是一个围绕我定位的原真‘世界’的中心”2,与之相似,他人的自我和他所处的位置同样是这样一个“中心”。从胡塞尔所说的原真领域的意义上看,这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因此他人主体及其周围世界不是我的本己领域的一部分。尽管借助结对和共现,我可以经验到他人及其本己领域,但是这种“统觉/共现”永远不能通过“体现”(Präsentation)得到完全充实3,而只能在新的共现中得到充实。因此,虽然他人常常被胡塞尔说成是另一个自我,是原真自我的变式,但其始终不能与我的原真自我相等同,也不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自我。在对他人的经验中,统觉不能以体现的方式所充实,这一点昭示着他异性的可能。此外,在对他人之经验的经验中,也同样可以说明他异性没有被抹杀。
根据胡塞尔的观点,在同感中被我经验到的是“另一个自我之意识”,但我不是像体验到和知觉到我自己的意识那样,“在内在的知觉中、在洛克式的反思中,体验到和知觉到这种意识的”4。对这种经验式的同感进行的现象学还原是一种“双重现象学还原”,即一个针对的是同感行为本身,一个是被同感到的对象5。
在双重还原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被同感的材料和同感行为本身不属于同一意识流。这表明,虽然他人及其经验被我同感到,但属于他的自我的意识流与我的自我的意识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被同感到的意识所属的另一个意识流统一体就是第二个自我。他人作为另一个自我被给予我时,我经验到的这种统一性“不是我的诸感觉之统一和通过诸感觉而进行着透视变形(Abschattungen)之统一”,而是“第二个超越论的主体性,它是在我之中本源地显示出来的(但原则上只对其自己本身而言才在自身反思中是可被知觉的)”1。
在原真还原的情况下,原真自然不是像内在体验一样作为实项内在于我之中,而是作为意向相关项在构造物的意义上内在于我。而wTITYmZ+vSIkppt2dLUsiA==另一个“我”,既不在实项意义上内在于我,也不在作为一般的空间事物的意义上内在于我,而是“在某种原真的多样性中(在我的进行深入理解的、赋予灵魂的诸经验中)”被构造起来,并“作为另一个自我为其自身存在”2。对另一自我的构造之所以不同于对一般的空间事物的构造,主要是因为他不是直接被我经验到的,不像自然物一样属于我的原真领域,而是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他以一种独特的意义“为我存在”,即他也是一个超越论的主体,为其自身而存在。他人的自我超出了我的原真领域,是一种“新式的超越性”3。
他人的主体性通过他人身体的显现被我经验到,但不是直接被经验到,我直接经验到的只是一个躯体和身体行为。事实上,在“第五沉思”中人们就可以看到,我既不能像经验自己那样直接经验到他人的自我,也不是借助推理得出这个自我,而只是在共现中间接地经验到他人的自我4。这意味着,他人的主体性永远不能直接被我把握。然而,从批评者的观点来看,我仿佛能够直接经验到他人的主体性。这种误解随即导致这样的认识:他人的超越论主体性是我的构造成就,和其他自然事物一样属于我的原真领域,因而他人只是我的原真领域的一部分。由此,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唯我论的结论。
(二)作为构造主体的他人
至此已经清楚的是,对他人的构造的确体现了我的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但这并没有抹杀他人也是构造主体这一事实。在胡塞尔那里,“处于中心的不是构造的交互主体性,而是交互主体性的构造”5,即他更多讨论的是作为被构造者的他人,而不是作为构造主体的他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人只能作为被构造者而存在。
其实,以托尼森为代表的批评者们并非没看到他人作为超越论主体所具有的构造作用。只是托尼森认为,即便作为构造主体,他人的自我对我的构造这一行为本身也是我的同感所意指的对象。不仅如此,被他人同感到的自我成为众多单子中的一个,这意味着,如此这般被构造的我的自我脱离了绝对性特征,这既是对我的绝对自我的贬低,也是对他人的绝对自我的贬低6。显然,托尼森误解了他人对我的自我的构造的含义,也没有注意到自我与他我在被给予方式上的差别。
从胡塞尔讨论交互主体性问题的初衷来看,他人作为本己自我以外的超越论主体,其构造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同一个自然的构造上。胡塞尔指出,被我经验到的这个自然也可以被还原到他人的经验系统上1。不过,在超越论态度中,这同一个自然不是以如下这种方式被经验到的:自我与他人首先在彼此完全孤立的状态下经验到这个自然,然后这些经验借助莱布尼兹式所说的“前定和谐”相互关联,最后形成对客观自然的经验,也就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经验。实际的情况是,自然始终在自我与他人的相互同感的伴随中以共同的经验的形式被意指。
他人的构造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同一个自然的构造上,也体现在他人能够将我视为其意向相关项这一点上。从认识论的立场看,就像他人的自我不能成为我的直接经验的对象一样,我的超越论自我也不能成为另一个超越论自我直接经验的对象。这就是说,在对他人的经验中,我只能经验作为现象的他人,而他人的主体性则只是以共现的方式被间接经验到。反之,他人对我的经验也是如此。
绝对主体意义上的自我是因意向性和超越论悬搁而产生的,尽管许多自我可以一起实行超越论悬搁,但每个自我只能就其自身和他所经验到的世界进行悬搁2。与之类似,对超越论自我的直接经验只有在每个自我对其自身的反思中才是可能的3。而在对身体的经验中,我的身体“是在主体的显现方式中被给予我自身的”4。
在他人对我的经验中,他人作为被我同感到的主体,“以一种外在的显现方式拥有”5我的身体,也以外在的方式经验我的自我。尽管他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构造作用是被我同感到的,但这只是强调了“被我意识到”这一认识特性,而不是表明这种构造作用是我赋予他人的能力。
正是在陌生经验的基础上,每一超越论的主体都被客体化为人,“这个人是主体,与它相对,有处于其对面的另一主体……这个主体对于其自身而言是在‘内在的’方式中(以唯我论的方式)被给予的,而在外在的方式中(在交往中)它被给予它的对面者,并且这是相互的”6。“内在的方式”指的是我对自身而言作为绝对主体被给予,胡塞尔所理解的唯我论的方式其实就是内在的方式;“外在的方式”则指我对他人而言作为其对象被给予,并且彼此处于相互交流中,这时我就是被他人构造的,是他人的意向相关项。
在这种交互主体性经验中,第一人称中的绝对自我才能被客体化,从而与他人一样被经验为众多单子中的一个。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自我对他人(陌生自我)而言是他的构造成就,我的存在意义来源于他的意向性。由此,胡塞尔才提出:超越论自我既是相对于其现象而言的绝对的、无人称变格的自我,也是可变格的自我、作为众多超越论他者中的一员的自我,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只是表面的7。因此,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与作为众多单子中的一员只是自我的两个面向。
总而言之,每一个自我,内在地看是包含其他单子的超越论主体,外在地看则是众多单子中的一个。每个单子自我既是独立的,也与其他单子自我相关联。在这种理解中,作为超越论主体的自我与作为众多单子中的自我可以是同一个8。因此,使我成为众多单子中的一个,这既不意味着对我的主体性的贬低,也不意味着对在构造活动中将我的主体性客体化的他人的贬低。不仅如此,每一个超越论自我都通过同感认识到他人也是一个超越论自我。而这意味着,我和他人都是超越论主体,我们具有同等的绝对性。
五、结语
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所面临的唯我论指责主要是从实践哲学和伦理学立场作出的①。透过这一立场,对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这些唯我论指责,实质上可以看作从类似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角度出发,用他者的绝对性对胡塞尔现象学中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提出的挑战。但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首先关注的并非伦理学中的他异性问题。假如人们能正确理解超越论自我的绝对性和优先性的意义和作用,而不是从伦理学和存在论角度曲解,或许会同意,超越论唯我论即使存在,对于胡塞尔的整个现象学体系而言也不是致命的。
不过,即便不是从伦理学角度,而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内部提出唯我论的批评,其实也是不成立的。这不仅是因为,不能将超越论自我与交互主体性经验相等同,由此也就不能把超越论自我的经验看作是唯我论的或私人的经验;也是因为,超越论自我兼具向内的统一性和向外的开放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不是缺少与超越论自我同源的伙伴,而是每个自我都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寻找认识的坚实基础。这个自我在内部是统一的,但不是封闭的。与其说这是唯我论,毋宁说——如大多为胡塞尔辩护的研究者所认同的那样——是自我学。只有在人们只看到超越论自我的内在统一性并将其误解为自身封闭“单子”,而没有注意到其向外的开放性的情况下,才会将其理解为唯我论。虽然胡塞尔自己也会误导性地使用“唯我论”这个表达②,但在他的现象学中,除了赋予“唯我论”以特殊含义外(一种内在的、第一人称的经验方式),这始终只是一种方法上的权宜之计③。而且对他来说,自我只是起点,而非终点。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