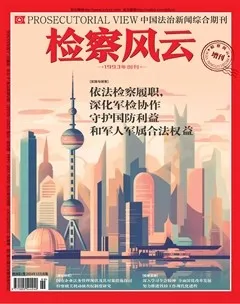基层检察听证制度实质化研究
一、检察听证制度的价值
(一)检察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积极依法履职的重要实践。“枫桥经验”就是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新时代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履职,利用进社区、进校园、到案发地等多种下沉式听证方式,发动群众来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做到了矛盾不上交,与此同时对群众也起到普法教育的作用。
(二)检察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创新。检察机关改变以往书面审查的办案模式,将当事人及相关社会力量纳入其中,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集咨询、论证、群众参与于一体,全面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听证员独立发表客观、中立的第三方意见,更加准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这样将相对封闭的办案活动放在人民监督的聚光灯下,能够促使检察人员更加谨慎、规范用权,让公平正义经得起考验。
(三)检察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化解矛盾纠纷,促进诉源治理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推行听证制度,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相关办案单位、独立第三方听证员之间构建起一种良性法律互动机制,通过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充分释法说理,消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办案的疑虑,解开当事人心结,促成和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二、基层检察听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G市检察院近三年统计数据,2021年组织听证25件,其中公开听证24件,占96%;不公开听证1件,占4%。2022年组织听证78件,其中公开听证77件,占98.7%;不公开听证1件,占1.3%。2023年组织听证30件,其中公开听证29件,占96.67%;不公开听证1件,占3.33%。
院领导多次主持召开听证会,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相关社会团体参加听证会,同时创新性采取进医院、进驾校、进学校、进矿区等听证方式,探索建立人大代表联络点,将听证会开进人大代表联络点。听证案件类别主要集中在拟不起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听证案情较为简单,听证所涉罪名主要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危险驾驶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故意伤害罪等法定刑在3年以下的轻罪为主。
从近三年数据可以看出,G市检察机关对于检察听证工作比较重视,但仍存在开展检察听证的案件数量占比不高,距离最高检“应听证、尽听证”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一)听证案件的功能作用有待加强。当前,G市存在部分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不存在争议的案件也举行听证会的情况,结果通常是听证参与人一致同意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听证过程中也缺乏意见交换,听证会难免成为形式性活动,有“为听证而听证”之嫌,未真正实现检察听证的功能作用。当前出现听证结束,制作办理相应的文书后案件即办理终结的情况,对于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后续的跟踪帮教,也都缺乏相应的规范性操作,导致利用检察听证促进诉源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检察听证启动有待完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以下称《规定》)第9条规定,当事人及辩护人、代理人可以向审查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申请召开听证会。但从G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召开的听证会来看,均为由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依职权启动并组织召开,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民众对检察听证制度了解不够,申请渠道不够畅通,导致检察听证启动方式较为单一。
(三)听证员权益保障不到位。听证员是独立作出判断并发表意见的人,有助于实现案件公开公正,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关键角色。但实践中听证员在听证会即将召开前才能接触到案件信息,了解到听证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时甚至为了追求公正和过分保障听证员的中立性,听证员在听证会召开前完全不知晓案件情况和相关信息,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时间,仅仅依靠短暂的听证过程,难以提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意见,检察听证之“证”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
(四)听证活动事后宣传不够。基于案件信息保密等相关原因,对听证活动的事后宣传往往是通过官方公众号进行发布,发布内容通常为活动信息,有关案情及说理内容部分较少。同时,检察机关往往不能很好地利用新媒体等平台进行有效的宣传,宣传手段单一,社会影响力有限。
三、检察听证工作完善路径
一是规范听证案件的适用范围。要对需要听证的案件予以细化。具体来说:根据《规定》第4条规定,将存在较大争议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纳入听证案件范围。其中,“争议较大”应当包括对案件事实仍存在疑问,且该事实部分直接影响着检察决定,或者案件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决定存有异议等。“重大社会影响”,则是指该案件受到公众普遍关注,检察机关的决定已经或者可能引发舆情。此外,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认为需要通过听证程序公开收集更多意见,或有必要让当事人及公众有机会了解检察机关作出决定的依据的,也应当纳入听证案件范围。通过多方参与人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充分讨论,为案件处理结果提供实质性意见。要将检察听证与训诫教育相结合。强化犯罪再预防工作,探索建立“不起诉+训诫谈话+社会公益服务/公益基金”工作机制,要求被不起诉人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或缴纳公益基金。
要将检察听证与检察建议相结合。检察机关应强化社会治理,深入挖掘听证案件背后的根源性问题,将听证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发现的社会治理、行业监督管理漏洞及时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二是提升对检察听证制度的认知。一方面要建立告知当事人申请听证权制度。检察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案件有必要启动听证程序,应当制作事项告知书,并及时告知当事人,主动让当事人了解、熟悉听证。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听证制度宣传力度。可对不同案件性质区分,对于可以公开的案件基本情况,应积极公开,并确定公开内容,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发布听证公告,拓宽检察听证公开途径,提高普通民众参与度,扩大检察工作的民众知晓度,获取对检察工作认同。在听证常态化后,可以尝试采取时间相对固定,类案集中听证等方式开展听证活动,并通过会前公告制度,提高公众参与检察工作的积极性。
三是保障听证员充分履职。案件承办人应在听证会召开之前对案件进行仔细甄别,在不影响听证员对案件作出客观中立判断的前提下,积极加强与听证员的沟通,保证其充分了解案件情况、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掌握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具体来说:承办检察官应在听证会召开三日前向听证员发出听证邀请函,并提供案件相关材料,介绍案件情况,需要听证的问题及相关法律规定,为听证员充分履职提供保障。
四是提升听证案件影响力。在开展公开听证活动时,要以结果为导向,谨慎选择听证案件,做好风险评估及前期工作。同时,应完善公开听证活动效果评估机制,着力提升检察官运用公开听证办理案件的能力。会前为听证员了解案件情况提供便利,会中及时回应参与人员的疑问,会后做好听证效果评估和听证效果宣传工作。应结合听证目的,从化解矛盾、释法说理、彰显检察担当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工作。针对刑事申诉案件,还应尝试通过听证,建立检察机关同其他机关化解社会风险、妥善息访罢诉的协调机制。
(作者:刘利霞,古交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马艳梅,古交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