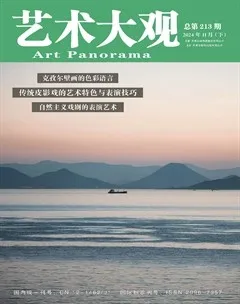人物形象的交响化处理

摘要:交响诗《黄鹤的故事》是施咏康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作品,1956年在北京首演于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这部作品改编于民间故事,故事中共出现了三个人物形象,分别是“老马”“黄鹤”和“官老爷”。施咏康重点围绕“老马”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塑造,而该形象无疑是用比喻的手法代指封建社会的农民推翻“官老爷”统治,带领人民获得胜利,受到人民的爱戴,“黄鹤”也是如此。研究管弦乐作品的交响化音响必定离不开对织体、音色的研究。因此,为人物形象赋予交响化的音响时,乐器音色的选择与分配、织体的处理方式深深影响着配器风格的形成。本文将依托上文所述交响诗《黄鹤的故事》中所出现的三位人物角色形象,从音乐形象塑造的角度对作品音响进行分析,探讨施咏康管弦乐作品《黄鹤的故事》的配器风格与特点。
关键词:施咏康;《黄鹤的故事》;音乐形象;配器特点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7357(2024)33-00-03
施咏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作曲家之一,他创作了大量、各种体裁形式的作品,还编写、出版了两部配器理论专著。在交响作品方面,他共创作了四部管弦乐作品《黄鹤的故事》《纪念》《幻想叙事曲》和《东方的曙光》。施咏康先生的四部管弦乐作品都是与英雄题材内容相关的交响乐作品。为何施咏康先生钟爱写这类题材的作品?这个问题可以用“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回答。施咏康出生于1929年,正逢历史变革时期,社会局势动荡不安,而后又经历了各种战争等,可以说施咏康先生见证了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也见证了我国从落后到成长为当今世界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只有经历过,才深知革命胜利曙光的来之不易。正是施咏康先生的切身体会,激起了他用音乐发声的强烈欲望。施咏康先生用音乐去讲述英雄的故事,用音乐去传递革命胜利的喜悦,也用音乐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赞扬了他们为革命献身的无私精神。
一、作品概况
《黄鹤的故事》是施咏康先生的毕业作品,创作完成于1955年,1956年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首演,于1957年获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音乐作品三等奖,并被国内外多个著名交响乐团表演。
该作品的结构采用奏鸣原则,呈示部主部主题描写“老马”,副部主题是对“黄鹤”的刻画,展开部是对“官老爷”出现后掠夺“黄鹤”等内容的描写,再现部是对“老马”“黄鹤”和人民共同反抗“官老爷”及对反抗胜利后的幸福生活的描写。
交响诗《黄鹤的故事》的编制是乐队在常规双管编制的基础上,作曲家根据人物音乐形象塑造需要,增添了几个乐器音色。为表现“黄鹤”似百灵鸟一般的鸟鸣声,木管组增加了一只短笛的使用。铜管组方面使用了4只圆号、3只小号、3只长号与1只大号。打击乐组使用了定音鼓、铃鼓、小军鼓、三角铁、钹。色彩性打击乐器除了竖琴,还使用了钢片琴来描写“黄鹤”的灵巧、活泼。弦乐组为常规五部弦乐组。此外,作曲家还为作品的主要人物“老马”选择了特殊的乐器音色,即我国民族乐器曲笛以现出“老马”乐观、善良的民间吹笛艺人的形象[1]。
二、人物音乐形象的分析
人物角色的音乐化表达贯穿着作品的发展,不同阶段的音响处理影响着人物角色形象的塑造是否鲜明、立体。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中所出现的三个人物形象的音乐表达,来探究不同音乐形象对交响化音响的塑造。《黄鹤的故事》中塑造了“老马”“黄鹤”“官老爷”的音乐形象,这三个人物所体现的形象、特点会随着故事情节、曲式结构的推动、发展而变化。最终,在作品结束时,每个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都丰富起来,进而导致作曲家会通过作品织体、音色的处理方式等配器技术的改变来丰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管弦乐音响色彩。
(一)“老马”乐观、积极向上的吹笛人形象
该作品呈示阶段的主部围绕“老马”的形象进行塑造,主题第一次呈示(36—57小节)是由民族乐器竹笛族中的曲笛(中音笛)吹奏,所使用的乐器音域基本保持在高音区,以突出“老马”乐观、积极向上的吹笛人形象。在这22小节的主题中,音响色彩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两个织体层次构成,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都被分为三个声部,以拉奏出极弱力度的面状和声背景层次,该层次所奏出的三度音程上方加二度的叠置和弦绘制出具有浓郁中式色彩的画面。竖琴通过琶音演奏技术在“线”和“面”之间加入“点”,使单一色彩的画面更引人注意。作曲家通过立体化的方式使各个织体层次主次分明、清晰可辨,最终得到音响的“空间感”。第二阶段在整体三个层次不变的基础上,丰富了音色的呈现方式,背景层次的圆号与小提琴声部构成混合音色,两个乐器“性格”差异性极大,但作者通过泛音技法弱化了圆号的金属音色,同时使用其高音区的明亮音色又获得了小提琴般的“空灵感”声音。点状织体部分是由低音弦乐组构成的纯音色来获得的,大提琴、低音提琴的拨奏技法增加了轻松、愉快的氛围感。第三阶段的音响进一步复杂,其线条层次出现了与主题对比的双簧管声部,竖琴声部分解和声式琶音的和声节奏也加快了速度,背景性的长音也从小提琴声部到了大管声部,低音声部的“背景”得到了加强。每个织体层次的乐器音色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与作用,也在不同的音区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
从第58小节开始,主题进行第二次呈示,是单簧管在主题旋律下方五度的模进,旋律的音高关系保持不变,弦乐组的点缀是由两个低音弦乐乐器和其余三个乐器先后交替出现的拨奏完成的。两只大管演奏了常见于钢琴的和声式伴奏织体,趣味性十足,大管纯音色担当了一种织体因素。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长笛和第一双簧管两个声部还与弦乐组乐器在背景层次组合出了混合音色。选择这两种乐器完成对弦乐组背景性长音加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想在保持弦乐组基本色调的同时改变与前一部分相同的色彩,以使音乐色彩获得细微的差异化;二是出于对交响乐团位置座次的考量,这两名木管乐手通常坐在相邻的位置,能够合成不分散、集中的混合音色,这易于两名乐手的演奏,音响也可以更好地融合,从而相对减弱两个乐器的个性化。第70小节旋律是短笛、长笛声部的纯音色,其和声性因素由单簧管、圆号构成的混合音色完成。第88小节时乐队达到主部的高点,长笛、小提琴、中提琴共同构成了主题旋律的色彩,铜管组分量加重,和声性因素主要由铜管组完成,整个主部在较为明艳的色彩中结束。
主部中的“老马”主题在旋律声部的音区、节奏、音高关系上基本保持了统一,但作曲家在配器处理上做足了功夫。不管是各个织体层次的数量,还是音乐色彩的淡与浓都呈现出递进关系,音色在横向的转换和纵向的结合上获得了丰富多彩的变化。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施咏康先生对配器技术的使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2]。
(二)“黄鹤”能歌善舞、宁死不屈的正义形象
“黄鹤”主题是在副部中出现的,整个副部是对“黄鹤”为人民跳舞这一舞蹈性场面的描绘。副部的节拍采用八六拍子,小快板速度,铃鼓、小军鼓奏出的“伴奏鼓点”几乎贯穿了整个副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旋律线条不再由一种乐器担任,四小节的旋律线条是在小提琴、单簧管、长笛三个单一音色中分别重复三次,在第四次重复时变为木管组和部分弦乐器热闹非凡的大齐奏,四次音调的重复出现与“老马”主题如出一辙。两个角色音乐形象在配器方面都采用了织体层次以渐进式增长的方式增加,从而使音响色彩逐渐丰富起来。
首先,仅有小提琴旋律的单一色彩;其次,单簧管的旋律线条与铃鼓、弦乐组、大管、圆号组合形成多因素伴奏织体层次;再次,整个木管组、弦乐组与铃鼓、三角铁构成的混合色彩;最后,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铜管组、小军鼓,乐队齐上阵共同渲染出舞蹈正式开始的盛大场面。
“黄鹤”单独登场。通过短笛、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四种乐器构成从横跨木管组最高音区到中音区共四个八度的四小节用短倚音和长音的组合制造出关于“鸟鸣”声音的模仿,明亮又清脆。这一节奏音型时值的不断缩小,也告知听者“黄鹤”不厌其烦地服务于人民的勤劳形象。横跨四个八度各木管组乐器的音区分配按木管组声部排列顺序,从高至低每种乐器仅分配一种音区,以突出乐器高音区音色的尖锐。但第一单簧管与双簧管声部重叠,另一只单簧管与其构成八度音程关系,这一做法可以防止在中、中高音区引起音响的分离,减弱各乐器间的个性差异,使音响更浑然一体。在第134小节后,乐队音区继续保持以中、高音区为主,低音区仅使用低音弦乐器的拨奏和定音鼓的单音来强调每小节强拍位的重音。
(三)笨拙、丑陋的“官老爷”
在第201小节前,音乐都是欢快、轻盈的,但在第201小节,音乐性格突然发生了巨大改变。连续的不协和和声进行和多组半音关系间的颤音,以及非常规调式音阶关系的级进上行五连音的多次模进使音乐紧张起来,通过对置的手法体现了不速之客“官老爷”的出现。强弱力度、音响幅度、速度的直接对置是非常明显的,如乐队强力度全奏停止后立马仅剩双簧管与大提琴两个单薄的音响声音,两只双簧管演奏出下行跳音,大提琴分部奏出两个包含相反指震音的声部,以突显“官老爷”形象的滑稽。五连音、六连音及三连音的弓震音在“官老爷”段落中也至关重要,通过时值短小音符的音型化写法描写“黄鹤”、人民此刻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心中充满不安与焦灼。第251—256小节,大管、大提琴混合出音区来回跳跃且节奏感十足的低声部线条,塑造出人物一瘸一拐的笨拙形象。其余木管组音色奏出带有半音关系的倚音并与小提琴分部奏的拨奏技法合力构成和声性因素,加重了整个场面的诡异、荒诞,更加丑化了“官老爷”这一反派人物的形象。
从第257小节开始,作曲家主要使用弦乐组来表达人民此时生活的索然无趣,“黄鹤”被抓后的悲伤心情,也是对以前幸福生活的怀念。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为旋律声部的底色,偶与木管组乐器、大提琴形成混合色彩,其余弦乐作为和声背景。
(四)人物形象的丰富
一段竖琴华彩过后,迎来了曲笛音色的出现。曲笛的再次出现象征着“老马”的回归,意味着此时作品来到了再现部阶段。“老马”从恶人手中解救出“黄鹤”,带领人民回到载歌载舞的幸福生活,这时“老马”的形象特点得到丰富,体现了他挺身而出的英雄形象。因此,第300—341小节先后出现了作曲家所塑造的三个角色形象,先是曲笛代表的性格积极向上、助人为乐的“老马”,然后是大管、大提琴与其他木管组乐器代表笨拙又滑稽的“官老爷”,最后是木管组代表的歌声灵动、美妙的“黄鹤”。三个角色在塑造时,不管是所使用的乐器数量,还是乐器的选择都不尽相同,甚至音色的处理方式也有许多差异。“老马”是采用曲笛纯音色演奏旋律音调,“黄鹤”则通过除大管以外的木管乐器进行音色的交替来体现“黄鹤”在天空自由翱翔,“官老爷”是以混合音色的旋律作底色,其他木管声部在弱拍位置吹奏出和弦。当然,乐器选择的不同,同时也对应着三个角色音区上的对比。但三个角色音乐形象塑造的共同之处可能也就只有都采用了吹奏类乐器。作品结束时除“官老爷”自始至终保持了他反面角色的形象以外,“老马”“黄鹤”都在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特点方面又得到了额外的形象升华,他们身上都增添了不向恶势力低头、正义凛然的“英雄”特点。
三、结束语
《黄鹤的故事》的配器处理原则大多是按照异质性织体分离的原则进行织体处理,得到主次分明的立体化音响。而处理同一织体因素时,则采用同质性结构织体处理的重复原则,使在某一织体因素内部选用相同或不同音色合成出一定程度融合、统一的音响。音响形成融合与分离共存的复合形态,是古典-浪漫时期“传统”配器风格的体现。但音色变化又异常丰富,使色彩常以渐变的形式发展,又如同以色彩见长的印象派一般,同时还包括在背景层次中运用晚期浪漫派模糊性技法“壁画式风格”等都体现出施咏康对古典-浪漫时期以来配器技法的熟练掌握。
施咏康先生的这部作品对材料的使用也是非常节省,各个角色在作品不同结构阶段出现时所使用的材料素材贯穿整部作品,导致每个形象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易于听众解读作品内容,使交响音乐这一“高雅”艺术“接地气”,对于作品所描写的民间故事也更易于作品的传播,听者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作曲家在作品背后所真正想表达的内容。作曲家在本作品中依托于交响诗这个需体现矛盾冲突的交响作品体裁,它常是具有表达深刻内涵与哲理的作品,《黄鹤的故事》讲述的是民间传说故事,但表现出“老马”“黄鹤”,甚至是人民与“官老爷”之间的冲突。笔者在解读完作品内容后,认为施咏康先生最终所想传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旧社会、打倒列强开启新社会建设的内容,不然作品三个角色形象为何只有“老马”使用的是中国民族乐器竹笛?无非是“老马”形象所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且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代表中国。形象的特殊性使得作曲家选择了特殊的乐器来暗示作品背后的意义,同时也是西方交响曲体裁中国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杨立青.管弦乐配器教程(上册)[M].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
[2]周永莉.交响诗《黄鹤的故事》音乐形象分析[J].艺海,2011,(02):44-45.
作者简介:华敏(1999-),女,山东潍坊人,硕士,从事配器、作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