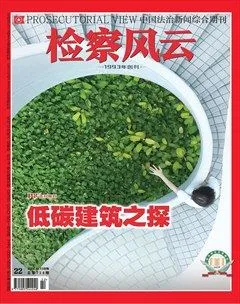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挑战

双元制教育是德国职业教育的重要武器,其培养、输送的大量高水平技能人才对该国工业制造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起源及发展历程
今年6月17日,德国联邦教研部(BMBF)、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和莱布尼兹教育研究与教育信息研究所(DIPF)共同发布了第十期《教育报告》,全面展示了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最新动向,报告指出,双元制职业培训在德国的需求持续上升。
双元制职业教育又被称作现代学徒制,其概念起源于英国。1919年,《学徒制度管理宣言》在纽伦堡通过,其不仅是一项条例,更是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的第一个草案,为后续职业教育相关立法奠定了基础。
1969年,德国颁布《联邦职业教育法》,以联邦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其职业教育基本法的地位,明确了政府、行会协会、企业和职业院校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上的相应责任,从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了双元制地位,确认受教育者具有双重角色,不仅在学校要接受学校教育,同时在企业也要履行员工的职责。
该法构建了现行职业教育制度的基本框架,阐述了职业教育的目的和实施要求,为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明确了学徒与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使学生以技术工人、工匠的身份进入企业及劳动力市场;首次规定企业应向学徒支付适当津贴,发放标准应根据学徒年龄进行评估,并随着初始培训进行,每年至少增加一次津贴额度。
在《联邦职业教育法》的基础上,《手工业条例》《培训师能力条例》《联邦青年劳动保护法》《继续教育促进法》和《远程教育保护法》等相关法规起到了补充支撑作用。围绕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企业基本法》及其他相关条例也进行了更明确的规定。
为更好保障相关法律实施,德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通过细化相关规定要求,增强了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可操作性,有力吸引了企业的积极参与。比如围绕职业认定的相关考核,颁布了《职业培训条例》《标准考试条例》等法律,规定每个职业考试的最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双元制培训的高质量。
2019年5月,联邦政府审议通过了《职业教育法案修订案》,旨在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推进实现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同等价值。一方面规范统一传授高级职业资格的层次划分,明确传授高级职业资格的职业进修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颁发“考试认定的职业专家”“专业学士”及“专业硕士”文凭,增强这些具有高级职业资格的职业人才的流动能力,增加其职业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明确提出实施职业教育报酬最低限额制度,增强双元制职业教育学习者生活待遇的保障,要求在2020—2023年间,逐年提高双元制职业教育报酬最低起点限额。2020年新入学者职业教育报酬最低额度为515欧元,2021年为550欧元,2022年为585欧元,2023年为620欧元。同时规定,最低限额以第一学年最低额度为基础随学业进步逐年按比例提高,相关规定有力增强了学习者的权益保障。
并且为了更好地引领“职业教育4.0”数字化建设,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数字契约学校”上达成行政协议,从“数字基础设施”专项基金中拨款50亿欧元,改善所有中小学包括双元制职业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立“全国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研究联盟”和区域性的数字化能力中心,支持前沿技术研发,提供技术创新保障。
分工与协作支持
2024年5月,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发布了《2024年职业教育与培训报告》,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BIBB)也发布了《2024年职业教育与培训报告补充数据报告》,两份报告的信息显示:2023年企业为双元制职教生提供的培训课程数量增加了3.4%,与上一年相比,培训需求增长了3.6%;双元制职教生新签订的培训合同数量增长了3%。
作为一种蕴含契约式分工合作精神的教育模式,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以企业培训为基础,将职业学校和企业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实现企业主导、学校辅助及行会参与的“三方共赢”模式。
在该职业教育模式中,学校和企业是法律规定的合作伙伴,企业占主导地位,学校为辅助,只负责学生的专业理论教学,且学校的理论教学与企业的技能培训并非各成体系,而是做到了教、学、用的相互融合。培训标准则由学校、企业和行业协会协商制定,考试则由行业协会主持,这样学校、行业协会、企业有共同目标,既合乎学生和企业利益,也使培训达到最佳效果。
企业的积极参与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很多企业深度参与学徒招募、人才培养,经济投入远远高于德国公共财政的投入。而在2019年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中,再次强调企业是进行职业教育的主要场所,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主体地位。
有数据显示,德国近2/3的企业为职工和社会提供培训教育,是职业教育最大的承载者和主力军,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深度介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将其作为提升员工技能的重要途径,为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德国行会组织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教育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1969 年《职业教育法》第71条首次赋予工商行会以公法法人地位,承担政府委托的管理职业教育的职能,这也是行会首次被赋予直接治理职业教育的最高权力。
在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运行中,行会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协调功能,承担起调节市场与教育间的协调责任,负责协调发生的劳资纠纷,担负起行业企业与职业学校之间的协调者、组织者、监督者等多重角色,推动将企业追求“利润”与学校“育人”目标的协调统一。
二是规范功能,基于行会组织的权威地位,其被赋予制定规范、监督规范落实情况的职能,包括决定申请者是否具备从业资格、各专业领域对应的教育标准以及相应的考核等。比如《职业教育法》规定,各类行业协会负责组织和实施本行业职业培训的考试并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组织和管理由与培训无直接关系的行业协会负责,这对提高生产质量、提升工艺品质等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德国政府的引导保障作用也不可或缺。除了立法支持、政策引导之外,还承担了教学经费、日常运营费用的拨付,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改革项目的资助以及技术创新的保障等,这些都为双元制职业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撑。
技能人才短缺的挑战
虽然德国培训名额总体供应量以及接受职业培训的年轻人数量都有所增加,但同时也出现未填补培训名额的情况。近期,德国联邦劳工局(BA)旗下的IAB研究所发布报告称,2023年德国有35%的培训职位未能成功招聘到新员工。加之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影响叠加,德国熟练技术工人整体呈现紧缺态势。德国经济研究所(IW)最新研究报告预测,到2027年,德国专业技术人才缺口将达到72万8千人,其中销售、儿童保育和社会工作领域的人才缺口位居前三。
围绕应对技能人才短缺的挑战,德国在进一步深挖国内潜力的同时,持续增加技术移民的数量。同时,德国移民的相关立法也进行了修改。从2024年3月1日起,德国《技术移民法》的新条款生效,具有非受监管职业工作经验的人员可以进入德国就业,而无需寻求正式认可。这些职业包括所有双元制培训职业,所需要的只是符合特定要求的专业或大学资格证明。同时,雇主必须提供具体的工作邀请和一定的最低薪资水平。
《技术移民法》的修订有助于缓解德国学徒岗位空缺的态势,同时也加大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流动势必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