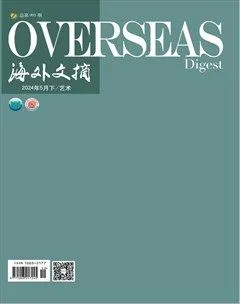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中国古代美育文化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不仅在文化领域流芳百世,影响深远,而且在美育方面也开创了先河。在全球化背景下,孔子的美育思想对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孔子美育思想的分析,探讨孔子的美育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1 孔子的美育思想
在《论语·泰伯》中,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说[1],这一论述深刻阐述了君子素养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孔子美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认为,《诗》、礼、乐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美育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将礼制和社会规范内化于心,而且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能够塑造个人的品德与行为。这一思想体系构成了孔子美育思想的总体框架,强调了通过艺术与文化的熏陶,实现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的双重目标。
孔子认为《诗》、礼、乐在社会和教育中极为重要,因为它们能培育人的情感和道德品质。他强调通过《诗》和乐的教化,激发情感,使人熟悉礼制。孔子的教育方法更符合人性情感,易于被接受,不仅培养道德,还能使人达到性情平和。总而言之,他提倡的美育与德育紧密相连,注重对主体的道德培养。
除此之外,在学习中,孔子十分重视知识性和体验性,并针对这一观点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这里的“兴”指通过审美激发情感,提升精神;“观”指艺术形象引导积极联想,形成正确价值观;“群”强调人际和谐;“怨”则是发泄情绪,表达对社会政治不满,在此之后寻求心灵平和。总体看来,孔子注重通过《诗》的美去激发人的情感,令人自觉产生一种启智增识的道德情感,从而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广大其心,导达其仁”的理想境界。
而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美育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给人们注入了一种“仁”之精华,旨在通过对其人格上的培养,促使其在生活中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并向善发展,即“在德育中融入审美的因素,在美育中适当注入道德内涵,才能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3]”孔子将其“仁”的理论融入诗教、礼教、乐教中,通过文化教育、道德教育、艺术教育来完成他的美育任务,培养“文质彬彬”的仁人志士。
孔子在教育领域所倡导的美育与德育的融合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后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他的教育理念和创新的教学方法既丰富了中国古代美育的内涵,也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孔子的美育思想,强调对个体德性的培养与审美情感的陶冶相结合,为后人提供了关于如何通过教育塑造和谐人格与社会公民的深刻洞见。
2 世界视角下的美育思想
美育的滥觞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先秦与古希腊,孔子与苏格拉底等伟大哲学家为这一领域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尽管东西方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他们的理论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彰显了美育的普遍价值和深远意义。
2.1 以“仁”为基础的美育理念
首先,在中国古代,“仁”作为儒家学派的核心理论,一直很受重视。孔子思想中的“仁”是由“人”派生的同源词。《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句话被研究者们视为孔子对“仁”内涵最直白的阐释。“仁”的理念在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中有不同的体现,在血缘关系中,“仁”以“孝”为主要特征,在非血缘关系中表现为“忠”和“泛爱众”。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他看来,“仁”与“孝”是有关系的,“子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孝悌是人之本,在家做个好孩子、好兄弟,在外就能做个诚信的人,因此孝悌之心对于仁爱之心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泛爱众”主要体现在君民关系中。在孔子看来,广泛地去爱民众,可以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进而有利于国家的治理。综上所述,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从“亲亲”扩展至“泛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古希腊时期的“仁爱”思想强调人际关系中的相互吸引和友爱,亚里士多德将其分为实用、快乐和德性三种友爱,其中实用和快乐的友爱基于利益和愉悦,而德性的友爱则基于双方德性的相互吸引和纯粹的善。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提出“友爱”是一种德行,旨在弥补自身的不完满,是在追求美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友爱追求高尚,爱的是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以弥补不足。柏拉图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更具有抽象性,但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2 以“乐教”为核心的教育方式
“乐教”是美育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各个教育家都十分重视的教育理念。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在启发人的情感上有着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音乐的作用从人们对自然、对生活、对生产活动的歌颂与表现被转移到教化民性上来,这突显出统治阶级乐教思想背后对‘乐’本体所寄予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内涵的重视。[4]”孔子十分重视乐教。他将“成于乐”置于美育的最后一步,也是整个美育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权衰微,孔子出于对自然人性和生理欲望的肯定,把音乐教育作为主要的美育方式,指出“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提倡通过有益的音乐对人们进行教育。
古希腊哲学家们普遍认为音乐对美育至关重要。自古希腊神话起,音乐就被视为陶冶心灵的重要力量,如俄耳甫斯的竖琴和悲歌能吸引动物。毕达哥拉斯学派视音乐为和谐的象征,能净化灵魂。亚里士多德也认同音乐的净化和陶冶作用,但强调不同音乐调式适用于不同目的,如道德教育应听合乎道德的乐调,心情愉悦则听愉快的乐调。古代中西方哲学家均认为音乐教育对美育至关重要,能培养情感、激励人心,对教育有深远影响。
2.3 以政治功利性为目的的教育观念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古人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古代东西方各学者的美育思想都是具有政治功利性的,呈现出相似的“大同”的社会目标。孔子提倡周礼,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经常梦见周公旦,将继承周公的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任务。在春秋时期,礼乐崩坏、政治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孔子希望采取一些政治教化手段来稳定当时混乱的社会局势。后人将其总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5],将政治教育贯穿在美育的始终。他认为只有人人克己复礼,约束自身,“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会有和谐的社会氛围,而这种和谐的社会氛围最终也会惠及人民,实现天下大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国外哲学家的美育思想,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柏拉图主张文艺应服务于国家政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美育与城邦稳定和人生目标的联系,重视公民道德教育。亚里士多德提出适度原则,他认为“每一种技艺之做好它的工作,乃是由于寻求居间者并以它为标准来衡量其作品”[6]。这同孔子的“中庸”思想十分相似。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古代的东方还是西方,美育的核心——仁爱、重视乐教、具有政治功利性的美育目的,都有共通之处。古代学者关于美育的思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代教育实践和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3 孔子美育思想与当代文化培育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美育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发展,都离不开美育作用的发挥。因此,在当代教育中重视美育显得尤为必要。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孔子提出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这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对社会道德的追求。“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推广美育旨在通过文艺教化民众,培养高尚人格的学生,以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其美育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当代社会将构建和谐社会的审美理想融入文艺作品,通过优秀作品感动和陶冶人心,用高尚道德情操塑造人格,促进社会的友好和谐。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7]”通过接触“尽善尽美”的文艺作品,人们会培养出追求美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尊重美、寻找美、发现美、创造美,推动社会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此,文艺工作者应强调“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念,提升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关键作用。当代美育应借助优秀作品传递美学思想,激发社会正能量,以“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的方式坚定理想,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在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当代美育承担着培养有理想、有担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重任,同时致力于弘扬中华精神、凝聚民族力量,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来提升国家软实力。美育不仅丰富了个人的精神世界,还通过艺术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促进了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它在教育体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为国家的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注入活力。通过美育,可以将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相结合,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展现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文化魅力和软实力。
4 结语
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没有美的滋养的人生必然是单调的、干涸的人生。孔子的美育思想,不仅丰富了当代美育思想,更是对后代的教育事业、社会建设以及价值观培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巧妙地将宏大的中华文化融入诗的韵味、礼的庄重与乐的和谐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滋养着受教育者的心灵。
将孔子的美育思想融入现代美育体系,不仅是对当代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深刻借鉴,更是对其的一种精彩传承与创新发展。面对未来,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孔子的美育思想,不断挖掘其内在价值,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这样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我们能够更好地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促进全球文化的交流与和谐发展。
引用
[1] 傅佩荣.儒家哲学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方韬.论语全解[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8.
[3] 彭修银.论先秦时期儒道美育思想的特质及其当代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5):125-130.
[4] 张宇辉.中国乐教的历史传统、现状与价值取向[J].乐府新声,2019(1):11-18.
[5] 孔子及其弟子.大学·中庸[M].李君兰,译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寸开.美育思想的产生及意义[J].陕西教育·高教,2013 (z2):48-49.
作者简介:古丽茹合萨·扎米尔(1997—),女,塔吉克族,新疆喀什人,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