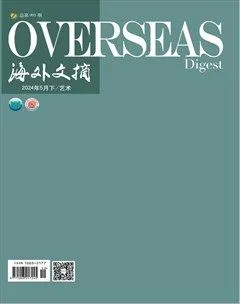舞剧《李白》的舞台美术分析
本文结合“舞台美术”课程的相关内容,分析舞剧《李白》的舞台美术运用。具体从舞台布景、舞台灯光、服装造型、道具运用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李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李白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舞台美术在展示李白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心态、不同境遇时的作用。《李白》对舞台美术的运用,在舞蹈编导过程中也经常用到,因此分析《李白》的舞台美术,对于舞蹈专业学生日后从事舞蹈编导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1 舞剧《李白》的简要介绍
《李白》是一部原创舞剧,讲述中国故事,由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和马鞍山市艺术剧院联合制作。舞剧主要聚焦于李白晚年的生活,特别是他在经历安史之乱后的抉择与命运。剧中,李白毅然投笔从戎,成为永王李璘的幕僚,却因永王兵败而被发配夜郎。这一重大转折促使他深刻反思自己的一生,尤其是步入仕途的种种经历。在宫中,李白因才气过人而挥斥方遒,意气风发,但因他不谙人情世故而遭到奸臣忌妒,因群臣进谗言而慢慢失去圣上信任,官场失意的残酷现实使他放弃为官的梦想,辞官翰林院,转而追求“愿与弼为辅”的理想生活。他自恃清高,寄情山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浪漫主义情怀,遥寄理想于天际,仿佛大鹏展翅,高飞远翔。
全剧采用了分章节叙事以及倒叙的方式,序曲部分为月夜思,讲述老年李白寄情于山水之间,在月夜下回忆起年轻时的往事。第一幕是《东巡歌》,写的是经历了安史之乱,一心扑在永王帐下,怀揣家国忧愁,披挂上阵的李白的故事。永王兵败后,李白也因曾作《永王东巡歌》的诗文等而锒铛入狱。饱含人生无奈与悲苦的李白在流放路上的经历,挣脱不了命运的羁绊,在前进的路上艰难前行。第二幕是李白梦到自己在长安的往事,在流放的路上,这是梦中的李白。李白怀揣着家国梦,应诏入宫,为翩翩起舞的杨贵妃作了一首《清平调》,被宫女们簇拥在宫中。但具有诗性才情的他,在官场上的行为却是如此的狂放天真,他最终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皇帝的赏识,报国无门的他只得挥袖别翰林。第三幕为归去,流放的路上,有诗友、乡民陪伴在李白左右,从这一幕中,乡民能感受到李白的那份快乐。他与乡民一起踏歌,在大自然中徜徉,与乡民同乐,他和乡民一起,寄情山水,与乡民结为一家亲。至此,李白几经困顿,终于释怀了尘世之念,在山水间挥洒了自己的豪情,也让他的诗酒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回归。结尾处是大鹏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舞剧的结尾,一代诗仙以生命的豪迈情怀,伴着悠悠古诗,伴着明月飞舞,荡气回肠。这对于大浪淘沙的诗人们来说,或许应该是一个该有的风流归宿。
总体而言,《李白》在抽象化诸多事件的同时,没有语言对白地放大了情感,起到了“情动于中,形于言”的效果,是一部十分扣人心弦的舞剧。本文将从舞台布景、舞台灯光、服装造型、道具运用四方面分析《李白》的舞台美术运用。
2 舞台布景中的山水仙境与宫廷斗争
2.1 舞台布景中的山水仙境
序曲“月夜思”的舞台布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在唐代山水画的基础上,呈现出白色云雾飘荡在深色山中的场景,云雾之间错落摆放着形态各异的山石来构造立体场景,李白随着诗歌“乘长风而来兮,载明月以归兮”的旁白在云山雾绕的场景中悠然自得,身着一袭白衣穿梭在云山雾绕的仙境中,身后电子屏幕上的山水水墨画卷轴随着李白的行走慢慢展开。这一幕舞台布景中着色并不多,主要以白色的云雾和黑色的山石为主,黑白两色的结合以有限的着色去接近生活的本质和生命的真谛。
序曲部分整体背景均采用了卷轴形式,一方面与传统中国画的构图方式相同,结合李白此时的情绪,使观众仿佛与李白一同置身于山水仙境之中;另一方面,序曲的卷轴给人印象深刻,尾声部分的大鹏赋也采用了相同的卷轴布景,相互响应,表达李白在经历世间坎坷后心境的豁达。
2.2 舞台布景中的宫廷斗争
第一幕东巡歌中,舞台布景由前后共三组屏风缓缓展开,屏风后是面向舞台的李白,手中举着东巡歌卷轴,转身向舞台内侧走去,借由屏风展开的布景,展示李白向永王献上《永王东巡歌》的过程。事实上,细细端详登场的屏风,是从李白书法与唐五代山水画相结合的盛唐建筑与纹饰中,提炼出的黑金配色概念,重新构架而成的一套完整的屏风。在整个篇章式的虚实切换的剧情中,这些屏风装置与空灵的山水和灯光表现以及富丽的宫廷元素都兼容得很和谐。同时,这个看似写实的贯穿形象也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黑金的框架如同是李白一生难以逃脱的世俗禁锢,清透的山水诗意如同他狂放不羁的心灵向往,共同构成了这个矛盾的李白,以及他穿越古今的浪漫和壮怀。
3 舞台灯光的留白与空灵境界
舞剧《李白》并没有使用过于炫丽和过于明亮的灯光,更多是以简单的色彩搭配来突出舞蹈动作和人物心境,结合人物服装搭配,突出展示人物内心的变化。比如在尾声最后一幕中,李白在《静夜思》的思绪下慢步走入昏黄的灯光下,通过灯光与人物的光影效果,表明了月亮的存在。李白孤独站立的倒影与舞台上大片的留白场景共同构成了舞台造景,虚实结合的方法表现了月亮深邃空灵的意境,李白月下自恰的诗意在此刻自然流露而出。
利用灯光与颜色描绘人物情绪的方式,在该舞剧的大部分剧情中都存在,特别是李白在遭受群臣排斥而被流放时,内心充满了对世界的怀疑和自己未能实现抱负的自我价值观矛盾。此时,舞台灯光使用了蓝色与白色的聚光灯束,周围的舞台陷入黑暗,光束只投射在李白身上,呈现出李白内心的挣扎,也将观众的目光聚焦在李白身上,体会李白的心境变化,这一体会因观众自身的人生经历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体会,丰富了观众的情感体验的想象空间。在李白流放的过程中,在明白人生的真谛,与田间地头的农民跳起踏歌舞时,舞台灯光也同样为暖黄色,照亮整个舞台,也暗示着照亮李白的内心。《李白》的舞台灯光运用,不仅是为了剧情需要进行使用,同时也向观众传达了李白的内心情绪。
4 服装造型呈现李白的不同形象
服装设计作为舞美设计的重要部分之一,赋予舞剧演员表演角色的属性,也让观众通过服装获得更丰富的人物信息[1]。舞剧《李白》中在主演和群演的服装设计上集中使用了大量白色,而李白在其诗歌中充满了对白色的体现,因此白色是体现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重要手段,同时借助白色服装,暗示李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突出李白的仙风道骨。
在序曲中,李白一身白衣,身后披着长长的白色披风,拖挂着占据了约半个舞台的长度,结合着现代科技营造的仙气飘飘的氛围,营造出李白的仙骨风韵。到了第一幕,李白拜于永王门下从军。至此,为了符合从军的利落形象,李白换上了一身干练的白衣,与群演饰演的其他参军士兵一身红衣铠甲形成对比。在第二幕中,李白受到玄宗赏识,拜见玄宗时一身白色官衣,头戴白色官帽,一方面显示李白拜见圣上时的庄重素雅,另一方面显示李白对于朝中百官的不屑一顾,不愿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在李白遭人陷害流放途中,虽然仍为白衣,但与之前庄重素雅的官衣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李白的落魄。
在第三幕“归去来”片段中,与李白一起开怀畅饮的樵夫,其服装也使用了黑白相结合的色彩搭配,头上的斗笠将传统的全遮面白纱简化为条带状白色丝带,裙摆处使用了大量的墨色进行装饰,樵夫的服装在饮酒跳舞过程中随着身体舞动而自由飞扬,朴素简单的服装和自由的动态突显了道家美学的自由、恬淡。李白服装上黑色与白色的结合,巧妙地与舞台布景中的山水水墨画融合在一起,二者的巧妙搭配既表明了道家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现,也刻画了此时李白纵情于山水的自由心态和精神层面的真正解放。
5 运用道具呈现角色的内心世界
5.1 第一幕的道具展现李白所处环境的变化
在第一幕中,李白向永王献上《永王东巡歌》,舞剧对于这一场景进行了艺术化的描述,李白身着一袭白衣配合着快节奏的鼓点音乐,手中拿着卷轴和毛笔指挥将士,大开大合的动作好像正在舞剑,就好像是李白亲自站上战场,指挥将士,亲自杀敌。而到了“夜郎泪”片段中,同样是李白自己所做的诗歌卷轴,此时该卷轴将李白团团束缚,使李白无法挣脱,象征李白深陷“谋反”指控无法脱身的状况,连同李白的报国热情和不甘一起捆缚。在李白与政敌斗争的过程中,对手身着官袍,用快节奏的动作对李白步步紧逼,没有任何台词但却针锋相对。官员的两位帮手搬出凳子要李白坐下,李白不愿坐下但是退无可退,最终被逼地坐在了凳子上,这个凳子其实是对李白罪名的比喻,将官员对李白的罪名具象化地展现出来,李白最终被逼迫着坐在凳子上也就是确认了其叛乱罪名。
5.2 第二幕的道具展现李白的狂傲不羁
在第二幕《金銮别》中,李白的世俗成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他因才气出众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成了唐玄宗身边的红人,经常侍奉在其左右,写下了众多流传至今的经典佳作,人生得意风光无限。然而好景不长,李白的才气与他狂傲不羁的性格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从李白的众多作品中可见一斑。正因如此,李白得罪了奸臣,正所谓人言可畏,李白因受迫害而失去唐玄宗的信任。李白在辞别时上演了一出舞剑的独舞,剑对于李白而言是实现人生抱负的寄托,而此时李白只能借舞剑表现其抱负无法实现的不甘。并且这段独舞是在李白醉酒状态下进行的,李白醉酒的理由有很多,此处是因内心困顿不甘和怀才不遇而借酒与剑抒发情感、表达心境。
5.3 第三幕的道具展现李白心境的变化
李白看清官场的黑暗后,发现这里并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抱负,于是转身离开。整日通过醉酒来排解心中的困顿,可见剧目对于李白困顿的消解,主要以醉酒来完成。这既符合李白嗜酒的史实,也符合仙者形象的塑造。这种醉酒,是潇洒痛饮,是欣然大醉,是对黑暗现实的轻蔑,也是李白对内心的守护[2]。
最后一幕《九天阔》中,李白展现了一出月下醉酒独舞,李白在酒精的催化下从舞台一边慢慢舞动至舞台中央,不停地做出敬酒动作,并不停地起舞。在月光下李白的影子也与李白一同起舞,呈现出李白对影成三人的诗歌意境。最终李白回到舞台边缘的石桌旁,对着月亮拱手膜拜。舞剧中多次出现对于月亮、酒、剑的运用,演绎了李白不同时期不同的心理变化,最终李白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归宿。
6 结语
民族舞剧《李白》对李白形象的塑造是一场历史与艺术的融合,它不是李白生平的再现,而是对李白内心的表达。从“人”到“仙”的转变[3],李白追求政治,向往自由,娓娓道来。在舞美设计团队的携手合作下,民族舞剧《李白》被赋予浓郁而崇高的民族化特色。舞剧舞美设计所体现的美学价值,提升了观众对中国古典美学理想的认知,同时也为今后同类型舞剧的美学构思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实践了弘扬中国美育精神的核心任务。
引用
[1] 李易霖.民族舞剧《李白》舞美设计中道家美学的呈现[J].美术文献,2022(6):114-116.
[2] 卢莉,姚舒月.从困顿的“人”到自由的“仙”:论民族舞剧《李白》中的李白形象[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 43(1):25-33.
[3] 关冠.《李白》:一场融诗于舞的盛宴[J].戏剧文学,2020 (6):106-108.
作者简介:周琳(1995—),女,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太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