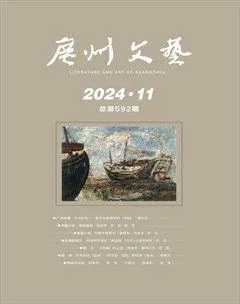一个人,两棵树
2011年,我从上海回广州读书,毕业后又留在广州工作。在这十余年里,广州,还有岭南,与我生活、经验、记忆关联渐深,以至于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对于岭南的了解无疑比以前更多了,不过我又经常觉得,自己对于岭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深。我对岭南的当下世界有很多切近的经验,对岭南的历史世界却所知有限。对于岭南的历史世界,我以往主要是在国族史的视野、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框架去理解它,把它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视为中国的一个地方。而岭南是有世界性的,除了从国族史的视野去理解它,我们还应该从全球史的视野去理解它。国族史的视野,是指以民族国家作为空间分析的基本单位或最大单位。全球史的视野,则是指在观看、思考时,所选择的路径是跨区域、跨国家、跨文化的,重视不同国家、区域或文化之间的连接与互动,主张人类彼此互联、共享一个世界。这两种历史视野,在历史分析的方法、内容、目标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我试图以这双重视野去走读岭南,认识岭南。
两年前,我和好些作家朋友一起去黄埔。一天的行程里,所走的地方并不算多,却也有三四处。如今想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海神庙。它位于黄埔的庙头村边,是中国四大海神庙中唯一保存下来的海神庙。南海神庙是历代皇帝祭海的重要场所,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它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自隋唐以来,历代皇帝都会派遣官员来此祭海。南海神名叫祝融,也有史书称其为祝赤。关于祝融究竟是谁,民间有许多传说。在有的传说中,祝融是中国帝王,是一个音乐家。也有传说认为祝融是黄帝时专司辨认方向的司徒,是楚人的始祖。祝融还被认为是火神,是南方之神。让我特别留心的是,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据说此别称的由来,与一位名叫达奚的异邦人有关。相传在唐朝,古波罗国(古印度)有一位朝贡使叫达奚。那时候,很多国家都想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会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来中国朝贡,达奚是其中的一员。他乘坐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到唐朝京城朝贡后,回程搭乘的商船停靠在了南海神庙码头。达奚在神庙游览祭祀,还将从古波罗国带来的两棵波罗树种在庙中。达奚对神庙还有周边的美景非常入迷,商船都开走了还浑然不知。误了行程无法返乡的达奚,于是常年望海悲泣。他经常把左手举在额前,望向大海的深处,望向他遥不可及的故乡,最后立化在海边。人们感念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就照着他生前的样子,为他在神庙仪门东廊塑像。南海神则封他为“达奚司空”,让他参与处理神庙的事务,并享受人们的祭祀。南海神庙中的达奚司空像,身穿唐代官服,头戴中国官帽,做眺望远方状,在民间就有了“番鬼望波罗”的俗称,南海神庙也因此被称为“波罗庙”。
从南海神到达奚司空,南海神庙的不同历史情景与传说,很是耐人寻味。它是地方的,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达奚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吗?如果是的话,当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眼中的异邦最为吸引他的又是什么?达奚错过返程的海船后,又有怎样的经历?彼时人们最初是怎样看待这个“番鬼”?又经历怎样的波折,达奚得以成圣、成神?这种种疑问,有的有相对确定的答案,有的则往不同的方向发生分叉。比如在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波罗神的传说。它发生于南海神庙东边的海光寺,主角是一个日本小孩。时间则是在明代,说的是有一艘来自扶桑国(日本)的商船来到南海神庙对开的海面,船员们都下船来参拜海神,其中有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到神庙后独自乱走,离大人们越走越远。直到海船开航后,这个孩子才发现已错过商船的时间,只能望着远去的商船号啕大哭。之后,他每天都大哭,一哭再哭,直至有一天在波罗树下立化。当地的乡民怜悯这个孩子,于是为他塑像,立于海光寺大殿一旁。神奇的是,庙祝每天打扫庙宇时,总会发现塑像下有水迹,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一个诗人到此游历,听闻故事后若有所思,在塑像前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日出扶桑是我家,自从流落在中华,鸡鸣犬吠皆相似,到处杨梅一样花。”神奇的是,从此以后,水迹再也没有了。
在这个版本的传说中,叙事变得更为日常化和世俗化,还彰显了文学的力量,强调了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我能够得知这些往事或传说,则得益于今人的口述和整理。(本文中关于番鬼望波罗的故事和众多细节,得益于张沃兴、彭潜、张灼然等人的口述——由黄应丰整理,特此说明和鸣谢口述者、整理者。)在民间的口头传播之外,“番鬼望波罗”也有大量的文字记载。这些口述和文字,构筑了一条又一条想象历史的道路。
和南海神庙一样,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同样让我感到震撼。去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前,我已读过不少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岭南的著作。我已知道,从明代以来,广州,也包括岭南,就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区域。尤其是在1757年到1842年,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唯一的对欧美通商特区。这使得广州、岭南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政治互动、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那个时期的广州非常有意思,在跨文化实践上,产生了很多让人眼界大开、脑洞大开的事物。比如外销画、外销瓷、广钟等等。它们往往用大胆的、激进的方式把中国和异域的不同文化元素、观念等融合在一起,在观念和技术上都做到了极致。虽然已有这种知识上的准备,在走进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后,我还是被震住了。当形形色色的外销画、外销瓷、广钟等物品无比具体地出现在眼前,我知道了更多更为具体丰富的细节。比如当中的很多外销扇,扇面的内容既与传统的中国绘画有关,题材脱胎于中国文化传统,又经过微妙的变形,融入了异域的趣味和眼光。有的扇面,可能是分别由擅长中国画法和西式画法的不同画师共同完成的,或是出自同一位兼备中西画技的画师之手。中国的和外国的元素,并置于同一平面上,内在于同一扇面中。而透过这样一把小小的扇子,中国和世界有了联通的渠道。
今年广东文学馆的开馆,也让我感触很深。广东文学馆坐落于白鹅潭,那里也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走进广东文学馆时,我很快就感受了一种大历史的气场。置身白鹅潭,我再一次体会到,岭南文化是很早就有跨文化属性的,是有先锋性的。当时的很多观念和事物,也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当下。比如大湾区的想象和实践,既来自对全球新形势的考虑和判断,也和广州、和岭南在历史上的殊异不无关系。
行走在岭南,回顾我们的文学、文化和文明,我也深觉,起码从晚清以来,岭南就拥有了最具现代性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无疑是文学的富矿,值得深入挖掘,掘地三尺。许多年前,我的梦想是当一位小说家,完全没想过日后会以文学评论作为主要的言说方式。不过如今,动笔写小说的念头,也还是会不时涌现。比如,写一部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小说。是的,很多与此相关的事物其实一直吸引着我。如果有一天真的会动笔,我想,我的想象会回到既古老又崭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会回到黄埔。我想回到旧时的南海神庙,去看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许多陌生面孔,看看他们眼里的惊异、好奇、喜悦和哀伤。
在故事的起初,有一个人,两棵树……
责任编辑:朱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