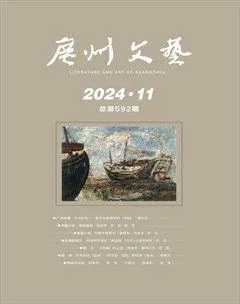芥末须弥(组诗)
芥末须弥:寄胡亮
五十多了,更渴望在自己划定的禁地
写作
于芥子硬壳之中,看须弥山的不可穷尽
让每天的生活越来越具体、琐碎、清晰
鸟儿在枯草丛中,也像在我随心所欲
写下的字、词、句、篇的丛林中散步……
我活在它脚印之中,不在这脚印之外
寒来暑往,鸟儿掉下羽毛又长出羽毛
窗外光线崩散,弥漫着静谧、莫名的
旋律
我住在这缄默之中,不再看向这缄默
之外
想说的话越来越少了,有时只剩下几
个字
朝霞晚霞,一字之别
虚空碧空,裸眼可见
随身边物起舞吧,哪里有什么顿悟渐悟
一切敞开着,无一物能将自我藏匿起来
赤膊赤脚,水阔风凉
枫叶蕉叶,触目即逝
读读看,这几个字的区别在哪里
芥末须弥,这既离且合的玄妙裂隙在哪里
我被激荡着,充满着,又分明一直是空心的
惠安女
皆裹靛蓝碎花头巾
笑容皆散淡
体内皆有艰深跋涉异于他省女人
我冒酷热到此一游,结识惠安女三人
一人以她四岁的清亮瞳仁磨洗我
一人以脏皮革裹奶水的辛酸劳作覆盖我
一人正坐对面藤椅上
昏昏欲睡
以她九十年冗长的家族往事沉溺我
我有灰白的心理病历
和诸般精神辎重,须在此卸下
——只是碰巧。随手抛掷于翻腾的海水中
海水咸而不安。惠安恬静
海中有一滴记得我
我转身犹如上岸
羞 辱
我曾蒙受的羞辱。那些扭曲的人,或事
时常回到我心里。像盆中未尽的炭火复明
但不再有一个我,感到烧灼——
这些年我在退缩
仿佛我的多产,也是一种退缩
像阴影为强光所驱逐
退缩,一直到我曾经难以隐身的
那些羞辱之中
依然可以在那儿坐下,走动,醒来
当我醒来,觉得
……它平静的利爪仍踩在我脸上
受辱依然可以成为,我诗句的一个源头
而我不必再急于否认
……当它重来。窗外的
小雨中梨花尽白
仿佛这个神秘时刻
可以一直持续到
我们真正垂亡之时
而早已湮灭的那些日子,那复杂的远行中
我未曾抛弃过任何一件笨重而阴郁的行李
纸上舌头
一个以文学翻译为生的老者逝去
我能拿出的祭品
是持续多日的这场,沉浸的冬雨
一个衰竭的生命依然会关心他将
变成什么——灯盏,还是
灯光?雨点,还是雨燕?
形体之变在谨慎地偏离原貌
回忆卷入……他在重症室昏迷多日的
谵语,断断续续,渐渐让
他曾藏起来的翅膀张开了
羽状触角为蛾,锤状触角
为蝶——世上最艰难的转译莫过如此
对二者之别
有谁来问?他闻而不答
而我们可以倾听的,只剩他纸上的舌头
梨子的侧面
一阵风把我的眼球吹裂成
眼前这些紫色的葡萄
白的花,黑的鸟,蓝色的河流
画架上
布满砂粒的火焰
我球状的视觉均分在诸物的静穆里
窗外黛青的远山
也被久立的画家一笔取走
我看着她
——保持饥饿感真好
我保持着欲望、饮食、语言上的三重饥饿
体内仿佛空出一大块地方
这种空很大
可以塞进44个师的
轻骑兵
我在我体内轻轻晃动着
我站在每一个涌入我体内的物体上出汗
在她的每一笔中
只有爱与被爱依然是一个困境
一阵风吹过殡仪馆的
下午
我搂过她的腰、肩膀、脚踝
她的颤抖
她的神经质
正在烧成一把灰
我安静地垂着头。而她生命中全部的灰
正在赶往那一天
我们刚刚认识
我伸出手说
“你好”……
风吹着素描中一只梨子的侧面
除夕鸿泥
阴沉的除夕午后,偶尔云开
几束光线射入,照着高大书架
我将睡在故纸中度过这惶惑一日
退至某种硬壳中寻求庇护的
愿望,如此可笑……
孔子的牛车,鲁迅的阁楼,佩索阿的假名
何尝不是一种壳,又全都如此不堪一击
将自身全然暴露在风雨中的
岁月。被击溃的碎片古来多见
“人,会不会沦为另一种
叙事语调的囚徒?”
因电压不稳而闪烁不定的白炽灯
忽明,忽暗……幸好,即便像纳博科夫
终生只埋头研究蛱蝶也能拯救一个人
风
坐火车穿过蚌(埠)宿(州)一线
向着豫东、鲁西南敞开的千里沃野
地图上一小块扇形区域
哺育生民数以亿计
高铁车窗外圆月高悬
圆月即是
他人之苦
是众人之苦的总和,所有的……
秋天的田野空下来
豆荚低伏,裂开,种子入地
黝黑平原深处,埋着犯人
路上,新嫁娘不紧不慢
在摩托车队中……上辈子在骡队中
她并不完全懂得自己要
担负的三样(或是一样)东西:
追溯、繁衍和遗传——
高铁车窗外秋风阵阵
我一直纳闷,在此无限丰饶之上
那么多的生死、战乱、迁徙、旱灾
那么深的喂养、生育、哭泣
那么隐秘的誓言、诅咒、托付……
最终去了哪里,都变成了什么
为何在这大风中,在这块土地上
三百余年没有产生哪怕是
一行,可以永生的诗句
风
“那些年,围墙的铁丝网上
蹲着成排成排的麻雀
淋雨了也不飞走
不管它们挨得有多近
我只记得,那抹不掉的孤儿气息”
后来你告诉我,世上
还有更干净的麻雀
更失落的,铁丝网
内在旋律
旷野发出呼唤恰在它灰蒙蒙的时刻
它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内在的旋律
只有泥和水的内外如一
不规则的沟渠被坚冰冻住了
枯草在上面形成奇特的花纹
或许这并非对人的召唤
无人知晓,物化、庸碌的人生之梦究竟有
多长
人的世界欲两两相知
就得相互磨损
在皮开肉绽之中融入爱与被爱的经验
此刻想赤脚深深扎入泥泞
而坚冰将我们拒绝于外
旷野灰蒙蒙的。只有磨损
没有接纳
只有岑寂的敞开,没有一点点内在的旋律
孤月图鉴
松上月,沟渠中月,井底月……
在城里我已多年没见了
月亮的亿万分身,没有一个让人焦灼
最沉闷的物种,只有我们
小时候,我推门,月亮进门
小院月,小镇月,黑松林
之月,闷罐车之月……
万籁俱寂,骑自行车二十分钟
万般挣扎,又浑然不觉
它如痴如醉荡漾着的样子
我已经多年没见了
今日之我怎么可能从
昨日之我中,生长出来
我只是在那儿不寐过,动荡过,失踪过
它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板结的
发光体,一座光的废墟?
从什么时候起,它的浓度
被稀释了,歇斯底里的消磨开始了
牺牲者的面容显现了……今夜它
仿佛只是由这些具体的
轻度的、我能数得出口的创伤构成
它在碑顶,在井底,在舌尖
但没人再相信它
可以无畏地照临
薇依临终时曾指月喃喃:
“瞧,不可蚀的核心,还在”
而今夜,我笃定、佯狂
同时驱动,炙烈与清凉这两具旧引擎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