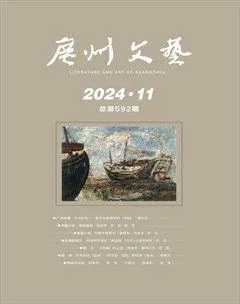寻找属于自己的“异域之境”
段爱松:浩兄好,受《广州文艺》之邀,让我找一位北方作家对谈,我心中第一时间闪现的念头就是您,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们却时常能在微信或电话的交流中,感受到文学的温暖和力量。南方和北方,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相对概念,基于地域差别,您是如何看待南方写作和北方写作的?
李 浩:对文学写作来说,地理概念并不单纯,它是一种具有复杂影响的、作用于日常和记忆的重要因素,它和童年因素、家庭及遗传因素、知识背景因素和宽阔的、未知的X因素共同构成“本质性影响”,而地理因素对作家的影响更为丰富、复杂,甚至可以渗透到所有的相关因素之中。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有批评家武断地、片面深刻地认定,作家的“所谓个性其实更多地是地域性”。
在我看来,南方作家多灵动,诗性,温润,平和,“水气淋漓”,在句秀、骨秀上表现突出;而北方作家则多宽阔、质朴,硬朗、粗犷,多在尖锐和冲撞的点上用力,相对的差别还是明显的。我们看属于南方的作家余华、苏童,与属于北方的作家莫言、陈忠实,在写作风格、问题意识以及语言使用上都有不同——而现在提及的“新南方”,它又是有所不同的地域,是的,我们在以往的审美理解中或多或少对江南更南的地域性呈现有所忽视。这个“新南方”的确值得有更多的重视——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北方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学标志性”还是有诸多区别的。
我也不止一次地“自我标榜”,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向往温雅的粗人”,希望自己能够具有南方性,希望自己能够多从南方性和南方作家的身上汲取——我喜欢南方作家的语言方式和艺术质地,喜欢南方作家的精致、细密和意犹未尽。这是北方作家多数所匮乏的,当然也是我所匮乏的。
段爱松: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地域概念集中和缩小一点儿,您出生的河北和我出生的云南,在中国版图上,拉了一个遥远的对角线。您认为这两地作家作品,整体风格特征各是什么?有哪些显著的异同点?
李 浩:我愿意再次强调地域性对于作家的赋予,它是重要的——尽管地域性未必是最为重要和核心的要素。而且,地域概念连接的不只是地理区别,更重要的还有文化历史的种种不同,还有风土人情和其他因素对人的影响。
如果谈及两地作家的特征和区别……就我个人片面的理解,云南的作家其特征性大约是:他们具有“新南方”写作的某些特征,譬如比南方作家多一些粗犷的、阻隔的、野性的成分;风土人情、民族习惯的影响更大些,它本身即保持了陌生和差异;或多或少带有些“巫气”,也就是说云南作家的身上依然带有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自然灵性的东西,它在当下的写作中显得极为特别和重要。河北作家,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占有主流,多数作家的书写集中于日常发生,生活化的特征明显;习惯审视故事发生背后的诸多因素,愿意在尖锐和锋利上用力;新的一些作家先锋性品质也较为明显。
我们也必须看到,作家除了会携带种种的所谓地域文化特征外,他们试图要做的是突破PoxnR748rlvKTVCPqOByGA==,是“个人呈现”,是个人的异质性。譬如同是云南作家,于坚和雷平阳的风格方式就有明显不同;你、和晓梅、陈鹏、包倬、胡性能、潘灵的小说风格就极为不同。在河北作家中,像刘建东的、胡学文的、张楚的、付秀莹的小说,像郁葱的、大解的、韩文戈的诗歌,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没有一个作家愿意成为渺小的后来者,没有一个作家愿意依附于地方的共性后面——这也是我想在地方性的话题中略有强调的。
段爱松:我知道您作为河北作家,多次到访过云南,与云南不少作家都成为朋友,在与云南作家的交流中,您是如何看待云南作家的写作的,对云南作家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
李 浩:云南的作家群让我敬重,无论是诗人还是小说家——毋庸讳言,诗人似乎更突出点,他们更具鲜明性和世界影响。我说云南作家群让我敬重并非外交辞令,而是源自真诚,我承认,在云南作家的启示下我在不断地变更和调整自己的写作——包括你的《金缕曲》。我愿意从你和所有优秀作家那里汲取,无论他是河北的,
云南的,美国的,欧洲的,还是日本的。
在云南作家那里,我有着丰富而丰沛的汲取,譬如在于坚的写作中我学到了日常口语和诗性的调和,在雷平阳的诗歌及散文写作中学到了诗性和神性的调和;在胡性能的小说写作中我学习着貌似不用力的用力,在你的小说中学习着历史、传说和现实的神秘交织术,在和晓梅的小说中学习着建立意犹未尽的回荡……我也在像刘年、王单单的诗歌中学到了许多。
不过,我想,你让我“对云南作家说”,可能并不是试图让我枚举云南作家能带给我的,而是希望我以一个有差别的地方作家和文学同道的身份,对云南的年轻作家“提几点要求”,是不是?作为一个恬不知耻的、好为人师的人,我也就按我的猜度对云南的作家乃至所有的青年作家说几句话吧。
一是,我愿意云南的青年作家充分利用好地方性资源,充分利用好差异和独特,以它来建立更强的个人标识。这是突出差异化的一个特别“便捷”的渠道,特别好用。
二是,多读书,多出来走走——即使我们使用地方性资源,也需要一个世界的、人类的宽阔背景,我们要努力把所有的地方性都纳入人类的共同知识和智慧的前提下进行考察。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这句片面深刻的短语其实有个前提——所有的地方性、时代性因素,都是在能够让其他民族、国度的人理解并能从中获得智慧的前提下才能有效。
三是,南方的人要多向北方人学习,北方的人则要多向南方人学习——文化互鉴、文明互鉴并不只是针对不同国度的人来说的,也是针对南方和北方,针对不同的个人来说的。一个写作者,只有融合了南方和北方的不同特点,才能让自己的写作“达到极致”的好。
段爱松:您认为国外作家有没有南方写作和北方写作之说?请举一些例子详细说说。
李 浩:哈哈,考我的文史知识呢?据我所知,同样是阔大的美国,是有南方写作和北方写作之说的,而在欧洲,因为多数国家都是“小国”,所以南北不那么容易划分,于是他们就以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语言来划分这一“南北”,使用法语和使用德语的、使用英语的、使用捷克语的……我个人认为,环境的不同、语言的不同一定会对作家产生诸多的影响,民族和肤色的不同也会对作家产生诸多的影响——即使他们不使用所谓的“南北”概念。
段爱松:2017年,何平教授主持《花城》杂志新栏目“花城关注”时,我提出过一个观点“有自己独到的异域之境,就应该写出不一样的小说”。所谓的异域之境,其实指的就是我生活的南方小镇晋城(小说里的晋虚城),给予我的文学地标与启示。不知道您作为北方作家怎么看?是否您也有这样的文学地理?它对您的小说有什么影响?
李 浩:说得好。有自己独到的异域之境,就应该写出不一样的小说:我极为认可这一观点。有时候,这个“异域之境”还是自造的,它可能未必是(至少未必完全是)地理特征。譬如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譬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譬如苏童的香椿街,譬如徐则臣的花街……它们可能并非原有意义上的地理属性,而是一个充分被“异域之境”化的安置点,从而成为故事的原乡。
怎么看?羡慕,嫉妒。因为你们的这个“异域之境”本身就包含了差异性、独特性,带有天然的陌生感——陌生,对文学写作来说是何其重要!在北方的作家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作家特别羡慕你们的这一点,因为我们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甚至有些省与省之间的差异都是小的,极小的,我们看到的多是基本和共有,无法从这个点上完成区别。我承认,特别承认,你和那些“新南方”作家,以及像阿来、次仁罗布和写出《天·藏》的宁肯,都能如此天然而自觉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之境”,着实让人羡慕。
我?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能,也有。只是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和历史的影响之下,我故乡的地方性特征并不那么彰显,要建造它,人为的痕迹会相当明显——何况,有莫言在前,我也不想成为渺小的后来者。于是,我试图建造的“异域之境”则是另一个策略,我将它建筑在“象征性的人物”身上而非地理标识之上——所以,我写下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父亲”,让他携带着父权的象征,北方男人的象征,民族性的象征,以及……在我的小说中,“父亲”是一件制服,它部分地也充当着你所说的“异域之境”的成分——当然,我更愿意自己能拥有与你大致相同的“异域之境”,因为它会变成保持差异性和陌生化的“双保险”。
段爱松:请讲述下您作品中的北方写作特征。另外,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过南方的影响?
李 浩:我小说中的北方特征可能更多是地理学的,譬如我会反复地书写我生活过的村庄和当地人的生活,譬如我长篇小说《如归旅店》的叙事背景是沧州泊头,《灶王传奇》的叙事背景是张家口蔚县——尽管,强大的虚构产生真实,虚构一种陌生生活是作家的必备功课,但如果书写自己熟悉的事物会更让自己轻松,更让自己专注于故事而不是细节的真实感上。我想我小说中的北方特征可能还有:第一,对于所谓大话题的关注,对于家国、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某种关注……第二,粗砺感,甚至部分的粗糙感,这是我想掩饰也掩饰不住的,时常过于粗枝大叶,匮乏耐心收拾的信心与能力。第三,注重大块的关系处理,而在细部的精妙处理上同样不够。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有北方作家的厚重和沉实,但它是希望,并不是已经达到。
至于南方作家的影响……哈,这是往枪口上撞啊,我甚至可以说,影响我最多、最大的就是南方作家,持续对我的写作有影响的更多也是南方作家。譬如鲁迅、余华、于坚、孙甘露等等。鲁迅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他现在依然是我心底最信任的偶像,我希望永远有他的陪伴甚至争吵;我不止一次地提及过我对余华语言的模仿,故事结构的模仿,以至于多年之后,我不得不从米兰·昆德拉、君特·格拉斯、尤瑟纳尔和杜拉斯的语言中汲取,以使自己“不像”余华,看不出这一种师承。我喜欢苏童,喜欢他文字里的气息和那种语言的绸缎感,喜欢他文字里的水气和润泽,后来我在北方作家张楚的小说中读到了同样的意韵贮含。我喜欢孙甘露语言的缠绕和神秘感,喜欢他和所有南方作家在故事讲述中的精妙和自如……我当然受过南方作家的影响,甚至,南方式的写作一直是我的向往。
段爱松:当下科技与社会发展迅猛,在文学界,以前类型小说的概念,已悄然发生改变,比如科幻小说等。在这些小说中,您认为有没有南方或者北方地域写作的差别?
李 浩:是的,文学中的互通有无始终在发生,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敞开,让自己有一个宽阔,或者更宽阔——我们不止要在中国南方和北方之间互通有无,甚至要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互通有无,要在人类共同命运的前提下互通有无,在保障自己的个性差异的同时致力于影响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程。至少,以智识性的、创造性的努力让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国度的“最强大脑”服气。这一点上,我可能部分地、片面地认同文明无国界,智慧无国界,精神资源无国界。
但同时,我也会在强调了A的同时强调它的反面——B。正是基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正是人类知识、智慧和发展的共有,我更愿意对所谓的地方性差异的保持做出强调——南方和北方的差异是存在的,这种差异一边在消融一边在坚固,可能会变成新的结晶体。我也希望我们的写作能为此助力。
段爱松: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南方写作和北方写作如何保持独立?又如何实现交融?
李 浩:我的意见是,首先保障和实现交融,尽最大可能地从对方的、不一样的地方汲取,尽最大可能地让自己变得宽阔、丰富和敞开。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满足于成为一个地方性的小作家也许……哈,我不知道该怎样使用具有定义性的词合适,不过我以为你是明白的。我们首先要保障的是让自己不狭小、平庸。独立,是在这一基础上来谈的,有了交融性的宽阔之后才可以谈独立——我的这一看法也许是偏见,但我不做更正。我们写作的独立性往往在于,我们肯用自己的眼而不是他者的眼(权威的眼、导师的眼、批评家和读者的眼)去看世界,只要我们愿意用自己的真心和真诚去淋漓书写,这种独立性会自然而然地获得呈现。同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写作不同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也不同于帕斯捷尔纳克——我们在强调地方性地域性的同时,也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强调,就是作家的独立甚至包含着他对地方性的抵抗,对于那个地方约定俗成的部分的有意区别。你说呢?
段爱松:有没有作为北方作家的身份,写一写南方或者云南题材的计划?
李 浩:有,太有了。我特别想写我臆想的、想象的、幻觉的和带有强烈个人理解的南方。我原来有一个长篇,《浅行板》,想以自叙的方式写下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生活和理想,但最终夭折:因为我太害怕写到细节了,我甚至要为那些革命党人和革命党人的妻子安排好属于当地的器物,否则他们一定“坐立难安”。我也有一个写一写民国后期在藏族民族地区的一段历史,土司的武装、马步芳的武装和其他的武装都来到了这里,都在争取……我承认它足够庞大但我同样也害怕着细节。是的,南方,或者说云南,也一直是我向往的、试图书写的一个区域,我甚至想和南方的、云南的作家“较量”一下——譬如说远征军题材。我在想,也许有生之年,我会完成它。我会以我的方式,以一个中国作家的方式来完成它。
责任编辑:朱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