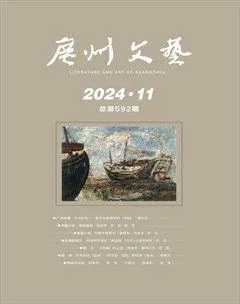“新南方写作”关键词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方性书写中,恐怕还没有哪一类写作像“新南方写作”那样,集丰富与差异、临界与跨界于一体。它既带有生猛鲜活的地方经验和奇诡迷人的美学特质,也有着跨文化、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特点。
“相较于糟糕的清晰,模糊有其长处”,讨论“新南方写作”,不妨暂且放下对精确的、统摄性的本质观念的执着,将目光投向具体文本,探寻概念的实在表现。“新南方写作”不是封闭的,而是向世界敞开的。以动态关系的视角来考察,会发现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角力已然构成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基础,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性书写的重要特征。换言之,“新南方写作”本身就是在地方性与世界性的不断搏击中发展起来的。从“下南洋”到改革开放的对外交流经验,高度活跃的人口迁移,杂居多样的区域族群……这些因素提示着“新南方写作”的生成背景,它与世界性有天然的联系。
对“新南方写作”来说,世界性不仅是一种召唤,更是一种现实。讨论其世界性,不是为了凸显概念范围进行“圈地运动”,也不是凭一腔热情空喊口号以纾解焦虑,而是地方经验不断挖掘之后亟需思考的问题。陈思和曾指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识、世界眼界以及世界性的知识结构,也包括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以及各种来自‘世界’的构成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性也包括中国文学的自身因素。循着世界性来考察“新南方写作”,从“世界中”的接受再造到“到世界去”的跨域书写,这一创作实践不仅蕴含地方叙事的自觉,也标识着“全球南方”背景下文学对文化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多样理解方式。
一、在“世界中”阅读与书写
一个好的作家,一定也是一个好的读者。他从来不会轻易避开与世界、与经典相遇时的目光。莫言就曾直言福克纳对自己的影响,多次提及福克纳是自己未曾谋面的导师。这提醒我们,相较于个人在地经验和成长经历所带来的地方性知识,阅读的世界性也在重塑作家的认知。
正如布鲁姆所说:“文学的伟大在于让一种新的焦虑得以显现”,作家的创作不仅直面着当下,也直面着来自远方的叙事经验,必须与传统、与他的先驱和前辈产生竞争势态。毕竟,谈及文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人们总是会想起狄更斯的伦敦、哈代的威塞克斯、梭罗的瓦尔登湖、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文学地方的重要资源。比起马尔克斯等人所处的时代,在全球化的今天,地方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地理距离不再是一种限制,时空压缩让我们觉得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互联网的发展更是时刻更新着人们所接收到的有关世界各地的信息。用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感觉结构”来看,“但新的一代人将会有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我们对于地方的感知,对于世界总体的感受,已经截然不同于以往。
这便是我们当下所面对的现实,也是文学所面对的现实:人们生活在地方,但早已身处在世界性的语境之中,很少有人能置身其外、与世隔绝。对创作而言,作家来自哪里、身处何地固然重要,但潜在的阅读谱系及接收到的世界信息,也构成了感觉结构的重要来源。讨论世界性,不能单纯将本土文学视作被动接受外来文学的产物,也不能完全抛开世界文学的影响。狄更斯、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创造的文学地标并未磨灭,关键在于,如何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感觉结构”中寻找到融汇世界性认知与地方性经验的方式与方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南方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似乎未被“影响的焦虑”所困扰,他们毫不掩盖对外国文学及影视作品的喜爱,坦然地在创作实践中表露自己的阅读偏好。从陈春成笔下那一枚博尔赫斯站在甲板上往海里扔的硬币,到林棹自言是那种“愿意随时随地向纳博科夫致敬的读者”,再到路魆笔下闪烁的阿金图的红发,新南方作家多次在小说中寻求与世界文艺作品对话的可能性。他们不仅大胆尝试现代叙事技巧,同时也将经典意象改写,试图重新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建构着一种新的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
在现代叙事技巧的实验上,新南方作家始终保持着求新、求变的姿态,表面上看,文本中使用了大量的现代与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比如心理分析、时空倒置、内心独白、梦境、意识流、隐喻等。与其说他们特意选择现代派的技巧,不如说来自“新南方”的经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超现实的叙事方式。现代叙事技巧的实验固然属于形式的一种,“而在形式背后永远应该具有新的形式带来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生活世界,就像伍尔夫的意识流揭示了潜意识和深层心理,卡夫卡的寓言形式贡献了对世界的预言,海明威的‘冰山文体’呈示了初始境遇,罗伯-格里耶的‘零度写作’描绘了世界的‘物化’一样。形式必须与它发现的世界结合在一起才不是苍白贫血的,也才不是短命的。”在现代叙事技巧和形式实验的背后,新南方作家也尝试将形式与他们所发现的“南方以南”的世界结合在一起。
比如陈崇正《美人城手记》《香蕉林密室》等小说中,潮汕民间的传说,乡间的巫术,“万物有灵”的信仰,狂乱的风暴,茂密湿漉的香蕉林,与桀骜不羁的冒险精神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故事的神秘与荒诞。路魆《夜叉渡河》《阴蜂》等小说中,昏暝潮湿的乡间有吵闹的人群,也有喃喃自语的迷失者,“某种诞生自古老混沌的恐怖”始终萦绕在小说中。在这些带有魔幻、寓言色彩的小说中,“新南方”不是一个具体的区域,而是一种氛围。读者无须知道小说的背景地,却依旧会在小说的气候中感受到南方以南的魅惑气息。有别于江南式的婉约、哀愁与浪漫,这种新南方的氛围不是一种乡愁式的心灵符号,而是活生生的经验表征。它存在于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乡野见闻,存在于席卷而来的狂风暴雨,存在于未知的附魅。在新南方作家笔下,种种难以名状的浑沌感注定无法让小说停留在叙事的平面,于是选择跳跃的非线性叙事,是新南方作家进入现实、展开想象的重要方式,这构成了先锋而大胆的现代主义叙事姿态,反映出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张力。
在叙事风格上,新南方作家总是显得不那么“安分”,他们有着打破常规、溢出边界的尝试,也有着致敬世界文学经典的勇气。珠玉在前,面对世界级大师们的创作母题,新南方作家们努力书写着自己的“世界性难题”,关注时代人的普遍处境。他们不仅仅是世界文学的阅读者,也努力成为世界文学的书写者。
陈春成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案例。评论多认为他的风格近似博尔赫斯,他也毫不掩饰对博尔赫斯的喜爱。但他小说所传达的主题,实际上与博尔赫斯存在很大差异。每一个读过《夜晚的潜水艇》的人,都会记得《竹峰寺》中那一份“藏”的玄机。从情节来看,《竹峰寺》中“我”将心爱之物藏在隐世石碑下,这一情节与博尔赫斯《沙之书》中藏起一本没有最终页码的《圣经》的情节遥相呼应。但陈春成表达的精神内核却又截然不同于博尔赫斯对宇宙无限的哲思。
在博尔赫斯笔下,“沙之书”是一本翻不到尽头如同恒河中的细沙一样不可计数的无限之书,但“我”在拥有它之后反而倍感恐惧,于是“我”便把这本书藏进国立图书馆的尘封书架上了。博尔赫斯自言小说写的是“那些看似奇妙、后来却变得骇人的东西”,个体始终是有限的、生活在此时此地的,而宇宙时空是不可知、无限的。陈春成深谙博尔赫斯《沙之书》中“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地方是森林”的藏法,但他还是想寻找广袤之下个体得以立足的那个最安实的基点。《竹峰寺》的人物看起来在藏,实际是在找。这不仅是藏与找的心事,更是一份青年人面对未知世界的心事。也只有找到这个点,找到这么一两桩“确定无疑的事情”,“也就足以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了”。这样的书写方式恰恰标识着当下青年人面对世界时最直接、最深切的感触。
而且这种“找”,是有落地、有回声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带有中国古典美学中在无限中回归有限的意味。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人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环往复的”,俯仰之间,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意境并不是无穷无尽的一味放远,而是回环往复的吐纳循环。在陈春成笔下,想象固然辽远、轻盈,但并不是一往不返、不着边际的,而是有那么一个实在的基点。这个点不仅是《竹峰寺》中藏与找的心事,也是《夜晚的潜水艇》中永远悬停在深蓝色梦中的潜水艇,是《裁云记》中充满诱惑的知识洞穴,无穷之下的探险即便找不到终点但也有过程的快乐,所有意象的表征都回到了那么一个最初的起点。
类似的还有林棹、陈崇正、王威廉等人的作品。无论他们的想象如何扩散、变形、跳跃,但都有着相近的、实在的基点,有一份寻找的意义。这份意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富有实感的。“世界的文学,基本是内涵的问题,而不是全部的效果的问题,而是感受的深度的问题。”即便是在科幻作品中,也能看到这份寻找的意义和感受的深度。面对科技迅速发展的态势和全球化的世界大潮,王威廉《野未来》聚焦全人类、普遍性的生存话题,致力于在个体与生命之间建立联系。陈崇正《美人城手记》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人类身处困境时所做抉择的瞬间和不懈寻找突破口的努力,“人类最宝贵的已经不是基因,而是看不见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新南方青年作家表面上建构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世界,但关注的仍是现实世界中被忽视的情感与生命的联系。
王德威曾用“世界中”作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键词,他指出海德格尔将名词“世界”动词化,意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地在那里,而是一种变化的状态、一种存在的方式,以“世界中”来考察中国文学,不仅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新南方作家对世界文学经典的接受与再造,并不是停留在单向度的影响层面,同样拥有“世界中”的开放心态。一方面,新南方作家对世界文学乃至于多种文艺形式的接受,使得他们的创作与世界文学经典形成了互文、对话的效果。用陈春成小说的话来说:“找寻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向博尔赫斯致敬,像一种朝圣”,世界文学经典的滋养和召唤并未消逝,只是变得更加寻常、更加内在。但作家的处理方式,并不完全是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式的,仍带有中国传统的部分。另一方面,在对世界文学的阅读与接受之外,他们并不急于“走向世界”,而是更加关心“世界中”情感的深度与个体的连接。他们对于经典的改造,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边界的探寻,持续更新着文学的感知力,从而形成了融汇传统与现代的新南方美学。
二、“到世界去”的跨域想象
对“新南方写作”来说,世界性不是一种口号、召唤,而是一种现实。除了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阅读、接受和再创造,新南方作家也在跨域、流动书写中寻找历史与自我。
溯源“新南方写作”,必须看到这一现象与世界性有着天然的联系。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曾这样评价以广东为首的西江流域:“其两面环海,海岸线与幅员比较,其长率为各省之冠,其与海外各国交通,为欧罗巴、阿美利加、澳大利亚三洲之孔道,五岭亘其北,以界于中原,故广东包广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梁启超看到以广东为首的西江流域作为交通要道的作用,他在另一篇文章《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进一步指出:“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在梁启超看来,广东在世界史和中外交流文化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莅广东同乡茶话会演说辞》中他还强调了广东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以世界的眼光观之,则吾粤实为传播思想之一枢要也”。
梁启超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强的启示意义,从地理位置到对外文化交流,岭南一直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正如谢有顺指出:“广东不是广东人的广东,而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广东——正是这种文化自信,近代以来处处领先的广东人立志成为汉民族新的代言人。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世界视野的建立显然与此相关。”这意味着“新南方写作”并不是异军突起,它背后有着一份世界视野。广东是移民出洋最早、最多、最广的省份,频繁的对外交往,促成了广东人开阔的全球视野和向海外寻找发展空间的传统。以华侨华人为代表,他们的活动不仅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见证,更是跨语际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本身就具有“到世界去”的意义和跨地域的色彩。
陈继明《平安批》、熊育群《金墟》、陈崇正《归潮》是近年来“新南方写作”中聚焦华侨华人故事的代表性作品。关于华侨华人历史的文学书写,有其特殊性。一是,华侨华人跨域流动的历史从近代一直延续至今,经历了几代人的生活变迁。这不是某一段屈辱或狂热的历史,而是具有延续性,从中既能看到近代岭南、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也能看到当下的变化及百年来不变的传统。二是,华侨华人的跨域流动并不是单向的,在下南洋出海的同时,他们始终与故乡、与眷侣保持着重要联系,国内外信息交流的过程也为本土带来了世界性的因素。当新南方作家触及这幅百年画卷时,他们以个体的生命史为起点,从个体到家族再到国家,一步步钩沉起华侨华人的百年创业史、移民史。正如陈福民评论《金墟》时说道:“中国近代海外移民,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讲述当中,特别是现代史的讲述当中,因为陈嘉庚的影响力,我们主要讲的是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侨乡福建。但现在,我们看到了《金墟》中的开平、台山等五邑地区,以及广东沿海更为广大的侨乡,那些无名的、没有被记录的历史。”
虽然华侨华人历史素材丰富,但文学书写的,是历史微观处的生命细节和感受。在历史意义之外,作家首要处理的一个问题,那便是随着华侨华人的流动,他们如何面对世界,以及做出何种反应。这一问题实际上带有很强的隐喻色彩,因为华侨华人的流动,恰恰隐喻着近现代中国在走向世界时的自我想象和文化自觉。这标识着现代岭南、现代中国如何与世界如何联系,彼此产生了怎样的关联,而不仅仅是“冲击-反应”模式的单向影响。
《平安批》中梦梅出海之后面对世界的剧烈动荡,始终坚持着大义传统和实干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打通陆路,帮助运输物资、传递侨批,搭建起华侨与家眷的联系之桥。陈继明在小说中还饶有意味地安排了一个英国人类学博士乔治,与梦梅结成义弟。在两人的交流中,潮汕地缘文化品格在岭南与世界的交汇中进一步深化。而一切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区隔,在个体走向世界的那一刻,都变成了一种共同的坐标,甚至带有肉身性:“中国的中原,不在中原也不在南方,在哪儿?在途中,在远行的路上,在流浪者的心里。或者说,有两个中原,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原,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中原,后者可以称作流浪的中原。”维系故乡与南洋的是血脉,更是共同的文化传统。
陈崇正《归潮》聚焦陈、林两大家族百年来的奋斗史和几代人的“归潮”历程。出走与返回,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林雨果幼年历经艰辛随亲人从曼谷回到潮州,当年老之际她再度踏上从潮汕前往曼谷的行程,不仅是为解开家族的不解之谜、打捞沉潜的记忆,更是为寻找那份生生不息、血肉相连的印记,可被带着走马观花仿佛游客一般游览完曼谷之后,林雨果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直到陈锦桐收集资料整理成展览,林雨果才心有所安。因为这还原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一份生命的痕迹。“这个世界的许多事物都是这样,连接起来就好了。”小说不仅刻画了动人的家国情怀,更展现出文化精神的生命力。
熊育群《金墟》以江门赤坎古镇的更新改造为中心,与历史上的华侨华人建设家乡的线索交叉展开叙事。小说关注到早期华侨华人的艰辛创业历程。一百多年前司徒家族便有人前往美国,却在天使岛一度遭遇了极其屈辱的不公对待。即便如此,司徒族人仍投身美国华工组织运动,维护华工权利。这部分血泪史,是无尽的悲痛,但也照见了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努力。时隔多年当司徒誉再度来到美国时,他重访天使岛遗址,告慰先辈今日之中国已不同于以往。半部华侨华人史,正是中国近现代化历程的缩影。
区别于海外移民作家的离散书写,新南方作家以“在地”而非“他者”的视角,关注华侨华人带给移民地的变化,也关注变革中文化传统与价值伦理的变化。他们的跨域想象,以当代中国为起点,延伸至近代岭南、近代中国的历史,通过对华侨华人流动经历的书写,作家揭示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也展现了传统中国与现代世界接轨的多面性。当个体命运与家族流变被放置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考察时,“迁徙、流落、求生、逃亡、土地、回归、文化认同,这些命题事实上的确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但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的确更强烈,更极端,更有意味。”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华侨华人故事或是潮汕、赤坎故事,更是岭南故事、中国故事。
除了书写“下南洋”的历史,新南方作家也拥有着全球史的视野,从而在跨域想象中不断建构着融汇传统与现代的美学特质。“尽一个岭南人的全部努力去想象冰川、白夜和极寒”,林棹的《潮汐图》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文本。小说不以人物而是以一只巨蛙作为叙事者,同时在巨蛙的世界旅行中容纳世间万物。小说的题名“潮汐”本身就带有世界性的意味,周而复始、覆盖全球,在地球演化中无数次推动生命流徙,这也为小说中水陆两栖的巨蛙一路游历提供了可能。
正如李德南指出:“跨区域的视野,让小说的叙事空间进一步被打开,使得这部小说的全球史视野得以凸显。即使是写广州、澳门的部分,林棹也试图勾勒当时的世界全景图,呈现世界各地的横向联系,展现不同文化、事物的交流、传播与碰撞。《潮汐图》的叙事跨越了东方与西方、地方与世界、现实与幻象、本国与异国、过去与现在的边界。”在巨蛙的观察中,不同的人眼中的世界是不同的。比如苏格兰人H眼中“世界状似巨卵,广州就是不小心落上去的微尘”,他对巨蛙的话透露出一股自诩为文明的优越感。在澳门画师冯喜眼中起初好景花园就代表着世界,是一艘可以躲避灾难的诺亚方舟式的船,后来发现世界本身才是一艘大船,“世界是大的,因此,听过风的海客不甘受困于囹圄”。于是冯喜也踏入寻找自我之途,不再限于好景花园的囹圄。在巨蛙最后寄居的湾镇的教授眼中,世界不是世界,而是“地球”,带有同呼吸、共命运的色彩。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世界,林棹秉持的,始终是以万物有灵、生命至上的视角。在这样的世界观下,《潮汐图》的地方性书写也蕴含了普遍的、广阔的世界性追求。小说把岭南放置在近代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结点,捕捉到不同文明、文化的复杂互动。岭南的形象是通过人们有血有肉的生活反映出来的。小说中的岭南,是疍家人对海洋的信仰,是众声喧哗的十三行,也是珠江与海洋的风,是巨蛙最后满载快船涌入的黄埔。这样的书写方式,并没有局限于某一处地方,而是跳出岭南、跳出中国来看广州,是真正意义上的站在世界的版图中来勘探“新南方”。正因为如此,小说传递的不是地方中心主义,而是一种普遍的、广阔的世界性追求。
正如法国理论家菲利普·拉特讨论文学的世界性时曾指出:“如果没有文学扩展视野,人类短浅的目光便无法知晓眼前所见以外之物。文学把想象力延伸到我们的感知范围之外,并显示出一个重要思想:在我们个人经验的藩篱之外,还有许多东西。”从新南方出发,到世界中去,作家不仅在小说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跨域流动与冒险,更通过想象连接世界万物,连接历史与当下,让地方知识在异域空间中复现了“南方以南”的传统与生命力。
三、全球南方与主体重塑
“今天的世界文学不是西方、欧美的文学,而是源自那些太长时间被忽略、创造力和创造性都在爆发的地方。”长期以来,岭南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位置。但新南方作家对世界文学经典的接受与再造、对跨域想象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新南方写作”不仅仅给当下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新质,更拥有在世界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中生长的态势。
正如王德威指出:“新南方之‘新’固然来自南方文学地图的重绘,更重要的则是认识论空间的开展:‘新南方’既是‘南方’的不断延伸,也是‘南方’的卷曲、翻转和叠印,因此打破既定的南北二元逻辑。”这意味着新南方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它带来新的认识论空间有着更为广阔的世界。余夏云进一步指出“新南方”也是一种关系学,“它鼓励我们思考和‘旧南方’‘北方’‘全球南方’的关系。在不断的组合对比中,逐渐使自己的形象凸显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讨论“新南方写作”时为思考中国与世界、历史与当下、文化的传承与革新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区别于“前殖民地世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非西方世界”“边缘地区”等术语,发轫于地理位置与发展程度的“全球南方”,如今已不再仅仅是南半球和较低发展程度的含义,它标识着经历了非殖民化冷战和冷战后全球化的洗礼,经济上开始起飞,政治上觉醒并在百年变局中浮现出来的全球性的新兴经济与政治力量。中国始终强调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并积极参与和引领南南合作。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包容的文化和开放的视野,还是跨语际实践中与世界性的天然联系,“新南方写作”所展现出的开放性和先锋性,不仅展现着地方叙事的自觉,也标识着对多元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理解方式。
“与其北望中原,不如走向世界”,朱山坡是一个拥有写作抱负的作家,他以世界为维度,以新南方为锚点,建构着直面世界的叙事。在他此前的创作如《蛋镇电影院》中,世界是一个想象性、带有寓言色彩的符号,如《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中,被人瞧不起的胖子最大的愿望是去美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自制小船要越过边界。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结尾充满开放性,谁也不知道胖子到美国没有。而在小说集《萨赫勒荒原》中,关于世界的符号化的象征开始落地、落实,作家笔下的人物开始真正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深处与边缘处。其中有远赴非洲救死扶伤的援非医生,有走进索马里的偏远部落坚持放映中国电影的母亲,还有为了爱情来到中国学习的国际友人和坚守岗位不谋私的非洲司机。但作家无意渲染他们的不凡,也没有落入宏大叙事的窠臼,而是从小人物和普通人出发,关注人类的喜怒哀乐与生离悲欢,在万物平等中关注生命的韧性。
“用不着担心,到了明年春天,荒原上的一切又会重生”,这是《萨赫勒荒原》中“弃子救众”的萨哈对“我”说的话。刚到非洲参加医疗救援的“我”原本想花时间掉头去救患上疟疾的尼可,却被萨哈制止。萨哈是尼可的父亲,尽管心痛不已,却依旧以荒原的枯草重生为例,坚持不谋私利按时护送“我”到驻地。在生命面前,医者仁心的大爱精神与最为朴素的生命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荒原的亮色。在《索马里骆驼》中也能见到生命的坚韧与隐忍。哪怕流弹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母亲仍穿越孤独的荒野,坚持到各个遥远的部落放映中国电影。此时电影不再是作家叙事的装置,而是联系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媒介。小说也由此借由生命的温情,在国际视野中传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
这样带有普遍关怀的书写,在其他新南方作家笔下也能见到。比如陈崇正的“加纳三部曲”《开门》《开窗》《开播》立足时代经验,串联起人与人的关系,也将个体的创痛敞开,将表面的真相重构,在时代和个体之间展现命运与共的联结。葛亮《书匠》中主人公从伦敦到香港,牵引出古籍背后的留存与等待,照见了中西不同文化精神下的传承。吟光《港漂记忆拼图》关注移民二代的文化失落与认同缺失,探讨都市物质变革下人心何处寄托。
正如曾攀指出,在世界性视野中,“新南方写作并不局限于自身的地域属性,而是以‘南方’为坐标,观看与包孕世界,试图形塑一种新的虹吸效应”,同时它能够“突破传统的地域界限,并在狭小文化囿制中脱化开来,形成敞开式的文化形态”。从新南方到世界,借由跨地域、跨文化和跨国界想象,新南方作家完成了一次次跨越。他们的叙事向全世界敞开,传达出对世界文明互动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共同的关怀,从而建构起从新南方到全球南方再到世界的普适性意义。
无论是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对话,还是在跨域、流动书写中寻找历史与自我,最终还是离不开“新南方”的地方经验。面向世界并不意味着无限无止的扩展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现代叙事技巧与寓言化书写的“壳”之下,仍然离不开南方经验的“核”。作家多样化的尝试不仅捕捉到了中国与世界交流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火花,同时也重塑新南方这一主体,在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角力中源源不断地释放着文学的潜力。
长期以来,我们在讨论文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时,总会提及要超越地方、走向世界。仿佛只有摆脱地方的限制,才能走向世界、走向普遍性。这固然带有期待色彩,但也反映出地方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一种焦虑,一边是追赶着扩大世界影响的迫切,最终变成口号式的虚妄,另一边则是地方范畴的窄化与割裂,仿佛只有边地少数民族的书写才称得上“地方书写”。
在我看来,当下的“新南方写作”所需要的不是“加法”,不是急于超越地方、走向世界。恰恰相反,立足既有的世界性视野,重新回到地方深处,在流动与碰撞中不断挖掘地方经验,才有可能在螺旋式上升中获取更为真切、动人的世界性,才能从“我要”转为“我有”,进而实现“我给”。
所幸也能看到,近年来不少新南方作家开始以一种扎实绵密的笔触和非我不可的勇气,转向书写萦绕在心中的那个地方、那些人,在扎根地方中直面世界,展现出丰富的可能性。比如被誉为“都市独流”的张欣,一改以往书写现代都市言情的方式,转身扎进民国广州历史。她的新作《如风似璧》,将生猛鲜活的岭南重新带进众人视线之中。“不知从何时起,我很想写一部独具广州特色的小说”,这何尝不是一种直面世界的勇气?但张欣并不是要写一部民国广州风物志或者美食图鉴,她关注的,始终是个体与生命,关心的是城市不变的精神基底。她写出了“一丝风都没有”的凉意,更写出了个体对抗世界无常时挣扎着活下去的炽热,“就是有一种广东长夏一般炙热难耐的韧劲”。同样转身的还有黎紫书。时隔十年,她挥手告别《告别的年代》中现代主义式的写作,以一部“吾若不写,无人能写”的《流俗地》,展现马来西亚华人小镇的众生相。黎紫书和张欣都是钟情于日常书写的作家,这种对日常的钟情,同样是一种世界性的抱负和雄心。
写作有时候恰恰需要一种“非我不可”“我来写”的信念。也许是千帆过尽之后非要写点儿什么的冲动,支撑着作家纷纷开始回到地方的内部。青年作家地方书写的表现也不俗。林森《海里岸上》《唯水年轻》等一系列小说仿佛带有海盐的颗粒感。老水手、老船长也许会逝去,但是一代代“以海为田”的人与海洋相生相息。福建作家龚万莹归国之后以一部《岛屿的厝》回望南方小岛上的人生百态:“第一本书,我想要为岛屿、为闽南而写。”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毕业、曾担任欧洲跨国企业品牌经理,作家的这些跨域经历并没有被放大、转换成一个离散、漂泊的故事,相反,正是在域外流动的过程中,故乡成为生命中时刻召唤着的原点。广西作家杨映川《独弦出海》围绕海洋经济、边境贸易、滨海建设等发展现实,铺开南方港口城市一幅热火朝天的图景。区别于乡土经验,这些带有海洋气息的地方书写,都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新的叙事经验。
“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此地有、别处没有’来为‘新南方写作’确立存在感。相反,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不是简单地因差异而求他人的关注,而是因独特且有普遍性而能够自证价值。”“新南方写作”不是一个汇总和累计的概念,它无法也不能将区域的所有文学都叠加在一起,它与全球南方、与世界的复杂关联充满变数,它的内部也有着驳杂的图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种向世界敞开的文学实践,正处于不断地演变和生长中,展现出了独特的地缘特色和时代精神。它不仅关注南方以南的故事,也关注远方;它在讲述地方性的同时,也在探索普遍性,寻求与更广泛世界的对话和连接。
这无疑令人期待着,期待它带来的更加开放、多元、通达的文学未来。
责任编辑:朱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