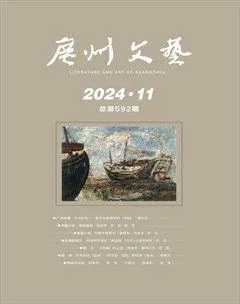乡下的那些事
替母亲回娘家
金钱坡是娘的外家。几十年间只去过三回。头一回是跟娘去,大概是我十一二岁时,或者更小,印象不深。只记得走了很远的路,进村口时,全是竹林,至于见了什么人,全然没印象。
第二次是十年前小表弟结婚,从城里回来吃喜酒,宴席设在峰表弟新屋门口田野边上,天气炎热,偶有田野风吹来,有股熟悉久违的乡土味。
这回是峰表弟约的时间,正好大年初五,原本没有去金钱坡的计划,是我先约峰表弟下午来凤尾坡见面。峰表弟说,来我家吃晚饭好,表哥来,我要亲自下厨。想想也是,借此机会,替娘回去看看她的外家。
娘的外家对于娘,只能称是出生地。几岁时,娘随外公外出教馆,四处漂泊,最后外公在他三十多岁时,病死硇洲岛。娘卖给当地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后被外公徒弟文瑜舅爹从这户人家拯救出来,带回家乡。
这时娘也成年了,她没有回到出生地金钱坡,而是回到她继父家中。外公走后,外婆带着我小姨另嫁人。我后来的外公与我家同住一村,自我懂事时起,我就认定同村的外公与我娘有血缘关系,是亲外公。结果在我八九岁时,家里来了一位老人,我娘对我说,他是金钱坡六伯公。
六伯公嗜酒,每次来,父亲都让我去村中铺子打半斤白酒,鱼肉不少,让六伯公酒足饭饱回金钱坡。我娘从不对我提金钱坡外公的事情,只知道外公功夫了得酒量很大。后来才陆续听娘外家人说到我外公零零散散的一些往事。
外公是习武之人,健硕魁梧,用当地人话说,拳头打爆石。外公徒弟文瑜舅爹对我说过,你外公一拳打死一条黄牛。文瑜舅爹说那次跟我外公到山区教馆,夜归时经过一片蔗园,月影朦胧中一只“老虎”从蔗园里蹿出来,外公一拳把“老虎”击毙在地,定神一看,才知是条奄奄一息的黄牛。
关于外公传奇故事,后来听了不少,足可以写成一部书。但在我娘和我外婆嘴里,从来不提外公半个字。1970年代金钱坡有个舅舅经常来我家,我们叫他“尧舅”。尧舅是我娘堂弟,每次来,尧舅都会挑来一担番薯,总是满头大汗微笑着进我家门。我娘对尧舅特别亲热,总是找来毛巾给尧舅抹汗。我娘在世时,尧舅好些日子不来,便问我娘,怎么总不见尧舅来?娘说,你尧舅走了,然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娘的外家除了族亲,外公家也就断了香火,无子继承。后来听峰表弟说,清明祭扫,外公忌日,都是他们严家族亲去办的,按习俗惯例,一次不缺,我听了很感动,外公在九泉之下当安慰了。
大年初五傍晚时分来到金钱坡,其实现在看来金钱坡离小城只有一二里路,并不觉得远,但小时候,这段路走起来却是遥不可及。十年不来,峰表弟家门外的那片田野,几乎建起房屋,要不是他派人出来接我,几乎找不到家门。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灯笼拉彩旗,年味还非常浓郁。
峰表弟家来了不少亲朋密友,我猜是他把朋友们招唤过来的。他总是以我这个表哥为荣,其实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旁人如此仰慕,一介书生,事业平平,峰表弟如此“兴师动众”,我内心总觉得对不住各位。趁他们聊兴正浓,我悄悄走出峰表弟家门,拐过墙角,朝着院子后面那片荒林地走过去。
寒风夹着细雨,尽管雨点稀疏,落到脸面上也有股走心的凉意。我想,那片荒坡上是否有外公坟地?出门时我也不好问峰表弟,毕竟是过年,问这话总觉得不吉利。我迈着沉重脚步向坡边走过去,又突然驻足,向着荒坡地深深鞠躬。
那个地方就是我外公短暂一生的归宿吗?不敢深想。此刻视线有些模糊,我感觉到娘就站在某个地方,看着我。娘再也无缘回娘家,今天我替母亲回娘家省亲。看看她的出生地,代她看望她的族亲们,然后对苍天作揖,下跪这片土地。因为这里,是我生命基因的源头,是娘童年时离别,再也回不来的故乡。
老 哥
能让我称得上老哥的,没几个,你是其中之一。
那年我半月板肿痛,动弹不得,朋友丅君开车把我接到你家中,他与你有交情。丅君说,这个人性格有点儿特别,但医术绝对一流。
是个天气炎热的夏天上午,你蹲在家中庭院一角与几位村民在商量什么事情,上身圆领短袖白汗衫下身蓝裤衩,头戴草帽,也就是个五十出头的强悍汉子,壮硕得像个乡间武夫。这一身打扮,要不是丅君带着来,我还以为走错门了,哪像个大名鼎鼎的郎中。
我手持拐杖弱不禁风地出现在你眼前,丅君介绍我时,你只侧面看一眼,说,你到二楼等吧,我现在很忙,村里修路的事要商量。我看你也有点儿滑稽,那只巴掌大的手机,卷在裤头里,露出半个外壳。
我自作清高,招呼不打,拄着拐杖与丅君上了你家二楼。有个年纪比你大的瘦黑汉子在忙着配药,自称他是你的助手,我点点头找个位置坐下。二楼是你家主楼的侧楼,一楼厨房餐厅,二楼是你平时接待患者的诊室。摆设老式,木质老椅,木质茶几,木质八仙桌,墙上挂的几条瓷画,画框油漆都掉光了,看上去像清末至少是民国初的老东西。半小时过去,你还迟迟未上来。心想,咱是来求医的,等多久也无妨。
你上来时你助手把药配好了,正在一边捣弄膏药。你摘下草帽坐在我身边木椅上,然后给我把脉。问了一下病情,话锋一转:“你是诗人?”心想,这人有点儿怪,看病就看病,还关心别人的隐私。诗人也好,官员也罢,到你这里求医,什么也不是,就是个病人。也许是丅君之前向你提过我。虽然不高兴,我还是回答你:“算是吧,平时得闲无事就写写。”
你让我伸出舌头给你看看,说,知道了。听起来高深莫测,知道什么呢?你不说,我也不问。你起身从木桌抽屉取出一本小学生作业本,上面写着几行整齐的诗句,权当是律诗吧。你说,这是你写的一首诗,让我指教。我哪敢。但我还是很认真地看了你的诗。写的是你闲时喂鸡鸭、听鸟叫、看星星的小情调,虽然无韵无律,但也挺有情趣。
心想,这家伙肚子里还是有点儿笔墨的,对你的偏见有了些许改变。你不像刚见面时那种旁若无人的傲慢态度,与我探讨起诗中的一些问题。我不能说恭维话,只是说“有意思”。然后提出诗中有一字是你生造的,你问哪只字?我说“厂”字下面一条“虫”这个,我印象中没见过,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只是提问疑问而已。听完我的话你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小子还真有料,这个字就是我生造的,但看过这首诗的人,没有一个看出这个字是生造字,服你了。
你助手正准备给我上膏药,你说“让我来”,然后吩咐助手取来麝香粉,撒了一层在膏药上面。在旁的丅君说,吴医生下猛料了,丅君对着我会意地笑笑。
我知道,麝香是名贵药材,价钱不菲。药钱多少,你不说,我也不问。我拿出一千多元放在茶几上面,你看我一眼,然后从中抽走两张百元,对我说:“第一次来,收你二百,多余的你拿回去。”我也不客气,拿起剩余的钱说声“谢谢”,与你道别。
庭院里一地阳光。我拄着拐杖走出你家大院正门,上车时,你站在院门边说,诗人,有空就来找我。我领悟你话中的分量,对一个萍水相逢的病人,一句平实而真情的话,很让我感动。
觉得你这人特有意思,就写了篇小文在报纸副刊发表。我没告诉你发文章的事,是你的熟人看到这篇小文后,与你说的。记得当天你给我打电话,说我把你写活了,说完哈哈大笑,乐得像个活佛。你说儿子看完文章对你说,老爸人家是在批评你,对你有不满。你说,儿子说的可能是真话,但我喜欢你这小子。他笑,我也陪着笑。
就这样,我们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隔些日子,你总会给我电话:“你啥时来呀?”我说想与你斗嘴时就来找你。你听完哈哈大笑。
你不仅是个给人治病的郎中,还是个审美情趣不低的乡间隐士。你早年从军,当过首长卫兵。有一次首长病了,喝中药,皱眉头,然后说声“白沙”,其他人都没领悟,你从首长身边跑去厨房,抓了一把白糖给首长,首长哈哈笑起来,说,还是你小子机灵。临将退伍,首长想留住你,你却执意要走。退伍后去了一家医院当骨科医生。你家祖传五代骨科名医,你是第五代传人。你还随国内足球队到越南当过队医,后来也不知怎的,你辞去公职,回乡下老家当郎中。
院子占地八九亩,有山林,林荫道,池塘,菜地,还给自己弄了个半个篮球场大的游泳池,一庭花草,几群鸡鸭,鸟叫蝉鸣,白天好是热闹。你给自己院子起名叫“业敬”园,业敬是你大名,匾字出自一位部队老首长手笔。你得意地说,从左边读去是业敬,从右边读回是敬业。说完哈哈大笑,那得意的样子真让人羡慕。人都活出佛的境界,活得自在,看得通透,也就无所顾忌了。真好!
那年外出采风,有一站是登泰山天街,临出发前两天,又患脚疾,痛得不能下床。我打电话给你,说了情况,问两天后能不能出行。你说行。然后说,来我家给你宰鸡炖汤,再弄弄别的,保你没事。我半信半疑,心里还是不踏实。
当天,朋友开车送我到你家中,见我进来,你拍拍我肩膀说:“没事,老哥帮你弄好,后天你放心出发。”厨房里,有人在杀鸡弄菜。你把我带进家中,七上八下地弄了几下,然后贴上膏药,说,喝汤去。
喝完汤,吃过午饭,你说,早点回去休息。我被你的真情和乐观深深感动。也不知你下的啥药,当晚痛感全消了。出发那天我还不放心,带上一支拐杖,结果到了泰山登天街,拐杖毫无用处,走那么远的路,登那么高的山,全靠双腿。
那些年,与你的交往,若即若离。有时想起你,心血来潮,就约朋友开车去你家,半小时车程,然后砰砰砰叩你家院门,大热天时,你穿条大裤衩出来给我们开门,一副无拘无束的大佬模样。有病人时,你就挥挥大手,让我们自个儿到院子四周转转。见到水池里的鹅鸭,就捡起小石头砸进池水里,吓得鸭鹅满池扑腾,溅起一池水花。有时我们还偷吃你家的水果,院子里栽着好几种果树,还有黄花梨和沉香树。
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到深夜,天上满天星斗,四周虫鸣蛙叫,我们还舍不得回家。这么大的院子,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假期节日子孙们才从外地回来。我说,老哥,住这么大的地方你就不怕寂寞吗?你瞧我一眼:“你说呢?”我说你不找个人做伴吗?你哈哈笑过后,说,你小子比我更有想法。与你聊天,真是件特开心的事情。
三年新冠疫情,我们几乎没联系,总觉得,人们都在保命,不想打扰别人,也不太想社交,活在恐惧和孤立之中。前天忽然想起你,疫情都过了,可以走动走动。当我打通你的手机时,好久没人接,后来接电话的是你大儿子。我说老哥你忙啥呀,半天没接电话。电话那头说:“我是他儿子。”我说你爸呢,你儿子停顿一下,声音低沉地说,他走了。
我一时难以接受,抱着手机痛哭起来。你儿子安慰我,叔,不要太伤感,保重身体。我爸走时,叮嘱千万不要打扰别人,有人来电话,就说他到很远的地方去遛了。
老哥,你好坏!就这么甩手走了,这种洒脱,也太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了吧。想给你叩个头,烧炷香,再喊一声老哥的机会也不给,你做人太绝情了。尽管如此,在人世这边,我还是为你祈祷,老哥,天国安好!
詹叔走了
前日回乡下,遇见詹叔儿子,问了声:“你爸还好吧?”
詹叔儿子说,他走了。走前还特意提起,你帮我家那件事情。
我实在想不起,帮过他家什么?但此刻,我心情沉重,用手拍着詹叔儿子肩膀说,保重,你爸是好人。
我转头走开,眼里含着泪水。再不走,情绪难控。詹叔于我、于我家,不仅仅是好人,更胜亲人。我父亲走了那么多年,每逢清明,他都提前来我家,与我兄弟几个上山祭扫我父亲。清明将至,他总会来电话提醒我,找个时间回来扫你父母墓吧。我总觉得,父母走后,詹叔就是我们家长者和看护人,替我父母看着这个家。
詹叔是我父亲三五知己中走得最晚的一个。西街打锡伯,南街黎屋巷生伯,都比我父亲走得早。詹叔走了,父亲的三五知己也就没剩谁了,想想悲从心生。
疫情三年,加上腿痛不便,清明都没上过山,只在老家厅堂对着父母遗像,默念吊拜。记得前年詹叔还来我家,骑一辆老式旧单车,支架在我家门口边。他与我说起父亲生前的事,把我说哭了。说我父亲在珍珠养殖场当场长时,我和我弟经常会去珍珠养殖场找父亲,场里是集体食堂,每次去,父亲都把他的那份饭菜给我和我弟吃了。詹叔说,你兄弟吃了饭菜,你父亲这天就得挨饿了。如果不是詹叔说,我永远也不知道这个秘密。
在村中,詹叔与父亲关系最密切,父亲在世时,我每次回乡下,父亲都会把詹叔叫来,两个老友坐在家门外说说话,抽着水烟。詹叔总会问我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事情。我当时在报社当记者,家里出了一个吃国家粮的儿子,父亲是引以为荣的。他内心的那份喜悦,也只有与詹叔分享。
父亲走后的那些年,詹叔偶尔会给我电话,对我说,你父亲不在了,要多点回来看看你娘,看看这个家。老家的大事小事,他都时刻装在心里。
有一次我回乡下养伤,住了半月,他每个晚上都来,骑着老式旧单车,把单车支架好,就在一棵花树前坐下抽水烟,默默地抽着。这时,我总会想起他的老友我的父亲,他们俩在一起抽水烟时的惬意。詹叔言语不多,偶尔搭讪,家门外没有灯火,他的声音是从灰暗里传来的。如果父亲还在多好,他们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詹叔是好人,这么多年,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到我家坐坐,看一眼这个家,与我乡下家人打个照面,又骑着单车回去。我跟我弟说,家里有好饭菜,留詹叔吃个饭,喝口汤。可我弟说,詹叔从来不肯,蹲在家门外,抽口水烟,说说话,就回家。即使是做清明,爬了大半天山路,给我父亲土坟除草培土,累了大半天,回到家中,本想留他吃饭,他也不肯。
年纪都这么大了,每个清明“扫山”,詹叔都来,他肩上扛着一把锄头,领着我兄弟几个,往山顶爬,他熟悉这段山路,知道埋我父亲的那座山头。有一次下山时,迷路了,我们各自走失了。后来在山道边见到詹叔从丛林里钻出来,戴草帽打锄头的詹叔,浑身上下都湿透。这也是詹叔最后一次祭扫我父亲时,留下一个慈祥苍老的面影。
想报答一下他,总是找不到机会。有一次我带了一把陈年熟普给他,他高兴,说这茶好。然后说,茶虽好,要花钱,以后可别送了。知他性格,再送茶,他是不会收的。疫情期间,回过几次乡下,心里也念着詹叔,但考虑到詹叔年纪大了,也就没请他过来。以为他能活到百岁,活到他厌倦时间,活到他心满意足。谁知一个问候,他不在了,居然不在了。
詹叔在我印象中,年青时是个美男子,浓眉大眼,气宇不凡。村里看过《铁道游击队》的人,都说他像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在村里,也只有詹叔和我父亲,才与“文化”搭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父亲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我父亲看过,詹叔就接过来看。只有詹叔和我父亲,才知道外面的世界。
如今,两位老人都不在了,他们都去了极乐世界。我想,在那个虚空的世界里,詹叔与我父亲,老友重逢,他们照样会抽水烟,照样分享那份白纸黑字的《参考消息》。
詹叔,走好!
与家桥说春天
家桥这身打扮,与春天显然极不协调。
光头是他改变不了的事实。加上他这一身亮紫色上衣黑裤,反衬着他干练精瘦外表,优哉游哉地与我在田地边谈论人生说春天,倒真是有点儿意思,样子委实滑稽。
家桥一路滔滔不绝,像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硬生生地把我搁在一边当他忠实听众。
这个春天我惹了谁呢?原本想自个儿沿着菜田地边散散步,没想家桥这家伙放停手边活赶上来,与我并肩前行。两个人散步倒也是可以,偏偏又遇上一个老抢话题的家伙,我也就只能当他忠实听众了。
这些年我知足了,守着一片田地几口鱼塘,后来又接待过不少四面八方的客人,钱赚得不多,名声也有了,虽辛苦,一家人日子也过得挺自在的。
家桥像在背家书,边走边说,自言自语,也不瞧你一眼。可说的都是他心里话。与他聊天,不是对牛弹琴,是你在听牛弹琴。别看他这副农夫模样,当然不是老实巴交农夫,是那种设圈子套你进去的精明农夫。他常常语出惊人,口吐莲花。
他说前几天来了几位写文章的城里人,聊天时,一位诗人对他说,“你也可以写诗呀。”家桥问我,这话当真吗?我反问家桥,你说呢?
我们都笑了。这个春天有点意思,让我遇上一个有点意思的人。
菜田里种着四季豆、圣女果,还有比家桥高出半个头的玉米地。再远点是鱼塘,几个大人带着小孩在池塘边网鱼。山不远不近,环绕着田园坡地,是个好地方,但平时来的人并不多。只有周末,农庄才热闹起来。
家桥很满足现状。他说人多了,踩踏庄稼的人也多。城里人见了庄稼喜欢,你不能不让人家喜欢。
不符合商人逻辑。但家桥这家伙不是纯粹商人,顶多是个圈了块地半商半农的“小地主”。曾经有人引荐外地商人与家桥合作,扩大经营范围,打造成园林式旅游点。家桥狡猾,说他不差钱。其实他太差钱,只是不想让带资本来投资的人糟蹋这个地方。真是大大狡猾的家伙。
大年初四立春,初五来凤尾坡,也许是巧合,入春第二天,就与家桥这家伙和早春撞个满怀。要是同僚与我说春天,那也是雅兴雅趣雅谈,可与农夫家桥谈论春天,真有点儿说不通的理由。
家桥秃顶,睿智,风趣,骨子里就有那么点儿艺术钙质。据说他街舞跳得好,还特骚。农庄有台卡拉OK,没客人时,他与老婆夫唱妇随,吼几声信天游,唱一曲港味十足的小情歌。风来雨去、日沉月落也不管,唱他个天翻地覆。
在家桥秃尖脑壳里,春天就那么小?小得狭隘自私,容不下旁人。他说,你看,过了那块田,就是别人的地了。也许没错,但在两个人议论春天时,春天是不能论亩计的,也没谁狗胆包天把春天说得那么小气,家桥这家伙敢。
两个人走了一段很长的田埂,往回走时绕过菜田边,路边长满绿油油的盐子菜,原以为是家桥播的野菜种子。家桥说,我才不那么傻呢,是地里自个儿长出来的,我还指望它卖钱,十多块一碟盐子菜卖给客人,还真赚了不少。
真是个黑心的家桥,不劳而获的家伙,尽占土地的便宜。不过复想,家桥这家伙做的挤水盐子菜,味道还是挺好的。
与家桥说春天,都说了啥啦?除了聊了一堆废话,没一字一句是与春天有关的。想了想,与这家伙说春天,等于白说。
爆仗花披盖过半个屋顶,还有多余的挂在屋檐前,家桥坐在半片屋顶下的石磨茶几旁,泡了一壶自制的凤尾坡茶,招呼我过来喝一杯。
半个春日,陪他聊了那么多,不,是听他唠唠叨叨一堆废话后,就只换得一杯凤尾茶。家桥这家伙也太小气了吧。
责任编辑:朱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