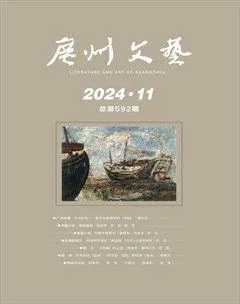一个人的队伍
1
医院的过道里挤满了寻求光明的人。如果不是有白大褂进进出出,大呼小喊,我差点儿要误以为这是某种教派的布道场景,更或者是做传销的盛况再现。人来人往的拥堵,夹杂着焦虑、迷茫与悲伤。我牵着妈妈的手,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
我刚在电梯里看见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偷偷抹眼泪,他的小爱人的安慰像她个子那么矮小,仿佛与他隔着一米的距离。她仰望着他,目光中的惶恐上下移动,楚楚可怜。他说,我的一只眼睛就要报废了,看不见了。她说,做了手术就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他说,别相信什么见鬼的概率,落到谁的头上都是百分之百。万一我瞎了呢,瞎了呢。
她追撵着他,迅速靠上去依偎着他,想用拉近身体的距离来消除正在升腾的恐惧和无助。我也向妈妈靠近了一些,悄悄对她说,别害怕,帮你做手术的医生,是云南最好的眼科医院里最好的医生呢。我知道,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正如妈妈所说,上一次做开颅手术都没害怕,还会怕这个小手术吗?可我分明感觉到她指尖上传来的颤抖和冰凉。
是的,我更能确定害怕的人是我。手术室外七个小时的漫长等待,那种煎熬和惶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每一次听到手术室有响动,都以为是我的妈妈出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慌忙迎上去,可惜我们都不是医生呼叫的家属。秒针,仿佛比分针还慢的秒针,它重踏过我们的身心,虐待般疼痛。爸爸的53岁,走得那么突然,轰隆一声大厦倾倒,压住妈妈和我们。还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又要经历一个个劫难,祸不单行的日子,刀刀见血,痛进骨髓。
失火烧毁的家园,失去的只是财产,而财富就像四平村门前的那条河流,只有煮饭的、烧水的、喂牛的、洗菜的,才真正属于自己,其他的都要流到别的地方。爸爸的豁达与幽默,像他的五官一样,分布在他的孩子们的身上。他说,要听老人家的话,只要有人在,什么都有可能实现。爸爸未曾实现的愿望,自动交接到我的肩上。我曾听见他跟老朋友们这样说:我的大女儿,样样操心,其实她就是我的大儿子了。
事实上,大弟才是爸爸的大儿子,彼时他刚大学毕业,参加考试未果,尚无力多管诸事。从他上高中,我就一直带着他读书,后来又带着妹妹读书。等他们都上了大学,侄儿侄女们,表弟表妹们又来了,我在小城的居所成了驿站,承担着某种从乡村到城市之间的特殊使命。那时年轻,并不觉得负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只为一声声需求与召唤,我就要挺身而出,两肋插刀。
如今,我常常觉得身后有对沉重的翅膀,让我耗尽移山心力也不能抵达。妈妈心疼我,偶尔会历数我的愚蠢,让我少管些闲事。我清楚地记得我的两次跨越式的长大,第一次是13岁,妈妈的双手腕骨折,两亩多的蔬菜不能烂在地里。每一个集市我都在风里雨里和太阳下,努力克服一个少女的羞耻心,为占地点与人争吵,学着讨价、还价、用秤、算账,揣摩买菜人的心理。一个暑期结束,我从13岁长到了18岁。第二次是父亲去世,我初为人母就见死亡扑来不由分说地带走了爸爸,任我哭天抢地,任妈妈肝肠寸断,x/G7E9CSWPhk2EI/mv6pjrzPLHx6AAvBd8javmlIVgs=房舍无色,四壁无声,也未能叫回我亲爱的爸爸。这一年,我变成了奶奶和外婆的样子,想用自己的方式试着疼爱她们的人间。只可惜,她们在短短几年中,相继离世。无法言说的悲伤,让文字找到我,为我剖开一条河道,用于宣泄眼泪。
被死亡一次次侵犯过后的身体,像枯木一样。有风吹即朽的败象,在我和我的亲人们身上铺陈,尤其是我的妈妈。她在短暂的五年中,失去丈夫、母亲和自己的家园,这些浸润着她一生心血的爱与愁,让她陷入痛苦的深渊,万劫难复。她的身体瘦得像一根细竹竿子,深陷的眼窝中已经没有眼泪,就连我也感觉自己已经衰老了。不能承受悲痛的时候,我甚至有了以求速死的念想。这个春天,我在柜子里发现了曾经暗藏的秘密,剧毒药与野生蜂蜜,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证明我从前的绝望。
我不敢与妈妈讨论那些艰难的时光,我害怕我们会被暗藏的黑洞吞噬。我知道,妈妈最大的安慰是她的四个孩子都读书成器了,实现了跳出农门的愿望。再苦再累的日子,她都说值了。万没想到的是,爸爸会走,走得那么突然,一句话也没有,一点儿机会也没有。
那一年,单位组织职工体检身体。当医生告诉我,我的身体有一个肿瘤的时候,我没有一滴眼泪。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她又要失去女儿。第二个想到的才是我的孩子,他会有个后娘,他会受很多委屈,但他总是要长大的。而我的妈妈,她将永远失去我。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后诊断为良性,至今也还在我的身体里与我相依共存,和平相处。也算是死亡给我提了一个醒,让我有一个准备的姿态。其实,我并不害怕死亡,我只是害怕有一天会痛苦地死去,耗尽亲人的情义与钱财,那将是我在人间造下的大恶呀。
历历的劫难,给我的身心造成莫大的伤害:失眠、脱发、心慌、手抖。医生的诊断书上写着:受刺激过度引起的植物神经紊乱。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心脏安抚到正确的位置,面对阳光和花朵,我终于可以微笑了。可是,新的厄运又来了,带妈妈在体检中查出脑膜瘤。我拿着片子奔波于各大医院,想寻求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妈妈却想用“生死由命”来消极抵抗,在儿女们的万般劝说下才同意手术。
当妈妈终于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们像是取得老天的特赦令,有种山呼万岁的洪恩浩荡,从脚底到眼睛,匍匐,涌起,升腾。医嘱的细节,连标点都没放过,只想好好守护着我的妈妈,从ICU到普通病房,擦身、排便、喂药、换洗。我生怕弟弟妹妹们照顾不好,非要不舍昼夜守着。后来他们都有意见了,说我钱要把着出,人要把着看,而妈妈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长大,可以承担责任了。也许他们不会明白,一个太害怕失去的人,在内心有多么恐惧和不安,我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呼吸,她在叫我,她需要我,我才能心安。
病床上,她紧闭着眼睛,术后的高烧让人心焦。我多希望她能对我扬起大巴掌,说要拍死我,或者用娇嗔的语气对我喊“滚”。“滚”是她的口头禅,爱的时候说,怒的时候也说,其中的意思完全隐藏在她的语气中。她和四平村的所有老人一样,无法对人说出我爱你,听到别人这么说都会以为是有病。爱就是滚,滚就是爱。此刻,我多想在她的言语中滚来滚去,成为一个可以撒娇耍赖的孩子。如果她的手中还拿着条子,呵斥我们要不要吃跳脚米线?那就意味着老天已经还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妈妈。可是,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这样的妈妈了。
跳脚米线是四平村的大人们体罚孩子的工具,手拿一根从山上折来的细条子,抽在小腿上,每打一下都痛得直跳老高。在物资贫乏的年代,出于对吃一碗米线的强烈向往,打孩子这件事就被戏谑地称呼为吃跳脚米线,且在滇东北一带流传甚广。能吃到米线的机会很少,但调皮孩子可以每天都吃跳脚米线。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不少,尤其是小弟。妈妈的细条子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一片起起落落地号哭。除了小弟会拔腿往外跑,其余三个都抵着挨打。妈妈曾经痛心疾首地对奶奶说,这三个都是憨货,打了都不会跑。
其实,她也没放过往外跑的小弟,如果不能一把揪回她的小儿子,她就提着条子追着他满村子跑,一边追一边骂:“等老娘拿着你,要让你身上蜕几层皮!”她追不到就气急败坏地回来,在我们身上出气几下,就挑着桶去浇菜了,到了晚上也就忘了要打小儿子的事情。反正有那么多的农活,需要拿出比打骂我们更大的力气。而我们三个,打死都不跑,奶奶示意多次,不跑就是不跑。奶奶只好长叹一声:细条子是长眼睛的,就你们三个没长眼睛!
我占领着病房门口的条椅,以不同的姿势送走一个又一个的白天和黑夜。连日的焦虑和操劳,让我的咳嗽无法忍住了。医生说,一定不能让妈妈受到感染。我静听病房里的动静,戴上口罩等待妈妈的召唤。只等到有一天,她在病房对我发脾气,能大声骂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快好了。一个从小在妈妈的打骂声中长大的孩子,有一天妈妈沉默了,那必定是有大事要发生了。我害怕沉默。这本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最多时有九口人吃饭,爷爷说,不管喝酸汤还是稀饭,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生生的比什么都重要。每一顿饭,只要有一个人还没上桌,爷爷都不许动筷子。过年舀米饭的时候,要从周围开始,舀出一个小山包的样子,才是团团圆圆的年。如今,他们的牌位都请上了楼上的供桌,恭敬地站立在天地国亲师位的两侧。每一个春节,由妈妈带着我们举行跪拜和祈祷的仪式,以翠柏、青松、斋饭、茶酒、香火、纸钱寄托哀思。
当妈妈顺利出院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与死神的对峙终于赢了一次。后来我不断听到因为做脑膜瘤手术出了问题的,有人不会走路了,有人不会说话了,有人死了。若是早知道这些病例,我是万万不敢让妈妈上手术台的。我观察她很久,发现她依旧反应迅速,行动敏捷。唯一不好的就是头部缝针的地方凹凸不平,她说,那个帮她拆线的实习生,心思根本没放在工作上,总是拆一下,就甩一下头发,还要看一下那个帅气的医生。这桃花盛开的样子,不小心被妈妈看见了,也让她吃了大苦头。好多年过去了,她头上的凸凹不平依旧很明显,摸上去还会有轻微的痛感。
这些年,妈妈辗转于儿女们的家,带大了一窝孙辈后,就嚷嚷着要回四平村。她坐在每家客厅里,都像个客人的样子,让我不安。仿佛她不是来享儿孙绕膝的福,倒像是来代替儿女们受罪。她以能减少孩子们的负担为第一要义,并固执地认为只要她还能动,就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我们拗不过她,就只能由着她的性子,无奈地把“孝顺”二字缩减为后面一个字。
回到四平村的妈妈,猪、鸡、鸭、鹅养了一堆堆,土地上的庄稼样样规整,水果蔬菜应季而生。甚至她又重新操起她的旧业,上街卖菜。她说以前是为了挣钱供我们上学,现在就像玩一样,让我们别干涉她。她买了三轮摩托车,仗着从前自行车技术一流的底子,生龙活虎地往返于街市之间。有一回,我打电话过去,她正在卖红薯,为三元钱一斤的红薯价格而开心,还后悔自己种少了。听说我这边在买红薯,她就抱怨这时空带来的距离,不能让我吃上好红薯。那些大棚土地里打的什么药水,膨大的,缩小的,催红的,去虫的,除草的,老板们为了多赚点儿钱什么事都干。还要延伸到人类的生育和繁衍,说人吃了这些,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好歹老娘土地上种些东西出来,你们来了,拉一车回去,吃的吃了,丢的丢了也不可惜,总是好的。
我们的冰箱里常年塞满妈妈的馈赠,从蔬菜到肉类。我一想到我们每一回去,那些鸡鸭鹅也许都会瑟瑟发抖吧,就有种轻微的罪恶感涌上来,随即又放下了。妈妈说,养这些不都是为了吃的吗?收起你那点儿小假惺惺,有本事真别吃。妈妈认真地喂养它们,又熟练地宰杀它们,分装成小袋,冰冻好然后让我们带走。我不忍心让她太操劳,要去街上请人宰杀,妈妈说,与其有这个工夫,还要花那份钱,我早就自己弄好了。她像一个精明的会计师,说替人打工才70块钱一天,她早起宰完4只鸡,那就赚回80了呀。她心疼我们在城市里生活,吃片菜叶也要自己花钱,不像土地上种什么长什么。而我的心疼却不知该搁放何方。我试着对她说,我们小的时候听你的话,现在老了,你要听我们的话就对了。她大声赌气地对我说,听你们的话,除非老娘的脚直了。
我的妈妈,我年近七旬的妈妈,活得像一支队伍,一支雄兵百万的队伍。我们心疼她,她心疼我们。可是常常感觉不在一个频道上,遥控器却在她手上。年轻时,她骑着凤凰牌的自行车,肩上背的,车架上驮的,一次要运300多斤。现在换成三轮摩托车,威风凛凛地上坡下坎,有多少就能运多少。傍晚,车上还要载人回来。稍闲一点儿,她还要去帮附近搞种植的老板做活。这些,她都嘱咐村里的人不能告诉我们。如果说养猪,就说只养一头,种菜只够吃,至于帮人做工是绝对没有的事。
我差不多一年后,才搞清楚妈妈做的这些事情。村里的人,都与她结成了同盟军,口风紧实。那一次节日因为我出差在外,有朋友去家里看她,邻居说漏了嘴。她真把自己当成年轻人了,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不允许她摩托车载人,她说大家都是为了方便,嘴上答应不载了,背着我们依旧干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直到真把摩托车开翻了,伤到一个搭车的人,还好没有大碍。她得到了教训,终于不再一意孤行。帮人做工的事,搞不定她,我只好托人带话给那些老板,谁要是敢叫我的妈妈去干活,她感冒了我都要送到他家里去。这一招可真管用,从此我的妈妈不再为了一天几十块钱而在烈日下劳作了,可她依然不想闲下来。
2
前年春节,我教会妈妈刷抖音,我希望这会成为她的精神鸦片,以减少她的体力劳作。果然有了一些效果,坐着躺着,妈妈也成了像我们一样离不开手机的人。我在心中有些暗喜,她终于可以消停一点儿了。才一年多的时间,她就说她的眼睛看不见药书上的字,也看不清远处的山峦了。
我买给她的书,还一堆堆在桌上。要是从前,她早看完了。她痴迷中医,也许来自外公的传承,我跟着她上山采药,认识很多中药,十大功劳、千针万线草、黄芪、金毛狗脊、九死还魂草、桔梗、草乌、血满草等等。她用这些药泡酒,一个瓶挨着一个瓶,二十几个大瓶小瓶,就像一支长长的队伍,等她发令。她依着药性,按比例配制治疗各种疾病的外用和内服药酒。先把自己当小白鼠,试喝试擦,只要她愿意,总有那么多人找上门来。我每次回去,她都要配一瓶让我带着,消炎杀菌的威力我是见识过的,比市面上那些药膏效果好多了。尤其对疮痈肿毒硬块,简直是奇效。
我常常戏称她为孙医生,家里家外忙得不亦乐乎。一窝窝老年人,在村口的树荫下,在集市的河岸边,捧着自己身体的疼痛,互问冷暖。孙医生只要有时间,就会送上自己的一片赤诚。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又早过了赤脚医生的年代,人心早已不古,这风险就很令人担忧。儿女们看见了,就会阻止她一下,但也仅限于当时嘴上的一句小提醒。背过我们,她依然我行我素,只要有人捧着疼痛酸麻找来,她忍不住还是要帮人揉搓擦拭,热火朝天地把人家的脚、手抱在怀里,永远是那个想一把抓掉人间病疾的老中医模样。
这几年,经过反复提醒后,终于有了一点点效果:她不敢再像从前那样过度大方,用瓶子倒药酒给谁了。人间百态,实在难以预料,万一有人使用不慎重,把外用的内服了,那可是会闹出人命的。我们实在不想把一桩好事往坏处想,可又不能不多想一点点,把人间的轻重多掂量一些,以期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我亦深知,理放在门前,但情却在妈妈的心里揣着,我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她折腾去。
过完春节,妈妈答应跟我们来昆明看眼睛。视力检查结果一出来,我给妹妹打电话,告诉她:妈妈的左眼视力0.15,右眼0.2。妹妹在电话里大笑,嗨,都是玩手机害的,都怪她要躺着玩手机了。我们都一下反转成了家长,像当初她教导我们一样,她也顿时成了孩子,一副要痛改前非的样子。我们都以为只要帮她配一副眼镜,就能让她清晰地看见这个世界。
待所有的检查结束以后,医生的结论是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且达到手术指标了。我和妹妹都为自己在医学领域的无知而出了一把汗,妈妈像没事一样,拖着一双因长期高强度劳作而变形的腿,跟着我在医院上上下下。此前,见过四平村有人患了白内障的,整个黑眼球玻璃体都混浊了。仔细看妈妈的眼睛,只是左眼的黑眼球边上有一点点白,我一阵阵内疚。
年轻时的妈妈有一双清澈的眼睛,明亮,犀利,黑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开心时春风含笑般慈爱,生气时金刚般怒目扫射,只要我们谁做了错事,她的眼睛一瞅过来,我们都没法再撒谎,像是被她眼睛里射出的飞镖钉住了。她把眼睛看向遥远的山外,想尽各种办法让我们走出大山。有一年,家中有了些宽余后,爸爸便想去集市上买几个铺面,妈妈死活不同意,她认为要留着这些钱财供四个孩子上大学。这远比有几间铺面重要多了,等孩子们成才了,就是在四平村住着土房子,也一点不丢人。
这几年,妈妈的眼睛有些暗淡了,她自己的疼痛以及她的孩子们身上的疼痛,都积压在她的身体里,长成各种隐忧。但她看人看物的时候,依旧有种穿透力,像是要直抵某种真相。爸爸去世近20年了,我希望她能给自己找个老伴,可以互相体贴个冷暖。而她却严词拒绝,她认为大多数这年岁的男人都只想找个保姆回去,好歹有人伺候吃喝,却又心中装着各种算计,心不能拧在一起的日子有啥意思呢?她总是能搬出一堆的例子,让人相信她的判断。
洗手台的墙上有一面镜子,我看看妈妈的眼睛,又看看我的眼睛,我们该如何才能把这纷扰的世界看得清晰呢?看着看着,我觉得自己眼睛里的光也正在暗淡。过道里人头攒动,“借过”的声音连绵起伏,太像春运中的火车站。我想用“壮观”来形容,却又觉得把这词用在医院太令人哀伤。在这个永不停歇的生死场中,或许眼科算是最温柔的地方了。
手术台上只要20分钟的白内障手术,术前的准备却要花很多时间,检查的指标很多、很细。高医生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身体有毛病,来做白内障手术时才知道。妈妈的血压和血糖像是练过六脉神剑,一会儿是正常的,一会儿又飙高了。高医生小声对我说,会不会是老太太有些紧张了呢?如果她听见,她肯定要说不紧张的,一点儿也不紧张。
住院楼上,排队的家属座无虚席,与我从前经历过的完全是不同的景象。最明显的感觉是少了死神带来的压迫和窒息,人们松弛地坐在那里,大人小孩都在低头玩手机。待医生叫到名字的时候,有人进入检查室,座位迅速又被占满。高医生给我留言:小手术,放心。她是我生活中的朋友,“医者仁心”这四个字在她身上有淋漓尽致的表达,每每看见她的职业素养和教育孩子的精神,再看她一树花开的美貌,我都觉得这是天使降落在人间。白内障手术已经很成熟,再加上有这样一位朋友,我的心早早就放到了肚子里。
我们在长长的队伍中东张西望,等待一张张检查单上的结果。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躺上去,站起来,流水线一样的作业。如果说隔行如隔山,那医院更是一座好大的山。我翻阅着手里的一摞单子,对着一堆文字、数据、曲线、指标、图片,进入云里雾里,完全判不清医学表述的向度。其中有一张眼球的照片,太像遥远的月球,影射我的渺小。那一时刻,我有一丝丝走神了,在妈妈的眼球上,神游太空。
第15检查室的门牌右上方,蓝底白字:眼科A超、眼科B超,我和妈妈打量着这新鲜的A超,并小声地笑。我忍不住拍照,迅速就有人制止,说医院禁止拍照拍视频。这时,妈妈又回到一个大人模样,让我不要乱拍照。忙了一整天,终于可以把一摞单子都交到护士站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一个等待判决结果的人,得到利好的消息。
在医院里,妈妈太像个听话的小朋友,从没有玩过一次手机,对什么都带着好奇心,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她记住了两位高医生的名字,表扬其中一位口才好,以后定会前程远大,还把术前嘱咐都牢记在心里。我告诉她,护士说的我都记在手机上了,让她安心当一个老人。她还是操不完的心,一会儿问绿色瓶子的眼药水带来了吗?一会儿又说主管的医生太忙了,让我别去麻烦人家。
时逢元宵节,有人说节日快乐,那个护士抬起头来说,像我们这种人就不配有节日。旁边一个护士补充,80多个病人,才有十几个护士,忙得脚底板翻天了,还过什么节。妈妈就无比共情她们的忙碌,感叹每一个人的饭碗都不轻松。又教训了我一通不该熬夜写东西,把自己弄得腰酸背疼,说我干这活儿并不比她在土地上挖地更好。她挖完地出身汗,睡一觉后第二天又生长出新的力气。看着我日益减少的发量,她不无担忧。最后又嘱咐我如果哪里不舒服,就赶紧擦上她配制的神药。我和妹妹,都是这神药的拥护者和受益者。每次回家,她必备一个矿泉水瓶让我们带回。即使没用上,也得告诉她,这是好药,哪一次又受益了。她顿时就高兴得像个孩子,恨不能手舞之,足蹈之。
3
手术的那一天,我们7点多就到医院,履行各种术前程序。拥挤的护士站,站满了不同口音的人。来了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我和妈妈迅速起来让座。又来了一个受过外伤的人,眼球突出红肿,五官都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他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看不出他的眼睛有没有视力。我和妈妈侧着身子站在旁边,心也跟着一起痛。这人间劫难,谁要遇到什么都是未知。
妈妈小声说,能无病无灾,活到老的人少之又少。如果有,那就是人家前世修造太好。如果真有来生,但愿我的妈妈投胎到一个富贵温柔的地方,不要再受人间疾苦。而我,就不要让我再当人了,让我去深山老林里做一株植物吧,不要有人看见我,我只想拥有自己的四季。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孝,我还是应该跟着妈妈继续当她的女儿,或者让我们换个位置也行,让我可以好好爱她。
妈妈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发量越来越少,只有微弱的黑发在倔强地证明她曾经年轻过。要知道,妈妈年轻时有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为了粮食,她狠心卖过头发。那些年,乡间流行收头发的人,他们走村串户,专门在大姑娘小媳妇们的头发上打主意。妈妈的头发卖了个好价钱,换得口粮,抵交公粮。我见过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两根大辫子下的明眸皓齿,青春蓬勃,美貌无敌。那是妈妈的芳华,她曾经有过的梦想,都屈服于现实了。四姨曾说过,那个买头发的人,拿着辫子到了他们村里,外婆一家人一眼就认出这是妈妈的辫子,全家人的悲伤都败给了生活。这样的事情,四平村的女人大多干过。她们并不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的话,在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一天接着一天的日子,一天就要有一天的活路。
当这些回忆在我脑中跳跃时,我终于有些理解妈妈当年的执拗。在做头部手术的时候,医生要剃光了她的头发,她坚决拒绝,以不做手术来威胁我们。性格温和的医生,让我们先做好她的工作。我就不明白,头发难道比生命更重要吗?明年就长出来了呀。嘴皮子磨破,她依旧不肯顺从。如今想来,或许她有自己的心结。她是多么爱美的妈妈呀,剪去头发一定像被人夺爱般难受。
妈妈还是个少女时,为能多读几天书本,拼尽全力。她终还是那一盆要泼出去的水,多浪费一点儿碎银都会是娘家莫大的损失。外婆烧了她的书本,千方百计阻止她上学,她就假期去帮人打零工,用锤敲打出狗头石,量方算钱,一天能挣一块钱。勉强把读完初中,再不能继续读书。那时外婆生下了最后一个孩子,因为嫌弃女儿太多,想丢弃。妈妈捡起那个小婴儿,并承诺养大她,才让她免于被弃的命运,连出嫁时也一并带上。此后,外婆决绝地以剪断自己欲望的方式,拒绝与外公同房,在生育工具和劳动工具之间,她毅然选择后者,辛苦养大一堆儿女。
妈妈在乡间与县城之间往返,贩卖鸡蛋、饼干,没有车坐的时候,就用脚丈量40公里的山路。当时最流行穿驼绒大衣,她竟然从一分两分三分钱的微末利润中,积攒下钱来购置了一件大衣,26块钱,穿了姐妹五个人。最远的地方,她到过昆明,坐着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好几个小时。妈妈还记得快车5.3元,慢车4.4元,能买一根5分钱的冰棒吃下去,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如果想去公园,就得省下吃冰棒的五分钱去买门票。
有一次,她们几个人一块儿来昆明做小本生意,其中一个人所卖的茶叶被没收了。乱哄哄的场面,妈妈趁人不注意,悄悄把茶叶拖走,在火车上与人碰面,都觉得捡了个大便宜。这个人的家在县城,到站了非要叫她们一伙人去家里吃饭。走到家里才发现,尴尬大了。那个人的老婆偷过妈妈的鸡蛋,且被她现场抓到过。那顿饭吃得五味杂陈,几十年过去了,妈妈还记挂在心上。
其实,妈妈讲的这些故事都已经重复过很多遍了。看见听见某样互相关联的事物时,她又会兴致勃勃地讲一遍。少年时嫌她唠叨,现在愿意当最合格的听众。我不知道妈妈年轻时的梦想是什么,那个年代的吃饱和穿暖大于一切,而我的妈妈还曾经想穿好过。我从懂事开始就知道她的梦想是让她的孩子们走出大山,她没日没夜地操劳,养猪,养鸡,种烤烟,种蔬菜,冬天有点儿空闲就帮人做裁缝,我们过年的新衣总是最后一茬才穿上。在我很小的时候,她想给我做一条裙子,那可是乡村的稀罕物。最后她竟然把这件事情忙得忘了,而我的奶奶却记了一辈子。
我们姐弟四人相继出生后,妈妈外出做小本生意的时间就没有了。她把目光投到了自留地上,请求当生产队长的爷爷划一片土地给她试种蔬菜,这一个试验超出了种玉米的很多产值,后来她得到了更多的土地来种蔬菜,并带动村里的妇女们都种起了蔬菜。在这个吃水最艰难的四平村,却种出了集镇里最新鲜最早上市的蔬菜,也算是个奇迹。冬春季节,河流断床的时候,妈妈要点着火把,到一个山洞里挑水,从地面到水面下184级台阶。我从6岁开始就跟着她到洞里背水,到后来也可以挑水了,并且能让扁担在两只肩膀上自由相换。这些劳作,让她的孩子们个个腰圆肩宽腿粗,身材高大强壮。
我上中学时很是不理解,为什么到了烤烟的季节,我每个周末都必须干那么多劳动?后来才明白,她一个人干不完呀。爸爸要忙村上乡上的事情,她一个人承担的劳动太多。回到家里,再有一窝孩子烦乱,令她脾气暴躁,动辄打骂。但是对学校里的事情,她从来都没有松懈过,最关心我们考得几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不知道考几分她才不骂我。如果我考了满分,她就怀疑我是照抄别人的,即使班上只有我一个满分。如果我考了低分,那更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有时还会连累我的奶奶跟着挨骂,怪她惯着我。
护士在病区叫一个姓周的病人,连叫多遍都没有人应答。妈妈拐了拐我的胳膊,问我还记得小学的周校长吗?我知道她又要讲那个故事。那年我刚满6岁,妈妈带着我去报名上小学。周校长知道我是我爸爸的女儿,就不让我报名,非得让我爸爸带我来才行。妈妈据理力争,把一个校长弄得灰头土脸。原来是因为周校长想在我爸爸那里插个队,为学校屋顶换瓦片的事情。
四平村有两个窑子,专烧瓦片,生意红火,爸爸是生产队长,管土地和瓦厂的一切事务。每当瓦片出窑的时候,河边挤满了人,马车牛车一排排。周校长来的时候,我爸爸答应下一个窑子的第一个就排给他,因为其他的人家都等着盖房子讨媳妇用,看好了日子要扇瓦片的,不能插队。下一个窑子,也不会影响到学校的开学。两个男人差点儿打起来了。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好玩极了,我居然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这一次跟妈妈开玩笑说,原来我们家也是有矿的呀。
妈妈捋了捋我脖子上的头发,再一次确认我的脖子果真要长一些。在一次偶然的检查中得知,我的颈椎比别人多出一个椎体。医生说是在母体里发育畸形导致的,我是多么幸运呀,多长在哪里都不妥当呀,竟然恰好长在脖子上。想想我也是一个不省心的主儿,从在妈妈的肚子里就不安分,在她明知我是站着在她肚子里的,却冒着难产的危险在家里生下我。据说,奶奶看见我一只脚先露出来的时候,大惊失色。而后,我一只手抱着头,另一只手抱着肚子,就顺利降生了。我埋怨妈妈胆子大,她却说她一辈子都没做过坏事,老天不会乱来的。可是,爸爸那么宽厚仁爱的一个人,不也那么早就走了吗?妈妈沉默,我也不敢再多讲一个字。
终于叫到妈妈的名字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在病区的板凳上坐了三个多小时。帮她穿上睡衣和手术衣,还拍了照片发在家庭群里,随时汇报情况,好让亲人们安心。上午11:33进手术室,下午1:53出来,一切顺利,遵医嘱正常吃喝。晚餐时,大过节的我想让妈妈也喝一点儿酒,妹妹坚决阻止,她说喝酒已是非正常了。可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她平时也喝。甚至可以说妈妈是一个爱酒的人,从我记事开始,她就海量,有客人来了,她大碗地与人喝酒,我却没有一次关于她酒醉的记忆。有一次模糊的记忆,还是我的孩子四五岁时,妈妈带他回四平村,我打电话回去,孩子告诉我外婆喝酒醉了。我更愿意理解为是多了一口,并非真醉了。
一个严厉的妈妈偶尔来一次温柔的时候,给人的冲击力度会很大。有一次我因为喝酒的事情,被某人告状到她那里。我大概是遗传了妈妈的基因,年轻时亦有酒量,有友戏称千杯不醉。可是有一次我竟然喝醉了,某人心中不悦,他以为岳母大人会帮他教育我。妈妈却风轻云淡地对他说,我也会喝醉呀。妈妈的化骨绵掌,替我挡了一枪。自此,某人不再叨叨我喝酒的事情。
妈妈蒙着一只眼睛,坐在沙发上,接听来自亲人们的关心和问候,对她的孩子们争抢着要多出钱出力而倍感欣慰。妹妹刚满五岁的小儿突发奇想,问我一句,外婆是领导吗?一屋的笑声响起,我说,是的,外婆是领导,她领导着我们一个大家庭的队伍。这么说的时候,我的眼前顿时就飘过一个画面,那是去年夏天我回村里,看见她端着一盆粮食喂鸡鸭鹅时,那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向她涌来。家国天下和人间春秋,仿佛就有了一个支撑点:妈在,家在,世界就在。
4
医生说,第二天一早就可以来医院拆掉蒙着眼睛的纱布,想着妈妈就要重见光明,有些小激动,早早就醒来。春城的天气还有一点儿小冷,但春和景明的样子已灼然盛开,院子里有一树桃花,嫣然巧笑。带着妈妈吃了早餐,就奔医院而去。前面有一辆白色的车行驶缓慢,滴滴司机说,嗨,它是在散步呀,逛个大马路的。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以为他或许是个文艺青年。一路上态度友善,极力推荐他跑的平台公司如何好。我们下车时又笑眯眯地问我可否在平台上给他一朵小红花,我说,当然,等我得空就弄。我想,一个努力的人,配得上被真诚对待。
妈妈眼睛上的纱布才拆完,就忙着追问那朵小红花送出了没。打开记录,看见这是一位姓谢的师傅,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我和妈妈为送给陌生人的一朵小红花而由衷地快乐。一个姓氏中的谢字,是巧合,也是心意。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在细微处见诸真心,生发真情,触摸快乐的根;见光明,见人间一切值得的人与事。
医生说再过15天,就可以来做另外一只眼睛的手术了。想借机留她常住昆明,两个女儿都在,跟谁都挺好,也互相有个照应。她却早早就打起了退堂鼓,扔过来一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并且连接举了很多跟着孩子们在城里的老人,身体没有在老家健康的例子。她说,只要她还能动的一天,都别阻止她劳动,当是在锻炼身体。
一想到她坐在谁家的沙发上,都像个客人的样子,我和妹妹又心疼起来。终究是属于田野山间的妈妈,再挽留她,就是摧残她。我想到了自由,以任何名义束缚一个人的自由,都会是一种极大的罪恶,我们不能以爱的名义绑架她。是的,她要上山去采药、捡菌子,她要去地里亲近瓜果蔬菜们,她要养一帮鸡鸭鹅猪当成宠物来爱,她要建设一支支长长的队伍,用来革命生活的一切际遇。我常常在想,要是爸爸还在世,两个老人有个伴,做什么都很好。只可惜人间没有什么仙丹妙药,可以起死回生。妈妈手术这些天,接连梦见爸爸,感觉他就在我们身边,妈妈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我常想,爸爸或许生活在另一个维度,他是能看见我们的。
年龄越大,越明白“孝顺”两个字的含义。妈妈常与人说,她的孩子们孝心可鉴,这在方圆团转几十里路上都已出了名的,她在别人表扬的话里心满意足。一个“顺”字,却还需要我们再修习。这些年我已经把我叛逆的骨头削平了,期待有一天再滑一些,我的生活也许就不会那么颠簸了。
一窝蜂似的术后病人挤在一起,年轻的护士扯着嗓子发药,交代医嘱,没有耳麦,她的音域被嘈杂限制在低分贝中。年长一些的护士替换了她,她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迅速安静下来。眼药水、眼药膏,点滴的方法、时间和剂量,都被病人及家属慎重地装进衣袋。再嘱咐一句,如果哪里有不清楚,请随时来电。她又抛来一个故事:上一次有人打来电话,本来每天点三次的眼药水,不小心点了四次,病人会死吗?满堂一片哄笑。在未知的医学领域,在场的人或许都能确定自己不会成为那样愚蠢的人,可谁又能保证另一种愚蠢的出现呢?
看着蹒跚行走的妈妈,她也曾经有过大长腿的芳华,如今剩下一个摇摇晃晃的躯体,却还在操心她的儿女们如何能站得更稳当一些。我曾试图劝她更换膝关节,以减少行走的痛苦。她却断然拒绝,说这些长在身体上的东西,哪样不是原装的好,若有个闪失,疼的还是她自己,而且要连累大家不得安宁,都离黄土那么近了,就别折腾了。
“顺从”一词,在我的妈妈这里,大约只是空气。我如果再多说一句,我们小时候听你的话,现在你要听我们的话。她又要恶狠狠地丢来一句,除非等老娘脚直的那一天,你们爱咋咋的。当儿女们的苦口和婆心,也被妈妈嫌弃唠叨后,剩下的更多沉默,就让她种植在属于她的土地里。好吧,我们都是万物,幻化成诸相,各有各相,各有各的队伍,各有各的归宿。
责任编辑:姚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