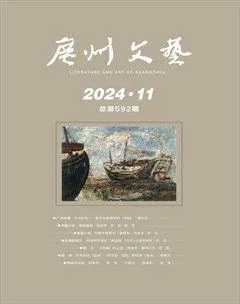蜡梅之约
颍州。苏东坡注意到,在一种清寂的语境里,梅树铁枝横斜的蓬勃造像。
这两者从未发生龃龉与抵牾,彼此就是为对方而彻底摒弃了昔日的友朋。寂寞如梅,寂寞如黄酒。浓到深处,因为寂寞而自生陶然,因为寂寞而自给自足,因为寂寞而豁然跃升喧嚷的生命。什么是孤独性?孤独性是人的本性,有些人的孤独与生俱来,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它,孤独扎根于其深处,构成并焊合了他的另外情感。在这样的阅读印象里,我推测,东坡的寂寞,必然是一头横卧在梅树上的、斜睨的豹子。
比利时作家马塞尔·德田纳在《处死的狄奥尼索斯》中声称,古罗马时代,人们认为豹子是唯一能散发香气的动物。在我看来,这是暗示了酒神与豹子合二为一的肉身化理由。蜡梅花是豹子的文身,豹子是一树狂奔的蜡梅花。但在我的感觉里,这分明是远东的香味,是真梅花的香味。梅与豹,是木性之精与行动的合二为一。扬雄《法言》说:“圣人虎别,其文炳也。君子豹别,其文蔚也。辩人狸别,其文萃也。狸变则豹,豹变则虎。”圣人老虎是王道之物,孤独的豹子停歇在梅树上,却终止了自己的进化。
红梅暴吐红艳的气象,更符合东坡的性情。
那么,蜡梅呢?
蜡梅和梅花并非一家,或者说蜡梅根本就不姓梅!从植物分类学上讲,蜡梅是蜡梅科蜡梅属,而梅花则是蔷薇科杏属,距离很远。
蜡梅又名金梅、腊梅,在宋代以前更流行的名字叫黄梅。也许,在于古人见“色”起意,在于蜡梅与梅花的花期相近,便以为它是梅花的一种,遂把它称为黄梅。黄梅原生于中国秦岭、大巴山、神农架等区域,至今在四川达州市还有古蜡梅种属,花瓣奇大,一般黄蜡梅的花瓣呈条状,看上去很是细碎,而大巴山蜡梅的花瓣呈片状,丰富多彩、婀娜多姿。据《中国蜡梅》一书所载,蜡梅有4大品种群、12个品种型、165个品种,其色有纯黄色、金黄色、淡黄色、墨黄色、紫黄色、银白色、光白色、雪白色、黄白色等,花蕊有红、紫、洁白等色彩,其中“素心蜡梅”“金钟梅”“檀秀梅”等为蜡梅中的极品。
毕竟蜡梅出道稍晚,不得不屈居于红梅、白梅的石榴裙下,一度寂寂无闻。宋代之前的文人雅士们见识蜡梅的机会太少了,所以宋代以前不入法眼,几乎没有吟咏的记录。黄梅能够出人头地,名声大振,其实还得感谢东坡与黄庭坚,正是他们命名了蜡梅,第一个写下了赞美蜡梅的诗作。
宋代诗人大都酷爱梅花。林逋是最为著名的一个,俗物不可入眼近身,不可方物,遂有“梅妻鹤子”之称。“拗相公”王安石也爱梅,慕梅之品格,以梅花孑然高洁、孤傲凌寒为高标:“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东坡毕生酷爱植物,单是咏梅诗就写了几十首。元祐六年(1091年)和杨公济梅花诗,意犹未尽,以至于“再和”,一口气写了20首七绝。不过,以前他并没有赏过黄梅,因此并无吟咏黄梅之作。究竟东坡先生是如何发现并把黄梅命名为蜡梅,并且首先题诗让蜡梅名满天下的,这就在于他的童心未泯与自幼形成的博物眼光。
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二十五日,55岁的东坡再次出京,来到颍州担任知州,其子苏迨、苏过同行。颍州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市颍州区,虽然颍州刚刚经历了旱情,好在并不严重,并未让这里的青山绿水蒙尘。这里也有一片西湖,与杭州西湖的美景相仿。
人生如水光一般起伏,均是梦幻,豁达的东坡渐渐视沉浮如浮云了。
这年的冬天,黄庭坚来颍州看望东坡。东坡很是欣慰,与黄山谷结伴而游,来到颍州郊外的山岭。岭上有一座书院,乃是民间传说中梁山伯和祝英台求学的地方。他们当晚就夜宿于寺院。到了半夜,一阵花香袭来,竟然让东坡先生梦中生景。他寻觅芳香来影去踪,不知不觉来到一片梅林中。原来这花香便是来自梅花,芳踪逶迤,袅袅而至。
清晨醒来,东坡先生才知是南柯一梦,梦中的他把颍州的山林与杭州万松林重合一体了……奇妙的是,梦中的花香盘桓不去,并没有按逻辑回到梦田。这就让我想起同样喜欢记录梦境的本雅明所说的一段话:“一个至今流传的民间传说告诫我们说:第二天一早醒来,不要空着肚子讲述昨夜的梦境。那时,醒来的人还处于灵魂出窍的状态,实际上,依然处于梦境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沐浴只是唤醒了肉体的表面和它外在的运动能力。而在更深层面,即便是在晨起的沐浴中,夜晚晦暗的梦境并没有褪去。实际上,它紧紧地依附在人们刚刚睡醒的那种孤寂之中。”(《单向街·早餐室》,陶林译,西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被梦中花香搅扰,东坡大感奇妙,遂将梦境告诉了黄山谷。山谷一听大喜,说不如让长老带我们前去寻寻芳踪如何?
东坡道:“这个主意甚好!”
恰在这时,住持前来问安,东坡又把自己的梦告诉了住持。住持捻须笑道:“善哉善哉!先生果然聪敏,寺院后山正有一片黄梅,刚刚开放,没承想这幽香竟然入了先生清梦!”
早膳之后,东坡与山谷在住持带领下来到后山,只见丛丛一人多高的黄梅铁干枝斜,枝头花朵有的怒放,有的半开,甜蜜而浓烈,香气荡漾山间,这份寂寞唯有东坡识之!
东坡大喜:“没想到这黄梅竟然如此美妙,花香蜜甜,清幽扑鼻。不过前人见‘色’起意,叫它黄梅实在俗气了些,我看它色如蜜蜡,花若蜡捻,仿佛出自美人之手,不如叫它蜡梅如何?”山谷拊掌叫好:“妙,就叫蜡梅!”
东坡又道:“为了让这个名字流传下去,我得吟诗一首以记之!”住持大喜,回到禅房,立命小僧磨墨铺纸。东坡挥毫写下《蜡梅一首赠赵景贶》:
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
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
天工变化谁得知,我亦儿嬉作小诗。
君不见万松岭上黄千叶,玉蕊檀心两奇绝。
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
归来却梦寻花去,梦里花仙觅奇句。
此间风物属诗人,我老不饮当付君。
君行适吴我适越,笑指西湖作衣钵。
东坡在诗中不仅描述了梦中追寻蜡梅的奇特经历,还鉴赏出了当时蜡梅中的极品玉蕊和檀心。这两品可能就是当今的素心蜡梅和檀香蜡梅。
如果以上所说属实的话,那么东坡于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1074)、元祐四年至六年(1089—1091)先后担任杭州通判和知州,那么江南一地最早的蜡梅记载就得上推至熙宁中叶了。这与北宋后期徐俯所说“江南旧时无蜡梅,只是梅花腊月开”,以及南北宋之交周紫芝诗云“东南之有蜡梅盖自近时始,余为儿童时犹未之见”的宋人观点,产生了龃龉。在我看来,蜡梅的北宋处境,与中唐时期蜀地海棠的处境颇为相似。唐宋之际一直是植物的“爆发期”,出现一些文人未及注意植物变化的情况,并不为怪,也不足以以此来
否认蜡梅在北宋时期的“不胫而走”。
这诗所赠之人赵景贶,乃是宋太祖第八子赵元俨的后代,当时在颍州任东坡的幕僚。他比东坡先生小十几岁,对东坡尊重仰慕得很,二人常有诗歌互赠并唱和。
他们走到了一个拐角,再次与蜡梅花的冷香迎面相撞。那里有一大丛花树,一直在冷风里簌簌落叶。风不像是来自外部,倒像是从叶片下斜飞而出,是树叶飘动而扇起了那股冷意。黄叶的美不亚于一旁同样派发落叶的银杏。两种黄叶不同,蜡梅花叶片上有一层茸毛,顺之则滑,逆之则毛起。
枝条上还有没有落尽的梅花果。蜡梅树是在春天结果,果子在成熟前是绿色,要到成熟后才变成灰褐色,呈橄榄状,有四五厘米长。冬季的果子已经变成灰黑,像是梅花的眼睛。果子早已干缩,里有很多枚种子,没有果肉。一般而言,没有经过修枝的蜡梅树结出果子属于常见现象。蜡梅果、树干、树叶均含有一种叫夹竹桃苷的有毒物质,而蜡梅果种子称“土巴豆”,有微毒,败火,可做泻药。
在黄叶与蜡梅果、深色的枝条之间,可见黄豆大小的花蕾。花未彻底绽放,但刹不住车的香气,却是急不可待地逸出了。
蜡梅花根据品种不同开的花瓣数有12瓣、14瓣,还有18瓣的。蜡梅实生树开花一般在10瓣左右。落叶的速度与花香打开的程度成正比。当落叶殆尽,蜡梅花的金发在空气里颤抖,就像尤奈斯库笔下的“秃头歌女”。现在,蜡梅花未能彻底登枝,但香气已经将空气撩拨开,周围白蜡蜡的雾开始退却出一袭裙摆抡圆的位置。那是梅树豹变的姿势。
真好!
晚上,明月朗照下的万松岭,月光与水流互为辽远。那一山的蜡梅花,让人感觉到是月光催开了花朵,月光从梅花的内部一点儿一点儿外翻出来。月光混有梅香,月光为香气赋形,梅花为月光聚象,交相辉映,无声无息,一派凛然。
但仔细一看,会发现在这静谧的月夜,蜡梅花发出了碎金的色泽,金花雀跃而起。月光在黄金之上不受力,四下打滑,为此月光显得更为纯粹。
有时,东坡能够听到蓓蕾打开为花的声音,就像在家乡的大平原上与阳光相遇。有时,他能够从流水声里分辨出亲人裙裾曳地的窸窣声,也能够听见她们从花墙上流淌出来的笑声……回到自己的寂寞深处,他还能听到她们的沉默。
那里有月光对梅花的承诺吗?
既然东坡开了头,山谷不能不跟上。他在《从张仲谋乞蜡梅》诗中吟道:
闻君寺后野梅发,香蜜染成宫样黄。
不拟折来遮老眼,欲知春色到池塘。
黄山谷还写了《残咏蜡梅》二首,其一曰:
金蓓锁春寒,恼人香未展。
虽无桃李颜,风味极不浅。
黄庭坚进一步认为蜡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功捻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指出蜡梅花瓣的蜡质特性并为蜡梅定名。《梅谱》里也认为蜡梅颜色酷似蜜蜂营造的酿蜜蜂房,故名蜡梅。
当然,有学者指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才是最早记录蜡梅的文献记载。宋哲宗元祐年间,黄庭坚等苏门文人在京城欣赏蜡梅、诗词唱和,极大提高了蜡梅的知名度。洛阳是当时蜡梅传播种植的关键地点。可以说,中国蜡梅始见于北宋中叶的西京洛阳、东京开封一带。
东坡咏蜡梅诗广为流传,不少诗人起而和之。其中一位名气甚大,名叫陈师道。他读了东坡蜡梅诗后颇为激动,和了一首《次韵苏公蜡梅》:
化人巧作襄样花,何年落子空王家。
羽衣霓袖涴香蜡,从此人间识尤物。
青琐诸郎却未知,天公下取仙翁诗。
乌丸鸡距写玉叶,却怪寒花未清绝。
北风驱雪度关山,把烛看花夜不眠。
明朝诗成公亦去,长使梅仙诵佳句。
湖山信美更须人,已觉西湖属此君。
坐想明年吴与越,行酒赋诗听击钵。
陈师道字履常,号后山居士,比东坡小16岁,乃“苏门”君子之一,江西诗派重要代表。东坡对他颇为欣赏,于元祐初年向朝廷推荐其诗文才干,起用为徐州教授,后历任太学博士、颍州教授、秘书省正字。陈师道在诗中描述了东坡先生创作蜡梅诗的神奇经过,把先生赞为“仙翁”。
到了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读了东坡和陈师道的蜡梅诗,既为他们的诗所倾倒,也为蜡梅的风姿而倾慕。他竟然写了多首蜡梅诗,尤其是《次东坡先生蜡梅韵》,再次大力标举蜡梅的声与名:
梅花已自不是花,永魂谪堕玉皇家。
小不餐火更餐蜡,化作黄姑瞒造物。
后山未觉坡先知,东坡勾引后山诗。
金花劝饮金荷叶,两公醉吟许孤绝。
人间姚魏漫如山,令人眼睛只欲眠。
此花寒香来又去,恼损诗人难觅句。
月兼花影恰三人,欠个文同作墨君。
吾诗无复古清越,万水千山一瓶钵。
与杨万里差不多同时的南宋高宗时状元王十朋,自号“梅溪”,今浙江乐清人。他既是东坡坚定的赞美者,也是一个十足的梅痴。他在苏、黄的余韵波及下,对蜡梅更是情有独钟,他不仅为蜡梅一咏再咏,并专门填词一首《点绛唇·奇香蜡梅》,把苏黄命名蜡梅,将蜡梅风姿、标格在天下广为传扬的行为大加颂扬,美赞之语跃然纸上:
蜡换梅姿,天然香韵初非俗。蝶驰蜂逐。蜜在花梢熟。 岩壑深藏,几载甘幽独。因坡谷。一标题目,高价掀兰菊。
正是以苏东坡、黄庭坚为首的一大批文人士大夫对蜡梅的吟咏,蜡梅在北宋晚期以后名满天下,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捧,与产自蜀地的丰瑞花一样被列为名贵花木。甚至像王十朋说的那样,蜡梅的声誉甚至盖过了兰和菊。
明代王世懋在《学圃余疏》一书中说:“考蜡梅原为黄梅。故王安国熙宁间尚咏黄梅。至元祐间,苏黄命为蜡梅。”这一说法直接肯定了东坡和黄山谷命名蜡梅的事实。
不过,东坡先生和山谷先生等并不是植物专家,他们虽然炒红了蜡梅,可是也没有搞清楚蜡梅是不是姓梅。估计他们也认为蜡梅只是梅中珍贵一品。
最先弄清楚蜡梅身世的是南宋名臣、著名诗人范成大,他是无愧于博物学家这一称号的。淳熙元年(1174年)十月,他任四川置制使兼成都知府,他十分留意成都的风物,写了不少与成都相关的诗作与笔记。晚年范成大隐居石湖,在范村种梅、赏梅,研究梅,写成《范村梅谱》,这是中国最早的梅花专著。他在书中记述了江梅、早梅、官城梅、消梅、古梅、重叶梅、绿萼梅、百叶梅、红梅、鸳鸯梅、杏梅、蜡梅等12品,描述了它们的形状、花色,品评了它们的观赏价值。
范成大把蜡梅放在最后,明确指出:蜡梅,本非梅类,以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蜡,故名蜡梅。他还说,蜡梅有三种,其中檀香梅色深黄如紫檀,花密香浓,此品最佳。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他既然认为蜡梅非梅,为何要把蜡梅写进梅谱?估计他是想附在最后,让人们广博见闻吧!
明代李时珍充分肯定了范成大的研究成果。他在《本草纲目》中的记载基本采纳了范的说法:蜡梅,释名黄梅花,此物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此名。他也说,当时蜡梅有三种,檀香梅为第一,花密而香浓,色深黄。
不仅古人欣赏蜡梅,当代人对蜡梅也是情有独钟,它在腊月里常常是不少人家里的首选插花。蜡梅著名的品种主要有素心蜡梅、大花素心蜡梅、罄口蜡梅、小花蜡梅等。
蜡梅凌寒而绽,高洁空灵,不仅馨香优雅,而且有美好的寓意。它的花语是:澄澈的心,慈爱的心,高尚的心。如今,我们在欣赏蜡梅之时,也别忘记东坡、山谷等命名蜡梅的那段蜡梅之约。
今年冬天,我窗外的蜡梅开得不及往年那般繁茂。我习惯于在倦怠时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拒绝反光的黑丝绒。孤寂,是漏斗形的孤寂,是孤独秘密酝酿、聚集、提炼香气的闭关时刻。所以黑色的梅花树立在那里,不过是蝉蜕之术。香气从孤寂的漏斗下逸走了。所以,只有静处,冷眼旁观时才能闻到;只有安静下来,才能看见。寂寞是一种自适,是一种有所顾忌有所约束的自适,而不是绝对的自由。寂寞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它对热泪与阳光总是略略反抗一下,它还是会融化,但总比别的事物要缓慢,也是最后收场的。
寂寞者与骑墙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寂寞者本身就是一道墙。所以无须骑,那太费劲了。
世界上真的没有过不去的墙,但是,南墙是寂寞者最后的依靠。南墙不但是弱者自我保护的屏障,更是他可以流尽眼泪的唯一地缘。临到最后关头,绝望总会扶他一把,因为绝望不是均质的,绝望有很多疏忽的漏洞,钻过窄门,他就不至于丧失道义与立场。这似乎应验了作家卡夫卡的话:“不要绝望,对你的不绝望也不要绝望。在一切似乎已经结束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力量,这正好意味着,你活着。”
世界在变,人在变,不变的不是孤独者的信念,而是一树蜡梅。这与孤独者的未来无关,所以它仍然在南墙内外飘香。孤独的香气,伴孤独者成长与老去,伴孤独者在人生的长路中体验无路的时刻:一回头,我总会看见梅枝上横卧的豹子。
立春之后,蜡梅花在一阵阵春雨下凋零、枯萎,长久发散的香气,似乎已经抽干了它的身体。置身高处的玉兰花,冷眼睨视,举起酒杯,小口啜饮。
责任编辑:卢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