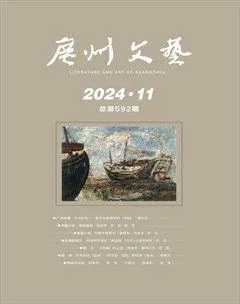小镇发明家
毫无疑问,焦窈瑶选择了一条靠实力靠文本说话的写作道路,而且一直以自己的节奏,不骄不躁不疾不徐地向着一座矗立在远方的灯塔航行而去。自201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男孩三木》至今,已近十五载,不算短的一段航程了。这或许是安静给予她的力量,或者说,这是安静之人才会拥有的力量。而在这十多年间,据我有限的了解,她在小说创作方面,一直在做着一件事情,那便是孜孜不倦地饱含深情地用文字创造着独属于她的文学地理和文学世界——芦镇。四年前,她出版首部小说集《暗夜魔术》时,我曾为其写过一段推荐语:
如果说写作也是在暗夜进行魔术表演的话,那么,焦窈瑶绝对是一位优秀的魔术师。她以短篇小说《男孩三木》为发端,为我们贡献出一个个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独特文本。这些深具现代意识的文本,展现出她对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再造和腾空飞翔的能力。她努力构建的“芦镇文学版图”,与我们熟知的那些文学版图息息相通,而且已初具雏形。这一份自觉,使得她在同代作家中的面目日渐清晰。
这当然不是场面话,更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某种客观审慎的评述,而且至今有效。只不过当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便是焦窈瑶创造芦镇,或者说构建“芦镇文学版图”,不是在其创作过程中逐渐滋生出的念头,而是在创作处女作《男孩三木》时就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和规划。现在,我还发现,她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生活在芦镇的孩子,是处于成长状态的。《男孩三木》中的三木,还是一个九岁的孩子,而在《与男孩三木重逢的夜晚》中,三木已成长为一个少年了。到了她最新的小说《阿波罗的琴弦》中,主人公已经长大成人,迈向了社会,而且逃离了父辈们生活的芦镇。
这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或者说小说中的人物和作为叙述者的小说家一样,都在经历残酷的成长,而不是停留在某一个舒适的阶段。这是清醒的写作认知。焦窈瑶正在拓展自己的写作半径,把手中的笔触向更为广阔也更为深邃的天地,开始书写成年人的烦恼人生。我们自此也可以看出,她构建的芦镇,并非童话城堡,也并非一个封闭的江边小镇,而是一个敞开的、经历着成长阵痛的、被时代车轮所裹挟的文学世界。
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焦窈瑶小说中的人物成长起来了,可童年时的遭遇并没有被忘却,记忆也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以另外的形式顽固地存在着,并影响到小说人物的生活乃至命运。《阿波罗的琴弦》正是书写和探讨童年创伤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中篇小说。故事的起点可追溯至单伟十岁那年的一个周末:小学五年级学生单伟无意之中目睹了父亲单英明在琴房猥亵自己的同班同学葛美蝶,尽管葛美蝶成功逃脱了,并未受到实质性伤害,但这件事“从此成为他摆脱不了的梦魇”和“深埋在他胸中的黑雾”。他念完初中,之所以考到市里的寄宿高中就读,后来又选择出国深造,不为其他,都是为了逃离父亲,逃离那个下午,逃离父亲的秘密对他的侵蚀。
可远离了父亲和父亲生活的芦镇,他在精神上就解脱了吗?在大洋彼岸某艺术院校深造时,他频频被噩梦侵扰,经常“梦到一间粉红色琴房在海上漂,正中间的椅子上坐着拉小提琴的男人,雪白的长发直垂到脚边像个巫师……”从国外毫无骨气地回来之后,他在酒吧厮混时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认识了“像一团烈火往他身上烧起来”的梁沫沫。而某次观看一袭白衣的梁沫沫演出时,他好像看见“有无数个倩影在梁沫沫的身上层叠着,摇摆着,震颤着……而她们的身后则膨胀起一团乌云般阴暗的黑雾”。可见那团黑雾,也即童年创伤如影随形,任你逃离到哪里,都难以摆脱。
葛美蝶其实也一样。作为当年那起像瘴气一样在芦镇蔓延的猥亵事件的受害者,她过得并不轻松,尽管事发后的第二天,她在学校和课堂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初中毕业后,她没有像单伟那样考到市里的寄宿高中去,而是去了芦镇唯一的五星级高中就读,以至于若干年后他们在阿波罗琴行见面时,单伟还以为她住在芦镇。实际上,她也是一个逃离者。“我大学在广州念的,当时就想离开这儿,离得越远越好。”她仅仅维持了两年的婚姻,追根溯源,很难说与这个事件没有关系。
而单伟的女朋友梁沫沫,虽然不是芦镇人,但很显然也受到了这个事件的影响。她是单伟和葛美蝶遭受的童年创伤的间接受害者。事实上,自从在酒吧和单伟认识的那一刻起,她就被卷入了这个事件。带梁沫沫回芦镇见父亲时,单伟要求梁沫沫穿一套女中学生校服,不止于此,他还逼迫梁沫沫用小提琴演奏圣桑的《天鹅》——当年单英明在那间粉红色琴房教葛美蝶拉的曲子;在梁沫沫演奏的过程中,单伟抄起单英明掉落到地上的小提琴狠命地砸向橱柜;被梁沫沫拖出卧室后,他反复说着“对不起”。梁沫沫显然受到了刺激,不仅梦见这可怕的一幕而从梦中哭醒,还抱着一把儿童用的小提琴去酒吧闹事。
这是焦窈瑶的深刻之处,但她更深刻的地方,我认为在于对单伟分裂人格的呈现。“他在那所大洋彼岸的艺术院校进修时交过几个女朋友,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她们共同的特点是身材娇小,且都有着一张烂漫如春的娃娃脸庞。”而且他经常梦到穿红白色校服的女孩子,变成花蛇缠住他。回国后交往的女朋友梁沫沫也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子,他曾在她身上看到无数个倩影重叠着。他一方面想着“去保护她们,将她们从黑雾里拯救出来”,一方面却又占有着她们,在她们的生命中制造着类似的黑雾。他对梁沫沫造成的伤害就是如此。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当已经成为母亲的葛美蝶偶然来到琴房为女儿购买小提琴时,他在酒后和葛美蝶拥抱,并感受到葛美蝶在他的背上轻柔地抚摸。这个情节很有可能只是单伟做过的一个超现实的梦,但这个梦和他经常做的那些梦,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解读,无疑代表着他隐藏在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无疑与他的逃离构成悖论。这也让他自己清醒地认识到,“没用的,再怎么躲也是没用的,他的血管里流着那个人的血,身体里种着那个人的基因,他不过是在努力延迟体内恶魔跃出的时间……”因此,与其说他是在逃离父亲,不如说是在逃离自己。在本质上,他和父亲一样。
单英明确实是十足的恶魔、混蛋,但单伟对他的报复很难说具有正当性。其时,单英明已是第二次中风,而且情况相当严重。此前,他就因中风不能再拉小提琴,变成了单伟梦中邋遢而丑陋的老巫师,已经遭受了命运的惩罚。但面对瘫在床上失去行动能力的单英明,单伟给予了他致命一击——逼着梁沫沫上演了单伟在噩梦里无数次预演的场景,导致“单英明在床上呜咽,像个尿床的婴儿”。不久之后,单英明死于又一次中风,葬礼凄凉。
以单英明为代表的父辈们是非常不堪的,经不起长大成人后的子辈的审视。他和妻子感情不和,妻子在单伟三岁那年跟着一个乐师跑去了国外;音乐世家出身的大鱼叔年轻时因为吊儿郎当和家庭闹掰,结过两次婚,女儿被前妻带走,但家里女人从没断过;梁沫沫的父母生活看似光鲜,但两人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唱男高音的龙叔,和前任太太离了婚,后来动手术后喉咙哑了,再也唱不了歌;葛美蝶的母亲葛春霞的婚姻生活也是一笔糊涂账……也可以说,单伟、梁沫沫、葛美蝶的感情或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与原生家庭脱不开关系。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阿波罗的琴弦》视为成长小说,但单伟等人真的长大成人了吗?尽管单英明去世后,单伟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他和梁沫沫的感情走向其实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答案,而梁沫沫最终做出的选择,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单英明。这不仅是出生于芦镇的年青一代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年青一代面临的问题。这篇小说本身呈现出来的复杂面向以及它对诸多社会问题的探讨,都足以见到焦窈瑶驾驭小说的能力和对家庭生活的深刻思考。
责任编辑:姚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