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什么,为谁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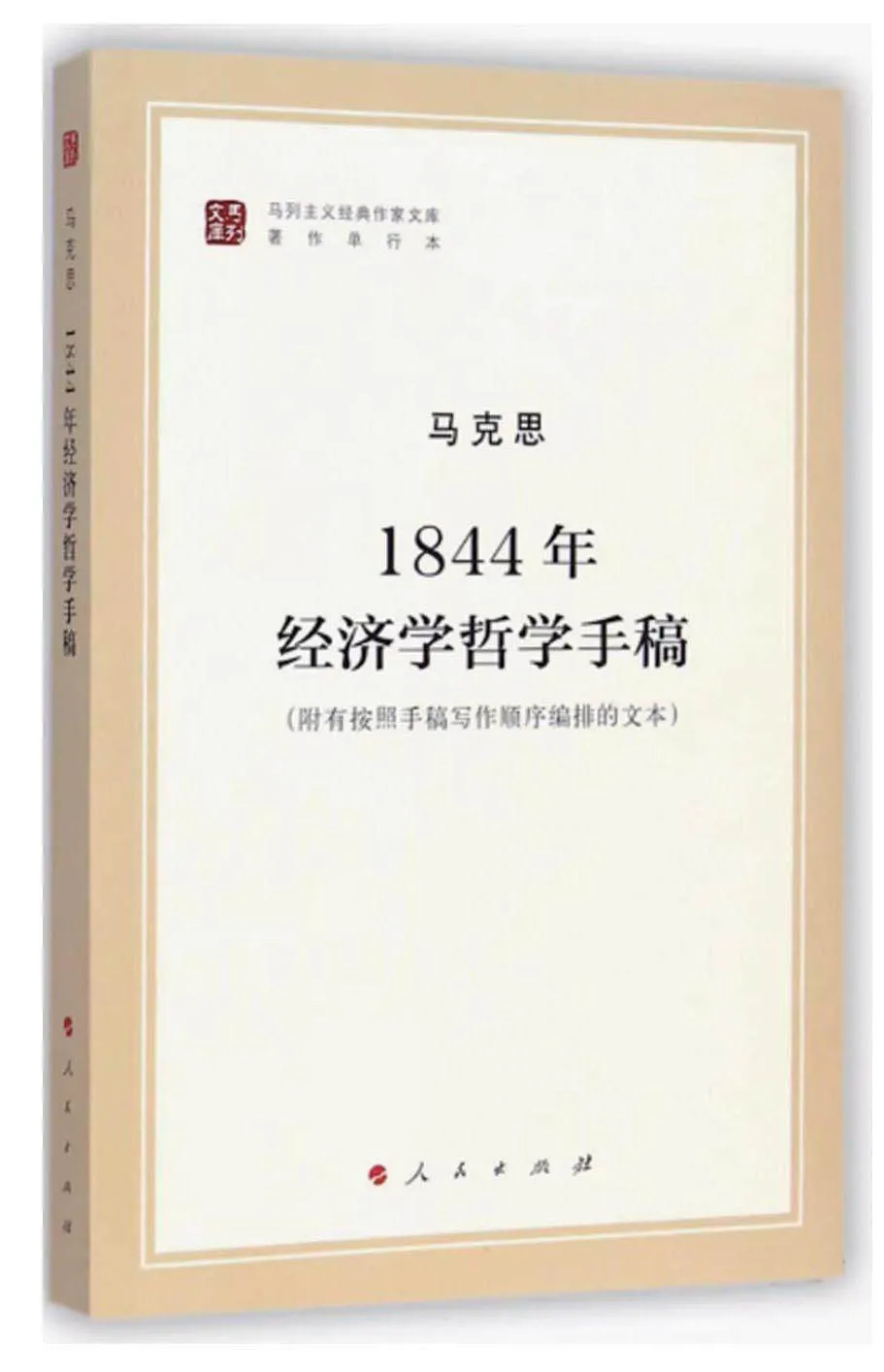
摘 要:马克思从特定历史形式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文学生产。文学生产论内在地具有技术、阶级、意识形态等维度,生产背后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协商构成文化领导权这一重要视野。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也是不同生产要素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动态过程。这一视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获得进一步发展。引入文学生产论的文化领导权视野有助于为我国当下的新型文学生产实践拓展研究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论;文化领导权;当代文学生产
“文学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键概念之一,从“创作”向“生产”的转变标志着将原先对作家、作品的关注转到更大的社会生产语境。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对文学生产论的讨论伴随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争论和文艺学体系建设,呼应着对以往文学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片面性和独断性的反思。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将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文学生产论开始直面新的生产现象,关注文学市场、经济、产业、制度等外部因素。这在带来新的研究活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文学生产论在实际应用中的不足,对生产机制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矫枉过正。各种生产机构和技术既是一般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意识形态机制的一部分,这一属性并没有因其物质面貌的改变而消失。研究文学/文化产业不能忽视对后者的考察,否则容易使我们停留在文学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表面关系上。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开拓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生产论的发展中,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以贯之的重要脉络。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生产,从文学自主到市场化、产业化,从自主的个体成果到资本、利润的广泛介入,从传统文学期刊到各种新媒介文学,从白纸黑字印刷到人工智能写作,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学生产现象背后贯穿着文化领导权问题。本文将从这一视野重新考察马克思文学生产论,以期为我国当下的文学生产实践拓展研究路径。
一、马克思的文学生产论
“文学生产”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生产”谈论艺术,“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马克思指出,某一时代有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取决于那一时代的物质生产状况和社会发展形式。古希腊艺术得以形成的土壤是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这些有赖于当时的生产方式。整体来看,马克思的文学生产观点是其整个“生产”研究的逻辑指向,基本层次是“生产→精神生产→艺术(文学)生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2]33。这是首次明确使用“艺术生产”一词,同时也显示出马克思考察这一概念时的历史语境。这里提到了两个“艺术生产”,前者指相对独立于物质生产并且能够超越时代限制而具有恒久魅力的人类精神活动,如马克思欣赏的古希腊艺术;后者则特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艺术生产。前者涉及到艺术的自律性,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的论题;后者则旨在揭示出在特定历史形式下的艺术生产样貌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如马克思所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3]296
那么马克思所考察的“一定历史形式”下的资本主义精神生产具有哪些特点?第一,生产技术的质变。马克思在考察不同经济时代的区别时,强调了劳动资料的重要性,“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4]。随着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到来,昔日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学也被卷入钢铁洪流中,利用新的技术形式实现“机械复制”,这也是文学得以和“生产”一词相关联的直接动因,标志着从“创作”到“生产”的转变。第二,生产关系维度,体现在作家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雇佣劳动制中。在这一生产关系下,文学生产要为获取利润和增加资本服务。马克思区分了非生产劳动和生产劳动,弥尔顿写作《失乐园》是出于“天性的能动表现”,只获取五磅的收入来维持自身生计,属于非生产劳动;而“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3]432。第三,文学的商品化、市场化。文学不再是某一阶层的私人之物,而是像其他商品一样被交易流通。如伊格尔顿所说,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文学“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5]。最后也最重要的是阶级与意识形态维度。由于新的技术和生产关系在文学生产上的作用,在识字率提升和现代治理技术等历史条件下,文学相比以往具有更浓厚的阶级与意识形态属性,文学生产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生产。在这一历史形式下,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这些都要纠缠于资本和市场的逻辑。市场会针对不同阶层的读者群体量身定做出相应的产品。资本主义利用整个精神生产活动来再生产出得以维系其生产关系的条件。
二、“生产—传播—消费”
机制下的文学生产与文化领导权
资本主义社会文学生产的这些特点使文学活动看上去不再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文学往日具有的神圣价值在工业化生产线上烟消云散,作家的主体地位在雇佣劳动制下日益萎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3]296
资本主义历史形式下的文学生产,不论是前所未有的技术应用,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作家劳动的异化,这些都为统治阶级在精神生产领域行使领导权提供了便利。文学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并被投入到意识形态再生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6]52统治阶级中的个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6]5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那些掌握着劳动产品带来的剩余价值的特权阶级,也掌握着“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7]。
然而文学生产论不仅仅是关于文学如何“生产”的理论,实际上包含着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路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2]14,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文学生产是包含整个生产、传播、消费的过程,在市场作用下,内部诸要素相互影响。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各自以对方为媒介,相互依存。“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2]15-16就文学生产来说,作者作为生产者,为读者生产了可供消费的作品,即提供了消费的材料和对象;而读者作为消费者,也为作者提供了生产的内在需要和动力。生产与消费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了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2]16。
生产和消费的实际过程中需要交换、分配来作为中介。这在文学生产里是文学传播的过程,可由书商、图书馆、诸教育机构等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文学传播根据市场进行受众分配,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阶级与意识形态因素是其内在动力。生产、传播什么样的文学,哪些语言可以被纳入文学生产体系,甚至什么可以算作“文学”,这些都要受主导的传播审查机制影响。但也正因为市场化,文学在不同阶层间的流通传播相较之前时期有更多灵活性。
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运动来看,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过程也是广大读者参与精神生产的过程。一方面,生产在“创造消费者”“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2]15。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的主体地位受到生产者的领导与决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文学生产进行渗透。而另一方面,消费也“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2]15“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2]14。读者在文学生产中并不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可以通过消费活动参与到文学生产中,完成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化,积极地实施选择。进行怎样的文学生产不是由某一方力量单独领导,也无法进行强制性的灌输,而需要参考多方意见。由此,在文学生产的过程中实际上打开了一个可以斗争、谈判的空间,不同意识形态在这里对话、碰撞、冲突、协商。代表无产阶级的作家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同读者一起积极地争取文化领导权,展开“阵地战”。这一文学生产活动可以遍布学校、书店、咖啡屋、工厂甚至监狱,通过报刊、书籍、手册等多种载体开展。
基于这一文化领导权视野的资本主义文学生产具有这样的矛盾:一方面高度体制化、模式化,具有自上而下整合的统治力;另一方面,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其相对之前时期又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既再生产着主导的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行使霸权;又在这一过程中生产着流通对话的空间,生产着“掘墓人”。文学生产也就成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动态过程。
三、生产技术与意识
形态生产下的文化领导权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文学生产论,其文化领导权视野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应用与拓展。布莱希特和本雅明都将文艺生产视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注重技术的进步对文艺生产方式的改变,强调对文艺生产中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布莱希特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欺骗性,使人民满足于目前的状况而失去批判精神,传统戏剧的移情效果则成为帮凶。鉴于此,通过新的艺术形式来争取文化领导权就具有紧迫性。其关键是要带动观众的参与和反思意识,将观看行为本身纳入到生产实践中来。布莱希特将一系列声光装置等新技术手段应用到戏剧上,加上人物表演、布局、结构等形式方面的实验,旨在消除观众的移情、共鸣,打破“第四堵墙”,获得间离效果,重获批判精神。
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认为,进步作家应作为生产者投入到社会生产中,自觉地站到无产阶级一边,为阶级利益服务。本雅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生产。如同生产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决定意义,文学生产技术也在文学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技术本身也和生产者在文化上的领导力相关,“文学的倾向性就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之中”[8]304“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来说,技术的进步也是他政治进步的基础”[8]310-311。技术的进步为变革文学生产关系带来契机,进而变革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布莱希特和本雅明都看到技术的进步性,但他们意识到技术也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霸权手段。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既看到了电影带来的政治实践效果,也指出电影资本促使的明星崇拜、名流效应等会成为麻木和操控大众的工具,生产出新的膜拜式“光韵”。因此,关键在于技术为谁而用,在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作家与读者一起争取文化领导权:作家要“引导别的生产者进行生产”“给他们提供一个改进了的器械”,不断地把读者和观众变为共同行为者[8]313。布莱希特也申明过这样的主张:“不提供没有尽可能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改造的生产机器!”[8]309
如果说布莱希特与本雅明是从生产技术出发,将生产工具为谁而用的问题考虑在内,思考进步作家与无产阶级群体在文学生产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具有紧迫的实践性和政治功利性,那么马歇雷和伊格尔顿则从文本批评入手,考察文本形式与意识形态生产之间的关系。马歇雷认为文学是有关意识形态的生产活动。意识形态不是直接地通过文学反映自身,而是作为原材料被加工、生产,被文本赋形。但这不代表作品仅是意识形态幻觉的合谋,“尽管文本由不定形的幻觉语言建构,并使自身围绕着这一幻觉,但文本在为意识形态赋形的过程中也站在揭露这一神话的立场上”[9]。因此文学与意识形态是一种“离心”而非“同构”关系。文本本身受制于意识形态,但同时也与后者保持距离,为揭示意识形态提供入口。为了让文本道出自身与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马歇雷构建“科学的批评”,引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关注文本中的“沉默、缺席、断裂、矛盾”,正是在这些关键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稳定性,其空隙与界限得以彰显。批评正是要使文本中的沉默发声,让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得以显露。
伊格尔顿进一步发展了马歇雷的文学生产论,构建了一套“唯物主义批评的范畴”:包括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10]79。所谓一般生产方式即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可以生产出一种主导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这三者之间又可以互相再生产。在这种紧密关系中,文学生产的文化领导权功能得以发挥:“所有文学生产都属于意识形态机制,它可以被暂定为一种‘文化’。需要被讨论的并非仅是文学文本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而是这些生产在文化意识形态机制中所起的作用”[10]96。文学生产方式与其他要素之间不是铁板一块的,内部存在着诸多矛盾和断裂。“相同的文学生产方式可能再生产出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结构。”[10]98作者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虽然嵌入在一般意识形态中,但彼此也具有一致、部分分离或对立等复杂关系。文学生产者可以是某些阶层的特权用人,某一社会团体授权的代言人,一个“独立”生产者,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反叛者,或是与读者群保持友好关系的“工人”。“文学生产方式,其自身就是历史上相异成分的混合物,因而它能使一般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中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成分结合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之内”[10]103-104编织文本的语言既是物质生产力量的一部分,也在本质上是政治的语言,是各方力量展开斗争的领域。“每个文学文本都在某种程度上内化了其社会生产关系——每个文本通过特有的惯例暗示出它被消费的方式,并在其自身内编码了它如何被生产、由谁生产和为谁生产的意识形态。”[10]84-85
四、当代文学生产现象与文化领导权
由以上论述可知,文学生产论的文化领导权视野涉及生产技术、传播消费方式、文本形式等多个层面。综合这些维度可以考察我国当代文学生产现象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相较我国传统文学生产,当代新的文学生产实践在技术因素上更突出,参与的生产要素更多、其相互关系更复杂,生产要素间互动更频繁、即时,生产与消费进一步辩证统一,传播更快更广。试分析几个重要的新生产现象。
(一)文学生产与大众文化产业的结合。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和文学市场化,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逐渐成为常态。较早的典型现象是文学生产与影视生产的结合,文学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作家与导演合作并为影视产业和自身带来丰厚利润,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者”。与影视生产结合的文学生产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权力关系,作家难以自主地进行文化输出,其写作受制于影视资本和受众市场,常需要根据影视产业的需求进行“命题作文”,甚至出现先有剧本后有小说的生产现象。文学生产与大众文化的结合还逐渐扩大到流行音乐、电子游戏等领域。由此,文学生产链扩大,生产要素增多,价值成倍增长,参与角逐的意识形态相比伊格尔顿提出的六大范畴要更复杂。媒体融合使文学生产走向更广泛的文化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官方媒体借助经典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以新颖灵活的方式进行文化领导,取得不错的效果。例如央视节目《经典咏流传》,将古诗词改编为流行歌曲,明星演唱与舞台技术相结合,邀请文学、音乐领域的专业知识分子进行点评,并通过新媒介与广大受众互动。《典籍里的中国》则以“戏剧+影视化”的形式,借助跨时空对话等手法让典籍“活起来”。相比于其他流行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娱乐化和个人化叙事,这些节目侧重于弘扬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具有鲜明的主旋律价值观,并在受众的自觉认同中成功地巩固文化领导权。两个节目的第一季在“豆瓣”分别获得了8.6和8.7的高分评价。这些现象体现了在文化产业盛行的当下重新发掘经典永恒魅力的努力,打破两个“艺术生产”的对立。让尘封于历史和象牙塔的经典进入大众视野,在各种流行文化众声喧嚣的今天发出声音,而借助的方式却是当下的大众文化生产机制,这或许是工具理性化、娱乐化的当下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一种“借力打力”、积极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尝试。
(二)网络文学生产。网络文学如今已成为新媒介文学生产的典型现象。网络文学相比传统期刊文学具有较低的发表门槛,为大众创作开辟了自主的空间。同时,因为网络媒介的便捷性、即时性,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更频繁、直接,读者意见会影响接下来的写作。本雅明在谈到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的文化领导权时以报纸为例,指出当时苏联的新闻报纸已经打破了文学体裁之间、作家和诗人之间、学者与通俗读物作者之间乃至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区分。在那里,读者随时准备成为作者,加入生产者的队伍[8]306。从网络文学的特征来看,作者似乎可以不受传统文学体制影响而更自由地创作,在文化场域占据一席之地;读者则有更多机会与作者互动,“加入生产者的队伍”。然而,这只是理想情况。随着资本介入和网络文学产业化的成形,网络文学走向类型化、批量化生产。作者收益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平台基本收入、小说字数、读者点击率和订阅量、读者打赏、第三方赞助等。在消费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技术的定向传播下,读者会更倾向于某些类型作品;读者意见又反过来“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直接影响作者专注于这类作品的生产,由此形成一种产业循环。网络文学也进一步扩大生产链,因自身审美特征而更适合被改编为影视剧、电子游戏,形成热门“IP”效应。这些生产机制背后是文化领导权的更迭,有论者指出,网络文学是在传统启蒙话语解体,精英文学丧失文化领导权的背景下提供了一个“满足欲望同时又生产欲望的幻象空间”[11],对应了网络时代个体的精神症候。
然而,如前文所述,文学生产中的文化领导问题不是某一方的单声部话语,而是众声喧哗式的动态过程。网络小说既有大量架空历史、悬置现实的“爽文”,也不乏以其独特方式和想象力关注社会、介入现实的作品。这种转变也有官方介入文化领导的作用。通过举办优秀网络文学大赛,将一些网络作家纳入各地作协,扶持某类网络文学改编为影视剧,如今的网络文学已被赋予书写中国故事、促进文化强国、向海外输出中国文化的使命。
(三)人工智能文学生产。2017年,微软人工智能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成为人工智能参与文学生产的标志性事件。从文学生产论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标志着从创作向生产的更根本转换。因为此前的文学创作虽然被纳入到物质生产过程中,受资本、商品市场等因素影响,但其创作主体主要还是人,而人工智能文学生产则由机器来完成。虽需要由人设计算法并提供学习材料,但最后的产出结果却不受人预料。
人工智能文学生产目前还具有实验性质,但在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紧密结合的时代趋势和“后人类”背景下,未来的文学、文化生产会越发人工智能化。技术已由原先的传播媒介位置横跨到整个生产过程,作为生产者直接参与其中。微软小冰以及Chat GPT等人工智能可以采取人机交互写作,大大降低了业余爱好者文学创作的门槛。但布莱希特和本雅明强调的技术由谁掌握、为谁而用的问题依然需要重视。我们不能忘记人工智能这一设想原自二战时期的“控制论”,可能构成对人的“抽象统治”[12]。当人工智能文化生产受到跨国资本主义的驱动,可能会在全球范围进行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
五、结语
文化领导权问题贯穿于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过程。自葛兰西以降,谈论文化领导权多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而从文学生产论来看文化领导权,既关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也涉及政治经济学视角。现代生产方式已使文学生产融入到一般生产方式之中,脱离物质经济层面单谈文化问题是不够的。反之,引入文化领导权视野得以丰富文学生产论,综合多维度的研究可以避免生产论陷入僵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对文学生产论的接受曾出现过将生产论与反映论、意识形态论对立起来,正是忽略了生产论中的多重视野。而当下在文学生产与技术、经济产业捆绑紧密的背景下,文学生产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更是不能忽视的重要维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第1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4.
[5]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5.
[6]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1.
[8]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C]//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10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9]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M].trans.Geoffrey Wall.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64.
[10]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M].段吉方,穆宝清,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21.
[11]邵燕君.在“异托邦”里建构“个人另类选择”幻象空间——网络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种[J].文艺研究,2012(4):16-25.
[12]黄平.人学是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J].文坛纵横,2020(5):18-33.
作者简介:牛旭阳,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