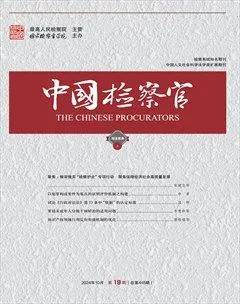知识产权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优化*
摘 要:完善知识产权领域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的关键是构建规范有序、严密高效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通过优化“出刑入行”畅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事实认定、责任追究的衔接。其一,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标准不宜唯数额数量论,应综合评价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二,构建“构成要件符合性出罪+可罚的违法性出罪”之双阶实质出罪机制,将不符合构成要件或者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排除出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圈。其三,给予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人过罚相当的行政处罚,形成知识产权保护闭环。
关键词:知识产权犯罪 行刑反向衔接 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 出刑入行
2024年4月最高检发布的《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2023年)》显示,2021年至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分别为9611件22011人、8489件20192人、12122件30684人,经审查,起诉20510件44337人,不起诉3279件9378人。[1]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呈现上升态势,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案件审查后,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7条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但是“不起诉”不等于“不处罚”。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既存在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政违法行为拔高认定为侵犯知识产权罪,反映出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标准把握不严、出罪机制不畅通等问题,也存在对被决定不起诉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追究不到位,出现行刑断档、不刑不罚、一放了之等处罚漏洞,究其根源则在于知识产权领域行刑反向机制尚不健全。对此,最高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建立案件线索双向移送机制,特别是完善知识产权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即检察机关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应予行政处罚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移送同级负责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进行处理,即“出刑入行”,主要目的是贯通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2]日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强调“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在知识产权领域构建规范有序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是今后一个时期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的关键所在,有利于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闭环。
一、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标准不宜唯数额数量论
(一)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标准形式化
我国刑法对于犯罪采取立法与司法双重定量模式,在立法上对罪量要素作出盖然性规定后,授权最高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综合考虑社会危害、犯罪态势、刑事政策等因素,以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罪量要素作出具体解释,以确定个罪的入罪标准。《刑法》第3章第7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规定的所有犯罪都以“情节严重”或者“其他严重情节”为罪量要素,反映侵犯知识产权不法行为客观的法益侵害状况,起到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作用,即如果没有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轻微就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范畴,进而不构成犯罪。在以情节犯为主导的罪量设置模式下,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多部司法解释对于罪量要素采取的都是“计赃定罪”的解释思路,均以数额、数量作为罪量要素的主要评价标准,包括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直接经济损失数额、销售金额、货值金额、标识数量、侵权复制品数量、点击数、下载量、注册会员数量等。
(二)综合考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单纯采取与不法行为相关的数额、数459ee873986a8139eae2cddb1efe5500f4f40c6fd33ed22a68721c7ee3d06f5d量等精确量化的形式标准评价法益侵害,存在明显的“构量入罪”之缺陷,缺乏对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价,客观上降低了入罪门槛,可能造成情节严重与否的认定出现偏差,极易导致没有侵害法益的行为被定罪处罚。例如,在王某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公安机关在被告人王某彪处查获未销售的假冒始祖鸟牌服装7090件,价格认定中心认定货值金额为109.2880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彪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货值金额超过15万元,符合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但成立犯罪未遂,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3] 然而,侵权假冒物品尚未销售即表明其还没有进入到市场流通交易领域,既未侵犯消费者的财产权益,亦未实质性损害正品权利人的市场占有份额及公平竞争关系,可见并没有现实的法益侵害。因此,司法实践中对于知识产权犯罪中罪量要素的认定,不宜机械地以数额、数量为唯一入罪标准,而应综合考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此判断情节严重与否以及是否定罪处罚。
二、构建知识产权犯罪的双阶实质出罪机制
刑事违法性是刑法对犯罪行为作出的客观的否定性评价,违法性概念有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前者是指“仅仅违反了禁止一定行为或命令一定行为的法规的情形”[4],后者则强调“对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侵害是实质上的违法,如果此等利益是与法秩序目的和人类共同生活目的相适应的”[5],即法益侵害性是其决定性因素。法益侵害不仅存在有无之分,还具有程度差异,刑法只能将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并予以处罚。这里的“法益侵害”应理解为“达到值得处罚程度的法益侵害”,在此意义上,实质违法性在刑法理论上又被称为“实质意义上的可罚性”。因此,认定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一般分为阶层递进式的两个步骤:第一阶层是判断形式违法性,即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果不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则予以出罪;第二阶层是判断实质可罚性,在行为符合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进一步判断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如果没有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程度的法益侵害则予以出罪。
(一)知识产权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出罪机制
就形式违法性的判断而言,关键在于解释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而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知识产权犯罪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犯,违反国家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是其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所指向的正是《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前置法,旨在发挥前置法对刑法定罪的限制作用。因此,应当将刑法中的侵犯知识产权罪置于整个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中理解与适用。具体而言,在解释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时,应当采取以法秩序统一性为基础的体系解释方法,尽量援引前置法上对于相关专业术语含义的规定,确保刑法和知识产权法对同一名词的内涵与外延之界定基本保持一致;在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时,首先要甄别某一行为是否具有前置法上的违法性,避免整个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自相矛盾,尤其是防止出现违反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情形:前置法上的合法行为在刑法上被认定为犯罪,反之,前置法上的合法行为可以作为出罪事由。
(二)知识产权犯罪可罚的违法性出罪机制
就实质可罚性的判断而言,重点在于认定不法行为是否严重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进而判断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所谓‘可罚的违法性’,不是单纯阐述某个违法行为是‘处罚的对象’这一结论,而是表明其违法性达到‘值得处罚’的程度的这种实质性评价。”[6]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基于实质的违法性所展开,某一行为虽然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如果违法性轻微、实质上没有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程度的法益侵害,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可以通过其他手段予以规制而不必动用刑法,即通过实质出罪机制将尚未达到可罚程度的法益侵害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例如,犯罪嫌疑人郑某霞在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以三轮车摆摊的方式在某市某镇销售光碟,被某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扫黄打非办、市公安局当场查获并扣押待销光碟1380张。经市版权局认定,被扣押的1380张光碟为侵权盗版出版物。本案中,郑某霞以营利为目的,以出售方式向他人提供盗版光碟的行为符合侵犯著作权罪构成要件中的“发行”,但销售数量较少,社会危害性较小,即“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法益侵害尚未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可以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出罪,不宜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7]
三、给予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人行政处罚
(一)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出罪入行”的审查流程
不法行为出罪仅意味着不追究刑事责任、免予刑事处罚,并非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此,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27条首次在实体法层面确立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反向衔接机制;同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健全检察机关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制度”。检察机关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应予行政处罚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移送同级负责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处理。如前述郑某霞案中,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郑某霞免予刑事处罚,通过知识产权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处理,依法给子其相应的行政处罚。再比如,在王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犯罪嫌疑人王某向他人购买假冒某知名注册商标的白酒后,以每瓶1300元至1350元不等的价格多次向李某销售60瓶,并收取李某购酒款80400元。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认为王某系初犯,犯罪情节较轻微且有坦白、认罪悔罪情节,不需要判处刑罚,因而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但该知假售假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破坏了正常的商标管理秩序,损害了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遂决定将本案移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对王某作出罚款8000元、没收60瓶侵权白酒的行政处罚决定。[8]
知识产权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具体运作流程为:人民检察院内设的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提出是否需要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并将案件卷宗材料移送至行政主管部门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的行政检察部门进行审查。行政检察部门受理案件后,应对违法事实、证据材料、社会危害性等进行实质审查核实,认为被不起诉人已达到应受行政处罚的标准的,经检察长批准,向同级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制发检察意见,建议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同步移送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材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在收到检察意见后,应对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并及时以书面形式向行政检察部门反馈案件处理结果或者办理情况。
(二)准确把握给予侵权行为人行政处罚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必须准确把握“可处罚性”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3款强调“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才应当移送,最高检《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第8条进一步要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审查是否需要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换言之,并非对所有侵犯知识产权不起诉案件都一律移送行政执法机关给予行政处罚,不能将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机械地理解为“不刑就行”[9],要结合个案中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预防必要性等因素对行政处罚必要性进行实质审查,综合考量是否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例如,如果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全额退赃,赔偿权利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双方达成和解,积极修复受损法益,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原则上没有必要再移送行政执法机关给予其行政处罚,否则可能抵消和解的效果,不利于化解矛盾纠纷。此外,即便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遵循比例原则,选择恰当的行政处罚措施,确保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过罚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