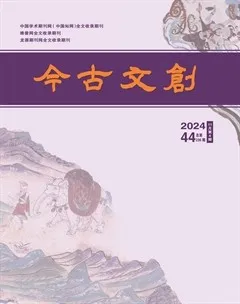流传与禁阻——文本文献视角下的民俗活动“ 社火 ”

【摘要】“社火”作为民间集体性游艺活动,不同于通常所见在固定场地、以专门演员为主导的传统戏剧表演,而是以生动形象的人物、念白、舞蹈等形式,进行民间游行的集体活动。今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仍有“社火”这一传统民俗活动流传。“社火”由土神信仰产生,因传统宗族制、群居制得以发展、流传,其内容、形式体现了民俗文化特有的包容性。民间活动“社火”走街串巷进行展演的同时,又与古代正统文化和思想相对,乃至被统治阶层所禁毁,为民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面貌和文献信息。
【关键词】社火;游艺;方志;宗族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4-011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4.029
“社火”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地域举办的民间性游艺活动,具有鲜明的娱乐性、通俗性,形式结合戏剧杂耍、歌舞唱跳,向土神、城隍等神灵进行祈祷。相关的文本内容见于诗歌、地方方志、俗文学等。作为一种民俗活动,“社火”不只娱乐大众、祭祀神灵,还以群聚性的组织形式、全民参与型的游行活动维系着人们的乡土观念和乡土情感,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号召力与凝聚性。在部分文献中,“社火”作为一种夹杂着鬼神崇拜的俗信仰,与官方文化相对而遭到法律禁止,与描写游行娱乐的通俗文献产生巨大差异。本文即从传世文献和地方方志出发,对“社火”的产生、流传、发展与禁毁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 从祭祀社神到群众游艺活动
《说文解字》 “社”字下:“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1]“社”字从示、从土,做“社神”之义,早见于甲骨文,与“土”同形,为“土地之神。[2]土地信仰在原始社会普遍存在,并有春社等在固定节日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宗族制使居住的土地具有了区分、维系“人口”的功能,“社”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由土地之神发展出人口单位这一义项。“火”为唐代兵制单位,十人为“火”[3],行军时共竈起火,称为“火伴”。本文所要讨论的“社火”一词指民俗活动,最早见于宋范成大诗《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记述行歌与狂舞配合的热闹场面。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对其所见“东京献社火”一事详尽描述,包括杂技、扮演、道术等。“社”与“火(伙)”均带有群居、聚集的义素,二者同义组合又发展出“同伙”义,如《水浒传》第五十八回:“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来寻山寨头领,必然是社火中人故旧交友,岂敢有失祗应?便当去报。’”基于此,作为民俗活动的“社火”一词也始终保持着“聚集性”的语义特色。
直至明清,文献中仍见“社火”的记载,如明《醒世恒言》第二十五卷:“自十三至十七,共是五夜,家家门首扎缚灯栅,张挂新奇,好灯巧样,烟火照耀,如同白昼,狮蛮社火,鼓乐笙箫,通宵达旦。”[4]从“共是五夜”“通宵达旦”中可见,“社火”在宋代宵禁制度逐渐解除后,具有了“夜游”的特色。社火的形式和内容也不断拓展丰富,《连环记传奇》记表演内容有鬼脸狰狞、朝歌羌调,《飞花咏》记扮苏东坡游赤壁、扮陶渊明赏菊等故事。
二、地方方志所记“社火”考
民俗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而方志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历史习俗的可靠材料。《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5]收录方言,对“社火”一词进行解释:“民间在节日的集体游艺活动,如高跷、秧歌、狮舞、龙灯等。西安正月十五的社火最热闹”,另有“看社火”“闹社火”等词条。笔者梳理“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的相关方志,以作说明。
(1)《重修琴川志》卷十:“至和之初,每岁季春,岳灵诞日,旁郡人不远数百里,结社火,具舟车,赍香信,诣祠下,致礼敬者,吹箫击鼓,揭号华旗,相属于道,又载父老之语。”
(2)《新修清水河厅志》卷十六:“十五日,上元佳节。入夜,街衢中悬灯笼火。有扮作文故事,沿街歌唱者,名秧歌;有扮作武故事,尚街舞打者,曰社火。又有以竹编船,用色纸糊饰,一人妆扮美女,在船中沿街游行,名为船灯。花爆盈耳,士女如云,颇觉热闹。”
(3)《续顺宁府志稿》卷五:“立春日,官吏士民往东山寺迎春,各乡里亦扮社火为渔樵耕读之类。父老鞭芒,春官献岁。”
相比传统文献,地方方志记载的内容更加全面。“社火”的时间由上元节拓展到季春、六月、九月等。可见,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在开始阶段以群聚性面貌出现,并非为特定节日专门造出。“社火”是一种游艺活动,具有时间灵活、地点灵活、样式多样的突出特点。在内容上,方志记述以更加具体、形象的语言彰显地域特色,如“秧歌、马社火”等。民间自发的游艺活动具有活泼、鲜明的特色,不拘于形式,而以娱乐民众、休闲取乐为目的。“春官”为周礼所记官名,《周礼·天官冡宰一》:“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大事则从,其掌小事,则专达。”[6]在后世又作为礼部代称。作为掌管礼仪的官员,其在“社火”这一民俗活动中被吸纳创新,清俞樾《茶香室丛钞·迎春社火》:“次日打春官,给身钱二十七文,赏春官通书十本。”[7]春官在“社火”活动中扮演了赋词铺排,进行唱诵的表演角色。“春官”一词从古代朝廷官名到民俗仪式中的俗化,展现了民间文化所具有的通俗性特点。
(4)《甘肃新通志》卷九十三:“姣服逍遥。社火技戏,鼓吹鸣铙。隐輷軯礚,达暮连宵。凡佳辰与令节,莫不忭舞而僬僬。两乃覃敷文教,礼乐是兴。从容庠序,郁郁彬彬。率文翁之雅化,沐黎伯之陶甄。洵风气之日上,作边邮之典型。”
“舞”在甲骨文中即见,人手拿类似蓑草的工具摆动即是“舞”。作为传统文化中祭祀神灵的礼仪传承,“社火”作为一种民俗活动,与古先民的天人感应、人神合一相合。“社火”以其丰富的形式既娱“人”,又娱“神”,从而通过舞蹈、社火戏等活动,达成祭祀、祈福的目的。我国古代狂欢歌舞的祭祀活动于先秦文献中已见。《周礼·春官·乐师》:“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5]后世随着民族交融,发展出各式舞蹈。在《陕西方志》中,与古代“傩礼”结合,通过向上天祈求达到“驱逐瘟疫”的目的。民国时期《重修镇原县志》卷五记“假面具”一词,则是记载了“社火”与“傩”的直接联系:
(5)《重修镇原县志》卷五:“假面具,俗名漫脸子。案:《周礼·方相氏》:‘黄金四目以逐鬼。’《后汉书·礼仪志》:‘以木面兽为傩。’《柳彧传》:‘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作角觝戏,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彧请禁断,诏可其奏。’《梦华录》:‘除夕,禁中诸班直钺,假面装将军,又甲冑装门丞。’此皆玩社火之所戴也。唐译佛经有《佛说救面然饿鬼》及燄口饿鬼等经咒。盖释氏谓饿鬼名面然,亦名燄口,言火燄岀于口,而面若然也。此又一事也。”
傩戏面具是傩戏表演活动中极为重要的道具,同时也是傩戏符号话语系统的重要元素之一。[8] 《后汉书·礼仪志中》即有所记,以青年男子扮“伥”,穿熊皮在前殿举办仪式,唱和十二凶兽后,手执火把送疫。在文献记载中,有戴面具扮鬼来耍社火的形式,如上引“假面子”,涵盖历史人物、宗教人物等,通过特殊的面具形态进行人与神身份的转换,构造审美距离,造成心灵震撼。今甘肃陇东地区“社火”仍然有戴面具、画鬼面脸谱的演出形式,傩戏以多元的面貌保留在“社火”中。
以表演歌舞、佩戴面具等方式进行的“社火”活动,沿古承袭。祭祀者以其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动作、语言、道具在现实世界中构建起祭祀神灵、与神交通的轨道,企图通过“娱神”的方式祈祷丰收、胜利甚至消除瘟疫。后世融合舞蹈、故事表演的“社火”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实际是古代祭祀发展而来,并杂糅各种元素进行表演。通过表演,观赏者和被观赏者在短暂的时空中被融入以仪式为互动方式的空间中,达成高度统一。
语料频次是当今人文社科研究的可靠标准。笔者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的方志条目,共检索140条“社火”(包括同义词“社伙”等)作为民俗活动代称的语料。语料中,《滇志》《建水州志》《临安州志》《云南通志》均记杨慎《临安春社行》一诗,因此去除部分语料,总计共138条,作表如下:
“社火”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多集中在山西、甘肃、陕西等北方地区,同时在浙江、云南等南方地区也有分布,总体呈现北多南少的样貌,且主要集中在近西北地区。笔者认为,祭祀社神、土神的活动应广泛存在于内地,但由于历史发展沿革,部分地区以祭祀名称(如腊祭),或生辰、庙会等指称“社火”有关的活动。“社火”活动作为一种沿历史而来,兼容并包,融合多种信仰的活动总称,实际内容必定超出现查文献,与多种民俗活动交叉。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表明:“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9]“社火”作为一个能指符号,在词汇构造和语义连结中生成,其内涵由于特有的民间性、历史性存在语义模糊空间。
三、“社火”活动展现的官方-民间文化认同差异
“社火”作为一种民间性的集体活动,具有广泛的演出空间和多样的演出形式,但从文献记载不难看出,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小说戏曲中,只在地方方志文献中分布较广。差异性的文献分布实际展现的是官方与民间、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价值认同、审美取向的差异。
前文所提对“社火”的评论多与“娱乐”“滑稽”等词同现,可见,在文人记载里,“社火”这一活动始终是作为娱乐形式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把戏”。黄震《黄氏日钞存》卷七十四:“提举司佥厅书拟照,执左道以乱政,假鬼神以惑众者杀,赛祠社会执引兵仗者,随重轻论罪。经典法条,炳如星日。”[10]“社会”活动中包含的假鬼神等行为要根据轻重进行论罪。尤见宋李元弼《作邑自箴》[11],将“社会”所依托的求神赐福这一观念进行批判,而以儒家伦理道德、家庭和睦作为规范和准则:
(6)民间多做社会,俗谓之保田,蚕人口求福禳灾而已。或更率饮钱物造作器用之类,献送寺庙,动是月十日,有妨经营。其间贫下人户,多是典剥取债,方可应副。又以畏惧神明,不敢违众,或是争气,强须入会。愚民无知,求福者未必得福,禳灾者未必无灾。汝辈但孝顺和睦,省事长法,不做社会献送,自然天神祐助,家道吉昌。汝若不孝不睦,非理作事,虽日日求神祷佛,亦不免灾祸也。
除政治和思想统治需要外,频繁发生的社会治安事件也是官方禁止“社火”游行的重要原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戊寅,诏:访闻关右民,每岁夏首于凤翔府岐山县法门寺为社会,游惰之辈,昼夜行乐,至有奸诈杀伤人者。宜令有司量定聚会日数,禁其夜集,官吏严加警察。”[12]因夜间游行而多发“杀伤”一类的案件。
一方面是宋代诗人施岑笔下“仙驾幸临多降福,故令士庶转诚加”的繁华场面,一方面是士阶层和统治阶层的批判与禁止,“社火”在文献中呈现的两面性、对立性为我们展现了民俗活动作为民间自发形成的团体集会对统治阶层乃至传统社会观念的冲击。“社火”将妇女群体从日常生活和闺阁中解放出来,有了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娱乐的机会,同时又由于古代治安等原因,难以避免地造成社会治安问题。正是多重因素,造成了文献记载的多样化和矛盾性,笔者认为,这种非单一、非正统的矛盾点正是忠实于俗文化的生动体现。
四、结语
“社火”起源于古代社神文化,又随着历史变革不断增添新元素,展现了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原大地的特色。在“社”中孕育出的宗族观念和地域特色,也系连着习俗活动参与者和参观者的乡愁与精神寄托。同时,通过细读文本文献,发现民间习俗具有与正统文化及观念相抵触、相矛盾的信仰及活动形式,展现了民间与官方共存于同一时空下的互动和对立。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20:5.
[2]王力.同源字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6.
[3]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2:2343.
[4]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355.
[5]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1931.
[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405,1713.
[7]俞樾.茶香室丛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5:402.
[8]张金梅.恩施傩戏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110.
[9]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07.
[10]黄震.黄氏日钞存[Z].元至元三年刻本.
[11]李元弼.作邑自箴[Z].清影宋钞本.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Z].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作者简介:
孟蕊蕊,女,甘肃泾川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汉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