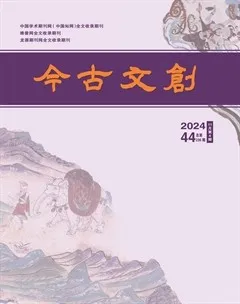资本主义批判视域下的主体性追问
【摘要】2024年上映的宫崎骏执导的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对当下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带来诸多启示,作为他极富个性表达的一部作品,电影本身有广泛的评论和争议。电影主人公在经历“异世界”的一番探险中,完成了对自我价值追问的回答,重塑了自身的主体性。宫崎骏用隐喻和意象在批判资本主义秩序下主体性不在场现象的同时,也结合真人成长经历表达了在面临此种境遇下对人生意义和出路的思考,给当下青年对主体性构建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动力。
【关键词】宫崎骏;《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资本主义;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4-008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4.022
2024年,宫崎骏执导的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上映,电影斩获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成为继《千与千寻》之后,时隔21年第二部获此殊荣的日本动画电影。作为宫崎骏经过7年沉淀的最新一部电影,同时也是带有半自传性质的自我成长影片,上映以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解读。作为艺术家的宫崎骏从审美的角度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并通过艺术直观进行提炼和复现,跳出了仅限于个人成长的自我影射,而呈现出一种关切到人类主体性的哲学表达。
一、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下主体性丧失的批判
(一)黑石和积木构建的世界标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1.“黑石”和积木的意象构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
电影中的“黑石”和积木都是以舅公为代表的掌控话语权的人所运用的工具。巨大的悬浮在空中的黑色石头象征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积木的搭建是一种理性主义或者是形式逻辑的象征,其特点是可量化,它在个体形态上是规则的,但是整体上又呈现出一种无序的杂乱无章的状态,其运行路径没有规律可循。
它们可以对应着资本主义以理性主义为逻辑起点的文明形态,虽然这种文明在明治维新后冲破了日本传统封建文化的枷锁,此后得以在日本社会扎根,但是它带来的后果是不尽如人意的。理想的面纱背后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两极分化,理性设想规划的通往终极至善的彼岸世界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就能实现,只能由无数人的牺牲铺就。最开始它似乎想通过各种手段掩盖其本来面目,但最终都是徒劳。
2.鹦鹉对黑石的态度隐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破产
舅公与“黑石”的关系揭示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舅公的力量显然来自“黑石”,舅公年轻时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艺术的熏陶,掌握了改造旧世界的手段,他毕生致力于用纯粹无污染的积木构筑一个新世界,进而成为维护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但最后舅公变疯魔的结局意味着,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追求西方式的“绝对秩序”和“终极答案”里迷失,进而自我异化。
资本主义真正的统治者——象征军国主义特权的鹦鹉急切解决现实矛盾和获得更多利益的愿望,使他们没有办法忍受舅公在意识形态里浸淫,随之用暴力手段毁灭积木,和舅公同归于尽。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和维护其意识形态的统治结束,也说明了舅公希冀从抽象王国寻找通往现实世界的道路的预期破产。
3.舅公的结局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维护者历史命运的预示
资本主义的维护者和设计者舅公拼命用积木搭建起来一个能稳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用知识和理性来合法化现实,并且不断填充新的积木,他用抽象解释抽象,在一次又一次意识的交锋中建立起一个体系,但终究没有办法解决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只能成为虚假的空中楼阁,摇摇欲坠,走向完全的崩塌。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构建模式是无法延续的,想用完全无污染的积木搭建一个“理想国”是无法实现的,想要一个纯粹理性的脱离“恶意”的世界是不可能的,迎来的只有二元对立的历史前景。抽象的模型只能构造现实的假象,无法完成对历史真正的推动和进步作用,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改变,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断对历史进行粉饰,却无法避免历史对它审判的最终结局。
(二)鹈鹕和鹦鹉的生存境遇折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主体性丧失的困境
1.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盲目大众——鹈鹕境遇的两面性
影片中的鹈鹕的典型场景是它们蜂拥闯进金色大门,想要夺走真人身上的东西,被勇敢的雾子驱赶。鹈鹕体现日本社会下广大普通阶层无序组织和竞争的状态,他们只能通过掠夺更弱势群体来维持自身存活,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留给他们的机会少之又少,庞大的数量和稀缺的资源存在极大落差。他们的后代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失去了希望,选择了抛弃自己的劳动能力,无限期地躺平或者摧毁劳动力本身,他们正面临着后现代的困境。
然而这些为谋生不择手段的鹈鹕又有着不堪的另一面,一只濒临死亡的鹈鹕留下遗言:“我的族人被带到这个地狱般的地方,海里没有足够的鱼养活我们,我们只能吃哇啦哇啦,我们的族人快要饿死了,所以我们尽可能飞得更高,飞到我们翅膀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但结局总是一样的,我们无法逃离这个岛,新生一代的鹈鹕甚至已经忘了如何飞翔。”反映了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无奈和妥协,他们成为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牺牲品。
2.暴力统治者——鹦鹉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
与鹈鹕相对的是鹦鹉群体的耀武扬威和放纵奢靡,他们时刻拿着武器和刀叉,依靠暴力占有了社会大部分财富,在真人闯入的“异世界”掌握了真正的统治权。他们这群野心家一直在背后窥伺机会,妄图取真人和舅公而代之。在面临可能被真人破坏“异世界”的秩序时,鹦鹉统治者徒手摧毁了舅公构造的上层建筑。
资本主义解放了人的生产力,创造出无比巨大的财富量,但这些财富都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独享,他们尽情享乐,不断加大对底层的奴役和暴力。戴着草帽的“黑影人”就是它的产物,他们没有人的活力和劳动能力,只能等待施舍和救赎。可见,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奴役和剥削的历史,在巨大的上层繁华背后隐没着底层的血与泪。
3.两者展现资本主义中人的主体性丧失的困境
鹈鹕和鹦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组对照组,鹈鹕的穷困和鹦鹉的奢靡形成鲜明对比,一方对资源的所有权导致另一方分配不足的困境。但是他们也有共同之处,都是单方面地依赖某一种生存工具争夺物质利益,鹦鹉是靠武力,鹈鹕是依赖夺取底层人的资源,并且过程充斥着暴力和竞争。在显性层面,他们在物质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但他们在资本主义体系下都不是全面和自由的存在,失去了人作为主体的本质属性,没有能动和创造,只有附属和依存。
在最终的结局上,也显示了他们的存在本身充满工具属性,没有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鹈鹕在临死前道出无奈和悲楚的感慨,在那一刻感受到一个命运个体在此现状下真实的痛苦,表明他们的异化程度之突出。异化的鹦鹉穿过塔楼的门来到现实世界时,变成了正常的鹦鹉,显示了他们的武力工具在正常社会的软弱和庸常。
二、主体性在场的不同表现形式
(一)雾子的抗争与前资本主义时代“野蛮精神”的保留
雾子和真人捕鱼的图景与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的画面存在意蕴一致的倾向。《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刻意远离现代化的土壤,远离商业化模式,用双手和智慧勤恳劳作。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老人是摆脱了绝对理性的束缚的典型,他身上具备的“野蛮精神”让他的行动和认知处处折射出人性英雄主义的光辉,他用这种精神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雾子在“异世界”是一个强健的女船长,为了新生代“哇啦哇啦”重生而从事捕鱼劳动的生产活动,她会和鹈鹕斗勇,她会用武力保护真人和“哇啦哇啦”,她身上有一种真实的“野蛮精神”。“哇啦哇啦”作为成长的新生生命,期待着脱离依赖的环境成为自由人实现重生,最终在雾子的帮助下获得通往真实世界的路径。真人在她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完善了人格和获取了责任意识。
雾子对真人最初的评价是:“你的名字是真人啊,真正的人,难怪你身上的死亡气息这样重,我们这个世界里死人多过于活人呢。”正因为雾子是一个真正有主体性的人,她能感受到其他人身上的死亡气息,也就是非人的气息。她努力帮助人争取重生的自由,并且通过实质的环节夺回劳动的主体性:通过自发性的劳动和创造,寻回自身的价值。
(二)火美的死亡与后资本主义时代主体性叙事的隐匿
火美是真人的生母,给真人带来了力量,在真人遇险时数次为真人解围,并且是真人在现实世界的精神支撑,为其提供爱与人生方向。她某种程度上对真人来说意味着主体性本身。她的火是与黑恶势力斗争的武器,是标志主体性力量的存在。火美的存在让黑恶势力不敢觊觎和践踏底层的生命,她能够驱逐代表剥削势力的鹈鹕,也能够烧毁封印夏子的纸张,让真人和夏子之间的隔阂被打破。
火美发挥驱逐邪恶的力量是有代价的,这是她主体性的凸显。当火美用火焰驱散鹈鹕时,不少“哇啦哇啦”也被殃及,真人劝火美停手不要伤害“哇啦哇啦”,而雾子却告诉真人如果这些“哇啦哇啦”不牺牲,那么他们所有的同类都会被吃掉。当火美带着真人闯入产房禁地,受到了雷电的触击,又在真人解救夏子遇到封印时,火美焚烧了白纸片导致封印解除,但也导致自己晕厥被鹦鹉群体所俘。当他们要一贯保持主体性时,势必要遭到外界黑恶力量的反噬。
火美因为闯进产房禁地的行为,被鹦鹉群体拿来作为与舅公的交易手段。火美隆重的交接仪式是邪恶的统治者的狂欢,标志着主体性力量的发挥从此成为抹去的记忆隐匿在历史中,以此换来舅公的忠诚和服从,保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合法性和顺利延续。火美作为主体力量的双重命运,显示了在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中主体性叙事无法存续的命运,并且承受着污名化的对待。但这种隐匿只是暂时的,年少的火美和年轻的雾子一同进了象征过去的门,但她们的主体性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三)白纸片对夏子的攻击与主体性的存续
真人的继母夏子躺在象征着死亡之地的晦暗的死寂的坟墓中待产,这里是“黑石”的力量中心。夏子知道舅公的过去,看清了舅公道路的本质,也知道家族无法改变的命运,他们的后代注定要继承他们的遗志,于是为了保护真人选择做出牺牲自己和孩子的选择。夏子的产房是“黑石”的魔法中心,她的难产预示着在资本主义意志无人继承的难产现象。
在真人进到房间救夏子时,象征着主体性追问的白纸片涌出来封印着真人和夏子,白纸片本身是纯洁的化身,在日本文化内涵中它的意义是神圣的。所以当夏子在现实中在邪恶的力量驱使下做出妥协,要诞下继承资本主义意志的后代时,就必然会接受主体性的审判。她也面临主体性即将不在场的困境,势必要做出抉择。
真人在救夏子时白纸片阻止包围了他们,正如《千与千寻》里在白龙偷了钱婆婆的印章后纸片人封印着白龙,使失去主体性的白龙的内心和肉体受到煎熬,纸片不断追逐着他,带来的巨大能量同时吞噬着他,这是他内心向善倾向的巨大能量的具象化,他做的事越与他的本真追求相违背,纸片对他的封印力量越大。纯白的纸片是人的主体性在场的指示,是对恶的禁忌,举头三尺有神明,大抵如此。
最后是火美用火把这些白纸片烧毁,真人和火美晕过去了,通往解救夏子的那扇门也暂时关闭,新生的主体力量为此付出代价,迎来了短暂的休眠。但是这些隐匿的主体性符号最终会复生,而成为和主体统一的实在力量,完成对真人主体性的完善和救赎。到那时,象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黑色陨石覆灭,夏子会重新醒来,走向现实世界。
三、真人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
(一)苍鹭和真人的关系本质
苍鹭利用真人对生母的思念即主体性的丧失引诱真人去往异世界,真人不堪其扰,最初用暴力的手段排斥和拒绝,因为他不愿直接面对自身的这一缺失,人原本是追求和维护自身完善和希望获得完美的外在评价的。他找到了可以对治苍鹭弱点的方法,亲手制作了弓箭利用第七羽来对付苍鹭,苍鹭被真人用箭射穿喙之后,开始受制于真人,丧失了飞行能力,也丧失了对抗外界和获得自由的工具。真人用聪明技巧控制了苍鹭,这是真人主体性的第一次发挥。
苍鹭是揭露真人内心真实的声音,它是真人主体性的表达,真人不能离开苍鹭,正是苍鹭表达的真实声音,他发现自身主体性缺乏导致和外界世界的矛盾时,促使他不断探寻真相,从而实现矛盾的解决。苍鹭的出现让真人意识到自身主体性的缺乏,意味着真人将要面向外部世界寻求答案,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所以守护他的老年雾子才会跟他说这是一个陷阱,不要听信苍鹭的谎言。但是真人的主体本能义无反顾地驱使他去寻找答案。
苍鹭的喙需要真人补全,真人只有亲手给他配备木头,才能让他重新获得完整,说明他是真人的一体两面。在真人主体性不在场时,苍鹭最开始对真人说“我可不是你的朋友或伙伴”,和真人之间以冲突居多。苍鹭在见到真人埋葬鹈鹕之后,真人表达的善意让他再次感受到他的主体性,不再站在真人的对立面。这是真人主体性在场的又一次显现,也是真人的主体性逐渐强化的体现。
苍鹭在异世界显现出人形,然而外壳是鸟类,他表面用这套外壳适应异世界的生存模式,苍鹭在面对真人质疑是不是他拐走了夏子阿姨时说,“欺骗是为了我们生存的智慧”“所有苍鹭都是大骗子”,但是内在仍维持人类的本质。所以他的主体性是在场的,苍鹭的恶意和欺骗只是针对丧失主体性的人有用,苍鹭本身就是主体性在场的呼唤者。对于真人来说,寻找主体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所以他无法回避苍鹭的存在并且不堪其扰。
真人在苍鹭的引导下不断探寻异世界的过程,也是他不断寻找主体性的过程。后面苍鹭勇敢地救出真人逃离鹦鹉的控制,说明真人在种种经历中主体力量逐渐强大,内外也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完成了对自己的接纳。在从“异世界”出来后,苍鹭选择忘记历史,因为这时真人已经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所以苍鹭才可以释然地说忘掉过去。
(二)真人主体性追问的历程
真人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母亲的死亡,父亲再娶,以及与继母夏子和新同学关系的隔阂后,为了寻找失踪的夏子,在苍鹭的诱导下闯入了导致外公失踪的“异世界”。此后,真人与苍鹭、雾子、夏子、火美和鹦鹉王国的相遇过程中重新塑造了自我,最终直面个体创伤回到自己的现实世界。
首先,真人最初的主体性来自他的生母,当生母因为火灾去世后,他的主体性是无法安放的,他在父亲和继母那里无法找到,所以他只能通过自残的方式表达他的缺失。继母也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感到为难,并且因为无力改变而只能通过剥夺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来赎罪,所以她的结果是难产。而父亲其实是无感的,只能通过物质补偿和转移物理伤害来为真人讨回公道,因为父亲也面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性不在场的处境。
真人在潜意识里意识到继母为维护他的主体性而剥夺了自身,他去往“异世界”寻找。在去之前他是主体性缺乏的状态,苍鹭是让他意识到主体性缺乏的元凶。当他最初意识到的时候,反应是反抗,他害怕打破原有的生存模式,因为指出他的缺乏同时也是对他的剥夺和攻击,他首先想到的是制作武器用武力打败苍鹭。他也学会了父亲的生存法则。
在被引诱到“异世界”寻找夏子之后,他的主体性慢慢显现。在雾子身上,真人发现可以运用自己的勇气和劳动能力获得人的主体性;在拯救夏子的过程中,真人认识到夏子为维护自己主体性付出的代价,看清了鹦鹉王国的本质,从而在心底认可了夏子;在与生母火美的相遇中,火美在真人即将被鹦鹉吃掉时拯救了他,把真人寄托在她身上的主体归还给真人;在和苍鹭的互动中,通过一次次互动和矛盾解决改变了对苍鹭的敌视态度,真诚地帮助苍鹭修补缺口,坚守住自身的善意;在回到现实世界后,真人选择捏紧手里的积木,攥紧了证明其主体性在场的记忆。
(三)宫崎骏作品的主体性追问沿袭
本文前面讲述了《千与千寻》中白龙和千寻追寻主体性的隐喻,在宫崎骏的其他作品中也有这类主题和形式的表达,比如《哈尔的移动城堡》中,苏菲在发挥主体性时,会从老年的面容变回年轻的面容,在《魔女宅急便》中,琪琪看到人性的灰暗面而找不到工作的意义时,失去了飞的技能,也意味着主体性的短暂消失。可见主体性是宫崎骏一直致力于探寻的主题,主体性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宫崎骏的作品中,或者是姓名,或者是劳动技能,或者是容貌。
宫崎骏曾在《宫崎骏论:众神与孩子们的物语》一书中提及,他想借由动画捍卫孩童的率真与豁达,免于被成人世界迷惑而失去纯性:“我想做出可以对孩子说‘不要被父母吃掉啰’这样的作品,献给世人。”孩童主体性的发挥在成人世界规则下受到很大规制,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下的人们来说,人人都是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下有可能被压制主体性的孩童,宫崎骏通过动漫情节的构建来达到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目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主体性被定义为“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互相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宫崎骏电影中的意象的主体性表达对理解这一表述有诸多启示,他塑造的人物经历有直达人的本质直观的倾向,也给观众带来巨大的震撼力。观众在观摩他者寻求主体性的同时,也发出了对自身主体性的追问,这正是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3]邓雪征.现代性语境下的主体性与自由——从黑格尔到马克思[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3,(02):79-87+348.
[4]王肖帆.资本主体性的成因及其消解——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8(01):163-168.
[5]杨晓林.宫崎骏动画之历史观探赜[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05):57-67.
[6]卢刚.隐喻与批判:《千与千寻》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J].求索,2023,(02):27-37.
[7]龚志文,刘太刚.论主体性的维度及成长进路[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02):39-44.
[8]朱耀平.自我、身体与他者——胡塞尔“第五沉思”中的交互主体性理论[J].南京社会科学,2014,(08):63.
[9]侯衍社,苏红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建构[J].山东社会科学,2024,(2):34.
[10]黄楠森.论人的活动的主体性[J].阵地,1991,(6): 19.
作者简介:
傅赞,女,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