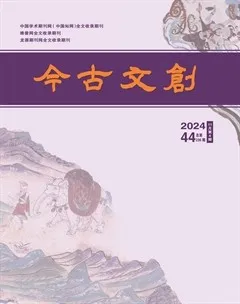清代清水江流域苗 、 侗族夫妻之道
【摘要】清水江流域的家庭是基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的核心家庭,夫妻相处和谐是家庭关系和睦的基础,在所有家庭成员的相处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黎平文书承载的家庭大多数为苗族与侗族,文书中多涉及苗、侗族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为我们窥探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夫妻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清水江流域在历史上作为“化外之地”,苗、侗族有着自身的一套习惯法则,其夫妻之间相对开放与平等,不同于中原地区被礼法束缚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其夫妻之道的特征表现为:一是琴瑟和鸣,二是妇齐于夫,三是夫妻一体。其形成原因在苗、侗民族对于和谐的追求、社会内部平衡的维系以及母系社会时期遗留习俗的影响。清代清水江流域夫妻之间所保留的相对平等的关系,凸显了清王朝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机保留了苗、侗民族自身的色彩。
【关键词】清水江流域;夫妻;黎平文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4-007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4.019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婚姻关系逐步发展为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在婚姻之中夫妻关系的和谐同家庭、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在清水江流域世代生活的苗、侗族亦是如此,而其婚姻观念又独具特色。众多学者注意到这片土地上婚姻文化的独特性,在历史学的基础之上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知识对其进行探讨。如吴才茂的《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一书中对苗族社会的婚恋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析[1];李向玉的《黔东南苗族婚姻家庭习惯法与国家法》梳理了黔东南地区婚恋习惯法[2];马静、纳日碧力戈在《清水江流域苗族开亲规则考》一文中分析了苗族社会婚姻缔结的内在规则等等。[3]
本文以李斌主编的《黎平文书》为基本史料,聚焦婚姻当事人,即婚姻的男女双方从相知相恋、婚姻日常、离异到再婚这一系列过程中,探寻对清代清水江流域苗、侗族夫妻的相处之道,分析对清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家庭之中的平等夫妻关系之成因,力图展现清代清水江少数民族夫妻的日常生活。
一、琴瑟和鸣
《诗经·小雅·常棣》中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对内心情感的满足是婚姻家庭和谐的关键所在,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更是意识到这一点。有清一代,随着“王化”的不断加深,“姑舅婚”的减少,以及大量的同姓不婚的规定颁布,夫妻之间有血缘关系的概率降低,情感的培养则变得更加重要。苗、侗族社会当中,男女到了适婚年龄时都会组织活动,从“行歌坐月”“玩山”“跳月”的以歌相识,到“爬窗孔”的表述衷肠,再到“坐仓楼”的互诉情谊,苗、侗族男女在这些传统恋爱活动中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只有夫妻双方两相情愿、互敬互爱,不论家庭关系的和睦,还是日常劳作的协调才能实现。侗族地区流传的《十二月份歌》中体现了未婚男女在一年的恋爱中共同劳作直至结婚:“年初正月,情妹和夫耕旱地。二月,情妹和夫耕备耙绳……四月采秧青,他人命好,有你情妹伴山头……十二月春节至,他人命好,将你接至家中称妻。”[4]在未成婚之前若任意一方改变心意,只要双方达成共识,在取得经济上的补偿之后便可解除婚约,如文书例1《石昌荣、石昌植兄弟二人典田字》载:
立典田字人石昌容、昌植兄弟二人为因二妹名唤妹喜,于先年凭媒许配本寨石文用之长子名号德政为妻,岂知二妹心不愿去,将土名奠岭兰路头田乙间,在禾拾弍把出典与石文用名下得典为业,当日凭中议定为典价银弍拾肆两整,其田自典之后,恁从银主耕种管业不□远近照价赎回,二比不得异言,立此典字为据。
凭中 石钟英 宗达 文仕 朝忠
代笔 石山阑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5]
这份文书中明确表示了妹喜已经凭媒许配给石德政为妻,但是妹喜心有不愿,于是妹喜的哥哥们将田业典与男方作为赔偿。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女性对自己的婚姻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选择权的,即使已经凭媒聘定,只要女子心有不愿也不会强行结婚,这体现出对女性自身意愿的尊重。在婚后情感破裂时,对于无子的夫妻而言,婚姻关系的解除也相对简单,如文书例2《吴国安清白字》载:
立清白吴国安为先年与风维配合,不幸至于己丑,二比男女皆有另嫁另聚(娶),女往吴家珍之子为妻,男娶抵□之女为妻,二比自愿延至今年约同寨老大家以酒席各配聚(娶),中等并不得固为,自今以後二比大家发达,男不得多言与女,也不得异言与男,恐后滋事固立清白承照。
凭中 吴楚朝 □□ □□ 绍武 林春茂 春美
依中人叔伯 代笔 吴晏堂
光绪十二年三月吉日立[6]
在这份清白字当中吴国安与风维原为夫妻,后夫妻缘尽解除了婚姻关系,其后各有婚配,两人约定在同一天宴请寨老以及寨中众人,这既是两人各自婚嫁的酒席,同时也是二人关系的断绝宴,表明二人自此之后就是两家人了。这份文书也展现了时人对待不幸婚姻的豁达之态。
一般在退婚文书中会明确说明退婚原因,如文书例3《薛老五退婚字》载:
立退婚字人薛老五因为先年与丁姓为妻,推知命运不辰,夫□亡故,次又嫁吾为妾,业已过门三载,没无生长,只内禄合,不岁夫妻反目,琴瑟不调,难言偕携老,料难终身,居宝自己,经中于亲戚于中退悔娘家,男另娶,女而退转归宁,彼□平悦腹愿,并非厌等,情□中人亲族退婚,理管了局,是以经中折悔,自愿情息理屈,日后不得蹈故辙翻悔之事,今出字樣一紙為憑。[7](下略)
与《吴国安清白字》不同,这份文书当中明确了退婚的原因是“没无生长,只内禄合,不岁夫妻反目,琴瑟不调”,也就是说二人成婚三载,并无子嗣,家庭经济问题中尚能达成共识,但是没过多久就产生矛盾,二人情感出现问题,因此不能再相伴白头。虽是“嫁与吾为妾”,但是与中原的妻妾家族社会地位、财产状况存在差异不同,清水江流域的妾和妻同样来自通婚圈内的家族,为了保持家族地位的平等,妻妾在家庭中身份地位也需要相当[8],因而在此可将其中的妾等同于妻看待。
这三份文书共同表明,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对于婚姻之中二人的情感基础的看重。夫妻二人担负着繁衍后代的家族大任,在生育后代之后二人之间拥有了血缘的羁绊,夫妻感情退居后位,但是情感基础依然作为婚姻的基调,如出现琴瑟不调、调解无果的情况,最终只有以解除姻缘结束收场,各自再寻良缘,以免再生事端,正如苗族离婚理词中所言:“冷饭捏不成,剩饭团不成。生捆不成夫妻,索绑不成伴侣”[9],对于已生嫌隙的夫妻不能强行继续婚姻。
二、妇齐于夫
《说文解字》中对已婚妇女的阐释为:“妇,言服也,服事于夫也 。”而在苗地并非完全如此,习惯上称男女婚配为“娶当家”,表明妻子与丈夫对于家中事宜共有话语权,而女性也并不被束缚于宅院之中。“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模式并不强调男性在其中是主导作用。清水江流域的男女在婚姻之中的经济分工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从两性各自相对擅长的领域出发,男子主要从事重体力的耕作劳动,女子负责包括织作、染布等家务制作劳动,农忙时节女子同样要参与农作,闲暇时节男女同样会去渔猎贴补家用。在家庭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当中都有已婚女性参与的身影,例如:
立断卖杉木字约人杨通见之妻名唤奶引花为因家下并无粮食无处所出……[10]34;立卖断棉花地字人周母奶富隆为因缺少银用无出……[10]89;立断卖塘曰人石氏奶贤、辛奶玉珍为因缺少帐务无甚偿还……[11]102;……自愿将土名归你者领(岭)扒杉木小团共有十二股,均分出卖一股与石秀芝名下……[11]153
这些文书当中对于女性的称呼明显是当地少数民族对已婚女性的称呼,这些女性广泛参与到了包括山木、棉花地、池塘等产业的买卖之中,可见婚姻中的女性掌握着家庭中的财产买卖权,清水江流域的已婚女性不仅仅是拘泥于家庭事务当中,更是拥有经济上一定的自由和处置财产的权力,她们生活的重心也并非只是家务,更是周旋于社会。这同样也得益于这一地区在经济上对女性有着较高的宽容度,父母也会给予女儿一定的产业,如文书例4《石明旺送字》载:
立送字人父石明旺,因生二女在家傭工苦力,我惟父土名景帅杉木一块係作二股,出送一股,又送土名乐杖田一坵,禾四把,杉木田坵送与亲女庚秀、庚连子妹二人名下。承蒙我父送业,惟女子孙耕种管业,石庚午、石月祥日后不得翻悔退回之事,一送百了,父送子休,慿有亲族立送一纸舆二女收存,子孙存照。
外有弄团山杉木,先年石照开所栽之木,子妹庚秀、庚连、秀芝三人名下共得栽股一半。
凭有 石相魁 化鹤 大科 成锦
石辉明笔
道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立
咸丰元年三月初十日,子妹二人将杉木卖月裕、禄兄弟二人,买转蓄禁归回,日后二比结送字清白存照,父批是实。[11]185
从这份文书中“在家傭工苦力”可以看出石庚秀、石庚连姐妹二人并未出嫁,且外出佣工劳作,表明本地女子不同于拘束于闺阁之中的汉女,她们也需要参与到社会劳动之中,与男子同样承担家中经济。在家中还有其他孩子的情况之下,父亲石民旺就已经立下送字将一部分产业赠予姐妹二人。石庚秀、石庚连作为两个闺中女子,已经属于有了自己的一份产业,后来二人将杉木卖与他人,表明对此拥有绝对权利。再如文书5:
立乘生字人石通义……诚恐一旦辞世,所遗一女唤春喜年幼,异日出室无有付送,乘我尚生,当凭亲族将土名……一共二处立字交予女子手执,以为日后出室培嫁资……[12]412
在这份文书当中,父亲在自己弥留之际就已经为女儿的日后生计和陪嫁做好打算。清水江流域的父母会依据自身情况给予未出嫁的女子一定产业,加之该地区本身就有着“姑娘田”和陪嫁彩礼归女方独自处置的传统,女性拥有经济基础并且能够与丈夫承担同等的家庭经济责任,夫妻关系由此达到“妻者齐也,与夫齐醴”[13]1611。
三、夫妻一体
在现代意义上对夫妻一体的理解为婚后夫妻双方的人格相互吸收,然而中国古代中原社会中,婚后女子的人格往往是被丈夫所吸收,成为其丈夫的附属,女性地位低于男性。而在清水江流域,文书中不乏存在夫妻共同成为契约人的情况,表明二人在婚姻家庭之中的地位相持,如文书例6:“立典字人石怀基,为因缺少账务无从得出,夫妻二人媇平议愿,将土名隥排田乙坵,在禾三把,今典与……”[14]91又如文书例7:“立断卖田约人下皮林吴登凤为因家寒夫妻二人商议,而夫曰卖,而妇亦此言,合而自愿请中问到兵洞石成虎家,亦贫寒,无有可奈,夫妇二人亦欲所议存卖为业……”[15]立契人虽然是男性,但是在其中明确表明了“夫妻二人媇平议愿”“夫妻二人商议”,因此对家中田产的出卖是夫妻二人共同商议的结果,妻子在家产的处理当中与夫共有话语权。
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当中对于女性的称呼并不强冠夫姓,这与其姓氏的来源的独特性以及传统亲属称谓有关。在黎平文书常见的对女性称谓如“杨氏乃兰花[10]5、石氏奶照姜[5]125、石氏乃盛华[5]168”这类名字是侗族典型的对已婚已育的妇女的称呼,即长子或长女的大名或者奶名前面加上表示母亲的奶(乃),比如:石氏奶照姜意为石照姜的妈妈。在侗语中这类称呼代表着对他人有孩子之后辈分上升的敬重,同样对已婚已育的男性也是如此,比如文书中出现的“石补洪寿[12]12、石补龙发[12]43、石补孟琏[12]28”这类名称中“补”的含义就是父亲,石补洪寿意为石洪寿的爸爸。这是侗族社会原始时期父母子女连名制的余迹,表明了对他人辈分上升的尊重,同样也是侗族社会中对一个家庭整体性的认同——以子女为纽带,深化夫妻之间的一体性。
四、平等夫妻关系的成因
清水江流域的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尽管改土归流之后,中原汉文化渗透至该地区,当地的少数民族人民依然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其中就包括了婚姻观念。在苗、侗、瑶等本地民族的婚姻家庭形式在普纳路亚婚向对偶家庭发展的过程中,依旧保留了大量的普纳路亚婚的痕迹。作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一夫一妻的对偶婚对女性的束缚更强——女性在家中和于父母亲人,贤于家庭事务,理于家中的日常经济开支管理。在苗、侗社会当中的婚姻也不外乎如此,妻要生育后代、孝顺长辈、料理家务,然而相较于中原社会的婚姻观念更加于偏重于男方,将女性置于附属地位,在清水江流域的传统社会当中对于男女双方的情感需求、家庭责任与义务、经济等分配得更为均衡,因而在婚姻关系之中更易达到和谐,这种情况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一)自然因素的造就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强调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自然中追求人的发展,因而二者的关系是平静相安的。《说文解字》中“和”一字原作“咊”,意为相应也。[16]《尚书》有言:“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7]《国语·郑语》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8]可见中国古代先民在差异中寻求统一以达到和谐,这种和谐并不是一味要求不同的事物之间某一方一味迁就另一方从而促进其发展,而是不同的双方相和共生。自古以来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就生活在重山险要的自然环境之中,苗、侗族人民在这种自然环境中耕作劳动、绵延百年,在人与自然的“和”之中诞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并且产生了“生成相资双有利,相制牵擎得平衡。相征我求彼有应,相夺我好彼有损失”[19]这样一种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平衡的伦理思想。重山之中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保留了较多原始古朴的群体本位文化下的“平等—平等”文化结构,即人格上的平等、经济上也平等的文化结构。[20]这种平等的文化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还表现于人与人——男女之间、村寨之间、族群之间,并且在夫妻关系之中表现出来。
(二)婚姻圈内平衡的维系
《尔雅·释亲》:“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婚姻。”[16]2593所以“婚姻”二字的本意就是两个家庭之间缔结关系的合称,婚姻代表着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合,夫妻双方同时也代表了两个家族。联姻的两个家族之间如果出现差距那么就意味着一个家族对另一个家族的索取,打破了社会之中所讲求的平衡,所以通婚的两个家族要尽可能的实力相当,因而婚姻中的男女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平等。加之作为母系氏族代表的舅权在清水江流域颇有影响力,承担着既要维护“母权”的存继,本身又是男权的助推力,就会帮助女方家族在婚姻中争取更多的权益。
(三)母系社会习俗的遗存
相较于汉人家族组织男为内、女为外的区分,以清晰的结构切割财产,侗族人民的财产是以女性、婚姻和延续后代这一社会再生产为基础的[21],女性在婚姻家庭的财产中有着承载性,这种特性让女性在婚姻有了更大的保障。最为典型的就是“姑娘田”和陪嫁产业,这使得嫁女儿就意味着要进行财产的分割,女性在娘家有着财产的继承权。
文书例8: “立转退姑田字人华官寨石现梅,为因先年□胞兄现瑀议聚(娶)罗闪杨氏□□□母为婚,当陪嫁□地名己得田一坵,约禾艺把,今胞兄□□俱故,将此田□□还□侄承杰管业,日后不得异言……光绪四年十一月廿五日立”[22]36。
文书例9: “立断卖田字约人罗闪寨杨承杰,为因先年姑母嫁与华官寨石现瑀为妇,当培嫁之田土名己得,今姑母去世,将培(陪)嫁之田仍然退转。今本名缺少银用费无□得出,自愿将己得田乙坵,栽禾壹拾捌把,自己请中登门问到,出断卖与华官寨石公照名下……光绪伍年正月弍拾伍日立契。”[22]37
综合这两份字契,“姑娘田”在杨氏出嫁之时作为杨氏的私产陪嫁,杨氏死后夫家退还“姑娘田”于娘家,并由其娘家侄子杨承杰直接继承,之后杨家将这份产业变卖给了石公照。“姑娘田”从始至终都与夫家无关,姑娘在时由姑娘营管且可以自行卖出,作为其经济来源之一,姑娘死后“姑娘田”产权转归娘家,实际上“姑娘田”不仅是婚姻中女性经济的保障,还维系着女性与娘家的联系,使女性在夫家不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在从江县占里村,至今保留着女儿继承棉花地,儿子继承稻田的习俗,同时在女儿出嫁也要陪嫁“姑娘田”,在老人的财产继承上,山林、菜园实行男女对半分成,房基、家畜归儿子,而金银首饰、布匹让女儿带到夫家。“不落夫家”即婚后女方依然住在娘家,称为“坐家”,此后三年间只有节庆和农忙才会回到夫家,这一习俗是原始社会“从妻居”的妥协性保留。这些习俗实际上就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过程中,母权对父权抗争的结果。
五、结语
中国古代夫妻相处之道表现于国家法、习惯法、意识形态当中,这些抽象化的观念在文书当中以具象化的形式再现于当下。清水江流域苗、侗族夫妻之间的相处之中重视双方的情感需求,女性在经济上拥有的权利使其在家庭地位上同于夫,由生育形成的血亲关系将两人延伸于一体。出于对自然的敬畏,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人民在繁衍生息中生成“和”之观念贯穿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因而在文书之中表现出了夫妻关系的相对平等,这种平等的关系是对千百年母系社会的追溯,同样也是对当时社会稳定的维护。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男、女之间由于生理上的各种差距,其在社会分工、家庭劳作之中的扮演的角色不同,随着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女性逐渐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在清代清水江少数民族社会中,夫妻之间还能保有相对平等的关系。尽管这种相对平等关系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条件的,但它反映了清王朝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机保留了民族自身的色彩。换言之,清水江流域的苗、侗民族面对汉文化同样能够以其强大的包容性与其融合共生,共同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多元。
参考文献:
[1]吴才茂.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
[2]李向玉.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3]马静,纳日碧力戈.清水江流域苗族开亲规则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04).
[4]姚丽娟,石开忠.侗族地区的社会变迁[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5:239.
[5]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九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237.
[6]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四十八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9:164.
[7]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四十五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9:5.
[8]雷昕.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苗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2:133.
[9]石朝江,石莉.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182.
[10]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二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
[11]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三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
[12]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六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
[13]阮元等.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七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
[15]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五十一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20:276.
[16]许慎.说文解字[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22.
[17]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219.
[18]徐元诰.国语解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470.
[19]雷安平.苗族生成哲学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1993.
[20]易小明.民族伦理文化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2013:244.
[21]王彦芸.都柳江流域“兜”的概念与侗人的亲属观念[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3,15(01).
[22]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十三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