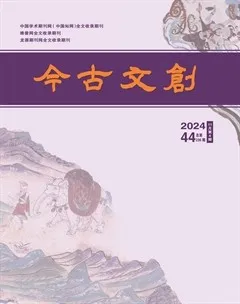《诗经》中“ 桑 ” 意象的解读及其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
【摘要】本文集中选取了《诗经》中与“桑”意象有关的篇目,根据诗章的题材、内容对其中“桑”意象的寓意进行分类解读,并简要探讨了此类寓意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沿袭与演变。
【关键词】《诗经》;“桑”意象;《小雅·小弁》;《卫风·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4-004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4.011
在《诗经》中涉及的诸多自然意象中,“桑”算得上是较为常见的一个。“国风”中有《鄘风·桑中》《卫风·氓》《魏风·汾沮洳》《魏风·十亩之间》《豳风·七月》等篇,“小雅”中亦有《小弁》《隰桑》等篇。这些主题不同、风格各异的诗篇,赋予了“桑”丰富多彩的意蕴。
一、“桑”与故乡情结
《小雅·小弁》中有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后世流传中代指“故乡”的“桑梓”一词,正发源于此。
在“该诗作者为谁”一事上,众多前人学者各执一词,观点不一。但在“该诗主旨为何”的问题上,各家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该诗表现了一个遭到父母抛弃之人内心的彷徨与苦痛。该节开头以“桑”“梓”起兴,根据朱熹所著的《诗集传》中的说法,古时桑树、梓树这两种树木,多是父母亲手种植在家宅、庭院之中,其用意在于造福后世,为子孙提供养蚕缫丝、制作器具的生活便利。主人公看见桑树与梓树而萌生恭敬之意,引出其对父母的尊敬与依恋之情,进而迸发出其处在被至亲放逐的境遇、内心极度压抑下的泣血控诉,情感上层层递进,恳切动人。至此,“桑”与“梓”自然而然地与“对父母的感怀”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因为“桑”与“梓”多植于家宅之前,使得这一词语除“思念父母”外,更多一层“思家”的含义。
在后世的流传演变中,“桑梓”逐渐成了一种固定的合称。其所代表的“思念”对象,也在父母、家园的基础上进一步泛化。东汉时期张衡所著的《南都赋》中,已有句曰:“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这也表现出,这个时期“桑梓”一词的寓意,已经完成了从原始的“父母之思”“家园之思”到“故乡之思”的最终定型。
《南都赋》中的南都,指的就是东汉时期的南阳郡。作为张衡以及汉光武帝刘秀共同的故乡,南阳郡的山光水色、丰饶物产、民风习俗,其承载的悠久的历史文化,都在此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字里行间,寄寓着作者张衡对于故乡人情风物的自豪与赞美,饱含着深深的怀恋,显现出一种独特的、亲切动人的感染力。可以说,让《南都赋》这篇作品得以达成“宏大而不显空洞、丰富而不显累赘”的艺术效果,从其他诸多堆砌词句、华而不实的赋作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就是这种“怀恋桑梓”的乡土之情。
东汉末年,女诗人蔡琰以才学著称。她生逢乱世,在战祸中为匈奴所掳,滞留在胡地,心怀故乡却不得返还,徒留一腔悲愤。其名作《胡笳十八拍》中,有“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二句,深切地表达了其对故土生死不移的眷恋与思念。魏晋时期,有“太康之英”美誉的陆机,在诗作中留有诸如“眷言怀桑梓”“辞官致禄归桑梓”一类的诗句,尽述其异乡异客之悲、宦海沉浮的倦怠,以及想要归乡以终老的愿望。与其并称“二陆”的其弟陆云,也在《答张士然诗》中留有“感念桑梓域”的怀乡之句。
唐宋诗人的作品当中,同样不乏“桑梓”的踪迹。唐初诗人王绩《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一诗中,有“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二句,展现了隋末离乱带给民众的苦难,表达了作者对家乡不幸遭劫、只剩一片断壁残垣的惋惜、苦痛之情。柳宗元《闻黄鹂》一诗中,有“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以黄鹂之鸣触发思乡之情。李德裕则在《早春至言禅公法堂忆平泉别业》一诗中,描绘了故乡清新静美的山水景色,尾二句“永怀桑梓邑,衰老若为还”直抒胸臆,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切怀恋。此外,还有宋代诗人曾巩《之南丰道上寄介甫》一诗中的“跋履虽云倦,桑梓得暂还”,以及刘敞《答徐无逸秀才寄示新文》一诗中的“归来守桑梓,寂寞安故庐”等等。
时至清代,在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张乡绅在造访刚刚中举的范进时,曾以“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作为开场的寒暄之辞,试图通过这一层“同乡”的关系来攀扯交情。毛泽东的《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中,也用“桑梓”代指故乡,却一改以往诸多包含“桑梓”的诗歌中怀恋家乡、不舍离去、念念不忘的写法。在宣告过自己决意离乡求学的决心后,诗人放出豪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一派洒脱豁达,展现了其非凡的胸襟和气魄。
除了能与“梓”合称为“桑梓”、代指具体的家园、故乡之地外,“桑”本身也作为农耕生活中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常与田园、隐逸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而演变成一种精神家园、精神故乡的象征;这种现象,不仅与“桑”在古代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劳作中所发挥的“养蚕纺织”的重要用途有关,也显现出后世文学作品对以“桑”为“家园、故乡”象征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中,尤以东晋陶渊明、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与孟浩然三人的作品最为经典。
陶渊明其人,是山水田园诗派之祖,也是后世诸多心怀隐逸之意的诗人争相效仿的名士。其在名作《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一诗中,就明确表露出不耐尘俗喧嚣、厌倦争名逐利之意,也抒发了己身对田园生活的喜爱与向往。诗中有“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一句,以极其平淡的笔调,描绘出淳朴恬静的农家生活画面。而此诗句中的“桑”之意象所寄寓的,正是诗人对自然的亲近,对返璞归真、自在美好的精神之乡的探寻。不仅如此,陶渊明《桃花源记》一篇中所塑造的、被无数文人奉为“理想乐土”的世外桃源之地,在文中也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描述,“桑”同样是作为一个与象征高尚气节的“竹”相并列的、重要的意象而存在的。而唐代的“王孟”,作为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二人的作品中同样不乏包含“桑”意象、描绘田园生活图景的诗句,如王维《渭川田家》一诗中的“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和《田家》一诗中的“饷田桑下憩,旁舍草中归”,又如柳宗元《过故人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可以说,这些诗句中“桑”意象的存在,展现的不只是王、孟二人对陶渊明描写田园农耕生活的艺术旨趣的继承,更是他们对陶渊明回归本真、追寻精神家园的思想追求的继承。
自先秦至今,“桑”意象的寓意历经几番演变,从最初的“思亲”,演化为“思家”“思乡”;又从现实中的家园、故乡之地,演变为精神家园、精神故乡。这一发源自《诗经》的文学传统,在后世历朝历代的文人笔墨中得以被承袭、被延续,可谓是“其源也远,其流也长”。
二、“桑”与男女情爱
作为与先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植物,“桑”因其叶生长快、其果实多子的特征,在远古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人口不足的现实状况下,顺势成了一种生命力、生殖力的象征。根据《吕氏春秋》中《古乐》篇的记录,黄帝之孙、被列为“五帝”之一的颛顼,就“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吕氏春秋·本味》一篇又记载,“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这个生于空桑之中的婴儿,就是后来商代著名的宰相伊尹。此外,《吕氏春秋》中《顺民》一篇,还记述了商代开国君王成汤在位期间,天逢大旱,于是亲身前往桑林祈祷之事。可见在“殷人尊神”的背景之下,“桑”作为寓意生殖力、生命力的文化符号,已经被尊为“灵物”,被赋予了神性的色彩。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殷商王朝虽然覆灭,但对“桑”的“生命崇拜”意识却在庸、卫等地得以留存和延续。而在《诗经》当中,将“以‘桑’寓意‘男女情爱’”这一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两首诗篇,当属《鄘风》中的《桑中》一篇,与《卫风》中的《氓》。
《鄘风·桑中》一篇,是以一名男子的口吻写就的;该诗每小节末尾重复咏唱的“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三句,正是在回忆他自己与一位美丽女子相约欢会、而后依依惜别的缱绻情景。末三句所描述的这种男欢女爱、大胆奔放的作风,也使得该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后世维护封建道统的卫道士的抨击,指斥其为“伤风败俗”的“淫诗”。但事实上,根据《周礼·地官·媒氏》中的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这一礼制的存在,正说明了在当时人丁稀少、鼓励生育的社会状况下,男女欢会的行为实际上是受到相当程度的宽容甚至鼓励的。根据学者郭沫若在其著作《甲骨文字研究》中的解读,“桑中”意为桑林所在之地,“上宫”即祀桑之祠,是诗篇中男女主人公的欢会之地。根据前代以“桑”为“生命”象征的历史传统,在桑林进行的祭祀活动,自然也就也有了祈祷作物丰收与人丁兴旺的双重意味,桑林则成了男女欢会的固定场所。在这样的历史渊源之下,“桑”与男欢女爱、男女情爱之间的联系,也就变得易于理解了。
《卫风·氓》一诗中运用“比兴”手法,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写到“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叶的枯荣变化所见证的不仅是时间的流逝、女子容颜的衰败,更是诗中女主人公的爱情从浓烈到淡漠乃至最终消亡的过程。
成婚前的女主人公对心上人情谊真挚、百般牵挂,会因为没能看到心上人的身影就“泣涕涟涟”,也会因为心上人现身而瞬间转悲为喜,“载笑载言”。然而在成婚后,女主人公并没有收获幸福,反而是多年以来一直过着贫困辛劳的生活,丈夫“贰其行”“二三其德”的前后不一、心意不定让她倍感痛苦,丈夫逐渐变得粗暴的态度更让她寒心。最终,女主人公遭到了丈夫的抛弃,彻底断绝与他的情分,心中只余下“及尔偕老,老使我怨”的悔恨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心灰意冷。有感于自身见弃的悲剧,女主人公怀着一腔怨愤,对着天下女子大声道出“无与士耽”的劝诫。斑鸠如果贪食桑葚的甜美就会昏头昏脑,正如女子一旦沉湎于爱情就会泥足深陷;男子沉迷爱情尚且可以脱身,而女子倘若沉迷爱情,一旦遇人不淑,就会误了终身。该诗正是在以“桑葚”甜味比喻爱情初期的甜蜜、以“桑”之枯荣比喻感情浓淡变化,生动而形象地写出了女子婚后感情上遭受巨大变故、回首往事唯余万般心酸的苦涩心情。
《诗经》中将“桑”与“男女情爱”联系在一起的诗篇,除《桑中》《氓》之外,还有《小雅》中的《白华》《隰桑》等篇。
《小雅·白华》一篇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与《氓》中的女子处境相仿的弃妇。诗中有云,“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维彼硕人,实劳我心”。如果以“桑”为昔日爱情的象征,那么伐桑烧火的举动,似乎也是在暗示爱情的消亡。虽然女子心中满怀被抛弃的委屈与怨恨,但对于负心的男子仍以“硕人”这一美称称之,可见对其余情未尽。桑在火中被燃烧炙烤,一如女子还因心中的爱意而饱受煎熬。
《小雅·隰桑》一诗分为四小章,第一章开篇用“隰桑有阿,其叶有难”一句,描绘桑树的枝叶繁茂、婀娜多姿,因“桑”起兴,引出下句的“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表达与心上人见面时的喜悦与快乐。之后的两小章,开篇分别为“隰桑有阿,其叶有沃”“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沿用了和第一章相似的句式,重章叠句、反复吟唱,愈显情意绵长。在此篇中,“桑”作为情感的触发物,同样与男女爱情有着莫大的联系。
在后世的诗歌当中,同样存在着将“桑”与“男女情爱”相关联的诗篇。如唐代诗人李白的《春思》中“燕草碧如丝,秦桑低绿枝”一句,就是以思妇的口吻,借碧草、绿桑两种意象寄托对远在边地的征夫的思念之情,引出下文的“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唐代诗人张仲素有一首《春闺思》,“袅袅河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这首诗也是站在思妇的视角,以“柳”“桑”承载思妇魂牵梦萦、盼君归来的殷切希望,婉转词句间自有一番深情。由此可见,以“桑”寄寓“男女情爱”的做法得到了后世的承袭。唐代李商隐《无题》诗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以春蚕吐丝不绝,来比喻思念之情的绵绵不绝;而蚕以桑叶为食,二者关系由来紧密,故而从后世诗歌中广泛存在的这种寓“思”于“丝”的现象中,也能隐约窥见几分其自“‘桑’与‘男女情爱’间的联系”转化而来的渊源。
三、“桑”与采桑女形象
在古代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分工方式下,养蚕、取丝、织布被视为女子的分内之事。又由于桑叶是蚕的主要食物,“桑”与“采桑”这项活动就自然而然地与女子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就有这样一段描绘采桑女子们的文字,“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可见在当时,“采桑”就已经成为女子们的一项群体活动。《诗经》当中涉及采桑女形象描写的诗篇,较为典型的就有《魏风·十亩之间》《魏风·汾沮洳》《豳风·七月》三篇。
《魏风·十亩之间》中“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两句,描绘了采桑女子们结束一天的劳作后呼朋引伴归家去时那种悠闲、快乐的情状。《魏风·汾沮洳》一诗中,则是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一句起兴,表达采桑女子对心爱男子的悦慕。对于自己的心上人,女子不吝赞美之词,称其“美无度”“美如英”“美如玉”。可以想见,“彼其之子”应当是气度高华、仪表堂堂的。男子资质优秀,采桑女在看待这位意中人时又别具一分发自内心的厚爱,自然而然地,在采桑女眼中,男子愈发显得卓尔不群,也即诗中所说的“殊异乎公路”“殊异乎公行”“殊异乎公族”。
比之《十亩之间》中桑女结束劳作后的闲适,与《汾沮洳》中桑女一边劳作一边心中有所思念的甜蜜,《豳风·七月》一篇中的采桑女,其生活显然多了几分悲苦的意味。《七月》中提及采桑女的有以下两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作为一篇记叙底层人民劳动生活的诗,《七月》中明显流露出对底层劳动者的怜悯、同情意味。春日和煦明媚的阳光下,采桑姑娘伴着婉转的黄鹂鸣声辛勤劳作。这样的景象似画一样美好,然而画中人物的人生际遇却远谈不上美好。身为底层的劳动者,采桑姑娘们历经辛勤劳作换来的成果却是不可能为自身所享受的,而是必须要进奉给上层贵族、统治阶级,即诗中所说的“为公子裳”。不仅如此,她们自身的命运也常常是无法自主的。所谓“殆及公子同归”,指的就是“采桑女无法违抗贵族子弟的命令、被他们强行带回家”这样悲伤又无奈的处境。
在《汾沮洳》与《七月》两篇中,分别表达了采桑女对心上之人的欣赏爱慕,与采桑女害怕受到贵族子弟强迫的忧心忡忡,而类似的情感与情节桥段,在后世描绘采桑女形象的汉乐府诗《陌上桑》中同样有所体现。
《陌上桑》一诗,从内容上看可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铺陈词句,“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描绘主人公采桑女子秦罗敷的衣着外貌;接着,又分别描写了“行者”“少年”“耕者”“锄者”等人因贪看罗敷而入迷时的反应。通过正、侧面描写的结合,极力渲染出采桑女“秦罗敷”的美貌,进而引出了后半部分中使君见色起意、出言轻薄、被罗敷严词拒绝的故事桥段。
该诗后半部分中,使君调戏已经身为人妇的秦罗敷,要与她共乘一车,这种行为本质上跟《七月》中贵族子弟们罔顾采桑女子的意愿、强行带其回家的行为如出一辙,都是仰仗权势欺压民女。而面对着与《七月》中采桑女子相似的处境,秦罗敷并没有表现出凄惶不安,更没有曲意逢迎,而是直截了当地报以“使君一何愚”的痛斥,指斥使君身为有妇之夫却贪心不足,竟然对自己这样一个已婚配的女子起了非分之想。接着,秦罗敷更是当着使君的面,夸赞起自己夫婿的威仪赫赫、才干卓越、品貌突出,最后一句的“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与《汾沮洳》中采桑女子赞美心上人的“殊异乎公族”,二者不可谓不相似,同样寄寓了采桑女对意中人的倾慕与爱恋。
由此可以看出,《陌上桑》一诗的后半部分明显受到了《魏风·汾沮洳》《豳风·七月》的启发,诗中“采桑女”秦罗敷这一形象相关的情节桥段与思想感情,正是在上述两首《诗经》诗篇的基础上承袭而来的。只是《陌上桑》之中,还创造性地加入了秦罗敷痛斥使君、夸耀夫婿的桥段,以丈夫形象的高大美好,对比映衬出使君形象的猥琐鄙陋,展现出浓厚的讽刺意味。
此外,在后半部分学习先秦诗歌的同时,《陌上桑》一诗的前半部分中对秦罗敷美貌的铺陈描写,又成了后世描绘“采桑女”的诸多诗歌学习的对象。如曹植的《美女篇》中,诗人就主要选取了“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的生活画面,对女子之美进行描述,又以“金爵钗”“翠琅玕”“明珠”“珊瑚”等华美珍贵的饰品来装点其美貌。唐代诗人欧阳詹所作、描绘采桑女子美貌的《汝川行》一诗中,“轻绡裙露红罗袜,半蹋金梯倚枝歇”二句,也是同理。但是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提到的,这两篇诗作中采桑女子的装束,于“采桑”一事上似乎多有不便。虽是为了描绘女子美貌,但词句堆砌,未免渲染太过,有矫饰之嫌。相比较之下,反倒是《十亩之间》《七月》等诗作中勤劳朴实的采桑女子形象更显简净自然。
尽管后世诸多诗篇中借由“采桑”这一画面来描摹女子美貌的做法,为“采桑”一事蒙上了一层浪漫的意味,但归根到底,“采桑”其实是一种辛苦的劳作,是许多平民女子不得不担负的职责。而采桑养蚕得来的蚕丝,也多不能用于采桑女自身享用,而是要用于交税抵租,或是供给上层的权贵,也即《七月》中的“为公子裳”。后世诗歌中,描绘采桑女辛劳的诗篇也不在少数,如宋代诗人叶茵的《蚕妇叹》:“浴蚕才罢喂蚕忙,朝暮蓬头去采桑。辛苦得丝了租税,终年祗著布衣裳”;又如明代于谦的《采桑妇》,采桑女子在路上遇到一位“游冶郎”,面对对方“为何不梳妆”的询问,只能回答说自己是农家妇人,要帮助夫君一起经营家业,劳作辛苦,自然无心修饰打扮,以至于“自来不解施朱铅,但识荆钗与裙布”,面对他人的轻薄取笑,女子报以“妾颜如花心似铁,玉洁冰清天自知”的坚定回答,当马蹄奔驰而去消失在视线后,才终于忍不住落下屈辱的泪水,泪中尽是穷苦百姓的无尽辛酸。这种对底层劳动者生活的关切与同情,正彰显了《诗经》现实主义传统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延续。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综合运用“赋” “比”“兴”三种主要表现手法,将自然界中各式各样的动植物绘入诗篇,使其转化为诗人情感与思想观念的载体,承载着周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喜怒悲欢。“桑”作为被《诗经》所选取的植物之一,在诸多诗篇当中留下了印迹,同时也被诗篇当中所传达的思想或情感浸染,逐渐成了一个带有丰厚意蕴的意象,并随着《诗经》中对社会现实抱以极大的热情与关注的“风雅”精神一并流传,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姜亮夫.先秦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3]郭沫若.甲骨文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4]黄维华.桑·桑中·桑女——《诗经》与上古文化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2004,(3):125-134.
[5]尹雨晴.先秦两汉时期“桑”意象的文化内涵嬗变[J].小说评论,2011,(S2):90-92.
[6]赵会莉.《诗经》中桑意象的文化观照[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5):1-2.
[7]安建军,张莉.原型批评视野中的“桑”意象探究[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0,40(4):60-67.
[8]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1-132.
作者简介:
周金玲,女,汉族,辽宁沈阳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王荣林,男,汉族,辽宁铁岭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