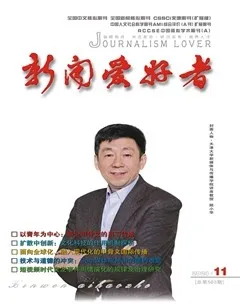从部落文化到媒介社会:民族志的物质性转向及意义
【摘要】作为人类学的核心方法,民族志在被引入传播学领域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期,芝加哥学派将其从人类学领域引入传播学领域。它挑战了实证主义范式,以建构主义立场发掘观察数据的意义。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后期,以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为代表的学者们倡导“物质性转向”,促使民族志把研究焦点从文化符号转移到技术的“物质性”方面。方法论的嬗变暗示了人们对“传播”的认识论立场发生改变。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媒介是人的延伸”的隐喻正在实现,民族志为研究“人和技术交互”提供了量化分析和理论批判之外的第三条路径。
【关键词】民族志;物质性转向;人机关系;文化表征;媒介技术
一、引言
民族志(Ethnography)是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一种人类学研究范式。从词源上看,“ethnos”意为“人群”或“民族”,而“grapho”意为“书写”。因此,对特定族群的书写和描述是民族志的天然“领地”。传播学在方法论层面博采众长并不奇怪:比如拉扎斯菲尔德偏爱使用的问卷调查法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而用来阐释新闻话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则源于费尔克拉夫的语言学旨趣。相对其他“舶来”的方法,民族志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关注最多:支持者们将它视为走出“方法失灵”困境、解决学科合法性危机的“良方”;反对者们则指出讲故事不等于学术研究,学者不应对冠以民族志之名的叙事抱有太大的好奇。[1]无论如何,民族志方法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当中的比重确呈上升趋势。自2003年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问世以来,可检索到的使用或阐述民族志方法的期刊论文达1000多篇。[2]新闻室民族志、网络民族志、自我民族志等一切带有“民族志”字样的方法似乎都被默认为新闻传播学可用的研究方法,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新闻学科可以理所当然地使用民族志?
“为什么可以使用民族志?”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民族志方法具有强烈的学科属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的核心价值判断和操作原则都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而非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实践中得来。那么,民族志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机遇下介入到传播学的研究并获得合法性?其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对民族志方法的实践从关注文化符号向关注技术物质性转移,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等人所倡导的“物质性转向”在学界持续发酵。民族志方法为什么会开始关注“物”的因素?这种转向对传播学研究有哪些新的贡献?通过考察民族志方法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介入、吸纳、调适和转向,能够帮助我们透过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路径,发掘它对传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二、从部落到城市:芝加哥学派对民族志方法的引介
马林诺夫斯基为民族志确立了三条基本原则:其一,民族志的核心实践方法是“参与式观察”。这要求研究者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或真实目的,充分融入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当中。其二,民族志最重要的资料呈现方式是“深描”。深描本质上是民族志的分析系统,它将研究者在田野中观察和感受到的行为、符号、社会关系与观念意义勾连起来,从而深刻解释某个特定族群的文化。其三,民族志方法的使用者必须保持对“反身性”的警觉。即便在民族志的田野中,研究者尽可能不去揭示自己的真实目的,他们也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主观性。在正统的人类学田野中,研究者不仅要做客观的调研记录,还要做表达主观情感和反思的调研日记。[3]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安群岛(The Trobriand Islands)田野调查的12年后,人类学家第一次将研究目光从原始部落转移到现代人所居住的城市。芝加哥学派的斯雷舍(Frederic Milton Thrasher)对城市帮派文化的研究突破性地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到传播学领域,其著作《匪帮:对芝加哥1313个帮派的调查》(The Gang: 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至今仍被视为芝加哥学派民族志研究的范本。[4]在田野调查中,斯雷舍把民族志方法运用到对芝加哥城中青少年帮派的观察中。为了真正理解青少年帮派的犯罪动机、组织文化和其内部交流的符号意义,斯雷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混迹街头,近距离地观察他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他们之间的交流机制和价值认同。经过七年的“参与式观察”,斯雷舍打破了传统实证主义对青少年帮派标签化的认知,从文化和符号角度“深描”出芝加哥帮派分子每天的生活、打斗、内部交流和身份建构。对“问题少年”正当化自己非法行为的深层动因的探究,正是斯雷舍民族志研究中与众不同的地方。通过对帮派青年的研究,斯雷舍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身上反映出的城市青年的共性,从而更深层次阐释了这个亚文化群体的交往和传播行为。
另外,想要完成对当时芝加哥帮派组织的研究恐怕也不得不依靠民族志方法——诸如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等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显然在实践层面无法触及帮派成员。实际上,民族志方法通过芝加哥学派进入到传播学领域不仅源于斯雷舍个人研究旨趣,更是帕克领导下芝加哥学派方法论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在问题意识方面,芝加哥学派重视“城市交往”研究,城市空间成为验证思想观点的“实验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潮的影响下,美国各大城市成为吸纳各国各族裔移民的“容器”。新移民原有的地域归属和身份认同被打破,导致新环境下人际交往方式和社区纽带等应用性问题亟须研究。因而,帕克等学者关注更加宏观的人类交往问题。帕克认为,人类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在与同伴接触、合作和冲突中逐步获得了人类的特质。交往与传播是一种社会心理过程,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是出于对同情、理解和认同等人类共性的迫切需求。[5]这种对人类本质与共性的思考,本身就与人类学家所探索的问题不谋而合。其二,在方法操作层面,当时的芝加哥学派苦恼于实证研究的局限性,转变方法论路径的想法萌芽已久。民族志方法对于当时的芝加哥学派而言是一种全新认识世界的路径,同时也是帮助他们实现范式转型的良方。从帕克对城市生活的论述来看,他在1925年的编著中关于“趋异类型”(divergent types)的基本观点深受《匪帮》对帮派青年阐释的启发。《匪帮》所提供的田野经验材料正是帕克一度缺乏的。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芝加哥学派没有固执于当时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占据主流的实证主义,而是欣然接纳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三、文化表征:民族志方法在传播学的“立身之本”
芝加哥学派对民族志的引入并没有撼动实证主义在美国传播学界的主导地位,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众传播经典理论多数仍通过实验或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完成。那么,相对于人类学,传播学研究中的民族志应该侧重什么,又可以放宽在哪些方面的要求?这些问题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在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中逐渐得到解答。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领导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后,民族志方法迅速成为支撑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范式。霍尔认为,文化研究的民族志继承自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的民族志是对米德“符号互动论”的复权。[6]在霍尔的鼓励下,伯明翰学派在英国掀起一股民族志研究的风潮。他们深入底层、边缘和亚文化社区,以观察和对话的方式研究工人阶级、青少年和妇女等白人中产男性以外的“非主流”文化群体,力图诠释他们的动机、行为、信仰、互动的规范和符号的意义。在田野调查中,伯明翰学派总结出一套服务于自身研究目的的民族志实践法则。这套法则不拘泥于传统人类学方法的教条,较芝加哥学派的民族志实践也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主要有四点:首先,确立传播学民族志的理论基础——符号互动论。符号和文化表征成为民族志研究的核心对象。民族志以发现和解读符号与符号系统为主要研究目标。其次,明确了民族志作为一种“定性方法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分野:在哲学立场上,民族志不赞同客体与主体的绝对二分法;在操作实践上,民族志不相信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可以绝对客观。民族志认为,理论可以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获得。再次,明确了“反身性”是民族志方法的“合法性来源”。反身性确保了民族志数据的“效度”。民族志最终呈现出的是主观因素与文化系统的关系,反身性是解答这种关系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身性”原则是民族志用以对抗实证主义的武器。最后,拓展了田野调查时的具体操作方法。民族志的实施手段不拘泥于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小组讨论、无焦点访谈都成为传播学田野调查中可用的方法。
伯明翰学派对民族志的实践和思考促成了该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科的调适。更重要的是,民族志“合法身份”的解决意味着学界在理解“传播”问题方面开辟出美国主流学派以外的一条新的路径。这条路径不再与哲学思辨或量化数据绑定,而是为经验材料提供了新的认识论立场。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将这种革新称为对“方法论”概念的解放,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反身关系的认可。[7]作为方法论的民族志完整实现了研究情境从部落文化到媒介社会的迁移。对传播学而言,除方法论的创新外,这种迁移还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对伯明翰学派而言,“民族志”成为各种质化研究方法集合的代名词。霍尔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时常将“质化方法”与“民族志”两种说法替换使用。严格来讲,质化研究方法还包括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扎根理论等与民族志并列的路径。如大卫·莫利(David Morley)的代表作《全国受众》(National Audience)采用的就是焦点小组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伯明翰学派不甚在意方法论名称的区分,莫利本人又是霍尔的弟子,也有学者误称其采用的是民族志。这种概念边界的模糊化,恰恰反映了由伯明翰学派在整个英国传播学界掀起的一股革命——以重视田野调查、重视建构主义为特点的质化研究方法来反思和批判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热潮。方法论的更新对传播学的范式革命起到了“催化剂”的效用。任何“人”,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还是大众媒体的“传播者”,在研究者眼中都不再被视为冰冷的“客体”。传播的意义不仅在互动中产生,研究的价值也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产生。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对民族志方法的采纳和调适,文化研究也不可能成为独立且影响深远的传播学范式。
其二,伯明翰学派延续了芝加哥学派对文化表征的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就察觉到了民族志走出原始部落、观照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一书中,他撇开了身为“现代人”的骄傲,指出自诩“文明”的现代人在面对原始部落中的阿赞德人时,不应该太高估自己的存在。这是因为现代国家里的人和原始部落里的人获得真实信念的本质是相同的。当面临未知现象时,原始人企图以巫术文化解释,现代人则试图用科学文化解释。尽管我们认为科学原理是胜于巫术迷信的,我们与原始人一样都依据自己所在的文化产生信念——而这个信念并不需要时刻通过“证据”来证明。[8]这个原理不仅适用于传统人类学对原始部落的观察,同样也适用于传播学者对媒介社会中传播现象的观察。这种观察的目的不在于“证实”某种假设,而在于“阐释”文化表征。这些所谓的“文化表征”,在普里查德那里是巫术仪式,在斯雷舍那里是帮派青年的涂鸦,在科恩那里是社区的街角商店和蓝领工人喜爱的音乐[9],在霍尔那里则是电视内容的语言和结构。对特定群体代表性文化符号的观察和阐释成为民族志从人类学到传播学一以贯之的关键。然而,在这一传承过程中,民族志研究的“物质化”路径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条路径自20世纪80年代由米勒提出后,在传播学领域的意义日益凸显。而通过将这一“转向”置于民族志在传播学领域的整个发展史中考察,对当代新技术条件下的传播学研究亦有新的启示。
四、“物质性转向”:新技术语境下的民族志
米勒用“物质文化研究”来概括自己的人类学旨趣,物质文化是民族志物质性转向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物质文化的研究里,参与式观察仍是田野实践中的核心方法,人类学的伦理规范仍然得到普遍尊重。但是,技术取代了文本符号的核心地位,民族志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物质而非表征的层面。在米勒一系列的“数码人类学”研究中,他以“物质性”的三个原则阐释自己对媒介技术物质性的理解:其一,物质性是数码科技的根基。其二,数码技术的物质性还指向其生产、再生产及传播内容的物质性,尤其是视觉物质性(visual materiality)。其三,数码技术物质性还指向语境的物质性。这种对语境的强调,实际上折射出米勒在民族志方法的实践中对人机关系的观照。在数码技术的支撑下,媒介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对人们注意力的竞争,而这种在幕后操持“注意力”争夺战的技术物质性层面,也正是米勒等学者戳破数码形式非物质性假象的关键。
米勒对数字技术的民族志考察既非专注于数字虚拟空间的网络民族志,也不是将技术与人进行二元对立。他强调民族志研究不应局限于分析符号的意义,而应把“整体论原则”作为指导方法论实践的主要原则。首先,人的日常生活是整体的,没有人只生活在数码技术建构的虚拟空间里,线下生活和线上生活都融于个人生活的整体中。其次,语境也是整体的,线上语境和线下语境在民族志的观察中同等重要。与伯明翰学派不同,转向技术“物质性”的民族志认为打破分析语言与意义的符号理论尤为重要。在具体方法上,米勒倡导将参与式观察作为民族志唯一核心的方法,并明确反对访谈法,这与伯明翰学派泛化“民族志”方法,将主要质化研究方法都归于“民族志”名下有本质的区别。米勒引导下的“物质性转向”,是从文化表征到媒介物质层面的转向,也是从泛化的民族志操作方法到集中的参与式观察法的转向。这种转向并非有意造成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现实生活与线上生活、表征与技术本身的对立。相反,“物质性转向”将人机交互、人机关系的建构作为观察的重点,试图打破民族志实践中的局限性,从而获得对人类数码技术使用的全面认知。
民族志的物质性转向对于传播学研究意味着什么?这恐怕不仅仅是提供了一种革新的研究路径、一种收集经验材料的方法,它与布尔迪厄、拉图尔等所倡导的对技术物质性的再认识是紧密关联的。经物质性转向的民族志用整体论的观点看待人机关系的建构,其前提是接受拉图尔等学者“技术并非简单地被人类创造和使用的工具”的观点。[10]只有在这个先决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媒介技术的物质性才具有了“主观能动性”,研究这种物质性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数字时代人在媒介社会中的生活状态。同时,这种转向的成功也为接纳拉图尔一派观点的学者提供了施展规范的经验研究的路径。事实上,一些学者已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朱利安·菲吉亚克(Julien Figeac)等研究者创造性地运用手机录屏的方法记录人们使用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刷手机”惯习为主要观察对象来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与移动终端的人机关系。[11]该研究考察的技术线索(technical cues)、空间线索(spatial cues)和思想线索(mental cues)三个维度,正是对米勒提出的整体论原则的实践操作。考虑到在对民族志方法的认知中,以网络民族志对应实地调查的民族志、以自我民族志对应观察他者的民族志等二元对立的思想仍有较大影响,米勒倡导的“物质性转向”中的整体论原则,无疑提供了观察人与新媒介技术互动的创新框架。
五、结语:文化表征与技术物质性,民族志的两条河流?
米勒对于文化表征持有怀疑,他相信文化的特征绝不局限于语言符号。米勒颇为赞赏布尔迪厄对“文化地图”的批判。他认为,语言往往是隐形知识的表征,语言交流的一方实际上是被另一方的问题规范了的。人类学家对这些语言的关注,容易导致将表征误认为是文化本身而采纳。或许正因为如此,米勒才对不会“说话”的技术抱有极大的研究热情,将技术的物质性视为更值得观察的对象。
本文无意讨论哪种民族志路径更“正确”,或者更符合当下学术界的流行趋势。民族志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它的物质性转向暗示了传播学研究领域认识论立场的转变。从传播学所关注的问题来看,民族志开辟了经验研究中有别于实证研究的第二“战场”,促使学者们将研究问题带到研究对象的生活空间中考察。在当下新媒介技术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情形下,民族志的物质性转向无疑开辟了新的田野,将经验材料的来源拓展到人以外的“物”上,从而帮助我们站在人类学的逻辑起点上重新审视人类的传播问题。
[本文为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涉华议题中社交机器人舆论干预机制与用户行为影响研究”(23YJC860033)阶段性成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8批面上资助项目(2020M68113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殷文,张杰.讲自己的故事就是“自我民族志”?[J].新闻记者,2017(12):79-86.
[2]郭建斌.民族志传播:一幅不十分完备的研究地图[J].新闻大学,2018(2):1-17.
[3]Hansen A,Machin D.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M].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13:64.
[4]Thrasher F M.The Gang: 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M].Chicago,IL: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27:80-81.
[5]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15-27.
[6]Hall S.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M].//HALL S,etal.(eds).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London:Taylor & Francis,1980:2-35.
[7]Willis P.Notes on Methods[M].//HALL S,et al.(eds).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London:Taylor & Francis,1980:76.
[8]埃文思·普理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M].覃俐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6-27.
[9]Cohen P.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y[M].//HALL S,et al.(eds).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London:Taylor & Francis,1980:66-75.
[10]刘国强.媒介化民族志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J].新闻界,2024(5):4-12+22.
[11]Figeac J,Chaulet J.Video-Ethnography of Social Media Apps’ Connection Cues in Public Settings[J].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2018,6(03):407-427.
作者简介:徐天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433),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全域认知与国际传播实验室研究员(安徽 430062)。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