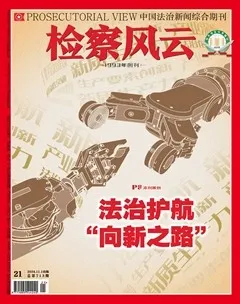为何司法既要稳妥也要积极
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增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诸多体制机制中,司法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一环,特别是高效、稳健、适度的定分止争,令司法程序得以为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演化和深度发展保驾护航。
依托于商业创新所产生的各类新经济业态,是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最重要载体。司法实践中如何回应新经济业态所涉及的争讼事项,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密切相关。一方面,新经济业态的运行在早期可能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相关司法纠纷便会面临如何适用法律的现实挑战。此时,司法机关的稳妥、包容态度,有助于鼓励市场主体在法律未明文禁止的一定范围内,积极开展探索性商业活动,促进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司法工作应牢守公正和安全底线,在面对新经济业态的复杂结构设计、多重法律关系和多层利益纠葛时,以“穿透性”思维引导资本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护航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面对新经济业态的谦抑性审查
与其他经济形态相比,承载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现象一般是此前未曾见过的新事物、新模式、新业态,也较有可能因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而呈现出“无法可依”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无法可依”并不是市场主体钻法律“空子”的结果,而源自法治的滞后性、稳定性与社会创新速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足够颠覆性的新技术、新业态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后,有些情况下已有的法律制度对其难以适用,这其实是较为正常的现象。此时,若新经济业态卷入法律纠纷,司法机关应恪守司法谦抑性,谨慎对待新经济现象的合法性问题,以免作出不甚妥当的评价。这有助于避免市场主体过分暴露在不必要的、过高的风险中。
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1条、第13条规定,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对于“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反垄断法》第1条明确将“鼓励创新”纳入“本法的实施目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55条规定对新业态等的监管要“鼓励创新”“留足发展空间”。近年来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也在落实“一单尽列、单外无单”。笔者认为,相关法律规定传达出如下内涵:在法律未明文禁止的相关领域,市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展创新性的商业活动。
依照上述逻辑,一方面,当司法面对市场主体开展创新业务的资质、权利问题时,宜侧重保障、鼓励市场主体积极拓展新业态;另一方面,当司法审查行政主体针对市场主体创新业务的强制、处罚等手段时,建议依循“法无许可即禁止”的逻辑,对行政主体管制市场的权力范围和尺度做控制。
由于欠缺明确法律规定,市场主体开展创新业务时可能会卷入是否合法、是否许可、是否符合资质的司法纷争中。针对新经济业态,司法机关对现有法律制度做扩张性的类推适用需要保持谨慎,为新事物的早期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为市场主体的商业活动营造相对稳妥、包容的司法环境。面对围绕创新业务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司法机关要避免超出现有法律规定,对新业态做出直接的非法性评价,在此基础上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作为
对待新事物的宽容并非是完全无前提、无底线的。市场经济领域的各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可能成为新质生产力初期发展的重要载体,但也有可能仅是人类历史上无数“试错”中的一次,甚至还有可能是一场饱含隐忧、为未来酿下巨大风险的“黑天鹅”事件。如果在司法实践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新经济现象存在社会风险,则应守住“公正”与“安全”的底线,在现有法律规则框架下,通过积极的司法裁判做出应有的认定,以审慎司法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的平台经济反垄断问题是以法治捍卫公正与安全底线的典型示范。在2020年以前,面对如火如荼发展的各类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与司法均保持了充分的克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平台经济的早期发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司法氛围。但当平台经济因无序扩张而展现出一系列典型社会问题,平台垄断排除、限制竞争的客观证据足够充分和可靠时,司法审查便通过必要、稳妥的方式予以介入,引导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我国《反垄断法》也于2022年进行了系统修正,在本次修法中,即将反垄断法的民生保障功能、平台经济反垄断审查、针对恶性垄断行为的惩罚性罚款、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等新制度、新规范写入,为通过竞争司法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
整体而言,在司法积极介入新经济业态过程中,应牢守“公正”与“安全”两大底线。
在经济发展视域下,“公正”除基础内涵外,还有着实质正义的旨趣。根据市场参与者的实际能力和表现作出的差异化的制度设计,衍生出对消费者、劳动者等弱势主体的倾斜性保护规则。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精细、系统的立法。
在司法实务中,对待新经济现象的包容、鼓励不应突破前述有关消费者、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制度框架。比如,在线下设店的新零售业务中,存在着以App或小程序线上操作、电子支付的形式取代线下点单、传统支付的情况,应当指出的是,经营者有义务为残障人士、老人等难以进行线上操作的特殊消费者群体进行代理操作。如果因拒绝而产生司法纠纷,经营者的上述行为或构成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和人格尊严受尊重权的侵犯,可能承担败诉风险。

与“公正”强调商业活动中的消费者与劳动者保护相比,“安全”则更强调对新经济业态整体社会风险的防范问题。当前经济社会深度发展,经济领域各环节、各领域深度绑定、彼此影响、风险相互传导,在此背景下,应谨防一些经复杂“包装”、以“创新”为名实施的非法业务,它们有可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埋下潜在风险。
司法活动理应对此类问题作出更积极、更主动的回应。对于在诉讼环节被充分举证证明违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具有传导性乃至系统性风险的新经济现象,司法机关应秉承“穿透性”思维,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积极地对相关市场活动予以规范、限制乃至完全禁止,不应放任经济风险的持续蔓延和扩张。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裁判者,应提高自身业务素养,通过科学锁定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精准识别和判断目标业务的法律性质等多样化的方式,实现对新经济现象的定分止争,真正意义上从司法角度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系湖北经济法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