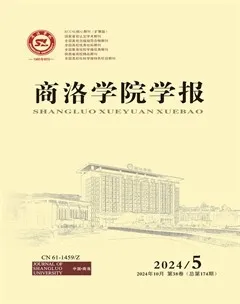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韩非中主论探析
摘 要:战国晚期,针对平庸者常处君位的现实与君权逐渐集中的趋势,韩非试图设计一套可操作的理论为“中主”服务。然而,真正能够如其所言兼用“法”“术”“势”治国、坚守公利为重、克制己欲、最终“尽人之力”者,绝非其所谓“中主”。韩非的君主理论本身存在矛盾,“法”的公开性、稳定性、公正性与“术”“势”的隐秘性、专有性难以兼容,更难被“中主”掌握。这使得韩非对“中主”的过高要求背离了为其服务的初衷。为实现君主“无为而治”的至治之世,韩非的理论中暗含将“中主”改善为“明君”的隐性需求,但该设想由于君主缺乏内部与外在动机仍难以成立,体现出其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韩非;中主论;君主;法
中图分类号:B2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24)05-0084-08
引用格式:陈颖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韩非中主论探析[J].商洛学院学报,2024,38(5):84-91.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ies: An
Analysis of Han Fei's Theory of the Mediocre Monarch
CHEN Ying-qi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Abstract: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response to the reality of mediocre people often occupying the throne and the trend of gradual centralization of monarchical power,Han Fei attempted to design a practical theory to serve the "mediocre monarch". However, those who can truly govern the state as he proposed, by employing "Fa"(法)"Shu"(术)and "Shi"(势) prioritizing public interest, restraining personal desires, and ultimately exerting their utmost efforts, are not the so-called
"mediocre monarch" as he defined. There ar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Han Fei's theory of monarchy, as the openness, stability, and fairness of "Fa"(法) are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the secrecy and exclusivity of "Shu"(术)and "Shi"(势) making it even harder for the "mediocre monarch" to master them. Han Fei's excessively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 "mediocre monarch" deviate from his original intention to serve them. In order to achieve an ideal era of rule where the monarch governs effortlessly, Han Fei's theory implies a hidden desire to transform the "mediocre monarch" into an "enlightened ruler". But this notion remains unattainable due to the lack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s within the monarch, reveal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iies in Han Fei's thinking.
Key words: Han Fei; Theory of the Mediocre Monarch; Monarchy; "Fa"(法)
战国之际,随着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各派学者皆阐述了他们对君主产生、君权正当性、君主职责等问题的见解,以期重建君主权威。与其他诸子相较,韩非君主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基于君主大多为资质平庸之人的事实,试图设计一套容易操作的方法论,使作为普通人的“中主”也能维系统治。关于韩非的中主论,王进文[1]从人格与位格维度对韩非君主理论进行分析,指出“以中人之智而实现法治之治,正是法家思想能够适应现实、符合实际,从而获得践行的关键所在”。马梦彤[2]认为韩非对中主和圣王的期待显示出其君主观中最为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法治同君主专制内在矛盾难以调和的体现。戴木茅[3]认为韩非所言“‘中人之治’针对的是普遍化的君主而非某个特殊人物”,这使得“韩非的君主具有‘非人格化’特征”。王宏强[4]88-91通过分析韩非的“贤势之不相容”说阐明其营造“人设之势”便是为中主治国服务。然而,韩非中主论在何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何提出、能否自洽且如其所言地发挥效力,则有待进一步分析。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韩非子》文本中韩非对“君主”有多种表述,如“君” “人主” “明主” “圣人” “圣王”等。由于中主之治是韩非所设想的君主治国须达到的最低条件,在选取有关材料时,本文以其明确使用“明” “圣”等字时的表述作为其对“明君”之态度的论据,以其使用“中” “庸”等字时或表达出“君主必须做到某事”之意时的表述作为其对“中主”之态度的论据。
一、君主世袭传统与战国君主集权趋势
在韩非所处的战国晚期,各诸侯国的行政体制已然历经数世纪变革,春秋时期诸侯国内基本衰落的君权在此过程中呈现加强之势,诸子也越来越倾向于认可君主的核心地位。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韩非的判断,构成韩非提出中主论的时代背景。因此,在分析韩非中主论前,有必要先阐明三代遗留的旧传统与战国时期的新形势对君主统治有哪些影响。
春秋以降,王纲解纽,随着周天子几乎失去有效权力,诸侯们也面临着权力衰落、“君弱臣强”的威胁,国君与其卿大夫间的冲突屡见不鲜。尹振环[5]指出,春秋时期至少发生了六十起以上的弑君事件与二十二起驱逐流放国君事件,其中大部分由君主大权旁落引发。与此同时,诸侯国内的君位更替过程不乏让贤之例,如《左传·成公十五年》载曹公子子臧以“为君非吾节也”为由,辞君位而“奔宋”[6]。《史记·宋微子世家》亦记载,宋宣公不传位于太子与夷,而“让其弟和”,“和亦三让而受之”[7]。在这种情况下,举贤禅让说在春秋末期思想界流行,如《论语·颜渊》云:“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墨子·尚同》云:“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公元前316年至公元前314年,燕王哙禅位于其相子之,却引发严重内乱和齐国武装干涉,最终齐宣王攻破燕国[8],宣告了禅让这一旧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燕国国内具体国情及诸侯国之间时局的诸多矛盾有关,但更不能忽视的是,战国时期各国已通过一系列改革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使得君权日益加强,世袭传统得以稳固,成为合法的权力继承方式。
从本质上讲,君主世袭原则是三族统治形式的延续,尽管周天子所建立的宗法血缘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旧有的统治习惯却并没有随之消失,嫡长子继承制仍在政治生活中被广泛实践,体现出历史传统的强大影响力。另外,由于诸子关于禅让的诉求并没有发展出具有可行性的制度,至战国中晚期,思想界已不再出现反对君主世袭的观点。如荀子认为,“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9]393即是说明,只要礼义的名分能够落实,就不必禅让了。韩非则对禅让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判,他讲:“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也”[10]509-510,认为尧舜“君而让臣”是违反君臣关系伦理的体现,背离了“定位一教之道”[10]510,会导致天下大乱。作为君本位论者,韩非主张由君主掌握一切权力,且君主必须独断专行以防止君权旁落。因而在他看来,唯有巩固最容易操作的世袭原则,才能确保长久的稳定。
战国中期以后,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加强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压力的增加与国家规模的扩大,强化集权统治成为现实需要,于是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形式日渐凸显,各派学者也越来越认可君主对于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纷争达到空前规模。孟子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1]。战争成为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常态。战争的扩大对君主集中调配各种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导致国君权力日渐强大与列国攻伐兼并规模扩大互为因果。萧公权言:“强大者兼并,既兼并而愈臻强大。侵略与自卫皆有待于富强。于是君权之扩张遂同时成为政治上之需要与目的。”[12]显然,韩非也看到了这一点,《韩非子·五蠹》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0]487他判断出,此时力量已成为诸侯国较量强弱的标准,唯有富国强兵才能在争霸战中取得胜利,而富国强兵又依赖于高效地集中权力进而运用权力,强化君权无疑是在列国纷争中取得生存权乃至争得霸权的重要政治前提。
如上所述,君主作用的凸显与君权加强的趋势相辅相成,而君主世袭传统已成定局又必然导致“世之治者不绝于中”[10]428。韩非提出中主论,即是要在此现实状况下解决如何延续君主统治、维护社会安定的难题。面对巩固君权的现实需求,儒家将以德治国作为宗旨,认为君主应不断修养道德、智慧等个人品质,从而施行合理政策,并为下民树立榜样、实现教化作用,如荀子所言“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9]277。道家则提倡由“圣人”担当统治者,因为圣人能够法“道”而为,“常善救人” “常善救物”[13]114,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13]153的境界,使天下安定。与儒家、道家相反,法家认为追求圣贤之治是不可靠的,他们并非意在完全否定圣贤明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而是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虑: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终归贤智者少,平庸者多,教化的力量也终究有限,强求圣人之治是罔顾资质平庸者常处君位的事实。所以,若想长久地维系政权,就绝不能依赖人主的智能与品德,必须找到适用于大部分普通君主的治国方法,韩非的中主论应此而生。
二、韩非中主论的提出
在韩非之前,已有研究者意识到不同君主的政治资质之异并开始根据君主的治国水平为其划分层次。如商鞅云:“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14],指出只有尧具有不依靠法度而明辨是非的能力,然而像尧一般明智的统治者终究难得,所以他认为大部分普通君主唯有依靠法度才能实现有效统治。又如荀子云:“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9]296虽然荀子此言意在为臣子提供应对君主的策略,但客观上他进一步以政治素养为标准将君主划分为圣君、中君、暴君三类,遗憾的是荀子未能顺此思路为不同君主提出建议。韩非则较为系统、深入地阐发了关于中主治国的观点,具体而言,韩非中主论的内容包括中主的范围、对中主治国的建议两部分。在《韩非子·难势》中,韩非明确了其所谓“中主”的范围:“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10]428,中主即是大部分夹在尧、舜与桀、纣之间资质平庸的普通君主,他们依靠世袭获得因身处君位而天然享有的权势,即韩非所谓“自然之势”。同时,韩非也针对中主提出了其设想中君主治国应遵循的核心原则:“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10]426-428他认为,中主空有“自然之势”还不够,必须在此基础上推行法治并掌握通过后天习得的“人设之势”,从而实现对权力的绝对掌控与有效运用。在韩非看来,这两点都是平庸之人也能够做到的,因此他以“抱法处势”为核心原则,从处理君臣关系与完善个人修养两方面对中主治国提出了建议。
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韩非认为君主必须做到“法” “术” “势”并用,以达到“尽人之力”[10]471的效果。法家坚信,“法”作为客观化的标准,有助于避免人治中因个人情感而产生的弊端,且更具有实际操作性,是统摄群臣、管理百姓进而保障国家机器平稳运行的有效工具。韩非讲:“法者,王之者也”[10]519,“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10]220,说明他将“法”视作最基本的政治准则,要求君主坚守以法律为主的各项规章制度,以法度治理国家。而“势”在韩非看来,则是君主行使权力的必要保障。他讲“势重者,人君之渊也。……赏罚者,邦之利器也”[10]170。其意在于表明,“势”具有使臣民不得不服从的强制力,只有当君主独占势位并能够落实到对赏罚二柄的绝对掌握上,才足以实现令行禁止。另外,韩非认为正确使用权术、避免被臣下迷惑也是身为君主不可或缺的能力。《韩非子·定法》云:“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10]433可见,韩非所谓的“术”与“法”一样重要,包含根据各人能力授予合适的官职、按照官职名分与人臣所言来考核其实际功效、依据核验结果实行赏罚等功能,最终达到使臣民顺服的结果。综上可知,“法” “术” “势”并用是韩非对每一个君主的期待,诚如其所言:“人主虽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10]397三者同等重要,相辅相成,都是君主必要的治国手段;中主也不例外,必须将其牢牢握在手中。
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韩非也提出了建议。首先,韩非认为君主天然地代表国家利益,应当明公私、审法禁,秉承公正无私的价值理念,积极维护其个人利益之外包括民众利益在内的公利。他讲:“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10]464,表明他主张君主意志即代表公利,当君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君主行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其言“君必惠民”[10]336,认为君主的职能就在于为人民做贡献,亦是此立场的体现。其次,韩非提出君主必须将自身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例如,君主不可以无限制地满足一己物欲,因为“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10]116,奢靡会消耗资源,对国家带来损害;君主也不可以随意释放自己的表达欲,因为“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10]45,一旦人臣摸清君主的好恶,就会趁机篡权夺位,造成变乱。在韩非看来,君主个人欲望的膨胀会使计划与谋略混乱,处理政事失去准则,既削弱君主的威势,又侵害民众的利益,从而导致灾难。再者,韩非认为人主须具备一定的智能,他讲:“人主不智,则奸得资。”[10]479需要注意的是,此处韩非所言之“智”不同于其他诸子所追求的君主之“智”,后者希望君王不断追求更高的智能,而前者对君主之“智”仅抱有最低限度的期待,即不要被奸人所惑,以免自身地位被威胁。在韩非的设想中,“法” “术” “势”即为统治国家的高效工具,因此君主的智能只要能够把握此三者,不至于丢失君位便已足够,所以韩非所言中主之“智”与儒家和道家对“圣人”的要求具有根本性区别。由此可见,韩非对君主个人修养的要求其实仍是为坚守法治、维护权势的原则服务,是以利用君主之势达到富国强兵、利国利民为最终目的。
统观上述,韩非对中主的期望,其中主论虽意在为平庸之君服务,但真正能够如其所言地兼用“法” “术” “势”治理国家、坚守公利为重、克制己欲、最终“尽人之力”者,绝非其所谓平庸之君。韩非自己也说:“以刑名收臣,以度量准下,此不可释也,君人者焉佚哉?”[10]397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却因未能遵循法度任人而被韩非视作中主之下的暗主,足见处君位之难。分析至此,也不难理解韩非所发出的“厉怜王”[10]114的感慨。然而,当君主独擅绝对权力,“法”与君之“术”“势”是否可以兼容?韩非的理论是否能解决君主与“法”的矛盾?我们将从韩非君主理论的内部理路分析其思想中君主与“法”的矛盾。
三、韩非视域下君与“法”的悖论
韩非的“法”不等同于现代所谓“法律”,而是其用以表述理想社会规范的专有概念。概括而言,韩非之“法”由君主制定,是一种公开的成文法,具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显著特征。在《韩非子·饰邪》中,韩非言“君之立法”[10]136,明确指出了君主的立法者身份。他还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10]433(《韩非子·定法》),表明“法”应明确地著录在官府文书中,并经过宣传与普及成为深入人心的思想意识。韩非也延续了早期法家学者的立场,认为推行法治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正所谓“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0]33,君主应“以法为本”[10]135,“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10]461,用法律保证臣民行为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可见,韩非的“法”出于君主,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由官府公布和执行,并要求君主之下的所有人一律遵守。但是,成文的“法”一旦公开,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必然作为一种客观标准独立于立法者意志之外;当君主意志有变,正在实施中的“法”与君主独有的、非公开的权力很难不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在韩非理论内部即表现为“法”与君势和“法”与君术的冲突。
首先,君势与韩非理想中的“定法”并不相容。在韩非的理想中,有一种最为适宜的“法”能使国家治理达到最和谐的状态:“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此之谓上下相得。”[10]216韩非强调,当“法”能够使君主与臣民相互协调,就不应随意改变,他讲:“法莫如一而固”[10]489,表明他主张“法”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韩非又借申不害之口说:“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10]348,鼓励君主独断专权。他进一步指出:“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10]429。韩非认为君主的命令是最应受到尊重的言论,法度也是政事中最应遵循的准则,如果言论不合于法度就必须加以禁止。韩非的法治理论比之商鞅以王令为法的思想固然有所进步,从表面上看,在韩非的思想中“法”权高于君权,可问题在于,韩非之“法”的立法权却隶属于君主。当独享威势的君主具有无上权力,他可以任意制定、修改任何“定法”,尊君与守法就将成为臣民的两难选项。当“定法”作为国家之本被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遵守,君主的个人意志完全被象征国家利益的“法”覆盖,他手中看似具有的滔天权势就将荡然无存,这是韩非难以自洽的悖论。即便他要求君主也不能悖法,“使法择人” “使法量功”[10]37,但君主自身本为立法者,“一断于法”与“君主之令最贵”间仍存在着难以掩盖的矛盾。梁启超谓,“法家最大缺点,在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15]。除此之外,“势”在韩非处具有价值中立的工具属性,它能够“便治”还是“利乱”,仅由使用者个人的道德与能力水平决定,所以若想依靠“势”稳固地统治国家,非圣明之君难以胜任。
其次,君主必须掌握的权术与韩非之“法”亦有矛盾,这种矛盾直接表现在“法”与“术”的使用范围和具体操作方法之中。韩非讲:“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0]415从此处可以明显地看出,韩非的“法”是公开的,要让所有人都清楚明白地知晓,而“术”则是非公开的,仅容君主一人知道并运用,以此驯服臣民,两者的使用范围并不一致。基于此,“法”与“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也会产生冲突。例如,按照韩非的观点,能力应是决定人臣受赏或被罚的标准,君主应当对立功的人公平地依法实施奖赏,如其所言“信赏尽能”[10]227。如此来看,君主对人臣的奖惩应是遵循法度的、完全公开透明的。但是,韩非又指出,君主不能把赏与罚的意愿表现出来,因为这样会使人臣从中获利:“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10]170与之相反,君主应“疑诏诡使” “挟知而问” “倒言反事”[10]227,以神秘化的“术”试探人臣的忠诚,这与“法”的公正性相违背。在韩非的理论中,君主既要依赖公正的、具有公信力的“法”促使人臣尽忠尽力,激励人臣为国立功,又要依赖隐秘的“术”时刻提防人臣潜在的犯上作乱的行为,甚至不惜使用欺诈的手段,此两者实现其一则破坏另一者实现的条件,因此几乎不可能同时存在。另外,由于“术”具有非法的属性,它对君主的性格、道德、智慧、能力等个人因素也提出了极大的考验,仅凭通常意义上的中君之资是难以运用的。
综上,君主之“势” “术”与“法”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不能奢求资质平庸之君能够将一套自身存在矛盾的理论合理有效地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不难发现,韩非的“法”并非仅为君主一人服务,相反,在国家整体利益尚未受损的前提下,他对君主一姓江山之维系毫不关心。尽管韩非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10]470,主张国家治理应顺应人性,但基于君主应为公利无私奉献的原则,他唯独否认君主个人情感与欲望的表达与释放。在韩非看来,作为人的君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满足私利,作为国家利益之象征的君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服务公利,因此他试图将人之为人的属性从君主身上剥离,最终目的是借君主之权来实施有利于国家的政策。于是,同“法”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一般,韩非眼中的君主也就“变成某种程度上无用的、没有个性的东西。他永远被督促着表现‘公’的属性……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彻底去个人化的君主,他变成一种fly0Gcse982nCPSJcUr4WLAXcGpM6kfv9ZZVS3RzsrQ=权力工具。”[16]从本质上讲,君主与“法”的矛盾其实是君主作为人与作为纯粹的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的矛盾,当要求具有主观性的、能够独揽权势的人与具有客观性的、公正无私的“法”合为一体,两者间必然会产生无法消解的冲突。不过,韩非虽没能消除君与“法”的悖论,但他在其理论体系内部做出过缓和此矛盾的努力,即希望个人修养与能力远超“中主”的“明君”能妥善处理“法”“术” “势”间关系。
四、从中主到明君:韩非改善君主的隐性需求
在《韩非子》文本中,韩非未直接劝谏“中主”努力修养自身成为“明君”,然而据王宏强统计,《韩非子》中共出现215处韩非对理想君主的表述[4]94,说明韩非并不满足于为“中主”出谋划策,而对描绘理想君主亦抱有强烈热忱。如果说韩非对中主的建议仅仅是治国的底线,那么“明君”即韩非所期望的理想君主,则被其寄予更大的期待。
韩非这样描绘他心目中明君的形象:“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10]223在他看来,明君要同时顺应天时、获取民心、掌握技能、占据势位,遵循自然规律,令行禁止,才能建功立业。受道家影响,韩非理想中的君主不仅要遵循自然之道,还应贵虚守静,以实现“无为而治”。如《韩非子·扬权》说:“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10]47。又说:“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10]48。韩非认为明君应将“虚”和“静”作为修养的方式,进而达到“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10]29的理想境界。除此之外,韩非对明君还有其他琐碎的要求,如希望明君具有辨别忠奸的能力与听纳忠言的修养:“夫药酒用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10]281;希望明君树立诚信:“明主积于信”[10]285;希望明君见微知著:“明主见小奸于微”[10]408;希望明君处事周全严密:“明主,其务在周密”[10]478(《韩非子·八经》)等。就连君主的情绪,也应成为可利用的对象:“明主之道,己喜则求其所纳,己怒,则察其所构,论于已变之后以得毁誉公私之征”[10]479。可以看出,韩非所设想的“明君”比之“中主”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能完全去除自身情感对政治的负面影响,在“法” “术” “势”的矛盾中找到平衡点,并及时修补三者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漏洞,做到“尽人之智”[10]471,最终“无为而治”,使理想的政治体制永远运行下去。
如此看来,韩非的“明君”必须努力完善自身修养与能力,以具备高超的政治素质,才能不断巩固“人设之势”,实现“无为而治”的理想。尽管韩非对儒家通过教育培养贤德君主的观点笔诛墨伐,但实际上,韩非对“明君”的过高期待亦暗示,完善君主品质是提升治理水平的必然需要。这使其又落入“尚贤”的窠臼,背离了自己为“中主”服务的初衷。即便抛开这些不谈,韩非改善君主的设想在其理论体系内仍然难以成立,原因有二:其一,从法家一贯所持的利害观来看,君主没有持续完善自我修养与能力以至成为“明君”的动机。在法家看来,人性趋利避害,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利益驱使。韩非云:“所谓亡君者,非莫有其国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10]60。此处韩非认为亡国并不等于此国不复存在,而是此国不再归此国君掌管。在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状况下,君主要么独擅势位、尽己所能地调动资源去争霸,要么失去权力及因权力而带来的各种利益回报甚至生命,这是韩非认为君主之利与国家之利能够被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原因。然而以纯粹的利害角度考量,君主克己勤勉成为“明君”固然能收获许多利益,但其所得建立在自己劳心劳力甚至压抑人性欲望的基础上。反之,君主失去权力固然会失去许多,但他将无需承担劳作的辛苦与个性的损失。究竟何者更佳?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价值问题。韩非无法确保君主做出他所满意的选择。至于韩非指出的最坏后果——身死,君主只需将治理水平维持在不会亡国的标准就可以避免。若如此,纵使君主在位时可以保全自身,对君位继承者而言则后患无穷。其二,在韩非绝对尊君的主张下,君权不受其他力量制衡,亦没有任何外部条件足以确保君主完善自身。作为君本位者,韩非强调了君主绝对权力,连立法权都完全把握在君主手中,更毋庸提君主本身不在韩非最有效的操纵利器——赏罚二柄的实施范围内。这意味着君主行为不受任何势力影响,因而也无法奢望劝谏等外部条件必然生效。
“中主”既无法把握本就难以自洽的“法”“术” “势”理论,又不存在使其持续修养自身成为“明君”的有效内部或外在动机,所以韩非将国家治乱系于君主一身的设想是靠不住的。然而,人们也应看到历史局限性对韩非思想的影响,在战国的生产力水平与时代条件下,韩非从“中主”治国的现实需要出发并试图解决问题的思路十分可贵。儒家与道家主张的“圣人”之治固然有其长处,但他们对君主的要求都过于理想化,道家则更缺乏能让君主直接运用于政治生活的具体方针措施,这使他们的理论无法完全付诸实践,而韩非的“法” “术” “势”理论虽然在深层次上难以自洽,却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在中国古代“外儒内法”的政治格局下,韩非提出的以“法”治国、考核官吏政绩、择优授官、善用赏罚二柄等中主治国之方融入了日趋精细复杂的国家机器,为千百年来的“中主”稳固政权提供着助力。另外,韩非坚持强调“法”的积极意义也无疑具有先进性,应当承认,客观化标准之于官僚体制的运作维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其中主论因此在后世政体理论发展与政治实践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五、余论
韩非虽提出号称可确保平庸之主安定天下的中主论,实际上却仍希望由明主治国实现至治之世。这就体现出其理论的脆弱之处。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君位依靠君主的智谋与武力保持才是常态,中主往往由于能力平庸、责任心弱难以抵御贪欲的诱惑,易致使国家走向灭亡。明主以国家利益为重,自会深谋远虑、励精图治,使国家强盛。韩非欲使中主维系统治的想法于是显得不太现实。他为中主设计出“法” “术” “势”兼用之策,初衷是为其解决有效治理国家的难题,然而他将立法权赋予君主,相当于把对健全的“定法”的期待又归还于君主,资质平庸之人自然无力回应这些期待。因此,韩非所构建的“法”是不完备的,无力支撑起真正可以“无为而治”的国家治理体系。这导致了其中主论过于理想的弊端。对于法家学说,人们常有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印象,但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韩非的一些观点也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尽管韩非考虑问题都能从现实出发寻求最大效益,然而由于他太过讲求实效,并执着于以“法”治国的观念,反而容易导向理论的绝对化,并使之产生不容于现实的一面。例如,韩非反复批判儒家的道德没有可操作性,但道德在战国晚期的效力或许弱于法度,并不意味着道德教化在政治生活中毫无作用,尤其是在三代所遗留的德性政治传统已具有深刻影响的情况下,完全放弃道德教化才是不可行的。任何一种理念或主义走向极端都会发生异化,这也是法家学说在秦朝的政治实践中致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
若想破除君与“法”的悖论,只能走出法家的理想,要么改变完全由君主独揽权势的局面,在“法”之外寻找限制君权或教化君主的手段;要么放松法家之“法”的标准,转而采取更温和、更灵活的规范——事实上这也正是秦亡之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趋势。一方面,为弥补秦制之弊,汉代学者将“天”这一概念纳入政治体制的设计中,试图以“天人感应”说将天象祥异与国家治乱相联系,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君权滥用;另一方面,随着诸子学的融合会通,儒法合流的现象体现在汉代及后世的政治生活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中国古代政治也表现出“外儒内法”的特点。汉代政治家董仲舒就提出:“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17]279,从政权合法性层面将君主置于“天”之下。董仲舒认为天设立君主是为了让其承担爱护百姓的责任:“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7]216。如果君主丧失民心,就会被天命废绝。同时,董仲舒强调德政教化是君王为政的根本,并进一步提出天谴说,将自然现象与君主为政得失相联系,以此为威胁劝诫君主,促使其反思。汉初政论家贾谊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法家思想,他也将君主分为上主、中主、下主,不同于韩非的是,他指出“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18]199认为对君主的教育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贾谊明确提出应针对君主进行道德教化:“而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惠然独先迺学道理矣”[18]261,使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环境因素,自君主幼时起便以此潜移默化地塑造其人格,将生为人君应尽的责任刻在君主的意识中。雷戈认为:“儒学的特点即在于为帝王提供责任伦理”[19],儒生们的道德规劝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相比于秦始皇,两汉中不少皇帝更具自我反省意识,如文帝的诏书中就曾多次出现“朕既不德” “人主不德”等语句[20],显露出其自谴自责的反思之心。
然而,儒家的道德教化也有其过于依赖道德说教而忽视制度设计的弊端。因此,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没有找到真正可以从制度上制衡君权的手段。而缺乏以权力限制权力的制度,导致君主、亲族、臣子、百姓等势力此消彼长、撕扯争夺,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即便是在“治”的状态下也不过是维持着岌岌可危的平衡,一旦这一平衡被积重难返的恶习或偶然突发的变故打破,就会进入“乱”的常态。但我们不能站在现代的高度苛责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两千年间,君主理论与“法”的体系总是在各朝各代学者的探索中不断完善,乃至于当今如何实现现代国家的高效治理仍是值得探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作为今人的我们惟当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在制度设计内外追求更加稳定的平衡架构,并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努力谋求理想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王进文.中主抑或圣人——以人格与位格为中心维度的韩非君主理论[J].环球法律评论,2013,35(4):48-66.
[2] 马梦彤.圣王抑或中主——《韩非子》君主观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6):59-64.
[3] 戴木茅.韩非君主观论析[J].哲学动态,2019(2):56-62.
[4] 王宏强.韩非子治道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5] 尹振环.从王位继承和弑君看君主专制理论的逐步形成[J].中国史研究,1987(4):17-24.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873.
[7] 司马迁.史记[M].裴驷,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1622.
[8]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100-101.
[9] 王先慎.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
[10]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
[11] 杨伯峻.孟子泽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60.
[12]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23.
[13] 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4]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2018:83.
[1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84.
[16] 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M].孙英刚,译.王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31-132.
[17]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18] 贾谊.新书校注[M].阎振益,钟夏,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19]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4.
[20]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81-95.
收稿日期:2024-07-20
作者简介:陈颖琦,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