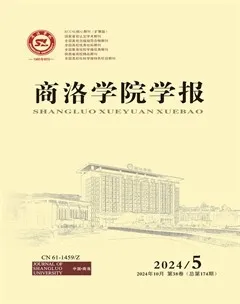解构与回环:残雪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
摘 要:残雪小说以其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哲学思考,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不可忽视的存在。残雪通过去中心化的叙事手法,以文本意义的零散与矛盾性,挑战了传统叙事的逻辑和秩序;通过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图绘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人的生存困境,并表达出对人的存在的深刻悲悯。残雪在解构传统的同时,不断建构与重构自己的文学世界,形成了独特的“圆的重复”叙事模式,通过出走与回归的循环建构了新的叙事范式,在当代文学中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残雪;解构主义;播撒;消解;圆的重复
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24)05-0039-08
引用格式:曹曲.解构与回环:残雪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J].商洛学院学报,2024,38(5):39-46.
Deconstruction and Recurrence: A Discourse of
Can Xue's Short Stories
CAO Qu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Shaanxi)
Abstract: Can Xue's novel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distinctive narrative style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have not only enriched the for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propelled it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ecoming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global stage. Drawing on deconstructionist philosoph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Can Xue's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ir innovativeness. Through a decentralized narrative approach, Can Xue's works challenge the logic and order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s with the fragmentation and contradictions of textual meanings. By de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binary oppositions, she dissolve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human being, mapping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s of individuals in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context and expressing a deep compassion for human existence. While deconstructing tradition, Can Xue continuously constructs and reconstructs her own literary world, forming a unique "circular repetition" narrative pattern. Through the cycle of departure and return, she constructs a new narrative paradigm, which holds uniqu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Can Xue; deconstructivism; dissémination; dissolve; circular repetition
在文学的浩瀚海洋中,残雪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风和阅读体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自成一格。其作品不仅是对传统叙事边界的勇敢跨越,更是对人性深度的深刻挖掘。解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哲学流派,其核心在于对既定结构、权威和传统的解构与颠覆,鼓励人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残雪不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框架,而是勇于打破逻辑与秩序的束缚,通过零散的情节、矛盾的人物关系,以及模糊的现实与虚幻界限,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既清晰又混沌的文学世界。自1985年第一篇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公开发表后,关于残雪独特的写作风格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歇。残雪与西方文学传统在精神上的关联与默契一直被学界关注。高玉[1]立足解构视域,指出残雪在小说文本中通过时空逻辑的混乱,非理性的现实及模糊因果关系等方式对作品意义进行肢解,以达到文本“反懂”的写作目的。王源[2]将解构视角和女性主义研究结合,分析了残雪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颠覆性描绘,指出残雪试图解构传统文学话语中的女性标签,重新阐释女性世界的价值观。总体上,当前研究依旧侧重于对残雪的小说文本及写作方式进行解读[3],或将文本置于不同文化语境下进行跨文化研究[4]。亦有学者开始将残雪研究置于更为宏阔的学科背景中进行考察,例如将叙事医学基本概念模型和残雪小说中体现的赤脚医生们的医疗行为相结合,分析小说中体现的自然医学观[5]。在残雪的小说中,读者几乎看不到明确的中心思想和固定的意义指向,取而代之的是意义的无限延异和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残雪通过对人物、关系及环境的解构与重构,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与世界的混沌无序,提供了重新审视文学叙事与人性反思的新视角,揭示其在当代文学中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播撒与弥散:无中心的叙事迷宫
解构主义是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德里达[6]在《论文字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这是对早期“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哲学理念的一种修正和新的发展。德里达将其概括为:“否定一切规范,狠起来也会否定自己。”当西方的哲学家以理性与逻辑为武器劈开结构主义的范式之时,东方一位文学天才正在用她的如椽大笔实践着文学的解构主义哲思。以解构主义审视残雪小说的叙事,其最大特点就是去中心化,小说中的意义像播撒种子一样被到处扬散,无法被归整到一处。小说文本明确,意义却漫无边际,无法确定定点,几乎没有中心可言。德里达认为,“通过无限的循环和指称,从符号到符号,从描述者到描述者,在场本身不再有地位,……人们再也不能支配意义,人们再也不能中止意义,意义被纳入了无穷无尽的意指运动中。”[6]“播撒”消解了作为意义归宿的“在场”,因此符号的确定意义被多层次地延异下来,又向四面八方发散出去。
德里达认为“播撒”会永无止境地瓦解文本的意义,使得文本的意义零乱且重复。而播撒最根本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彻底的矛盾性,二是意义的不确定性。
(一)零散:彻底的矛盾性
残雪的写作表现出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全然背离,她解构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在她的小说中,无连贯情节和逻辑,整个文本呈现出“零散化”的特点。而这种撕裂、异质的“零散”在文本中制造出矛盾。“为了产生无限的语义结果,播撒并没有被还原到一种简单起源的现存性上……也不被归结为一种末世学的在场,它表示一种不可简约的和‘有生殖力的’多元性。替补和某种缺乏的骚扰打破了文本的界限,禁止完备和系统地阐释它,至少不准将它的主题、所指和意义集中分类。”[7]这种矛盾性充斥在文本中,并且无法调和。比起打乱的拼图,残雪的文本更像是被撕碎的照片,就算被重新拼凑起来也无法还原至原貌。
一方面,零散的叙事方式造成情节和意义的非本质化。残雪的叙事经常是从一个病态心理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世界往往被描述为扭曲阴暗、破碎分裂的病态形象,因此给文本意义也带上了一种精神错乱的感觉,这种错乱又加深了文本的零散程度。人物的扭曲分裂被放大到整个文本世界中,于是“一种非历史性的‘感到……’句式构成了叙事的重心,真实就在这些零散错乱的感觉中消解为虚无的世界。”[8]精神病人心理、行为的不可理解性被放大,整个文本中人物的行为和他们的言语都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并且理解的过程中由于彻底的矛盾性,无法得出对作品意义的共识。另一方面,零散的情节又使得小说叙事出现矛盾,残雪小说中矛盾感觉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时间线的矛盾并且无法被还原。在残雪笔下,叙事时间被打乱、重组,叙事顺序变得难以辨认。残雪在叙事过程中,将现实与臆想、真实与虚幻等各种充满矛盾的片段相互交织在一起,试图用这些虚实参半、真假难辨的叙事片段营造一种共时性的时间体验。《不祥的呼喊声》中,老木西躺在一个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河流中央,动或者不动,都变成了主观性的认知而非客观实在。小说中表示时间的词语出现了很多次,给人以线性叙事的错觉,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并不然。基本上每段都会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自此“几个年头过去了”,“多年之后”,又从多年之后跳到“老木西刚到树林里生活时”。像“虽然时隔多年”, “大约往北走了半个月左右”, “好多年过去了”,“森林里下霜的那个早上”[9]194等,虽然都是在表示时间,但这些时间并不能连成一条完整的线,因为这些时间不仅零散,不能连成完整的时间线,甚至不能指向明确的时间。残雪在文中虽然使用了十年、五年、将近一个月等确切的时间,但同时也插入了“多年”, “好久”之类的词汇,使人无法真正摸清时间到底过了多久。正如小说开头描述老木西躺在一条停在河中的独木舟中,无法确定舟走或者不走一样,时间在叙事中也变得难以确认,按照文中的时间线并不能还原出一个具体完整的逻辑圈,甚至它不能还原到一条完整的逻辑线上。这种矛盾体现在文本叙事的方方面面。如果对残雪的小说进行分析归纳,就能很明显地发现文本的互相矛盾。这使得对小说中心的归纳变得毫无意义,研究小说的情节和意义也毫无用武之地。作品叙事的矛盾性导致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有很强的线性模式,残雪的小说却彻底颠覆了线性时间叙事,以心理时间替代了线性时间流动的模式,由零散叙事导致的文本矛盾性,进一步加深了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
(二)疑难:意义的不确定性
意义的不确定性对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阅读残雪的小说常常使人陷入一种“迷狂”状态,越想把握意义,意义越从指尖溜走。这种文本意义难以把握的状态德里达称其为“疑难”。“播撒不仅仅是指意义的异质多元性,彻底矛盾性,更准确地说是指意义的不确定性。它彻底搅乱本文,使人在到处散落的意义间游离不定,最终无法判断。”[10]当读者在面对这种种“疑难”时,似乎可看到残雪如同恶作剧的孩子在窃窃哂笑,因为她的文本是“反懂”的。
残雪的小说“反懂”的特征,从根本上是一种不被理解的形态,或者说是拒绝被理解的。“残雪小说的‘读不懂’,它不属于写作上的‘隐晦’和文风上的‘晦涩’,而从根本上是‘反懂’。”[11]因为文本不是按照理解的方式来写的,也没有描写人们可以理解的内容,因而不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无法以现实作为参照。残雪的小说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讲故事的模式,叙事在她的作品里显得凌乱,如果读者想把握她的写作意图,就会变得极为沮丧,因为残雪的创作本质上是刻意非理性的创作。在写作时放弃理性,放弃意识,她书写的是潜伏在意识底层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她在和施叔青的谈话中这样说:“写出上一句,还不知下一句在哪儿。完全没有构思,也没有提纲。”[12]
残雪写作不着重于现实世界,而是着笔于人的精神层面的现象,更准确地说是精神中不可言说的非理性的部分。她描写白日梦、幻觉、直觉、潜意识等非理性、不可捉摸、不可重复的现象。这种放弃真实,拥抱梦魇的写法在内容上增添了读者理解的难度。相对现实而言,精神领域显得更加捉摸不透,而对精神领域的描写,尤其是隐藏的无意识自身就具有神秘和混乱的特性,这使得意义在潜意识世界中难以被把握和理解。精神世界,尤其是隐藏在意识之下的无意识和潜意识的“非懂”性,造成了残雪文本的“非懂”。但是描写“精神真实”的同时,也是一个将无意识转化为意识的过程,不被察觉的被察觉到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精神世界具现化了。
隐喻等写作手法的使用进一步提升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但意义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文本意义的探寻。“疑难”并不意味着要人们放弃对意义的追求和思考,放弃认知文本,而是要放弃形而上学的权威式思考。意义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积极地思考除确定性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的思想。“意义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对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彻底解构,具有否定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不断地以开放的视域重新播撒意义,积极地解释本文,又具有肯定的价值。”[13]
残雪坚持以非中心化、去中心化展开一个个片断的、分散的、延异的“故事”,故事的意义难以琢磨,读者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会随着小说的铺展变得不安又烦躁,然而小说关于精神世界的描述又是那么迷人,于是阅读残雪的小说就成为一个个穿越迷宫的寻宝之旅。
二、解构关系:二元对立的消融
残雪的创作放弃了对现实的真实反映,而转向了挖掘神秘精神世界。她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二元等级对立关系进行拆解,在某个特定时机将这些等级秩序颠倒过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文学叙述。在叙述上,残雪一反传统的叙述手法,使用了无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的非线性结构,以及反逻辑、碎片式的叙述手法,营造出一种跳跃的神经质的语言效果。在人物塑造上,残雪主要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三个方面对人进行解构。
(一)人与自身:人物主体的消解
残雪对“人”进行消解,“人”丧失了在传统叙事中的功能,人物被扁平化和片面化。在残雪小说中,关于人物的信息会被刻意隐藏,最显著的一点是“我”的缺失。在残雪的第一人称小说中,这一特点格外突出,不仅主角没有名字,就连其他人物残雪也十分吝啬,不肯轻易赋予特有的名称。这使得人物的特性被磨灭,留下的只剩某种共性标志的符号。人物在文本中的称呼通常是“母亲”,“大狗的父亲”,“杂货店老板娘”,“祖母”之类,主人公也很少会在文中出现明显的区分符号。当第一人称“我”开始叙事时,没有关于“我”的身份介绍,也无从得知“我”的性格特征,就连“我”的名字也被掩藏在文本中,由他人在不经意之间提起,甚至“我”是男是女都要靠读者联系上下文进行猜测。这种刻意的淡化使得文本缺乏某些重要的背景。在残雪的小说中,很少有对主角的清晰描述,或者说残雪在刻意避免描写清晰、形象的人物形象。更多通过“妈妈” “我”等一些没有特定实在的个性意义而只有人的共性标志的称呼来代指文中的人物。没有或者很少有关于人物的背景介绍,通常只是简单的职业介绍,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这种刻意的模糊使读者无法捕捉到主人公的信息,在文中无法获取关于人物的性格信息,唯一能读取的只有疯狂。这种疯狂不只局限于主角,残雪文本中的人物都有疯癫这一特性,而其他的特征被作者刻意淡化。在《污水上的肥皂泡》中,开头说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我”是谁,“母亲”是谁,都没有在文中作出解释,唯一能猜出这对母子身份的只有一句“王尤其是我母亲机关里的一个小科长”[9]11。也没有对文中人物的进一步解释,从文中人物的行为举止中找不到任何可以读取人物个人的信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疯癫,一样的扭曲,一样的病态,在病态的程度和方面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都一样的,在推动情节方面更是少有作用。
除了人物形象上的刻意消解,减少人物在文本的作用,人的物理属性也被解构了。在本文中,人不仅难以保持理性,有时连人的形态和心智都难以保有,人被异化为非人。在转变为非人形态的同时,一部分关于人的认识也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兽性。“人”不再是人,而是一种介于人和兽之间的东西,界限被打破,人和非人的属性相互调换,相互融合。在《山上的小屋》中,“我”认为父亲在晚上变成围绕着房子嚎叫的狼,理由是她看见了父亲的一只熟悉的泛着绿光的狼眼。而在《污水上的肥皂泡》中,三毛的母亲化为了一盆肥皂水,虽然她溶化在了水里,但她却没有消失,三毛仍能从木盆中的水中听到母亲的声音,一个小个子用手戳扎了一个肥皂泡,但是却说自己戳到了一个女人的脊背骨。母亲在视觉上消失了,但三毛仍能从木盆底部听到母亲催促他送礼的声音。母亲在具体人类形态上消失了,但她的精神仍禁锢着儿子,对儿子来说,那盆肥皂水和母亲没有什么区别。在残雪笔下,人变成狼、恶狗、狐狸等动物,而这些动物无一不带有负面色彩,人在异化的过程中,将原本就疯癫的本性进一步显露。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异化不是单向的,人和动物在残雪笔下被全然解构,人像兽,兽像人。《索债者》中的索债者是一只猫而非一个人,但这种猫的行为举止却并不像一只温顺可爱的家猫,它更像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在阴影中趁其不意就对喂养它的主人发起致命的一击。“它回来了,不停发出恐怖的嚎叫,那叫声不但没有一丝祈求的味道,反而充满了怨恨、仇恨乃至威胁。它还用爪子抓,用牙齿啃我的门,啃一阵,咆哮一阵,使我不寒而栗地想:假如放它进来,说不定会趁我不备将我咬死”[9]158。这不像是一只被抛弃后找回来的猫,而更像一个上门寻仇的人。在残雪的笔下,疯癫扭曲充满恶意的不仅是人,动物也一样,人与非人之间不再是全然的二元对立,她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
在传统文学中,人物要有性格,从而构成典型形象,即既是具体的,又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形象,但残雪的小说中有对人的描写,却很难说有人物形象。残雪小说中的人物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所有的人物不管年纪、职业、经历、性别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神秘、怪异、病态,不可理解。人物的特性被抹去,留下的只有病态这一共性。
(二)人与他人:地狱是他人也是自身
亲情主题是残雪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题材,残雪喜欢描写亲人、情人之间的丑恶关系来表示对人性的怀疑和否定,传统题材中的亲情很显然在残雪这里是不存在的。她更喜欢描写人情关系之间的扭曲丑恶,这种丑恶关系和传统小说叙事中的丑恶有着很大区别。传统言语中的恶人由来已久,揭露亲人之间丑恶行为的也不在少数,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直接借狂人之口说出亲戚之间吃人的事实。但这些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清晰的逻辑线,谁恨谁,为什么而恨,在仇恨的驱使下对亲人做出了什么事,这些都有着明确的交代。在残雪的叙事中,传统的伦理秩序被解构,人物个体则陷入一种伦理的怀疑困境。亲人、爱人和朋友之间这些本该亲密的关系在残雪笔下被扭曲变形,亲人之间的怀疑仇视在残雪笔下变成了既定的现实——并不是有理而发,而更像是一种既定事实。亲人之间的仇恨是毫无理由的,很多作品中残雪更是让主人公自己说出别人对他的恶意,和他对别人的恶意。
萨特认为“他人即地狱”,即人与他人间的依附关系,是每个人都要以他人的目光来认知、证明、肯定自己。残雪文本中的第一人称视角是不透明的视角,她说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读者对说出的事情的感知等几乎就像一个笼子,读者被关押在笼子之中。不允许有双重视野,不能从外面瞥见事物,这意味着对话在内的所有内容,都是通过叙述者心烦意乱的心情过滤后传给读者。只有文本外的信息才能使读者识别出叙述者的异常状态。而文中第一视角的“我”看到的他人,其实是“我”在他人眼中的印象。亲人对“我”的各种恶意,也是“我”对亲人的仇恨的投射。扭曲的并非只是他人或者自身,而是所有人都处在“地狱”之中,无人幸免。“在他人眼里,‘我’是对象,随时都有被虚无化的可能。因此,在他人的注视下,我被掏空,感到羞耻。这是一种异化的状态,人就生存于这种异化状态之中,并由此而感到生活的荒谬,进而产生无边无际的焦虑和恐惧。”[14]
家庭在残雪的笔下从来没有一个正面的形象,父母和孩子及兄弟姐妹之间那种本该亲密的联系被恶意取代。所有的人都是病态的,他们之间充满了病态的控制欲和窥探欲,而且毫不遮掩亲人之间的杀意。在这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仇人而非亲人,看似正常的伦理秩序下掩盖着人物之间关系的敌对。《表姐》中,“我”对春节家人团聚这件事充满了抗拒,每到家人团聚的时候,就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饲养毒蛇的孩子》中,母亲对孩子充满了扭曲的控制欲,她监视孩子十几年,只是因为她认为她的孩子在饲养毒蛇。《天堂里的蓝光》中,阿娥受伤哭泣,认为自己即将死去姐姐阿仙的关注点却在妹妹那些精美的描画模板上。这种人际关系的扭曲不只局限在家庭之中,而是几乎贯穿了所有人际交往。情人之间美好的爱情也被扭曲,在残雪的笔下,配偶总是面目可憎,毫无生气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中,“我”与大狗的父亲已经结婚八年了,但在“我”的眼中,大狗和他的父亲的形象是身材又矮又小,脸上长满紫疱,嘴里满是浓烈的蒜臭味。孩子和丈夫这些本应亲密的人,却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敌意和疏离,值得一提的是,当大狗的父亲离开家后,“我”却觉得他脸上的紫疱好像没有了,人显得漂亮了很多。在和丈夫分居,两人联系不多时,丈夫在“我”眼里反倒是有了正常的形象。亲密关系却刻意疏离,这种反常的人际关系是对传统叙事的刻意反叛。
(三)人与环境:亦真亦幻的生存场景
残雪建构了一个与人们日常生活迥异的虚拟经验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孤立存在的。残雪精心描摹和建构的是精神王国,是潜意识的世界而非现实真实世界。但这个“潜意识”世界也不全然是潜意识或无意识,或者说她想表现是“无意识世界”,但却又不得不将其拉出意识的海洋,将人们不能认知或被感知忽略掉到的部分(即潜意识)转化为可知可见的部分(即意识)。残雪对现实世界进行解构,将现实打碎、叠加、重组成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里更注重的是“精神真实”而非现实真实,所以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各种匪夷所思的东西,这种怪异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对现实真实的拆解在文中从头贯穿到尾。将现实撕裂,分解,并在其中掺入虚拟现实,真实和虚拟的界限被打破,被颠覆,最终营造出半梦半醒的效果。
残雪的文本中,主人公时常通过旅行这一方式转换自己所处的场景,从一个相对平静、正常的地方移动到一个反常、扭曲的地方。地点的变化在小说中通常就意味着反常的发生。在小说《表姐》中,家伟喜欢自己的表姐,在春节的时候邀请表姐一起去海边度假,在海边发生了一系列怪事。最后“我醒来之际,四周亮晃晃的,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起了变化,一种陌生的欲望在里头跳跃着,与此同时,头脑也变得无比的澄清”[15]86。家伟和他的家人永远地留在了这个遥远的海边。文本中一开始就写表姐的生活,她的郊区小平房、她修建庭院的日常生活和她的感情生活。但这个看似正常的世界已经埋下了反常的种子,从细节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开头埋藏了一些病态的征兆:家伟的表姐对园艺有一种病态的痴情,培育不出完美的玫瑰花就用锄头将花全部刨掉;他的母亲在谈起意志坚定的表姐克死父母时“表情与其说是责怪,不如说是赞赏”[15]41;家伟在春节阖家团圆时就坐立不安,有强烈的离开冲动等。这些仅仅只是一些异样,还远远没有到令人怀疑的地步。但在他们登上火车离开的时候,这些异样就开始被放大。在火车上,表姐听到了并不存在的“那家伙在这里来来回回地走”[15]43的声音。到了旅馆后发现不会游泳的表姐在往海里走,跑到海边却没有发现表姐的身影,认为表姐落难后却在礁石后面再次发现了她,虽然脸是青色的,但衣服却没有湿。不光是表姐出现了一些令人疑惑的举动,旅馆里的厨师、门房鬼鬼祟祟的举动更是令人疑惑,最后表姐的前男友、母亲,父亲等人更是统统出现在这个海边的小旅馆中。扭曲是在场景转换的时候加速的,在《西湖》中也是如此,家政吴芳有洁癖,在她去西湖旅游后,火车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怪事,在她下车后去西湖时这些怪事并没有消退,接待她的经理也给人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开始吴芳对这些异常感到迷惑,但后来她也融入了这种异常之中,她接受了这个扭曲反常的世界,从疑惑到不再感到疑惑。这种转变并不只限于大型场景之中,从两个城市之间的移动到上山下山,几乎在每一个场景移动的时候都能捕捉到这种异常的波动。在短篇小说《天窗》中,躺在半空的草堆上,主人公看见了“像脓疮一样坐着患了晚期梅毒的父亲”,看到了“肥胖的,被糖尿病折磨的奄奄一息的母亲”,以及“兄弟们像猴子一样在那上面爬来爬去,在他们空虚透明的腹腔内,一个巨大的胃痉挛地渗出绿色的液体”[9]34。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在主人公跟随烧尸老人离开后出现。刚开头,他的家人的形象是“妈妈沉重的身躯蹲在瓦砾上,她艰难地喘着”,“我的一个小兄弟已经用半只眼偷偷打量我好几次了,还在喝汤时悄悄朝我碗里放入一粒老鼠屎来试探”,“父亲威严地从溃烂成两个小孔的鼻腔里嗡嗡地说”[9]30-31。但在烧尸老人暗黑浮空的屋顶上,他看到的家人是“老姑妈骑在一匹发狂的大母狗身上冲出来,在炉渣上兜了一个大圈,又发狂地冲进了地窖”,“母亲被装在一个浴盆里推出来,她满脸鲜血,一只手高举一大把白发,白发上沾着点点头皮。她喊不出声,声音被咽间的一根骨头堵住了”[9]35。这些恶象在平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端倪,但却深深隐藏在现实中,只流露出一个恶意的苗头。在主人公移动的过程中,这层纱被捅破,世界的走向开始模糊、迷幻。真实现实被打破,不合常理的事情开始出现,并且朝着更加阴暗的方向奔去。
残雪虽然没有对她的人物移动划定边界,但她笔下的人物仍处于一个围城之中,这种交错进一步展示了周围环境的异常,这个“围城”暗含在人物移动的轨迹之中。《归途》中,“我”去找一个房主人,在寻找房主人的路上,去的时候是微微倾斜的下坡,走起来毫不费力,但疑惑的是,回来的时候走的也是下坡路,不用费吹灰之力。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不符合人的思维逻辑,去的时候是下坡,回来的时候应该是上坡。“我”从未搞清这个逻辑,但在读者看来,梦境是不需要逻辑的,只有现实才需要逻辑。这种不合常规的移动真的有空间上的移动吗,还是只是在原地上生成了一个关于房子的梦境,此时这个场景的真实性就受到了怀疑。这种移动模式更确切地来说,像一个闭环火车,在向前移动,却又停留在原地不曾离开。现实的真实性受到了挑战,如果连开放或者是封闭都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这个世界还是真实的吗?真实和虚假的界限被进一步的颠覆。与其说残雪描写的是现实,不如说是“梦境”。真实世界变成了一个缺乏连续性和逻辑性的梦境时空体,真实和虚假的概念在这里被撕裂。
残雪在文本中挑战的二元对立并非仅仅将双方位置颠倒,而是将二者界限打破。她反对形而上学,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叙事方式,对真理绝对化加以否定,以求打破这种封闭僵硬写作体系的桎梏,强调写作中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梦境并非是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是呈现出一种新的亦真亦幻的生存场景,这种生存场景充满了荒诞,荒诞背后却是残雪想要建构的“另外的世界”。
三、“圆的重复”:出走与回归的哲学循环
残雪对现实世界的解构不是单纯的为打破传统写作而解构,而是为了解构传统写作模式,并在拆分的过程中找到新的角度来更深入地理解文本,理解秩序,理解世界。“创新的过程必然是从传统出走,但也必然又对传统多次回归,这样就形成不完整的圆的轨迹运动,经过省略的传统之圆,被突破而又增添新素质的圆的轨迹,有破裂、删除、有变形,因而不再是初始状态的传统。但创新的回归只是片刻的轨迹运动,很快又会离开传统,再度自由的进行无形的‘踪迹’运动。”[16]这个出走、回归的循环过程被德里达称为“圆的重复”。这种旧圆与新圆不断相遇,新圆不断出走与回归,螺旋式上升的新圆,才是解构主义追求的意义。解构的最终目的是建构,而残雪通过解构自己笔下的叙事,在跳出传统叙事的同时,找寻着传统模式之外的新方向。
(一)循环:建构—解构—重构的轮回
残雪在解构现实、解构传统的同时,也是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新的文学世界。残雪不注重传统文学中的情节,甚至刻意隐藏情节在叙事中的作用。但这种对传统文学模式的解构和反叛不仅仅是为了解构而解构,打破秩序是为了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而非一味的破坏。残雪的文学创作更像是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她将传统文学中的中心思想拆分,颠倒、重构各种既有概念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与实践上否定传统的写作原则。在分解中转换角度,将写作中原有的但是在传统写作中被固定了的意义拆分,由此试图产生新的意义。残雪的这种解构策略实质上是用解构的方式来抵御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危机。残雪的作品不是描写正常的、世俗的表层现实生活,而是对自我和人性的深层探索,描写的是一种潜伏在意识底层的潜意识活动,表现的是分裂的个性和灵魂,这是对传统小说叙述手法——某种价值形态的彻底的解构。
残雪解构的不只是传统小说叙述手法,她将这种解构挑战带入了读者的现实认知。残雪采取了一种新型的关系来与她的读者进行互动交流,她解构了读者对现实的认知。她不满足于在文本中拆解现实,构建“潜意识世界”,在文本之外也试图在读者的意识中挖掘隐藏在意识之下不被感知的潜意识。在传统第一人称小说中,读者带入的是一个叫某某的人,这个人有着自己的单独的人物背景,使得读者能明确区分文中人物和读者之间的界限。但残雪却刻意模糊这一界限,在残雪的第一人称小说中,看不到任何关于主人公的身份解释,对主人公的认知被读者从文本的角落零散地搜集,读者被动地处于一种将自身日常经验融入病态、混沌精神领域的过程。不光文中的人物丧失了对外在客观世界和存在标准的判断,“你自己就要发动你里面的自我意识来超越你的旧我”,文本外的读者也被影响了关于自我认知的有效评价。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以逻各斯为手段的努力的爆发成形,一次革命”[17]。这种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不仅出现在残雪的文字游戏中,同样也出现在残雪对读者的心灵影响中。
(二)上升:超越单线,叙事线条双重化
残雪并不是在玩一个不断循环的单一解构游戏,而是在循环时上升意义,这种螺旋式的上升暗合了德里达“圆的重复”的真正含义,也是残雪写作的真正愿望。残雪叙事线条中的复杂性来自多种形式的双重:叙述者的双重、间接引语中的双重、多重情节的重复、还有多种形式的置换等。
残雪试图颠覆逻各斯的秩序,将偏离中心、无理性或反逻辑性的因素引入中心化的、理性的、逻辑的因素之中,这会造成叙述中心的消失。在小说里插入故事,叙述者突然的从一种叙事声音转化为另一种,双重叙述者带来了整个叙事线条的双重化,“这种同一文本中出现的难以调和的不同声音、多重意识、或者言语中心,具有一种颠覆的可能性。”[18]《从未描述过的梦境》中,残雪写了一个描述者和他描述的故事之间的故事。但她并非是将缺乏逻辑的故事掺入理性的叙述者之中,而是将本应占据优势地位的理性和非理性颠倒过来,这种刻意的转换进一步加大了文本的颠覆性,也进一步揭示了残雪写作中的反叛性。文中有描述者和诉说梦境的人,替路人写下梦境的描述者从“不动声色地一一书写下来”,“描述者一天比一天颓唐了,然而他还是倔强地伸着脖子”到“作出认真聆听的样子,实际上什么也没记下”,“只好敷衍的作出在听梦的的样子”。最后,“描述者颓地从石头上下来,郁郁的沉思着”。路人从“他们的口述或机械或晦涩”到“他们诉说的梦境愈来愈离奇”[19],最终没有人再去找那个描述者了。所有的人都在朝一个深渊滑去,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那个描述者未能描述的梦境,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的身份在记录梦境的描述者和对着叙述者讲自己梦境的旅人中来回切换。被记录的梦境和从未被描述过的梦境则是另一条线,插入的梦境和描述者组成了双重的叙述者。变化的描述者和诉说者和那个一直无法描述的空白梦境,动静两条线条相互交织,描述者一直在追寻什么无形的东西,但他最后只是焦急地将目光转向天边,若有所思却一无所获。一个行为怪异,沉溺于自己幻想世界的描述者在寻找一个更为虚无缥缈的梦境,这种对虚无的寻找毫无动机和意义,最终造成意义再一次从读者手中流失。在描述者搜寻那个无法被描述的梦境时,读者也正在搜寻整个文本叙事的中心,最终双方都一无所获。
残雪将现实世界撕裂、重组,建立了自己的精神王国,这种不可以说的玄妙状态正是残雪所追求,也是她想呈现给读者的画面。这种对现实真实的无视确实使残雪在写作时更加深入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潜意识世界,但残雪也并非一味的出离传统,而是在螺旋式地回归。她在被解构的现实世界上,重构了自己的世界,那种无意识的流露建立在真实文本之上,也确实揭开了传统叙事下隐藏的他者。
《变形记》《荒原》《城堡》等作品探讨的是环境的异化造成人的异化,表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精神的荒芜。残雪创作小说的年代,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现代化及其发达的时代,工业化带来的人的异化并非当时时代的主潮。然而,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生活深刻的体悟,让她超越时代的掣肘,先于他人而观照现代性造成的人的生存荒诞性,对人的存在深深地悲悯。这也许是读者在艰难阅读残雪小说遇到重重困难之后,依然相向而行的原因。存在主义哲学主张存在先于本质,人的本质不是自然而然的是后天选择的结果。残雪的小说叙事既解构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本身,更重要的是解构了传统的人的存在,人不再是大写的人,而是无名无姓的“那一个”。在荒诞的梦魇一般的后现代环境下,人是缺乏自由意志,更没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正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特别强调的,正是对人的自由选择的确认,才让每个人在选择的过程中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残雪在看似荒诞、迷狂、梦魇甚至地狱般的小说场景描述中,似乎也在提醒人们,如果对自身的选择不能负责的话,那么世界就是“地狱”。
四、结语
解构主义哲学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残雪的小说以其零散化的叙事结构、矛盾性的人物,以及对现实与虚幻边界的模糊处理,达到了对既定秩序的质疑与重构。她通过非理性的叙事手法,深入探索人性的复杂多面与潜意识的幽暗深渊,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既矛盾又统一的文学世界。这一世界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景观。残雪的小说语言常常是夸张、讽刺、重复的,颠覆了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表现方式,语言意义呈现出不确定性。她的小说创作打破传统的线性时间叙事,采用非线性、碎片化或循环的表现方式,故事情节模糊不清,呈现出很强的“陌生化”效果。小说中人物角色和性格在故事发展中不断变化和转换,能指与所指流动、漂移、变幻莫测,这种不确定性成为她对人的本质、人类的精神世界深入思考之后的符号化表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残雪无疑是一位十分独特的作家。她以其独特的解构主义叙事策略,挑战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规范与审美标准,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范式。在解构与重构的循环中,文学与哲学的交融将不断激发新的思想火花,推动文学批评走向更加深远与广阔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高玉.论残雪小说的“反阅读倾向”[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9):59-69.
[2] 王源.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中的“解构—建构”模式[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34-39.
[3] 欧阳炽玉.精神反思与文化寓言——残雪小说论[J].南方文坛,2024(3):180-185.
[4] 柳慕云,甘菁菁.日本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视角的变迁——以残雪的《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给友人》为例[J].文艺争鸣,2023(7):178-182.
(下转第53页)
[5] 郭莉萍.小说《赤脚医生》中的医学人文关怀和叙事医学[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4,37(3):297-301.
[6]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39.
[7] 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M].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52.
[8] 周学雷.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叙事类型[J].文艺理论研究,2000(4):62-66.
[9] 残雪.从未描述过的梦境 残雪短篇小说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10] 周荣胜.论播撒:作为解构的意义模式[J].文学评论,2003(6):162-168.
[11] 高玉.论残雪小说的“读不懂”与文学阅读的“仅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12(6):124-135.
[12]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49.
[13] 周荣胜.文字场景[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4.
[14] 张方.萨特的存在主义及文学观——重读萨特[J].文艺争鸣,2007(7):44-49.
[15] 残雪.保安[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16] 郑敏.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J].文学评论,1997(2):53-60.
[17] 残雪,邓晓芒.于天上看见深渊:新经典主义文学对话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25.
[18] 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1.
[19] 残雪.残雪自选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358-359.
收稿日期:2024-05-07
基金项目:西藏民族大学2024年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Y2024037)
作者简介:曹曲,女,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