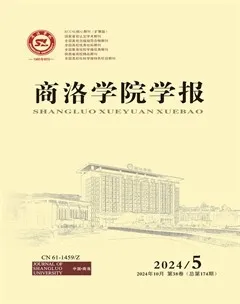郑敏对百年新诗反思的三重维度
摘 要:1990年代,郑敏在对五四新诗运动的反思中提出新诗应向古典“传统”学习而引起学界争议。郑敏提倡学习古典“传统”以达成对百年新诗的反思与总结,这既内在于世纪末思潮与新诗的自身发展,同样也是新诗阶段性自我反思这一传统的体现。郑敏的新诗省思以新诗本体为核心,可从新诗的美学评价、新诗语言哲学探寻及新诗史反思三条路径切入。郑敏立足诗歌本身而力图越出任何诗歌外部的评价话语,以打通古今中西的气度强调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美的艺术。郑敏受语言哲学启发思考一体化认识“文言—白话”的可能性,她认为作为新诗语言的白话应在作为民族无意识的中国古典哲学思维的浸润中趋于成熟。郑敏在对古今诗歌史的总结与反思中,强调在一种具备“历史感”的新诗史研究与新诗写作中,开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互动以走出新诗的独立发展之路。
关键词:郑敏;传统;静观诗学;哲学思维;历史感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24)05-0030-09
引用格式:李文彬,许永宁.郑敏对百年新诗反思的三重维度[J].商洛学院学报,2024,38(5):30-38.
Zheng Min's Three Dimensions of Reflection on Century-old New Poetry
LI Wen-bin1, XU Yong-ning2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2.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Hunan)
Abstract: In 1990s, Zheng Min advocated that new poetry should learn from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which was inherent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trend of thought and the tradition of self-reflection in new poetry. Zheng Min's reflection is centered on the new poetry itself,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the new poetr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anguage th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philosophy in new peotry, and the reflection of new peetry. Zheng Min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 of external evaluation discourse of poetry and emphasizes that poetry is an art of beauty in nature. Inspired by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Zheng Min ponder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S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Zheng Min emphasized a kind of new poetry history research and new poetry writing with "Historical sense".
Key words: Zheng Min; tradition; quietly observing poetic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historical sense
199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对20世纪的总结与反思。20世纪在人类的多灾多难与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中结束,这些经验与遗产沉重且丰富,故而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姿态下,以思考人类生存处境的文化反思于世纪末迅速兴起。以“人的文学”为本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反思内在于此,从王一川、钱理群等对现代文学大师的重排,到韩东的断裂问卷,再到葛红兵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现当代文学的“世纪末”反思始终内含着对文学本体的反思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此同时,中国文学自身也在这一反思与总结中,于1990年代迈入发展的新阶段。新诗作为现当代文学组成部分也在这一发展脉络中,它由1980年代初对社会情绪的抒发转向1990年代对诗歌本体的思考。诗人与批评家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对百年新诗进行总结与反思。
在对新诗的总结反思中,对新诗成就的质疑或辩护是其中一大核心问题,古典诗歌传统这一外在于新诗的强大他者或作为靶子或提供标准从而成为审视百年新诗的重要视点。在对古典诗歌传统的重解与激活中,存在两种逐渐走向偏执的观点。一方面,否定新诗成就的一方会强调一种普遍性的美学标准,认为新诗远逊于古典诗歌,这一论调在新诗史上屡屡出现,曾极端地表现为“古典+民歌”的道路①。另一方面,肯定新诗成就的一方则强调一种历时性的美学标准,如臧棣[1]强调新诗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必然形成与古典诗歌不同的美学追求,他认为新诗之于古诗的独特价值在于新诗因与中国社会现代性遭遇高度联系而开辟出一片未被充分展开的新的审美空间。前一质疑在显示出新诗的不足的同时更多体现的是对新诗的外部观照,后一回应局限于新旧之分的现代性标准且始终没有真正落实新诗的美学样态,从而最终沦落为话语层面的策略。
郑敏一定程度上越出两种观点的对立,她以新诗本体的态度承认现代诗与古诗因时代差异必然存在主题表达与审美追求的差异,但同时强调,无论古今中外,诗之为诗的基础首先是也必须是诗美的标准。另外,郑敏以新诗诗人身份强调以“传统”反思新诗一方面极具冲击力,一方面则内在于新诗自身传统,即新诗史上阶段性出现的藉由古典诗歌进行自我反思。郑敏以打通诗歌古今中西之区隔以求诗美的态度力图把握住诗歌本体这一真问题,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颇有分量的思考。学术界对郑敏的新诗反思多有研究,但现有研究更多以文化政治的眼光考察郑敏所提论题的文化史意义与社会意义,或是将郑敏放置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中,或是以后殖民视角爬梳郑敏的理论来源,反而忽略了郑敏论题中新诗这一核心对象,暗含了将郑敏标签化的危险。本文立足郑敏的当代性姿态及她对新诗本体的强调,从新诗的美学层面、新诗的语言哲学层面及新诗史层面来理解郑敏是如何借助古典诗歌传统反思新诗的,以求在驳杂的话语中探求郑敏诗论的可贵与独见。
一、“静观”诗学下的美学追求
在古典诗歌与新诗的对比中,当下新诗的美学缺憾自然而然成为郑敏百年新诗反思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郑敏提倡古典诗歌美学的切入点。郑敏认为,1980年代初,朦胧诗人就存在追求“颇像满山野花,然而没有多少根”的“浪漫主义+现代派强烈色调的一种美”[2]的问题。但朦胧诗尚有其社会价值,而后朦胧诗人进一步延续了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消化不良”,皮相地宣扬“反文化”等口号,以致在“反诗美”中走向“艺术赝品”之路[3]。如何重建对诗美的抵达,郑敏强调要从可被理解而后转化的自身“传统”出发,立足“传统”这一文化之根后吸收西方诗歌的优点才有可能不被西方同化,其秉持的乃是一种当代性姿态。于是,针对年轻诗人的“无根”写作,郑敏强调诗人应学习体悟古典诗歌中的蕴藉美学。以对古典诗歌蕴藉美学的体悟出发,郑敏联系到里尔克,又将冯至1940年代创作的《十四行集》视作沟通中西的新诗典范,为中国新诗提供了“静观”以达美的诗学思考。
第一,郑敏的“静观”诗学追求的是诗人创作时面向自我的真诚与宁静,其针对对象是1980年代以后颇为浮躁的年轻诗人。郑敏始终强调,诗歌乃是诗人生命的表达,真正的好诗所展现的是诗人真诚流露的自我与先在存在的有生命的语言相互抵达的时刻。有关这一点,郑敏在自己1980年代重拾诗笔的创作过程中深刻领会,而这一体验也内在于其1940年代以来的美学趣味中。郑敏曾谈及《心象》组诗的创作体验,她认为诗歌创作中神秘的灵感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不仅能给人以享受,而且能使读者和作者净化或释放自我,她说诗中“狮子和大象以它们美丽的金光闪闪的毛发和吼声击败了外界对我的压力,在这充满压抑的现代社会中艺术创作的心理医疗作用确实是不应低估的”[4]424。这种强调诗歌净化功能的观点带有古典主义意味,也内在于郑敏的诗歌创作中,有研究者言“构成郑敏诗作独特性的还有一个受中国传统诗意境影响的因素,它使得郑敏诗天然地倾向于纯象征与浪漫主义之间……诗写得非常轻柔神秘,很有点中国传统诗言尽而意未了的韵味”[5]。更进一步,郑敏在对古典诗歌的阅读中重复体验到那些大诗人在书写内心时以宁静自视的重要性。如郑敏分析苏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时认为,苏轼是在自然的寂静中转入对恍惚梦境的书写,而正是此种宁静中的自视使得苏轼“从个人的爱情、生死突然跌入宇宙的黑洞,顿时为诗增加了多少时空的深度。”[6]在这里,宁静状态不仅意味着诗人自视时的诚实,同时意味着大脑越过理性的藩篱后浮现出的更为真实的无意识。她说,“在宁静中让理智安眠,而过去的一些情景从无意识中徐徐升起,突现在心灵的眼前,可能比现场的捕捉更深刻,更强烈。”[4]417此外,郑敏在对年轻诗人浮躁的批评中更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郑敏曾说,“我觉得,诗人,特别是对中国青年诗人来说,有一个‘诚’字非常重要。”[7]264在郑敏看来,后朦胧诗歌以宣言与观念介入诗歌的写作是一种相当功利性的写作,例如某些诗人缺乏自白式精神分裂的体验却硬要模仿普拉斯,结果就是“造作的精神分裂只像衣服似的穿在外面。”[7]265这其间隐含着拉起大旗以占据文坛一席之地的目的。郑敏认为,诗人浮躁或粗暴地对待语言,必然无法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且此一状态下的诗歌语言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工具,故而郑敏劝告年轻诗人“在诗和语言面前要沉静一下容易喧嚣的自我,语言就会向诗人们展开诗的世界。诗来自高空,也来自自己心灵的深处,那里是一个人的良知的隐蔽之处。”[8]
第二,郑敏“静观”的诗学乃是静止与运动的合题,“静”是动态诗歌结构在矛盾运动的张力中所抵达的平衡状态,而静观则进一步表明以沉静的姿态对诗歌结构的展开、体会与沉思。在郑敏这里,“静”并非是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是运动所得以持续的那个平衡状态,其所欲抵达的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认识结构,而是在变动中补充、转化与发展的生命状态。郑敏相信,诗歌是一个各种矛盾力量形成的场,是一个完整地进行自我表达的动态生命,“诗的生命在于矛盾运动,但是在杰出的诗人与诗作中,各种矛盾的力线却能有机地组合在一个统一的场中”[9]。郑敏认为穆旦的诗歌语言即是一例,“它扭曲,多节,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超载,然而这正是艺术的协调。”[10]在郑敏看来,不仅意图表现现代世界冲突矛盾的现代主义诗歌如此,以圆融和谐为最高美学标准的中国古典诗歌同样内含着动与静的合题。郑敏多次分析中国古典诗歌中动与静的相互反衬,在她看来,无论是以静衬动,还是以动衬静,其间都包含着对动与静相互转换以达协调的认识,更深一层内含的是对诗歌结构与世界结构对应关系的想象。故而,郑敏认为,理解一首诗情绪的传达应该将诗的结构分解,观察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郑敏区分了展开式与高层式的诗歌结构,前者层层展开如中国庭院移步换景,后者如高楼矗立给人以直接的震撼。这两种结构分别对应动与静,而每一首诗的结构都是对两种诗歌结构不同程度的采用。
第三,郑敏“静观”的诗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一认识方式使得郑敏越出现代性逻辑下的新旧之分而强调的是诗人面对自然世界时的普遍感受。诗人,无论古今中西,都必然要在诗中处理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当诗人作为个体面对自然世界之时,其感受到的人的渺小或人与自然的相融都因越出时间与国族的限制而令人感动。在这一点上,里尔克的诗作与中国古典诗歌高度相通,二者的交点实际是郑敏早年就已形成的“知性诗学”。1980年代初,郑敏沿其1940年代的思路强调个人对生活的综合能力,强调针对时间、空间等普遍性范畴进行哲思,一如她在1940年代强调的战争背景下树的宁静。“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像我从树的姿态里/所感受到的那样深/无论自哪一个思想里醒来/我的眼睛遇见它/屹立在那同一的姿态里/在它的手臂间星斗转移/在它的注视下溪水慢慢流去/在它的胸怀里小鸟来去/而它永远那么祈祷,沉思/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11]。这种对“玄秘的静凝”[12]的追求,在里尔克和中国古典诗歌那里也能感受到。里尔克那种在寂寞中静观世界的感知方式可以让人体会到难以讲明且余韵悠长的情绪,这一点与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存在相似性。对这一体悟方式的强调使得郑敏把中国古代诗人、现代西方诗人和当下中国诗人都只看作面对自然与世界的个体,诗人正是在对人与自然的体悟中触及到“存在”问题,于是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相通性的里尔克和与中国古典诗歌,成为郑敏理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两大来源。据此,郑敏心中的新诗典范首推冯至的《十四行集》,她认为“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容反映了中国新诗与世界诗潮的交流和渗透,是4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一座高峰,它融汇了古典诗人杜甫的情怀,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歌德的高度哲理和奥地利早期现代主义诗人里尔克的沉思和敏感。”[13]224在这里,中与西、古与今都融汇在一起,它们共同在冯至的诗中体现出这个处于战争中的当代诗人对生命的沉思。郑敏年轻时更多强调里尔克“诗的雕塑品质”[14]的影响,1990年代郑敏更深刻地指出里尔克不是遁世者也不是纯粹美学追求者,他深刻地描绘了时代对人性的冲击。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杜甫恰好与里尔克在冯至的诗中相遇。于是,郑敏在美学层面冲出诗歌古今中西的区隔,强调诗歌所具备的普遍性的美学价值,一如她对这一认识美学下的诗歌样态及人生状态的文学化描述,“我突然看见一个小女孩,她非常宁静、安谧,好像有一层保护膜罩在她的身上,任何风雨也不能伤害她”[15]。
二、积淀民族无意识的诗歌语言
在对新诗美学成就不足的归因中,新诗所用白话文成为一个中心关注点。尽管相较于古诗语言于晚清的模式化,使用白话的新诗表现出无尽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古诗语言的精炼与圆熟也在某种意义上凸显出新诗白话的实验性质。如何进一步发展新诗语言?语言工具论视角下的看法常常强调打磨诗歌技艺的唯一维度。而郑敏在对胡适以通俗为最高目的的白话的反思中,以及在对索绪尔、德里达等人的语言哲学理论的借鉴中,以语言本体论的态度消弭了文言与白话的绝对对立。在对文言与白话一体化的思考中,她进一步发现,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都涉及到更为根本的民族思维方式与文化特性,丰富白话的重要手段是学习并吸收文言所蕴含的内化为民族思维方式的中国哲学传统,郑敏由此凸显出与存在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相通且贯穿了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史的老庄哲学。
第一,何以郑敏认为语言于诗歌而言能触及本体而非作为工具?这是因为诗歌语言传达了表现本真生命的无意识。郑敏的这一认识直接来源于西方后现代哲学,而其更深的渊源则在老庄哲学当中。受后现代主义哲学影响,郑敏认为无意识乃是生命意志的本源,而人们日常是在理性意识的控制下生活,诗人要寻求本真的生命就需要释放无意识。诗人写诗必然依靠语言,但语言本身即意味着被制造的非本真的思维结构,而“无意识观念只有物表象而没有词表象”[16],那么诗人如何能以意识的语言触及无意识呢?郑敏进一步借助拉康与德里达等的理论区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在郑敏看来,日常语言是以通俗表意为最高目的的符号工具,而诗歌语言是隐秘的有生命的存在,需要诗人寻找它们。在此,郑敏对两种语言的划分并非依据二者形式特征的区别,而是强调二者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即某种意义上日常语言乃是工具,而诗歌语言就是生命本身。郑敏诗学理论中常常将诗歌语言直接省略为语言,因为在郑敏看来,诗歌语言乃是语言的本质,因此有学者说“在郑敏的诗学思考中,诗、语言、生命这几个概念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最好的诗歌,是最凝聚和新鲜的语言,在那里面也就有最强的生命力。”[9]据此,郑敏进一步在对海德格尔的理解中强调语言与存在的相关性,“据我的理解,海德格尔的being就住在语言里这句话,being就是生命,活生生的运动中的生命。”[7]255那么诗人如何才能找到诗歌的语言?郑敏借助海德格尔的语言论在华兹华斯那里发现在宁静中体味心灵、认识世界才能在心灵澄明中听到诗歌语言。以此视野重新打量诗歌史,郑敏发现不仅中外诗歌都表现出这一特质,而且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古诗背后的哲学思想更早地触及这一问题,而存在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哲学正是受了老庄哲学的启发走向了对语言本质的深掘,“解构主义所主张的‘无’生万有的思维使它十分接受老子关于‘道’的宇宙观及中国的阴阳相互转换的理论”[17],“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强调‘实’中之‘虚’,‘有’中之‘无’,‘无’为万物之源时就走出了西方一贯的重实、重理性逻辑、重‘有’的哲学传统,而走近了东方的老庄哲学。”[18]郑敏对德里达等哲学家理论的运用遭受了诸多批评,许多批评家认为郑敏运用新兴理论时,缺乏对理论背后“历史现象的整体的尽可能准确的把握”[19]。但应当认识到,郑敏并非以学者的身份处理理论本身而是以诗人的身份思考新诗,故而她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东方哲学的角度看德里达”[20],即重点不在郑敏以后现代主义解释中国哲学,而在于以中国哲学的视角内化西方理论以解释诗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
第二,郑敏于1990年代的语言本体论思考是对1980年代年轻诗人语言论的反思与推进,这也是新诗自身语言观念发展规律的体现结果。新时期之初,朦胧诗因承担了社会反思的责任、为民众提供了情感价值而获得巨大关注,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诗歌写了什么。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诗歌丧失中心位置的同时也在自我深入,诗人开始更多关注怎么写的问题,语言成为关注的焦点,1980年代的年轻诗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在写作技法层面上借助了西方语言论诗学。韩东受到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影响提出著名的“诗到语言为止”,他的直接目的是反对以杨炼为代表的崇高美学,为新诗提供新的美学形式。由于尚未深入到对新诗本体的反思,所以即使诗人们后来在理论上将“诗到语言为止”扩展为一种略显空泛的诗歌理想——即一反中西古典诗歌以“隐喻”建立起的两座大山而另觅诗的新路。但是从诗歌实践来看,“诗到语言为止”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只成为一种叙事手法,甚至沦落到仅仅“玩弄文字技巧”[21],远未完成对诗歌本体的反思。诗人对“怎么写”的聚焦使得语言本身成为一个问题。而郑敏本身就是学哲学出身,她此时既沿着她的专业思路也内在于新诗自身的发展逻辑,在德里达对汉语的论述中首先找到了切入文言的路径,她说,“德里达认为汉语文字以视觉现实为基础的象形体系由于其不受抽象思维、逻格斯及语法的框限,可以免受形而上思维的危害。这些自然与‘字思维’的理论内核有极密切的联系,但又超出了审美范畴,而直接进入母语与民族文化特性关系的语言哲学层次。”[22]以民族文化特性为标准,郑敏认为现代汉语的欧化现象有偏离民族文化的危险,因此她强调文言之于白话文的借鉴意义,进而强调古代汉语中蕴含的中国古典哲学思维的重要性。
第三,郑敏认为诗歌语言内含着积淀了表现民族经验与智慧的民族无意识,故而白话作为文言在精神而非形式上的延续,同样承载着贯穿了中国诗歌史的老庄哲学的阴阳和谐思想。在郑敏看来,诗语乃是诗人在宁静中沉思而得,而中国古典诗歌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不仅积累了“倾听语言”[9]的经验,而且蕴含了民族思维方式与文化特性。况且古典诗歌的语言探索本就不以日常交流而以诗歌本身为目的,而新诗所用白话文起初是以通俗表达为目的,那么新诗写作者就必须想办法改造白话文。文言无疑是一个绝佳范例。郑敏由此倾向于把古典诗歌的文言看作成熟的诗歌语言,而把新诗所用的白话看作改造尚且不够的日常语言。在这一点上,郑敏遭受了诸多批评,许多批评家认为尽管白话作为诗语仍需诗人进行改进,但将“一种散文化的口语发展为文学语言”的行动应当放在新诗传统的延长线而非在否定了新诗成就后转而回望古典诗歌[23]。此处的问题在于,郑敏虽将古诗看作借鉴资源,但她为强调这一点过度突出了“传统”的制度性。批评家与九十年代年轻诗人分别认为这隐含了对新诗历史及当下新诗合法性的质疑,故而纷纷批评郑敏提倡“传统”是为保守。不过要正确理解郑敏对古诗的提倡,还是要看她提出的改造白话的办法。郑敏的答案是仍旧要回到“静观”上去,也即这仍旧是诗歌美学而非诗歌身份问题。如何做到这一点?郑敏强调的是古诗背后蕴含的老庄思想。具体来看,郑敏是以对古典诗歌语言艺术的分析入手,强调古典诗歌传统的审美意义,进而强调这些美学标准背后的古典哲学尤其是老庄思想对催熟现代汉语的重要性。在《试论汉诗的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一文中,郑敏所提最为核心的当为“简而不竭” “对偶”背后的阴阳和谐思想。“简而不竭”即用词简练但意蕴不竭,郑敏在分析杜甫《山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时强调的并非是杜甫选词能力之高,而是认为杜甫在结构诗歌时以动与静、近与远等“宇宙的两种力量”的“对称设计”完成了片语深意的效果。也即,杜甫《山寺》的简而不竭不仅仅在于杜甫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更关键的是,杜甫以中国古典哲学的自然观念在其心中重构了山所在的天地一方并此方天地为背景定位了山寺,这乃是“先验性的山水画式的场”[24]。郑敏在解释对偶时进一步直言其所要强调的是哲学问题,“对偶作为一种诗歌艺术,在美学上反映了中华哲学中的阴阳相反相成的原则。令人赞叹的是,几千年前中国哲学就能够既认识到宇宙间有矛盾的力量存在,而又不陷入二元对抗的狭窄思维……对偶并非形式,而是天地人间事态的差异及差异中的维系,从对偶的关系观察自然与人世,就能深入地了解天地的深奥,人世的庞杂。”而抵达这一点同时与诗人的精神境界相关,郑敏强调超我之境的高妙,认为“超我”之境是“在抒情写物之外”又一重天,“超脱、自由、潇洒的程度愈大,也就是境界愈高”,想要实现这一点,“诗人平时必须有‘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修行”[25]。
三、建立具备“历史感”的新诗写作
出于对彼时新诗缺点的历史溯源,也出于对百年新诗的整体反思,郑敏提倡“传统”时带有明显的历史眼光。郑敏在对五四白话新诗的反思中发现,二元对立思维致使新诗从产生之际就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式的阵地战思维,这一思维发展至极端表现为“‘文革’时期的批判文章与大字报汇编”的斗争语调,且一直延续至后朦胧诗人“Pass北岛”口号背后的前辈“不死”而我们就“不活”的“‘不破不立’的公式”[13]233。郑敏提醒年轻诗人们,诗歌并不会像电子产品一般被淘汰,古今中外的诗歌处在一个共时性的诗歌空间被筛选与阅读。于是,与新诗一味求新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旦拉开距离进入时间长河以审视古典诗歌,就会发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判断标准不是政治的而是美学的,古典诗歌的诗歌史本身即已呈现出可作为新诗典范的自足历史。那么如何解决新诗的独立性问题?郑敏给出的答案是,在一种具备历史感的新诗史研究与新诗写作中,重新开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互动,如此,诗人和批评家以历史的眼光不断对新诗史进行反思以获取经验教训,而诗人自己则在一种具备历史感的创作中建立真正的主体性。
郑敏强调在历史的眼光下以学术化的客观姿态反思新诗史,她所设想的是独立于社会运动之外的健康的新诗发展之路。这一被许多以文化研究为视域的学者认为是过于理想化的思考,体现出郑敏的大胆锐利及其明确的新诗本位立场。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一文有一核心观点:二元对抗式的政治思维断绝了新诗自由发展的多条道路。她认为,针对朱经农等“提出应当白话文兼容古典诗词的艺术”的观点,胡适等并非是通过学术辩论的方式使之溃败,而是“将学术讨论完全置于政治运动之下,弄得壁垒森严,以至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这一场十分重要的学术探讨没有能健康地进行下去。”在郑敏看来,“我们每次的文化运动都渗透非学术的政治性的激动”[26]。她将1950年代到1970年代政治语言对诗歌语言的影响看作是对二元思维的极端发展,并指出朦胧诗人“将逆反看成创新的驱动力……是长期将诗歌自身的发展看成人为的‘运动’的可悲的后果”[27]。郑敏承认五四设立二元的有效性,她认为五四时有效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失效之后却未被清除以致造成诸多恶果,郑敏的这一意见随即引发诸多批评。在当时,延续着1980年代批判传统的思路,许多人并不认为五四设立的“传统”与“现代”的对抗此后丧失了其历史效用,如许明就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思想杠杆”[28],即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问题都必须放到这一框架内看待,而新诗作为其中的产物之一也必须放入这一大框架内看待。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以许明为代表的学者所强调的现代化视野仍旧是新诗外部的问题,其根本的问题意识并非是新诗,而是新诗之外的文化问题。与之相比,郑敏尽管为强调新诗所受的损害而故意夸大了新诗史自身发展的紊乱,但这更体现出郑敏对新诗的深厚感情,以及郑敏基于自身经历所作的历史反思的沉痛、锐利与无畏。郑敏始终强调诗乃是生命的体现,再联系到她同时凸显的社会意识,郑敏显然将新诗史的理想道路放置在“人的文学”这一大结构中,也就是说,郑敏对新诗史的思考始终隐含着对一种“非人”的威胁的警惕。也正因如此,郑敏认为新诗始终未能在一种针对自身发展逻辑的反思与建构中成长起来,而对于汉语本身及汉语的未来,也始终未能展开以新诗为本位的讨论。如此,才能理解郑敏与学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29]整体氛围的深刻共振,也才能理解郑敏提出不断与古典诗歌发生交互的新诗道路才是正途的观点并非仅仅是逻辑或学理层面的反思,其间更蕴含着郑敏反刍自身经历后对新诗史的诚挚发言。
郑敏强调具备深刻历史感的新诗写作才是新诗能够独立发展的根本底气,她的针对对象是青年诗人匮乏历史感的写作。郑敏在1980年代末对年轻诗人所作的批评强调的是诗人应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反思,而于1990年代体现出的,对年轻诗人们以“历史的个人化”原则建立起的与古典诗歌的联系的不满,更多指向以历史为中心的伦理意识与承担精神的建立。
1980年代末,郑敏认为当时年轻诗人的创作完全丧失了历史感。她认为,第三代诗人转向只写“我”的后现代写作,所以“我”的厚度成为诗的核心问题,但第三代诗人的“‘我’的贫乏和成长的创伤是文化饥饿的结果,也是长期与世界思潮隔绝被从世界文化的大循环中割断的结果。本质上缺乏个性,营养不良,表面上又闪闪发光。这个贫乏、营养不良的‘我’,在意识深处没有历史,没有人类的命运,没有昨天和明天,而他(她)的今天又是如此闭塞,他(她)的敏感缺乏生活的挑战,和世界文化与心智的挑战”[13]237。于是,郑敏强调“传统”的丧失导致了青年诗人只能写出无历史感的“我”。如今来看,郑敏对1980年代末新诗的判断存在偏颇,其所涉及的仅仅是一部分青年诗人,且其所批评的诗人中如翟永明等涉及的文化意义上的历史反思虽确如郑敏批评的那样存在“忘记宇宙”[30]的倾向,但的确为女性诗歌打开了相当大的空间且其对女性意识的启发意义一直持续至今。不过,以非非主义为代表的“反文化”倾向确实在当时声势浩大,郑敏当时以此为基准整体考虑诗坛也应得到理解。
进入1990年代,年轻诗人在“历史的个人化”原则下同样要求建立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间的联系,然而在郑敏看来,年轻诗人所谓的“个人化”恐怕只是一种叙述手段甚至是话语策略,或如批评家所言是一种对“历史剩余的快感”[31]的沉溺。如何理解郑敏对年轻诗人的批评,可从1990年代年轻诗人对“杜甫”形象的塑造入手。1990年代,西川和萧开愚较为典型地意图建立与杜甫形象的联系,二人同样强调诗人要以主体精神对古典诗歌反刍后表现或解决当代问题,但同时却相当程度地求助于非“我”的、诗歌外部的文化实践。这一点正与郑敏坚定的诗歌本体立场相反,也与郑敏推崇的1940年代冯至对杜甫的转化不同。因此,二人并未真正在古典诗歌与新诗间建立内在关联,而是在外部比较的意义上对古典诗歌与新诗作一处境上的对照。其中,西川在对“我们已经是世界市场、世界消费的一部分”[32]的反复强调中塑造出相当无力的诗人形象,而在与不可复制的“杜甫”这一道德形象的对比中,当代诗人已然成为无奈但无过的犬儒形象,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西川《杜甫》一诗中“我”与“你”(杜甫)的区隔:“你的深仁大爱容纳下了/那么多的太阳和雨水;那么多的悲苦/被你最终转化为歌吟/无数个秋天指向今夜/我终于爱上了眼前褪色的/街道和松林……千万间广厦遮住了地平线/是你建造了它们,以便怀念那些/流浪途中的妇女和男人/而拯救是徒劳,你比我们更清楚”[33]。诗中的杜甫成为一个久已远去且不可再现的道德性形象,而“我”则终于放下了悲苦爱上眼前的松林。萧开愚则说道,“我写诗以主流自任……我年少时身上疯狂着一个慈悲的万能皇帝,‘他’后来降级为官僚。帮助我国诗人成熟性格和风貌的唯一位置官僚位置,承担职权的位置,儒家传统挥之不去;不是皇帝和人民,不是无所顾忌的超专业知识分子,只是斡旋实效的官僚”[34]。萧开愚所想象的是一种沿袭士的传统的政治责任,而当1990年代诗人进一步边缘化后所谓政治责任则变为一种无力的演绎并进一步降格为牢骚而非反思。例如,《向杜甫致敬》“该诗一共十节,每节都聚焦于当代中国最受诗人关注的一个社会或政治问题”[35]诗中所建立起的古今联系并非是以诗人主体为中心的精神关联,而是以外部环境所规定的诗人行动为中心的现实模拟,也即不是杜甫在当下会如何判断与反思人的处境而是杜甫在当下只能对社会议题怎么反应,杜甫这一形象中心在诗中并未承担起对现代中国的表现、总结与反思,而只是提供了对各类琐碎事件的政治态度。尽管相较于西川对古典的借用,萧开愚更进了一步,但这一效果借郑敏的话来说不是文学的而是政治的。事实上,郑敏曾经关注过西川1990年代初诗歌语言转向“混杂”[36]的变化,也曾就西川“写作风格发生的变化”的问题与他有过交流[37]。但郑敏此后仍然对年轻诗人的写作持批评态度,她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新诗离诗本身的历史任务很远。我们听到很多喧嚣声,然而那似乎只与流派的声誉、地位、排行榜有关;又有不少个人的个性展览,多少都带有一些闯名牌的气味。至于生命的价值、伦理观、人类的道路、未来的命运,诗人,这曾被雪莱誉为预言家的诗人,却很少有时间、有心思去过问。”[38]郑敏对年轻诗人所谓“在写作中被发明出来的”“拓展了诗歌审美的资源”[39]的个人化的历史颇不信任。郑敏的批评是准确的,1990年代的年轻诗人们以历史的个人化原则建立的与古典的关联相当表面化,不仅未能完成郑敏所期待的对民族无意识的继承发展,反而使诗人达成了蜷缩在日常生活中隔靴搔痒式的发言,诗人所谓个人化乃是一种抽身的姿态,即以“介入但不承担责任,‘见证’但不需要‘作证’的外在旁观态度”[40]处理现实从而演变为与现实的合流。针对于此,郑敏所呼吁的具备历史感的写作,也就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反思,而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以历史为中心的伦理意识与承担精神。
四、结语
郑敏晚年在对新诗史的反思中提倡学习“传统”,这既体现出她作为诗人对新诗的拳拳之心,也体现出她作为理论家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之深。事实上,郑敏的思考相当“寂寞”[41]。尽管1990年代郑敏引起了一定反响,但这几乎都发生在诗歌界之外,1990年代新诗创作很少受到郑敏提倡“传统”的影响。新世纪以来郑敏仍在推进相关思考,但诗坛内外的回应都越来越少。不过尽管如此,古典诗歌传统特别是郑敏由语言文字出发强调的古典哲学传统,将始终作为人们思考新诗未来发展时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以此来回看郑敏晚年对“传统”的强调,当看到一个锐意随心又沉潜寂寞的思考者形象。郑敏突然提倡“传统”,既是对新诗发展出路的沉思,又是将自己设为火力点以改变诗歌边缘位置的“策略”。郑敏曾说,“我认为诗歌里有三条道路。一条是文艺的,一条是哲学的,一条是政治的。最好的诗人是把三条道路结合在一起。”[42]郑敏始终努力践行这一点,她自觉把对现实社会沉迷物质的批判、对历史发展中有害思维的清理都划入自己的思考范围内,其文字既体现着知识分子承担的人格魅力也闪烁着智者的思维光芒。
注释:
① “古典+民歌”的诗歌发展道路由毛泽东提出,是195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末期有关新诗未来发展的主流观点,新时期以后批评家开始反思这一观点对新诗自身传统的忽视及由此导致的对新诗自身的损害。
参考文献:
[1]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J].文艺争鸣,1998(3):45-50.
[2] 张天佑.“和你通信往往促使我思考和计划”——郑敏致唐祈十一封信[J].新文学史料,2022(2):137-148.
[3] 郑敏.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J].诗探索,1994(1):16-31.
[4] 郑敏.诗和生命[M]//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周星.象征主义与中国诗歌传统的交融——九叶诗人郑敏和里尔克的比较研究[J].中国文学研究,1989(1):98-103.
[6] 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J].文学评论,1995(6):79-90.
[7] 郑敏.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下)[M]//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 郑敏.探索当代诗风——我心目中的好诗[J].诗探索,1996(2):1-7.
[9] 谭桂林.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J].广东社会科学,2003(3):37-44.
[10] 郑敏.诗人与矛盾[M]//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
[11] 郑敏.郑敏文集:诗歌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3.
[12] 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M]//唐湜.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143.
[13] 郑敏.回顾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展,并谈当前先锋派新诗创作[M]//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 张桃洲.从里尔克到德里达——郑敏诗学资源的两翼[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26-31.
[15] 郑敏.我的爱丽丝[M]//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14.
[16] 马元龙.无意识[M]//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420.
[17] 郑敏.文化的问题[M]//郑敏.郑敏文集:文论卷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07.
[18] 张大为.郑敏访谈录[J].诗刊,2003(1):17-19.
[19] 张志忠.世纪末回眸: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考[J].文艺评论,1998(1):34-47.
[20] 郑敏.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M]//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62.
[21] 于坚.关于“诗到语言为止”[M]//张清华.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81.
[22] 郑敏.余波粼粼:“‘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的追思[J].诗探索,1997(1):53-60.
[23] 陈太胜.口语与文学语言:新诗的一个关键问题——兼与郑敏教授商榷[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6):10-14.
[24]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岩波定本[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
[25] 郑敏.试论汉诗的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J].文艺研究,1998(4):83-91.
[26]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5-20.
[27] 郑敏.重建传统意识与新诗走向成熟[J].文艺研究,1999(1):107-110.
[28] 许明.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J].文学评论,1994(4):114-120.
[29] 李泽厚.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与陈明的对谈[M]//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北京:中华书局,2014:145.
[30] 郑敏.女性诗歌研讨会后想到的问题[J].诗探索,1995(3):60-61.
[31] 张光昕.“九十年代诗歌”症状简报[J].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6):27-31.
[32] 西川.传统在此时此刻[J].当代作家评论,2011(4):137-145.
[33] 西川.杜甫[M]//西川.西川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07.
[34] 萧开愚.回避[M]//萧开愚.此时此地:萧开愚自选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84.
[35] 王德威,刘倩.六个寻找杜甫的现代主义诗人[J].当代作家评论,2019(4):183-193.
[36] 姜涛.“混杂”的语言: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M]//李岱松.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300.
[37] 洪子诚.学习对诗说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1.
[38] 郑敏.诗与历史[M]//郑敏.郑敏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59.
[39] 西渡.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J].诗探索,1998(2):11-17.
[40] 余旸.历史意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90年代诗歌”现象再检讨[J].文艺研究,2016(11):66-75.
[41] 王家新.不灭的生命之光——纪念郑敏先生[J].文艺争鸣,2022(3):14-19.
[42] 张洁宇.诗学为叶,哲学为根——郑敏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4(8):80-86.
收稿日期:2024-07-26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HNJG-20230273)
作者简介:李文彬,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