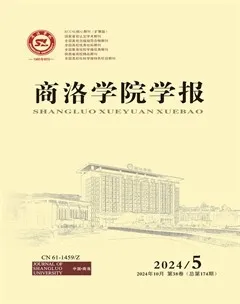《河山传》的世情叙事
摘 要:贾平凹《河山传》的写作继承与拓展了传统世情小说的叙事领域。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贾平凹承袭了世情小说对人物细致的描摹,构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小人物形象,作者抓住时代特征讲述了四十多年间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借此传达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在对农村与城市不同地域的世态风俗与社会人性的描述上他承继了世情小说对于社会众生相的刻画,加注了改革开放后四十年来的社会背景。在叙事语言上,作者将方言俚语与具有古典意蕴的话语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商州方言的陌生化与古典文学的典雅化夹杂,体现了新世情小说雅俗共赏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贾平凹;《河山传》;新世情小说;小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24)05-0009-07
引用格式:韩宇.《河山传》的世情叙事[J].商洛学院学报,2024,38(5):9-15.
The Narrative of the Human Relationship in
The Legend of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HAN Yu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BaoJi 721013, Shaanxi)
Abstract: The Writing of Jia Pingwa's The Legend of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inherits and expands the narrative horiz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novels about human relationship. In the shaping of the characters, Jia Pingwa inherit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about human relationship and constructs the small character imag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author captu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o tell the stories of these little people in 40 years, so as to convey the sense of national distress.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customs and social human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rural and urban areas, he inherited the portrayal of the social life of the novel, and adde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40 year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arrative language, the author skillfully integrates the dialect slang with the words with classical meaning, and the defamiliarization of Shangzhou dialect and the eleganc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embody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novels about human relationship.
Key words: Jia Pingwa; The Legend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new novels about human relationship; little people
贾平凹第20部长篇小说《河山传》较以前更加疏朗,作者也越写越从容,充分地彰显了贾平凹超乎寻常的概括力和提炼能力,作品以二十万字左右的篇幅叙写了从1978—2020年左右几代进城农民的故事,交织着民营企业家的风云际会。故事讲述来自农村的六趾洗河到城市邂逅了民营老板罗山,演绎了这两个小人物的故事,堪称一部小人物的“列传”和当下世风的“喻世明言”。底层人士、商界精英、政治官员在书中纷纷登场,以进城农民工和民营企业家这两个群体的命运书写了中国四十多年的发展进程。
《河山传》出版后学界的关注度很高,评论文章多从艺术形式、人物命运和创作方法等角度展开,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读者对该书的理解,还拓展了贾平凹研究的学术空间。孟繁华[1]认为,《河山传》是一部编年体长篇小说,有酷似古代中国史书的写法,即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和事件为纬。它本质上还是一部当下世风的批评书,是小人物或底层人民生存和精神状态的文学报告,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喻世明言”。张学昕[2]认为,作家在叙事中选择两位最重要的核心人物洗河和罗山作为“传记”的传主,其叙事意图就是通过两个小人物的命运和人性状写大历史,并采取对生活和现实的民间化、俗世化处理,将世相和人性的真实样貌呈现出来。王春林[3]认为《河山传》具有三个艺术形式方面的特点,一是编年体方式的自觉运用,二是一种双线合一艺术结构的营造与设定,三是戏剧性手段的适度运用,以及对一种以不写为写的暗示性描写方式的精妙运用。贾平凹的创作一直以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河山传》就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尤其在叙事上继承与拓展了传统世情小说的艺术手法,展现出具有当下社会特色的新世态风情,塑造了一群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形象。本文试图将《河山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世情小说进行更深入的比较分析。
一、新人物志:时代背景中的人物群像
世情小说在明中叶进入繁荣时期,因其“在自然流动中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发生的寻常人事来书,不追求凭借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达到吸引听众的效果”[4],受到市民阶层的广泛喜爱。孟繁华在《正史之余,也在正史之内——当下“新世情小说”阅读笔记》中对新世情小说做了定义,“所谓新世情小说是相对于旧世情小说而言,就是超越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陈陈相因的写作模式,而是在摹写人情世态的同时,更将人物命运沉浮不定融汇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社会变革之中。”[5]如果《河山传》只写了罗山或洗河便构不成世情小说,之所以称它为新世情小说,是因为书中有众多性格鲜明且与世情有关的新小人物。贾平凹继承了传统世情小说以简洁的故事情节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的特点,在小说中描摹了三类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作者将他们放在时代背景中,通过曲折离奇的故事书写了这三类人物的非寻常性。洗河既是踏实可靠的传统农民,又是在新时代下进城打工且站稳脚跟的新农民工;罗山既是精明狡诈的传统商人,又是知人善用的民营企业家;呈红与传统古典小说中大家闺秀的形象完全相反,她是具有“疯癫性”的新时代女性。福斯特[6]提出了著名的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的分类理论,其中圆形人物是指文学作品中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贾平凹在小说中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三类性格有矛盾冲突的圆形人物。洗河是成功融入城市的新农民工形象,他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农民工进入城市最后过上了好日子。洗河既是传统古典小说中善良、踏实、憨厚和没见过世面的农村人形象,又是新时代背景下进城的新农民工形象。
“进城农民工”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并非陌生话题,在其很多小说中都有涉及,例如长篇小说《高兴》,以及短篇小说《土地》《观我》《针织姑娘》等。《高兴》中的刘高兴、五富和黄八“他们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并对于自己如何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始终感到惶恐和困惑”[7],无论是新一代进城的农民还是传统的农民,他们虽然对城市的态度不同,但无一不承受着深重的精神痛苦。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中,永远也摆脱不了“他者”的身份和地位。在《河山传》中,洗河是成功融入城市的农民代表,这是“洗河”这一人物形象与以往贾平凹书写的农民工的不同之处。
尤恩在提出了用三根轴线区分人物类型的主张,其主张是对人物特性的宏观描述。胡亚敏在《叙事学》中将静态至发展轴解释为“静态一致的人物特征一般从头到尾无重大变化,人物一出场就固定了”[8]144。洗河作为典型的进城农民工形象,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洗河的成功首先是因为他自身聪明,这一点在小说中多处都有体现。例如在与文丑良聊天时,洗河虽然早就不上学了但是还能完整地背诵出《夸父逐日》。当洗河和楼生茂分离时,楼生茂想让他帮忙寻找女儿,于是把标记好信息的照片给他,但洗河没要照片,只看了一眼就记住了所有重要的内容。其次洗河非常重情重义。他对有知遇之恩的罗山绝对忠诚,尤其是听到罗山去世的消息时他反应非常强烈,先是不相信,直到看见尸体后昏倒过去。在身边的人遇到难事时,他会尽量帮忙。楼生茂的女儿楼小英因父亲的死求助洗河,他便拿十万块给楼小英来报答师父的恩情。洗河本就是善良的人,城市跌宕起伏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内心的本质。
作者将洗河突然享受高档生活时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形象地刻画了出来。罗山在西安参加会议时睡不惯高档酒店,便让洗河睡在酒店。酒店里一切都极其奢华,洗河一开始感觉到约束,不敢随便坐怕弄脏白床单,也不敢随便吐痰、掸烟灰。当他住了两晚后不仅放松许多,甚至产生了搞破坏的想法,“几次想抬脚要把鞋印踩在那高高的贴了壁纸的墙上,开窗时猛地用力去扳把手,想让把手断裂”[9]119。贾平凹对洗河这些想法的描写与《陈奂生上城》中高晓声描述的陈奂生第一次进入高档场所时的反应高度一致。作者运用心理描写和动作描写,把一个老实憨厚但没见过世面的农民骤然来到高档场所时的心态和情态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贾平凹在《河山传》中不再关注农民工自身的变化与成长,而是将城市作为变化的客体,跳出视角之外思考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对于这个群体的影响与改变。洗河之所以能成功融入城市并且扎根于此,是因为他聪明善良且重情重义,依靠踏实的工作与圆滑的处世站稳脚跟。同时,也因为他身处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中国以今日之趋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越来越包容,让更多进城后的农民工有了立身之处。
罗山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形象,贾平凹对他的塑造继承了世情小说《儒林外史》中对于商人正面形象的描绘,例如庄濯江是成功的商贾却没有一丝铜臭,他满腹风雅且慷慨豪迈,将生意让给别人。再如王太、季遐年、盖宽和荆元市井四大奇人,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低下操持着“贱业”勉强为生,但精神世界却极其丰富,他们个性洒脱、多才多艺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作者对于商人的态度与古典小说《镜花缘》有相似之处,两部小说都客观地展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之处,塑造了集精明能干和讲求情义道德于一身的商人形象,他们唯利是图但也善良、知恩图报、重情重义。在《镜花缘》中,每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林之洋都会竭尽所能,唐敖救助那些由花神转世的女子时他会全力支持,并且他还对唐敖的子女不离不弃地照顾。《河山传》中,民营企业家罗山有经商和企业管理的头脑,把事业做得风风火火。他作为企业的管理者绝对不会搅浑水,面对跟他最亲近的洗河也会公事公办。当洗河不按规定自作主张拿十万块赔偿给楼小英时,他并没有网开一面,而是说“这不是十万元的事,不按规矩办事,一分钱也不行。公司里,不论是部门负责人,还是一般员工,包括看门的、扫地的、烧水的,我要的是忠诚和能干,忠诚的庸才和能干而离心离德都是祸害!”[9]220罗山不用他家族的人,而是善用有能力之人。他用人时除了考察忠诚以外,还注重发掘个人的才能,会根据洗河擅长的东西来安排他的工作。他一开始看洗河会爆爆米花,就安排他照顾老爷子,负责逗老爷子开心。后来洗河用小聪明解决楼盘工区的一个大麻烦时,罗山便看重了他的能力,让他跟在身边处理琐碎的事务。罗山从来不以貌取人,肖光全嫌许从阳脸抽搐形象不好时他批评了肖光全,他不仅不嫌弃洗河的长相,还买西装改造洗河。
传统世情小说借助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深入剖析社会世态人心,以达到劝世救世和移风易俗的效果。贾平凹的新世情小说一改传统小说中善有善报的结局,罗山的一生轰轰烈烈,创下了很大的产业,但是最后却死得轻飘飘,简单又毫无意义。“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从骨子里承续了更多的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髓,与之有着一种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性。”[10]贾平凹受中国佛教文化浸润很深,对佛禅和老庄等人的思想深感兴趣,他是于尘世中静修佛性之人,他的小说也洋溢着佛道的意味。作者故意安排企业家折腾到最后却落得一场空的结局,有一种“佛性”的因素暗含其中。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随时发生变故,书中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和悲剧性。罗山带有突出宿命色彩的奇异死亡,可以看作是民营企业家的命运随着现实生活中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跌宕起伏。
小说中还出现了许多女性形象,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洗河娘为代表的民间化女性形象,二是以呈红为代表的新时代城市女性形象。在世情小说《镜花缘》中,李汝珍打破了女性地位低下且被视为男性附属品的传统观念,塑造了有才能、个性和思想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例如有才华的唐小山、勇敢的尹巧文和有思想的林婉如等,这些女性形象是独立自主的进步女性代表,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贾平凹在继承李汝珍先进女性观的基础上,塑造了洗河娘和呈红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在对比中更体现出作者对于新时代女性发展问题的思考。洗河娘的经历映射了农村妇女的命运,“她们不是知识分子精英视角下的知识女性或觉醒的女性,也不是革命历史视角下将命运投入家国洪潮中的女性,她们人生观念符合民间伦理的要求,身上充溢着天然淳朴的民间气息,或表现为传统美德在民间历史中的沉淀,呈现出博大宽厚的善良和仁爱。”[11]小说中描写洗河娘的笔墨不多,在短短的几行字中展现了她悲惨的一生。丈夫健在的时候他们感情不和,丈夫出门打工,她就在家料理家事,丈夫去世之后她便把全部的心血灌注在儿子的身上。以洗河娘为代表的农村女性没有走出去的理想抱负,她们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和丈夫操劳一生,淳朴善良但思想落后。
呈红是与洗河娘完全相反的女性形象,她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受益的女性。传统世情小说中的主要女性多是知礼的“淑女”形象,例如《林兰香》中集孝顺、贞洁和贤惠为一体的燕梦卿,《红楼梦》中集温婉、典雅和恭顺为一体的薛宝钗。呈红的形象与传统认知中的“大家闺秀”相反,她凭借出挑的长相穿梭在男人之间,借助男人慢慢使自己变强大。呈红先是成为专家夫人,后与健身教练谈恋爱,又很快变成市秘书长的夫人,当秘书长入狱后她又跟一个“小白脸”在一起。在小说中呈红并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她形象中的负面成分反而更加突出。尤其是她水性杨花、对待感情随意,男人成为她不断变强的道路上的垫脚石。在《结构语义学》一书中,格雷马斯在研究人物关系时提出了“行动元”的概念,他提出了三组对立的行动元模式: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帮助者与敌对者。发送者与接受者这一组中“发送者是推动或阻碍主体实现其目标的一种力量,它可以是人形的,也可以是抽象的。”[8]148作为接受者的呈红追求女性独立人格,而作为发送者的社会有时会阻碍她的愿望的实现。贾平凹在描摹呈红这一人物形象时,继承与创新了古典世情小说中对独立女性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呈红不会因为秘书长位高权重而故意恭维他,也不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贤内助,罗山问她“你不去做饭呀,让领导忙活”[9]100时,呈红却说“他炒菜可好吃哩”[8]100。住进花房子之后呈红在庭堂里挂上“如意”两个大字,她对于这两个字的解释是女人说话算话。呈红有女权主义思想,她认为女性应掌控自己的命运,说话有一定的分量,不必听从男人。在回怼门卫抱怨儿子对象是二婚的事件上,也可以看出呈红尊重妇女且思想进步,她有极强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女性真正解放后的代表形象。小说中塑造出了两类对立的女性形象,在对比分析中“将她们的生活态度、命运走向融入对时代的整体观照之中,在这些女性身上寄托了对传统文化的遥想、对现代文明的反思。”[11]不禁令读者反思在这个改革开放后的年代是否还会有像“洗河娘”那样思想落后的女性,以及如何使这类女性思想解放,逐渐具有呈红一样的女权思想。
“当代叙事文越来越不注意去刻画那些丰满有力的、能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淹没在芸芸众生的大海里的小人物。”[8]154这种反英雄化的叙事不仅表明了当代叙述者有意摒弃传统艺术手法,还反映出了新时代文化思想的转变。“我们的时代正处于由崇拜英雄、崇拜伟人过渡到自我崇拜和自我鄙视的时代,这是对客观外界认识的深化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8]154表现主义文学流派的卡夫卡在小说《城堡》中将人物符号化,主人公“K”作为符号可以指任何人,他是虚幻的、不确定的,小说逼真地揭示出普通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生存状态。《河山传》中的光是有姓名的人物就有上百位,除了一些政府官员以外基本上都是小人物,小说虽是为洗河与罗山立传,但主人公不是传统世情小说中的英雄,而是新时代下努力生活的平凡人。
二、人情与世相:日常生活叙述中的重释
世情小说权威性的说法来自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的归类,鲁迅称之为“人情小说”,“大概率为悲欢离合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染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12]1949—1978年,世情小说发展缓慢。直到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文学创作的重点倾向于民间与世俗创作,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和池莉的《烦恼人生》等新写实小说致力于描写生活琐事、性爱心理和生命冲动。汪曾祺的《世人二三事》、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等作品都将时代背景融入世俗书写中。从《废都》《白夜》《高兴》等长篇小说到新作《河山传》,都能看到贾平凹创作中不变的底色——在继承传统世情小说的基础上加入了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背景。
传统的世情小说指“那些以描写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历史、社会各阶层众生相为主,以反映社会现实(所谓‘世相’)的小说”[13],《金瓶梅》用写实的笔法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画面,小说以西门庆一家的日常琐事为核心,以一家涉及一县,后又把笔触扩展到了国家大事。新世情小说新在呈现了丰富的内容,贾平凹的《河山传》除了继承传统世情小说描写社会各阶层众生相外,还把这些故事放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注入了新时代社会背景。作者通过对民间、官场等不同的生活场景、社会人群和人际关系的叙述,立体地描绘出当下的世风世情,形成一幅丰富繁杂、生动形象且反映新时代特色的众生相。
“‘三言二拍’既有通俗文学中自然人性的流露与传奇故事推衍的世情要素,又有严肃文学开掘社会人性、观照人物命运的人文精神,体现出“雅俗融合”的鲜明特质。”[14]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偏重描摹劝善惩恶、因果报应和宿命轮回的世俗故事,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十五贯戏言成巧货》等。但贾平凹的创作并没有推崇小说的教化作用,只是汲取了通俗故事的讲述方式,通过故事揭示普遍的世俗常理,再融入现代化的叙事技巧,完成“雅俗融合”。《河山传》作为新世情小说,作者在还原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总体性和完整感的同时,不惮于在光明中揭示黑暗的一面,描绘了一幅复杂而生动的众生相和浮世绘,织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宽广的影像。小说中夹杂着传统与现代、新思潮与旧伦理、道德与生存困境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打开了思考的空间,表达了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环境在故事中具有多种作用,它可以形成气氛、增加意蕴、塑造人物乃至建构故事等。”[8]159环境中的社会背景影响着人物命运的抉择,“社会背景指由人际关系构成的社会活动。它既包括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风俗人情,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联合、分离等具体关系。”[8]160作者在作品中揭露社会习俗中存在的问题,书中有很多关于农村场景的描写,例如按照村里的规矩,在洗河娘死后得答谢一顿饭,这是农村普遍存在的葬礼习俗。洗河将家里的钱全部料理爹娘的后事,不惜把粮食卖了去置办葬礼,体现了中国的厚葬习俗。除了对洗河安排葬礼酒席的隆重与奢侈的描写外,还有对农村人吃席细节的描写,“碟子还没放稳实,七八双筷子就抢起来,场面混乱” “席间有人吃饱了,又盛了一碗饭菜,离开席说站着吃,连碗带饭菜却回了家”[9]9。酒俗酒礼是传统文化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和人们爱贪小便宜的心理,使此活动往往无序和混乱。
大多数农民工进城之后的情况和文丑良笔下描述的一致,“随着城市大规模的建设完成之后,已经没有了农民工的生存空间,但新一代的农民工又涌向城市。当他们一脚踏进城市,就不准备再回去,城市便成了他们放飞梦想的地方,也同时是他们埋葬青春的地方”[9]210。文丑良列举了十几位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没有稳定的营生,在社会夹缝中钻来钻去,他们大多挣一点花一点,属于没有什么正经工作的城市边缘人。他们懒于谋生路,抱着投机取巧的心态不做正经的营生,例如王五一散发卡片、西沙良做暗哨、刘静宜给人做情人等。贾平凹借助文丑良之口说出,时代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与农村的堡垒打开,作者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问题,因此《河山传》具有现代史意义。
《金瓶梅》中的人情是作者的着意处,其最大的特点是“真”,作者在司空见惯的故事中描绘出形形色色之人。书中人情往来大多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例如西门庆所处的以金相交的官场,互相竞争的同僚,围着西门庆转但没真感情的酒肉朋友……《河山传》和《金瓶梅》一样人物众多,并且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十分复杂,贾平凹在讲述城市中的人情时继承了《金瓶梅》中对人情的描绘。《河山传》在官场和商场中展现人们的勾心斗角,当罗山和兰久奎的楼盘工区划分的白线上躺了一具出车祸的尸体时,两个工地的人开始推诿扯皮,第一时间都想着如何与自家工地撇清关系,大家都是利益当先,对生命和死亡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在罗山商业版图扩建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官场与商场权钱交易、投机取巧皆为常态,他们的行为甚至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例如放高利贷,绑架人剁手指等。罗山出于慈善之心资助贫困大学生二十五人,之后来求赞助的人越来越多,有些未被赞助的人甚至会锲而不舍地纠缠罗山,严重影响到他的工作和家人的生活。本来赞助贫困大学生是一件十分有利于社会的公益事业,但是人性的贪婪令罗山给自己惹出了一身麻烦。作者通过书写城市发展进程中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来引发读者对现代社会人情炎凉的反思和之前较为单纯的人情世故的向往。
《河山传》在竭力表现一个民族艰难行进的历程,尤其注重展现人性的实际状况。作者在日常琐事里探讨人性之殇的话题,深度考察人的灵魂在不断变革的当代现实中如何产生“失重”状态。小说没有回避重重叠叠的人性之恶,人世间也永远是黑白交织的,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特点。作者选择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站在时代的远景和人群中,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间的经典画卷。
三、雅俗共赏:新世情小说语言的变化
作为世情小说开山之作的《金瓶梅》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尤其在语言上,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有学者认为小说中使用了山东方言,也有诸多学者认为是山西、河北和河南等地的方言[15]。大量方言俗语的运用使小说特别生动且具有生活气息。“贾平凹的文学语言,是深深扎根在乡野的民间语言中的,同时又受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传承了古典文言小说的语言形式,因此有着浓郁的古典与民间意蕴,从而在其文学语言的架构上有着雅俗共生的独特审美意蕴。”[16]贾平凹小说的语言以朴素直白中见真情与意蕴,他的语言没有过多的定语修饰,注重准确性与形象性,在平铺直叙中准确地表达人物的情绪。《河山传》继承了传统世情小说的方言写作,语言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语言之“俗”体现在小说中存在大量方言俚语,语言之“雅”不仅体现在文丑良对城市化问题专业性的评述中,还体现在小说中夹杂着具有古典意蕴的诗词。
贾平凹是陕西味十足的作家,他讲话带有十分浓厚的商州腔,在写作中他将自己的方言融入其中,因此他小说的语言是以方言口语为基础的语体结构。方言的运用能增强文学作品的陌生化效果,是实现文学性很重要的手段之一。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他认为“陌生化是艺术加工和处理的必不可少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要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受众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17]小说中,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商州地带,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地文化。小说运用大量的方言词汇,例如“碎怂鬼”在陕西方言中是带有亲昵色彩的“小兔崽子”的意思,一般用于长辈对晚辈的称呼。老爷子管傍晚叫“黑来”,在方言中将“黑张来”解释为接近天黑的时候。呈红在洗河喝茶的时候问他喝得怎么样,洗河回答“喝透了”,在酒桌文化中“喝透了”通常指的是将杯中的酒一次性喝完,也有表达喝尽兴的意思。陕南和渭河北的方言不同,老爷子与洗河关于亲戚的称呼问题就起过争执:老爷子管公婆称为“阿家”,洗河则称“婆婆子”。相较于单纯的普通话叙述,方言的运用不仅增加了作品的乡野质朴感,拉近了读者的阅读距离,还更准确地刻画出人物的动作、语言甚至性格,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小说语言简单质朴且通俗易懂,没有过多修饰性的词语。贾平凹用弥漫着浓厚乡土气息的语言描写风土人情,展现人物性格,刻画出陕西独特的人情世故和地域风貌。
在文丑良学术性的话语中,体现了贾平凹语言之雅。作者借文丑良的话探讨时代变化和农民工命运等具有深意的话题。文丑良借着给洗河讲《城市错误》这本书来回答他对城市的理解和新时期打工者现状的思考,文丑良在讲述的过程中运用专业化的术语列举了很多具体的数据,例如“城市剪刀差” “城市化率百分之六十点一” “城市化时代”等,这些专业的解释反映出作者对中国现如今城市化过程的深入研究。书中具有专业化的词汇增强了文本的学理性,体现了贾平凹语言的雅致。
小说语言之雅还体现在书中穿插了很多古典词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兰久奎将自己的房间称为“半半斋”。描绘他西院装饰的语言也十分具有古典意蕴,“西院里有海南黄花梨一桌两椅,小叶紫檀风水柱,金丝楠木古董架,门、窗、楣、栏、槛却用的沉木,似金玉的”[9]213。兰久奎不像商人,倒像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艺术家,他喜欢读书,爱好书法,还手持一本《道德经》。他还在房间挂了一首“半半诗”,这首用正楷写成的长诗中最关键的一句就是“看破浮沉过半,半之受用无边”[9]214,这首诗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量度,即“中”和“半”,达不到为不及,超之为过,讲求一切适度,有儒家的“中庸”思想蕴含其中。
地域文化对贾平凹的影响毋庸置疑,他从小生活在陕西省商洛市的农村,接受着陕南地区真实鲜活的方言土语和古朴活泼的民间小调的影响,使得他的语言具有独特的陕西特色。同时贾平凹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从古典白话小说中汲取营养,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现代白话文中夹杂着古典文学的气韵,小说的语言形成雅俗共赏、收放自如的特点。
四、结语
贾平凹《河山传》的叙事特色体现出对中国古典世情小说的继承与拓展,作者通过独特的叙事展现其写作主题。贾平凹在写作过程中不仅继承了传统世情小说细致描绘日常生活的特点,还将故事放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新的时代背景中,具备了孟繁华界定的“新世情小说”的特点。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中塑造了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农民工形象、精明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家形象和新时代女性形象。在叙事语言上将商州方言与典雅的文言诗词融合在一起。《河山传》以洗河和罗山两个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小说虽然是围绕这两个人物展开,但以小人物见大世界,作者通过对小人物的描绘,勾勒出了连贯的历史脉络。贾平凹总能很敏锐地捕捉时代的特征,尤其擅长写乡土社会,作品充满了对民族的忧患意识。这些平凡的小人物代表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年轻人和民营企业家,通过他们的故事作者不断反思这几类人的命运与国家未来的发展进程。《河山传》中隐含了作者深厚的悲悯情怀,作品中并未出现作者直接的感慨,而是将这种情怀隐含在洗河与罗山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当中,这种情怀大体可以概括为贾平凹对人类终极命运难以超越、无可改写的悲悯。
参考文献:
[1] 孟繁华.变革时代的人民传记——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河山传》[J].文艺争鸣,2023(9):141-144.
[2] 张学昕.时代变局中人性与命运之殇——贾平凹长篇小说《河山传》读札[J].南方文坛,2024(1):89-95.
[3] 王春林.编年体、双线合一与戏剧性——《河山传》艺术形式分析[J].当代文坛,2024(2):98-103.
[4] 江丹.古代世情小说叙事传统的当代传承与新变——以贾平凹《秦腔》、格非“江南三部曲”为例[J].当代作家评论,2021(5):33-38.
[5] 孟繁华.正史之余,也在正史之内——当下“新世情小说”阅读笔记[J].名作欣赏,2023(16):76-83.
[6]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英汉对照)[M].朱乃长,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72.
[7] 秦亚轩.“他者”的身份焦虑——论贾平凹《高兴》中的进城农民形象[J].长江小说鉴赏,2023(6):84-88.
[8]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 贾平凹.河山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
[10] 韩鲁华.贾平凹文学创作与中国传统文脉的承续[J].文艺争鸣,2017(6):50-55.
[11] 程航.贾平凹新世纪小说中乡村女性形象研究[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2021:14-44.
[1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60.
[13] 向楷.世情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3.
[14] 毛金灿.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对明清世情传统的承续与转换[J].写作,2024,44(1):61-70.
[15] 张简.《金瓶梅》中的内蒙古西部方言、方音及习俗[J].内蒙古电大学刊,1995(3):6-11.
[16] 邹江平.贾平凹新笔记体小说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20:29.
[17] 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6.
收稿日期:2024-05-07
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24年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wcyyjs2024022)
作者简介:韩宇,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