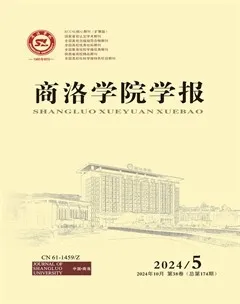贾平凹文学创作与商州经验的交融
摘 要:商州经验为贾平凹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孕育了他的文思情趣,铸就了作品独特的审美特质。贾平凹的文学叙事与商州经验紧密相连,他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乡土文化符号,是商州叙事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富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贾平凹表达乡音、寄托情感的集合体,更是读者了解商州文化符号的有效载体。熟悉商州文化的读者,在鉴赏贾平凹文学作品时会带入自己的乡土经历和情感,与作品中的描述“对号入座”,进而与作家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并在深层角度进行精神的交流和对话。对于陌生的读者来说,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他们深入了解商州历史演变、人文风貌及日常生活信息的重要窗口,更是他们重构其自身知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重要媒介。
关键词:贾平凹;文学创作;商州经验;《访谈》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24)05-0001-08
引用格式:景淑梅.贾平凹文学创作与商州经验的交融[J].商洛学院学报,2024,38(5):1-8.
The Integration of Jia Pingwa's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Shangzhou
JING Shu-m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 The experience of Shangzhou has provided extremely rich creative materials for Jia Pingwa's literary creation, nurtured his literary interest, and forged the unique aesthetic style of the wor47TG693ASGO2A1Fz0M/etA==k. Jia Pingwa's literary narrativ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perience of Shangzhou. The local cultural symbols presented in his literary work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expression of Shangzhou narrative. Literary works with strong local flavour are not only a collection of Jia Pingwa's expression of local accents and emotions, but also an effective carrier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Shangzhou. Readers who are familiar with Shangzhou culture will bring in their own loc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s when appreciating Jia Pingwa's literary works, and "sit right" with the description in the work, and then empathise with the writer spiritually, and carry out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from a deep perspective. For strange readers, Jia Pingwa's literature work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m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humanistic landscape and daily life information of Shangzhou,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m to reconstruct their own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Jia Pingwa; literary creation; Shangzhou experience; Interview
作家生命中的乡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历史和情感的集合体。作家在长期的乡土生活中积累的大量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为他们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作家通过描绘乡村生活的细节来展现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揭示乡土文化中的人性光辉和苦难,对乡土社会中的人情世故和历史变迁进行着深刻的反思,进而引导人们探索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和社会问题。地理故乡和文学故乡都是作家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是作家赖以生存的山河大地,更是作家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作家访谈是一种读者与作家面对面的艺术互动活动,通过精心设计的访谈,读者能够直接聆听到作家创作中关于灵感来源的阐述、构思过程的揭示、写作技巧的分享,以及作品如何反映和塑造社会、文化和个人观念等重要信息,甚至可以了解到作家创作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心路历程。
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与商州经验关系的研究较多,大多数研究者聚焦于贾平凹的具体文学作品,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出发,考察商州文化要素在贾平凹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及贾平凹商州书写所构建的文化乡愁与文学版图,如郭萌[1]、严文珍[2]、席忍学等[3]、盛慧[4]、谢尚发[5]等。部分研究者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入手,就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及商州人在杂糅共生的文化语境中所经历的焦虑与撕扯进行了探究,思考现代性文明进程中乡土社会的文化转型与建设困境,如王华伟[6]、袁红涛[7]、谢尚发[8]等。还有研究者将贾平凹的商州书写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乡土书写进行了对比研究,凸显了贾平凹在勾连“地方”与“文学”之间互文性关系方面的独特贡献,如包妍[9]、韩鲁华[10]等。前述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贾平凹的乡土文学创作做出了研究,而对贾平凹访谈文本中呈现出的创作理论的关注却不是很充分。基于此,本文主要以贾平凹访谈文本,尤其文论集《访谈》中贾平凹本人述说内容为中心进行考察,就贾平凹文学创作与商州经验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对文学创作中贾平凹如何将商州经验转化为艺术表现,将商州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反思,用文学回应现代社会的变迁,通过文本艺术回应乡土变迁中显现出来的社会问题等进行探讨。
一、商州: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根据地”
拥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的地理故乡,不仅是作家个人经历和记忆的起点,更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来源。“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11]地理故乡既是作家生命中的生活根据地,更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根据地。每一个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其身后都有一个充满着浓厚生活气息、能够安身立命的文学场,那就是他们写作的故乡。如鲁迅的鲁镇,老舍的北京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赵树理、马烽的山西农村,迟子建的雪野北国,阿来的松岗水电站、土司官寨、茂密山林、四姑娘山,刘震云的延津世界,毕飞宇的江淮水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等。贾平凹也有自己的写作根据地,那就是他的商州乡村、秦岭世界。
商州为贾平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商州的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社会变迁都激发着贾平凹的艺术灵感,成为他作品中艺术形象塑造和情节构思的基础。为何要选择商州而不是别的地方,贾平凹的回答是:“我为什么在商洛有收获?因为我就生活在那个地方。这一棵树苗就是哪个土上长的,土里有干旱还是水涝,我知道,有没有蝗虫有没有风沙,我知道,长什么是啥样子我小时候体会的深得很,所以我再回去我就不做技术上的考核。”[12]168在贾平凹看来,作为“血地”的商州,是他最熟悉的地方,那儿能给予他的灵感要比别的地方多得多,“我从小在这儿长的,这儿人是什么样的,人的习性是什么样的,五谷杂粮是怎么长的,气候是什么样的,山川是什么样的,这些我了然于心。我再去只找一些人和故事,只找那些东西,我去一天相当于我到另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了一年,可以这样说,这里面有血肉联系,所以到那儿去就容易拿回来好多东西。”[12]168因为出生、成长在商州,由于基因和血缘的关系,贾平凹一直关注着商州农村和那里的农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熟悉,感情也深,小时候的好多记忆又特别深刻,这样,很自然地一提起笔就是农村,就是农民。” [13]40 “我的祖辈都是平民,天生的血液里流的就是老百姓的血液,我19岁以前都是在乡下生活,过得是中国人群中最基层的人群的生活。”[13]133商州给予贾平凹丰富的社会阅历、厚实的生活积累,这也是他写作中得天独厚的资源,利用这些素材,通过文学的方式呈现贾平凹内心的商州,反映商州的生活,这是贾平凹将商州作为写作根据地的首要动机。
在贾平凹看来,巨大的时代变化给作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机遇,不仅丰富了作家的创作素材,也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文学想象空间。“这种变化对文学创作却有莫大的好处,身处这一时代,作家的想象、思维空间被扩张到最大,创作素材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作家身在其中是极大的幸运。作家在一个什么时代生活,必会有这个时代的影响,参与着、欢乐着、痛苦着、思索着、想象着我们这个时代对作家是有益的。”[13]296贾平凹出身农民,对农村、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虽然走出了农村,但始终关注着农村的一切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他的故乡商州这块山地上同样在演绎着一部民族史剧。“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有着中华文化的东西隐含其中,有各种人文结构,有它流传已久的各种生活观念,来维系着社会的正常的运转”[14]。其破缺和修复也是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见证,更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结构、其民族心理结构从整体来看是和别的地方同在一个地平线上,对世界的感知,因袭的重负,历史的投影,时代的步履,与别的地方大致相同。”[13]3因此,以商州为写作大本营、根据地,用美学的、历史的眼光,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上对商州进行全面叙说,是一种记录时代变化和个体生活状态的最好方式。
用文字给商州立碑,是贾平凹写作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故乡作为作家与故土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承载着作家深厚的情感寄托,是推动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如果说“‘地理故乡’是父母之邦,是作家个体生命的‘血地’,而‘文学故乡’则是对‘地理故乡’的诗意想象与审美扩张,是无限开放的,可以不断生成新的时空意义,是作家‘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历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以展开审美想象的‘文化酵母’,是作家文学生命的‘文化血地’。” [15]在贾平凹看来,他的故乡商州虽然并不富饶,但却异常美丽。“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向,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构成了极丰富的、独特的神秘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仰观可以无其不大,俯察可以无其不盛。一座高山,一条丹水,使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我早年学习文学创作,几乎全是记录我儿时的生活,所以我正正经经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就取名《山地笔记》。确切说,我一直在写我的商州,只是那时无意识罢了。”[13]1-2正是因为贾平凹对故乡山山水水的眷念和商州生活的烙印,他在选择写作根据地时,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商州。“意识到我的创作必须要有个根据地,根据地必须写自己熟悉的地方,我就回到老家。”[12]167 “为了寻找我写作的根据地,曾经数次下商州,走遍了那里的山水与村镇,从此我再没有成为写作上的‘流寇’。”[13]253 “商州是我的故乡,那里有我的祖坟……从事文学创作后,商州一直是我的根据地,或许我已经精神化了它,但它是我想象和创作之本。”[13]354
商州是贾平凹生命情感的根源和寄托,它关联着他的童年、家庭经历和乡村故事。“我对自己的家乡和生活在那里的乡亲们,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30多年,但是我对自己的定位还是农民。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是乌在了骨头里的。所以要用忧郁的目光观察农村,体味农民的生活。我要用文字给故乡立碑。”[13]338深得商州山地恩施与滋养的贾平凹,报恩商州的心也是显而易见的。商州传统文化形态的一步步消亡揪扯着贾平凹的心,“这些年每次回乡,那里的变化离我记忆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传统的乡土文化一步步逝去,我于是冲动着要为归去的故乡竖一块碑子。”[13]259 “想要保存消亡过程的这一段,所以说要立一个碑。以后农村发展了,或者变糟糕了,与我都没有关系,但起码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13]245贾平凹对农村的一切变化及这些变化中存在的问题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近年我写了不少农村题材的作品,《商州初录》《浮躁》《高老庄》,这些作品中有我对陕南商州家乡的真挚情感。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我要用文字给故乡立一个碑,写作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形态。”[13]338贾平凹在农村题材领域取得的成绩,既是他受故乡沃土滋养的明证,更是他深情回馈故乡的文学表征。
二、商州经验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
商州既是养育贾平凹的土地,又是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更是他创作的精神家园。长期萦绕在贾平凹心田的成长环境、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成为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不仅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题材和弥足珍贵的灵感,还熏陶了贾平凹的“性格气质、审美爱好、思维方式、文体风格乃至写作习惯”[16]178,从而铸就了他作品独特的审美风格。
第一,商州经验是贾平凹文学创作材料的重要来源。丰富的乡土生活经验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基础,作品的写作素材大多都来源于作家最熟悉的地域,作家所熟悉的乡土经验都会以作品的原型或题材直接进入作家的创作之中。文学史上那些跳动着时代脉搏、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优秀作品,大都是作家以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为底本进行虚构的。自抗日战争时期便投身革命的柳青,对解放区和根据地的生活与斗争有着深厚的情感与认知。后来他选择在皇甫村安家落户,深入体验并熟知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这种深厚的生活体验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种谷记》《铜墙铁壁》,还是《创业史》,都仿佛是生活赠予作家的“恩赐品”,闪耀着真实而深邃的光芒。对于文学创作的本质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贾平凹有着深刻的认识。“我觉得要增加自己的大气魄的东西,对于现实生活要更了解。写现实生活你能够充分把人物写透,就能增加自己的这种东西。不能说写现实的就低下,写过去的就高尚,我们常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鬼谁也没有见过,现实生活任何人都能马上看得见、摸得着。”[13]35一地有一地之山水,一地有一地之风俗,自然环境、民风民情、方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等对作家的文学写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生存环境决定生存经验,“故乡的情节、故乡的记忆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宝库。”[17]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开始不断地重走商州、书写商州。“我熟悉的对我有影响的恐怕只有我老家……我就回去,开始几次返回商洛。商洛一共七个县,基本上我把七个县跑遍了。……当时为了避免谁闹意见这个原因,就把商洛不叫商洛,就写成商州。商州在商洛的历史上曾经叫过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写商州。”[12]162可以说,商州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沃土,“在他的一生中永远可以从这里获得生命力的发动。”[18]在贾平凹的众多作品中,有诸多的素材是源于商州。如《鸡窝洼人家》便是构思于商州采风过程中听到的一个故事:“吃完饭出来后,马涛给我讲这家的媳妇,讲这个故事。一个村子的人,你娶我的老婆,我娶你的老婆,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就说这是换老婆。”[12]169“《鸡窝洼人家》这部小说,基本上还是根据当时得到的情况,听到这个故事。了解两家人以后,那天吃完饭,又到另一家去看了一下,了解情况。整个商洛那种风俗那个方面我比较熟悉,就把这个故事直接融到那个环境里面慢慢构思的。”[12]170再如,《秦腔》叙述的是他的故乡棣花古镇的故事,“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中的东西。”[13]297与概念化的商州故事不同,《秦腔》涉及到的是一个村子和一群人的故事,表现的是人们在各种变革中的生活原貌。“《秦腔》写我自己的村子,家族内部的事情,我是在写故乡留给我的最后一块宝藏。以前我不敢触及,这牵扯到我的亲属,我的家庭。夏家基本上是我的家族,堂哥,堂嫂,堂妹,都是原型。” [cba6d58545de3a9d71f2ffd8f7b02c993db9eb53692ae58f7f0aecb98f5430eb13]246 “这些年每次回乡,那里的变化离我记忆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传统的乡土文化一步步逝去,我于是冲动着要为归去的故乡竖一块碑子。”[13]259
第二,将同类素材融入到不同的作品中,进而赋予它们不同的艺术生命,这是商州经验给予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写完《秦腔》后,贾平凹立马将注意力转移到商州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上。“城市里好多打工的,而且我的家族后辈都在西安打工,常到我这来聊天或者办事,所以写完《秦腔》村里那些人到城里去,就必然写到这些人到城里以后是什么生活,就写到《高兴》。这里面当然有我同学刘高兴这个人物原型,也有我的家族后辈人,年轻的孩子在城里发生的事情。”[12]193为了能写好《高兴》,贾平凹在孙见喜的帮助下,开始走进拾破烂这一群体并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在搜寻素材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又为贾平凹创作《极花》提供了素材。“事情还是出在老孙的那伙拾破烂的同乡里,一个老汉,其实比我也就大那么几岁,他们夫妇在西安拾破烂时,其女儿就在一家饭馆里端盘子,有人说能帮她寻一个更能挣钱的工作,结果上当受骗,被拐卖到了山西。老汉为了找女儿,拾破烂每当攒够两千元就去山西探,先后探了两年,终于得知女儿被拐卖在五台县的一个小山村里。老汉一直对外隐瞒着这事,觉得丢人,可再要去解救女儿时没了路费,来借钱,才给我和老孙说了。”[19]贾平凹在接受访谈时,对《极花》的创作灵感进一步作了说明:“有一个熟人的孩子被拐卖了,这就牵扯到以后写的《极花》这个小说。当时只知道这个故事,正因为这个故事去采访这个人,这个人正好是捡垃圾的,拾破烂的,我到他家里去,到他家去以后就了解到收破烂的人群真实的生活。”[12]193然而,同样的情节,被贾平凹再一次吸收到《河山传》中,“楼生茂顿时眼泪长流,才告诉了他是甘肃人,十年前就去西安收废品,那时收废品人少,倒是赚了钱,就租了屋,把老婆和小女儿也叫去给他做饭。小女儿慢慢长大,也想着自己能挣钱,碰上一个骗子,以招工的名义,将她拐卖了。” [20]
贾平凹对“捡垃圾”的不断使用表明,“就文学创作而言,仅仅有故乡的生命情感的记忆,显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对故乡的重新发现,或者再解读。作家的文学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于所叙写对象的再解读、再发现之后的重新建构的过程。”[21]
第三,贾平凹文学题材的本质是商州乡土经验的艺术升华。“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较高的意旨,并为这些较高的意旨服务。”[22]也就是说,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或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只积累材料是远远不够的,作家的生活体验不仅是丰富的、深刻的,而且应该是自觉的,这种自觉是指作家要用“文学家的眼光”认识生活,对生活进行精细地观察和深入地体验,在大量的生活经验储备中挑选出适合表达作家创作意图的材料。
鲁迅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事迹时指出: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23]。大凡是卓有成就的作家,都会有意识地从身后的那块根据地提取宝贵的材料。有了宝贵的材料,也不能只描写一件事实,用一片瓦建造不成完全的房屋,作家只描写一件事实是不能产生能够说服读者的典型作品的。蜜蜂想要酿蜜,就必须从各种花朵里一点一滴地采集最必要的成分,作家创作时提取材料的过程,便是如此。作家在进行作品布局时,要把堆积在生活仓库里的素材、真情实感及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熔于一炉,进而进行选择、提炼并主观能动地艺术加工、变形。尽管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与作家的乡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仅仅是作家乡土生活的摹本,文学创作决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制和照相。谈及《冰炭》的题材时,贾平凹说,“故事是七零八落的,且有的是有人亲身经历。有的是听人趣谈,有的是听了别人再加上自己的经历而充分想象了的,我只是把它收拢起来,后来又亲自去监狱、劳改场参观一回,采访几次,去伪存真,删芜取精。”[13]348我们常常强调文艺创作必须根植于生活,但同时更要超越生活的琐碎与平凡。如果仅仅满足于“源于生活”,而未能有意识地深入探寻其本质,缺乏提炼和概括的能力,未能找到富有感染力的叙述与表达方式,那么,这样的文艺作品在艺术上便难以散发出独特的魅力,终究难以达成“高于生活”的崇高目标。因此,对于创作者而言,深入生活、提炼精华、概括本质,并寻求独特的叙述与表达方式,是实现文艺作品“高于生活”的必经之路。对自己故乡的社会生活越是熟悉,感受越是深刻,作家的灵感才越会成为照亮材料的光线,才会推动作家在深厚的乡土文化土壤中分析和提炼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能够体现乡土之魂的、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
第四,商州经验铸就了贾平凹文学作品的独特审美特质。“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的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儿童则不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毫影响。”[24]也就是说,当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会把自己理解、把握到的乡间环境、风俗及人和事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创作中,或隐或现地表征于语言、情节、背景、风格等方面,最终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李继凯将民间文化和小说分别比作“大地”和“花朵”,认为“大地”和“花朵”的关系是命定的:“民间文化的瑰丽可以给小说带来瑰丽,但要在‘文化’层面得以彰显,则需要妙手的采撷和编织,才会形成精致的花篮,造就经典的小说。”[25]贾平凹自小生活在商州,熟知商州的方方面面,并深受商州语言、饮食、民俗、文化和社会等民间形态的影响。“商州可以说汇聚了这三种文化,这令我非常庆幸。有山有水有树林有兽的地方,易于产生幻想,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禳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13]372
贾平凹的作品中也映现了诸多商州民间文化元素,构成了其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如今,贾平凹虽然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他的父母也都已经离开人世,但他却不曾忘记返回商州祭奠他们。“起码保证清明节、春节,必须得回去,清明节必须要上坟去;春节大年三十晚上,必须回去坟上送灯。在我们那儿风俗大年三十到坟上去插灯,放上灯笼,你不放灯笼别人会认为后面没人了,绝死鬼了,必须要回去。”[12]145贾平凹e0d7f843bfc9c45453d959529495bdd4ea2e22ef6ba40168aa143fcb99b9f70c的“上坟”不仅仅是民间文化规约下“后继有人”的实践行为,更包含着对父母过往的感念。“每次回老家,肯定要去父亲的坟上烧纸奠酒,父亲虽然去世已有十八年,痛楚并没有从我的心上逝去,一跪到坟前就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当然,“上坟”还是兑现承诺的表征,承诺父亲用文字给故乡立碑。“但这一次我看见了父亲的坟地里一片鲜花。我的弟弟一直在父亲的坟地里栽种各类花木,而我以往回去却都不是花季,现在各种形态各种颜色的花都开了,我跪在花丛中烧纸,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和鲜花的气息是那样的融合。我流着泪正喃喃地给父亲说:《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我总算写了……”[26]贾平凹在此强调鲜花,是因为他再一次兑现了“用文字给故乡立一个碑”的承诺。“我在《秦腔》后记里还写过,我曾经给我父亲说过,我将来要写家族、写故乡,他说要我用文字给故乡立一个碑。”[13]293贾平凹还将“上坟”这种民俗渗透到了具体作品的情节中,如在《河山传》中,洗河给邻居万林寄钱并委托万林到父母坟上烧纸、上坟,以及洗河亲自回到崖底村上坟等情节,便是对商州民间形态乃至贾平凹个人“上坟”实践的再一次阐释。贾平凹是公认的善写民俗的“圣手”,他将吮吸到的陕南山乡民俗文化巧妙地编织在各部作品中,使其成为了作品中极富魅力的成分,这样的写作表面上看是有意而为的,实则是刻在骨子里的民间文化形态的作用。“小说中那些对待自然的事情,都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或见闻的,那里的生活形态就是如此,其生活形态也培育了一种精神气质,当小说中大量书写了这些,它就弥漫于故事之中,产生独特的一种味道。”[13]309
三、贾平凹文学叙事:激活商州文化的媒介
乡土经验与文学创作互相影响。商州经验为贾平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成为他宝贵的创作灵感来源。同时,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活动及他的文学作品,反过来又介入现实故乡,对商州文化进行重构,进而又丰富了商州文化的内涵。
第一,在写作生命中扎根商州的沃土、书写商州人民的命运、赋予商州文化新的内涵,这是商州贾平凹写作的生命力所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有一些人物直接借用了他商州老家的邻里,如他的邻居刘书祯既是作品《高兴》中高兴的原型,也是《秦腔》中书正的原型。贾平凹精心塑造的那个交际广泛、性格活泼外向、富有戏剧性的刘高兴,为商州刘高兴命运的改变提供了机遇。对此,贾平凹在访谈中曾有过说明,“刘高兴反倒比我还有名,当时好多电视台都请刘高兴讲。实际上这一本书的名字,把他叫‘刘高兴’,他也高兴,他是个嘻嘻哈哈的人,他自称‘刘高兴’。我是用这个名字,把他的形象和一些行为写进去。写进去以后,他一下子成了一个人物,到处接受采访,电视台让他做节目,他到南方哪个电视台去过两次……后来他名声大了,就不出来打工了,就在我们那个地方也成了一名作家……我听说现在反倒去了那儿的人,人家都找他,还热闹得很,现在日子过得很好。”[12]194-195
贾平凹的商州叙事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命运轨迹,而且在宣传商州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我的商州作品未产生影响前,外边世界很少有人知道商州。”[13]354“在写《商州初录》以前,文学作品中是很少有人提名叫响地来写这块地方的,而且即使写,也都是写作‘商洛’,‘商洛’是现在的真正地区名,‘商州’则是商洛的古时叫法。而如今‘商州’才慢慢被重新使用了,尤其文学界。”[13]3 “我发表的《商州初录》《商州再录》《商州又录》,这就变成出名的书叫《商州三录》。这一本书当时出来以后反响特别强烈,也给我好多鼓励,从那以后就不停地回商洛,了解那些情况。”[12]162贾平凹与他的商州系列作品,共同构成了商州文化的显性符号,对商州人民来说,这是一份值得他们骄傲的文化象征。正因为得到了商州人民的认可,贾平凹在商州写作上也花费了最多的精力。作为一个勤奋的笔耕者,他创造了富有商州浓郁气息的《鸡窝洼人家》《浮躁》《怀念狼》《高兴》《极花》《秦腔》《河山传》等诸多作品,继而将商州推向了全中国乃至世界。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不仅强化了商州文化的自我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还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如《秦腔》在棣花镇文化建设方面更是起到了重要的翻转作用。“小时候我见我们那儿的庙宇、戏楼、魁星楼、钟楼,那些原来都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毁了”[12]192,棣花老街“那条街道当时已经不行了,已经荒废了,快倒塌完了,当时人都搬走了,只有四五户人在那儿住”[12]192-193。《秦腔》是对物质现实中棣花古镇的筛选、分析、概括、提炼,以致想象、加工、虚构和润色的结果,包含着贾平凹对故乡的深情、记忆、想象、精神追求和对现实故乡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既有他小时候记忆中的棣花镇,也有他审美想象和诗意建构的清风街,而这些都成为了当地政府打造棣花古镇的参考。“我在《秦腔》里面我就写了我小时候记忆中的棣花镇,后来当地政府在打造旅游小镇的过程中,它基本上是参考了我小说里面很多东西。我那条街是一条老街,但当时叫棣花街,就指那条老街,但我小说里这条老街叫清风街,后来他说干脆把这条街打造出来也叫清风街。”[12]192扎根商州、书写商州人民的命运,这不仅是贾平凹选择商州为写作根据地的目的所在,更是他写作生命的职责所在。“商人永远缺钱,我永远少一本书。”[27]文学作为高级的审美意识形态之一,不仅是贾平凹自我感情和经验的再现,更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积极回应。贾平凹通过文学创作,借用艺术的力量赋予棣花古镇全新的面貌,影响着棣花古镇上人们的生活。
第二,贾平凹的文学叙事为读者了解商州民俗文化提供了媒介。“文本说教,读者建构。”[28]142如果说作家的文学创作为特定地域文化价值的实现提供了载体的话,那么读者的阅读则使这种文化象征得以不断延续,“文学对象是一个奇特的螺旋,只存在于运动中。想要它显现,就必须有一个具体行为,即阅读。阅读持续多久,对象的生命便延续多久。”[28]140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既是读者阅读期待视野与叙事文本的互动产生了共鸣,更是读者不断通过阅读对文本中的“空白” “不确定因素”等修复和消解的结果。
贾平凹作为商州的代言人和名片之一,既是该地域民俗风尚的示范者,也是该地域人民的知心人,更是观察、研究他们生活的有心人。贾平凹创造的那些富有浓厚商州气息和魅力的文学读本,不仅是他表达乡音、寄托情感的载体,更是读者了解特定地域文化符号的有效载体。贾平凹在呈现乡土文化景观时,总把自己对商州乡村那种深入血肉的感情。渗透在骨子里。同时,将在特定的地域和人文环境中形成的极其深刻的商州记忆和发人深思的道理,全都融入到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地域内读者和作家是具有同一性的,他们在鉴赏这些作品的时候,也会将自己的实际经历和情感带入,每个读者在读作品的过程中,都是“在读自己。作品不过是作家提供给读者的一个类似于光学仪器的工具,它能让读者见到自己心中那些无此书他便很难见到的东西”[28]136。也正是因为读者的这种“对号入座”,才使得弄清作者设置的种种“阐释代码”不再那么困难,并在深层角度进行精神的交流与对话,在精神的碰撞中对人和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而对于陌生的读者来说,他们“面对的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写的未必都是自己熟悉的故乡情事,他们经常面对的倒是陌生的‘他者’。在这种情形下,作品所呈现的则是新鲜的‘异域’风情,其所满足的是读者的猎奇心理和求异兴趣,并且能够重构其地域文化观念,充实其相关的知识结构与审美意识”[16]179。
四、结语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作品虽是作家虚构出来的艺术之花,但其中涉及到的生活信息又或多或少演绎着特定时空中的人与事。贾平凹将商州大地作为写作根据地,巧妙地从商州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搜集素材、提炼题材,并将烙印在骨子里的民间传说、方言俚语、乡土旧事、民俗民风等融入到具体作品中,进而为他的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商州气息和艺术魅力。贾平凹眷念着商州大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这里他获得了众多的灵感,并通过文字将商州及商州人民的故事带进了万千读者的视野。但贾平凹又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乡土作家,他那将现实与梦幻融为一体的文学创作,并非只是在单纯呈现商州人民的生活琐事,而是以商州为焦点,深层次求索、探寻商洛、秦岭乃至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追求和生存困境。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不仅是他表达乡音、寄托情感的载体,更是读者了解商州这一特定地域文化符号的重要媒介。通过他的作品,读者得以穿越时空,能够亲身感受到商州的独特风情和文化底蕴。另外,“商州之子”贾平凹和他的文学作品作为商州文化的显性符号,强化了商州文化的自我特征,使商州文化得以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展现其独特的魅力,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作品了解这片充满活力和韵味的土地。故而,作为商州文化的代言人,贾平凹用他的笔触和才华,通过独特的叙事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将商州文化以文学的形式进行艺术化的呈现,充分展现了商州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一定程度上还簇新了商州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郭萌,赵学勇.地理的空间与文学的意象——以贾平凹小说创作为例[J].人文地理,2011,26(2):108-111.
[2] 严文珍.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J].商洛学院学报,2022,36(5):11-16,28.
[3] 席忍学,杜薇.贾平凹方言写作的审美心理[J].商洛学院学报,2023,37(3):15-21.
[4] 盛慧.“如画”的风景:贾平凹小说中的地方想象与风景书写[J].文学评论,2023(4):72-80.
[5] 谢尚发.理解贾平凹的商州:风格化、地方志或“深描”[J].南方文坛,2022(2):153-160.
[6] 王华伟.来自乡土的“呐喊”——兼论贾平凹的中国经验[J].当代文坛,2017(6):63-67.
[7] 袁红涛.发现商州:一个“地方社会空间”——重读贾平凹的一种方法[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4):66-88.
[8] 谢尚发.作家“笨功夫”与寻根地理图——贾平凹1983年的“重返商州”[J].当代文坛,2021(3):39-44.
[9] 包妍,万水.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书写——以莫言、贾平凹为例[J].文艺争鸣,2020(8):171-175.
[10] 韩鲁华.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化心态比较分析[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3):28-32,36.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860.
[12] 张同道.文学的故乡访谈录·贾平凹和他的商州乡村[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0.
[13] 贾平凹.访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4] 贾平凹,杨辉.究天人之际:历史、自然和人——关于《山本》答杨辉问[J].扬子江评论,2018(3):29-37.
[15] 王西强.论贾平凹与莫言小说的文化母本与叙事空间营建[J].南方文坛,2020(2):160-165,170.
[16] 李继凯.文学与地域文化[J].民族艺术,1998(4):177-180.
[17] 莫言.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65.
[18]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4-64.
[19] 贾平凹.我和刘高兴——长篇小说《高兴》[J].美文(上半月),2007(8):3-11.
[20] 贾平凹.河山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10-11.
[21] 韩鲁华.故乡、他乡与行走——贾平凹文学地理考察随笔之一[J].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0(2):152-162.
[22] 歌德谈话录[M].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37.
[2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7.
[24]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5.
[25] 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48.
[26] 贾平凹.高兴·后记一——我和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450.
[27] 贾平凹.我想把故乡告诉世界,把秦岭告诉世界——在“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摘要)[J].商洛学院学报,2024,38(3):1,4.
[28] 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M].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收稿日期:2024-05-16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高水平成果资助项目(23YDYLG003)
作者简介:景淑梅,女,甘肃陇西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