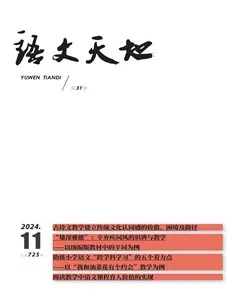《水浒传》中梢棒辨疑
[摘要]《水浒传》里武松打虎所用梢棒形制究竟如何,学界尚无确论。从文献记载以及《水浒传》所反映的宋元社会状况看,梢棒应该是直径较细、轻巧便携的杆棒,适于出行时携带,或较量武艺及日常居家时使用。从版本看,梢棒是早期《水浒传》诸版本比较正式的名称,到金圣叹评本则统一为哨棒。
[关键词]梢棒;哨棒;《水浒传》;杆棒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所用的梢棒(或作稍棒、哨棒),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器,历来读者众说纷纭,方家亦莫衷一是。许金发先生从用途归纳诸说,总结为挑具说、武器说、巡具说、吹具说四种,并认为“这四种说法比较起来,前两种更为合理一些。”[1]至于其形制,学者或释为“行路防身的长木棍”[2],或认为是人们“出行时用于防身的短棒”[3],还有方家认为“它的一头是空心的,是可以吹出声音的”[4],种种推断,不一而足。
实际上,《水浒传》文本中对梢棒的信息就有所透露:“武松缚了包裹,拴了梢棒要行,柴进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领新衲红绸袄,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儿,背上包裹,提了杆棒,相辞了便行。”[5]水浒故事长期流传于民间,尽管《水浒传》成书尚有争论,但它无疑保留了大量宋元时期社会生活的信息。武松行路只带了一种防身武器,《水浒传》先称为“梢棒”,后又唤作“杆棒”,这当然不是笔误,而是说梢棒可以与杆棒混用。实际上,结合《水浒传》中的描述,梢棒应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杆棒。
那么,杆棒又是什么样的呢?杆棒在古代文献中记载颇多,它是“用作武器的粗木棒”(《辞源》),也是江湖好汉出门行路最常用的防身武器,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杆棒的身影频繁出现。
石块与木棒,是自然界中的常见物品,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的兵器,正所谓“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商君书·画策》)。只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有了种类更多、功能更全、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因此,威力较差的木棒只能逐渐淡出战场。但是,木棒仍然有其独特的优势,难以完全被其他武器取代。比如,木棒无需锻造,易得易用,“不劳远求,指日可办。比弓弩则无挽拽之能否,比刀剑则无锻炼之工程”[6],故民间常斩木为兵——甚至官府也难以将其完全淘汰。更不用说在特殊时期,尤其是封建统治者严厉禁止民众携带、使用制式的金属兵器时,难以完全禁绝的木棒便成了民众的不二选择。
除军事斗争外,行走江湖的英雄好汉更是依赖木棒。他们一方面受官府严厉管制,无法使用制式武器,另一方面又要面对gQXqDMKMQXJTgTyRQqIEsw==风波险恶,常常面临着危及生命的武斗,因此,作为武器,杆棒是他们最主要的依仗。话本《杨温拦路虎传》中,杨温出门前先向杨玉借条杆棒作武器:“告仁兄,借一条棒防路。此间取县有百三十里来,路中多少事,却恁的空手,去不得。”《错认尸》里乔俊远行外出,亦是“驮了衣包,手提了一条棍棒”[7]。无名氏《白兔记》及冯梦龙《警世通言》中,他们甚至将杆棒形象地呼为“护身龙”。《醉翁谈录》将小说按题材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等门类,其中,“杆棒”类小说如《花和尚》《武行者》《飞龙记》《五郎为僧》等,皆以其所持武器杆棒而得名,讲述的都是英雄行走江湖的传奇故事,最为民众津津乐道。
武松打虎故事与杆棒的渊源颇深。在《水浒传》成书之前,武松打虎故事便流传已久。胡士莹先生认为,《醉翁谈录》中的《武行者》“当是讲说当时民间的武松故事,为后来《水浒传》中武松故事所从出”[8]。《醉翁谈录》中将《武行者》与《杨温上边》俱归于“杆棒之序头”,为我们依据《杨温拦路虎传》来推测《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所使杆捧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除此之外,《录鬼簿》里金院本有《打虎艳》,元杂剧有高文秀的《双献头武松大报仇》,红字李二的《折担儿武松打虎》和《窄袖儿武松》。金院本《打虎艳》,谭正璧先生怀疑:“未知是否演《水浒》‘武松打虎’事?”[9]赵兴勤先生以为“似应补李存孝打虎一事”,但他仍审慎地表示:“院本究竟演何事,待考。”[10]《折担儿武松打虎》的内容应是武松打虎故事,所谓“折担儿”,并非指武松所使武器为扁担,他仍有可能如宋元话本中英雄那样使用杆棒。话本中杆棒也常常用以担物,如《拦路虎传》:“这汉子座下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前面一个拿着一条齐眉木棒,棒头挑着一个银丝笠儿,滴滴答答走到茶坊前过,一直奔上岳庙中去朝庙帝生辰。”[7]但不管具体情况如何,即使仅仅只是依据名目,我们也能够看出它们与武松打虎故事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水浒传》里武松打虎所涉及梢棒与杆棒关系,是宋元话本故事中对当时流行认知的正确反映。
既然梢棒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杆棒,那么,它的特殊性在哪儿呢?综合《水浒传》中诸多信息来看,应该是杆棒普遍较粗,而梢棒偏细,直径较小。
强调杆棒为“粗”木棒,正是体现它在厮杀战斗中应该发挥的威力,因为木质轻软,只有双手使用粗长的木棒才能获得较大杀伤力,武器自身亦不易损毁。棍棒武器在典籍中又常被称为棓、白梃等,“白梃,大杖也”(颜师古注《汉书》),沙苑之役时“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桥”[11],唐李嗣业“常为先锋,以巨棓笞斗,贼值,类崩溃”(《新唐书·李嗣业传》)。《太平广记》更有江西钟傅酒后以棒搏虎的经历:“傅素能饮,是日大醉……时酒力方盛,胆气弥粗,以仆人所持白梃,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跃,挥杖击之。”[12]——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唐代版的武松打虎了。
白梃是钟傅与虎搏斗的得力武器。反观《水浒传》,武松初遇老虎时,双手轮起梢棒,用尽平生气力向老虎打去,可惜在慌乱之间,“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且不说“枯树”到底如何,就算它直径较粗,但梢棒一下子就被打断了,可见它确实不太结实。如果是粗大的杆棒,就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尴尬而危险的局面。与粗大的杆棒相比,正因为梢棒比较细,故而在武松使出全力之下被枯树折断。
那么,武松为什么拿比较细小的梢棒作为行路防身的武器呢?难道他就不把自身的安危放在心上吗?当然不是武松粗心大意,究其原因,武松带梢棒大概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杀伤力大的杆棒比较粗笨,不便于携带,俗话说,“远路没轻担”,要充分考虑体力并合理分配负载,而较细的梢棒既可以“拴”又可以“提”,极其方便省力。二是武松觉得回家的路途比较安全,没有太大的危机,无需加强戒备,“我是清河人氏,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事实上,从《水浒传》中也可看出,景阳冈本是通衢,经常有行人客商来往。有老虎出没的景阳冈尚且如此,那其他地方更应是坦途了。对于江湖好汉武松而言,自然无需太过于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了。
实际上,虽然景阳冈武松打虎时“梢棒”出现频率最高,但是,它在《水浒传》中别的地方仍然不时被提及。如第三十回,武松在都监府因“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里脱了衣裳,除下巾帻,拿条梢棒,来厅心里月明下使几回棒”,后来听说遭了贼,便马上提了梢棒去后堂赶进花园,结果遭到张都监的陷害。又如《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孔明“手里拿着一条梢棒,背后十数个人跟着,都拿木杷白棍。”这两处的梢棒,并不是人们长途行路携带,而是日常居家所使。武松是日常演练武艺,孔明是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拿了一根日常使用的梢棒。因为都不是准备搏命厮杀,所以并没有刻意去拿杀伤力大的杆棒。结合《杨温拦路虎传》中挑选杆棒的描述,似乎也可以推想,梢棒常用常见,而杆棒收藏较为精心,不会随意放置。
梢棒虽然直径较细,但并不算短。《武经总要》云,棍棒“取坚重木为之,长四五尺”[13]。“长四五尺”稍低于普通人的身高,与眉梢等,故而被常人们呼作“齐眉木棒”。武松后来又去“松树边寻那打折的棒橛,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打断了的棒橛仍可使用,可见梢棒其实并不短。当然,长短粗细毕竟是相对而言的,各人所执标准不同,如果跟超过身高的长枪相比,那么,稍短于人身高的杆棒实在称不上长,所以话本《勘靴儿》里又将其称为“齐眉短棒”。抛开模糊不清的“长”与“短”,如果以“齐眉”为标准,考虑普通人的身高,则木棒大概应是一米六至一米七左右。
梢棒因何得名,文献无征,但就版本而言,李评容与堂本、钟评本等诸本均作“梢棒”,双峰堂评林本则写为“稍棒”,唯有金圣叹贯华堂本统一为“哨棒”(不过,李评本及钟评本第七十三回出现一处“哨棒”)。原“梢”之义,《辞源》谓,“树枝的末端”,如“眉梢”即取此义(无独有偶,“稍”字亦可指“禾的末梢”),或许梢棒亦因此而得名。
现在通行的人教版语文课本将梢棒释为“行路防身用的棍棒”,界定了它的功能,虽无大错,却并不确切。《水浒传》中的梢棒,应是“直径较细、轻巧便携的杆棒”,它当然也具备防身功能,只不过因追求轻巧而致杀伤力有所削弱。结合《汉语大词典》中“哨棒”释义(《辞源》中无此条),我们似乎可以修改为“行路防身等日常使用的直径较小的木棒”。
值得稍加申说的是,此处“直径较小”是相对于“杆棒”释义中的“粗木棍”而言,不加限制亦无不可,但略加说明似乎更为妥当。《五代史平话》里说朱氏兄弟“平常间吃粗酒,使大棒,交游的是豪侠强徒,说话的是反叛歹事”。特意强调杀伤力大的粗木棒以凸显朱温等人的勇武,可作参照。
此外,早期《水浒传》诸本写作“梢棒”,名实相符,金本《水浒传》将其改为哨棒,不知何据。语文课本选自今日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传》,以容与堂本为底本。但在历史上,金本影响较大,故哨棒之名更加广为人知,但因此据“哨”字来解释其形义,恐有望文生义之嫌。当然,考虑到语言文字的规范性,无论是“梢棒”还是“哨棒”,在阅读《水浒传》时都应该依从它们的常用读音,以免造成新的误解。
[参 考 文 献]
[1]许发金.说“哨棒”[J].语文知识,2005(03).
[2]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三卷[Z].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358.
[3]胡嘉辰.“哨棒”辨讹[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09).
[4]王国兴.哨棒为何易折[J].小学教学参考,2005(13).
[5](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90.
[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7246.
[7]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0:125,523,126.
[8]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4.
[9]谭正璧著,谭寻补正.话本与古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16.
[10]赵兴勤.中国古典戏曲小说考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4:43-44.
[11](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66.
[12](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1441.
[13](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M]//《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3-5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出版社,1988:687.
[作者简介]潘雨晴(1990),女,湖北省黄石市开发区·铁山区太子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