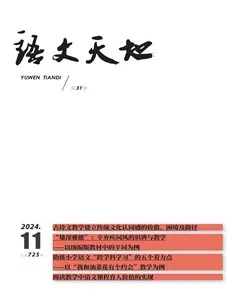“雄深雅健”:辛弃疾词风的识辨与教学
[摘要]辛弃疾词是豪放词的代表,于苏辛词共同的“豪放”风格之外,辛词风格又可细致辨识为“雄深雅健”。基于辛弃疾的审美情趣、心态变化,以及苏轼词作对其的影响三方面出发分析辛弃疾词风如何建构,从语言和手法的角度探究“雄深雅健”词风的艺术特色,教师则需要运用“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的方法以及“比较阅读”“专题阅读”的方式开展辛弃疾词风的教学,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关键词]辛弃疾;词风;雄深雅健
[中图分类号]G633.3/G623.2 [文献标志码]A
统编版语文教材中选取的辛弃疾词作有七篇,分别是四年级下册的《清平乐·村居》、六年级上册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九年级上册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九年级下册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以及高中必修上册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部分语文教师往往会先介绍辛弃疾的“豪放派”身份,再强调其“豪迈”的词作风格。广大语文教师在讲授辛弃疾词时,不能局限于“豪放”一词,要使学生全面体会辛词风格。本文试从辛弃疾词作风格的形成入手,揭示辛弃疾词作如何体现“雄深雅健”的词风,并尝试提出一些教学方法,以求能为有关辛弃疾词作风格的教学带来启示。
一、辛弃疾“雄深雅健”词风的识辨
从教材所选辛词的题材与风格来看,小学阶段题材较为单一,偏重于辛弃疾的清疏奔放的农村词;中学阶段题材丰富,包括咏史、咏怀与军旅等题材,词风汪洋恣肆、豪放壮阔又深沉婉转。刘禹锡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的序言中记载韩愈称赞柳宗元文风“雄深雅健”,与司马迁文章风格相似,司马迁《史记》的文风恢宏大气又婉而多讽;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细腻生动又清新俊雅;韩愈本人的作品奇险怪谲又密丽深婉。韩愈推崇此文风,可见“雄深雅健”意蕴丰富,襄括了上述三人的风格,大致表现可概括为汪洋恣肆,雄奇刚健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典雅密丽、清新淡雅、深婉沉郁的意味。辛弃疾本人也十分推崇这种文风,他在《沁园春·灵山齐阉赋》中用表现文章风格的句子来比拟灵山“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而“雄深雅健”四字恰好也可以用来涵括和界定辛弃疾词作的风格。巩本栋《辛弃疾评传》中将其总结为:“以雄奇刚健、清疏奔放或汪洋恣肆为基调,而又不乏深婉、典雅与丽密之致。”[1]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下,辛弃疾刚柔并济兼有百家之长的风格由此建构。尽管在辛弃疾的单篇词作中,以上两方面特征中的某一方面会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无论是整体上抑或是某些篇目中,辛词都体现出“雄深雅健”的风格特色,而这种文风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原因。
首先是因为辛弃疾广泛的审美情趣。辛弃疾在以词描摹景物、表情达意与反映现实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其广泛的审美情趣。一般读者都对稼轩词中雄浑阔大的战争场面印象深刻,《破阵子》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词人以醉为由,以梦为引,在迷离梦幻中回到了沙场点兵点将之刻,在卢马背之上于霹雳间穿梭,携三尺剑渴求立不世之功。此等对于军事意象的运用与战争场面的刻画,在稼轩之前罕有人为。除了对于宏大战争场面的描绘以外,词人也将视野投射至乡野林间,在《清平乐》中,词人于溪边青草上,低矮茅檐下,静观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画面;在《西江月》里,词人在浸润着稻花香气的夜色中听取蛙声蝉鸣、欣赏星稀月明,零星的斜风细雨也成了美好生活的点缀。由此可见,辛弃疾在追寻雄豪壮阔的情趣的同时也满含着对自然平易之美的兴致,从而使壮美之景与优美之景,代表军事的阳刚之美与代表乡村的平淡之美有机结合在一起。
其次是受苏轼“以诗为词”创作方式的影响。词这一文体自隋唐始,于两宋兴,但始兴之际的词作多是娱乐消遣之作,题材也以闺怨艳情为主,流行于勾栏酒肆之间。而柳永、张先、王安石以及苏轼等前辈词人的努力改变了这种现象,尤其是苏轼。苏词“以诗为词”的写法启发辛词“以文为词”的作法。“以诗为词”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突破传统词的“艳情”藩篱。苏词在题材方面做了空前的开拓,以诗的题材为词的题材,“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2]。以统编版教材中的苏词为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从具体的兄弟间的离愁别绪引发至普遍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从太守的射猎活动出发延伸至从军边塞,抗击外敌的爱国之志;《念奴娇·赤壁怀古》从古人古迹古事出发抒发自己对于英雄人物的神往;《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于日常行程中遇雨而联系到人对于生活中坎坷困难的态度;《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表达对亡妻真挚动人的悼亡之情,苏词在题材上的开拓为辛词在题材的挖掘做了铺垫。二是突破传统词的表现形式。题材的丰富与主题的扩充必然会带来多样化的表现手法,苏轼将诗的形式作为词的形式,将宋诗中较为常见的议论与说理代入词中,给词带来了更为繁复的书卷气息。而到了辛弃疾,又进一步将苏轼的“以诗为词”发展成“以文为词”,产生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
学界关于辛弃疾词的分期各有不同,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对于辛弃疾词创作时期的考证与五个阶段的分期[3]来看统编版教材中的七首词,《太常引》写于江淮两湖之什(1163—1181),这一阶段的辛弃疾虽有官职在身,但当时的政治局势偏安苟且,社会文化思潮懦弱萎靡,而作为“归正人”的辛稼轩只能将恢复难期的忧愁与壮志难酬的苦闷寄托于词作当中:在中秋佳节之际,词人被月光笼罩,本是美好之景但词人却反问明月“被白发、欺人奈何?”感慨自我年华已逝。《清平乐》《西江月》《丑奴儿》《破阵子》写于带湖之什(1182—1192),此阶段的辛弃疾被弹劾去职,心态也较之前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前两首词表现出他努力用儒家的进退精神抚慰自我,以颜回与陶渊明为榜样人物,寄情于山水田园;另一方面,由于辛弃疾对恢复故土的坚定信念,使其不自觉地在后两首词作中流露出对韶华流逝与功业未建的遗憾。《南乡子》与《永遇乐》写于两浙铅山之什(1203—1207),这是词人生命的最后阶段,虽然有感于人生大限的到来,但词人仍有坚定恢复故土的信念,《南乡子》中词人渴望自己的国家也出现孙权这样“坐断东南”的英雄人物,《永遇乐》中词人以历史英雄人物廉颇自比,“尚能饭否”的呐喊是稼轩渴求发挥生命余热的呼声。
二、辛弃疾“雄深雅健”词风的艺术特征
对于辛弃疾词风的艺术表现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可以让师生更为清晰地把握辛弃疾“雄深雅健”词风形成的规律,从而为古诗词阅读与教学提供一些可以遵循的方法。以下将从语言与手法两个角度来分析统编版语文教材辛词“雄深雅健”词风的艺术特征。
(一)语言的角度
首先是“以文为词”。宋人潘牥有言,“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1]244,精准地指出苏词与辛词在语言上的艺术特征。南宋陈模于《怀古录》中最早提出“以文为词”,其中“文”是指文章,“词”是指词作,“是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1]244,“以文为词”就是以散文手法入词,集中表现在运用问答体,发议论,用典故以及句式散文化等方面。以统编版教材中的辛词为例,“以文为词”的表现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语言散文化的特征。散文化的语言使词作整体更为流畅,削减词作的跳跃性的同时增强词作的连贯性。《永遇乐》末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破阵子》末句“可怜白发生!”都采用散文化的句式与语气。《南乡子》中“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更是将叙述与议论相结合,在抒发对历史人物崇敬的同时又隐晦地显现出词人对于恢复故土的期待。二是结构的叙事性特征。由于词人在词作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方使得词作能够在简短的篇幅中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永遇乐》一次性将五个历史人物串联在一首词中,《破阵子》以梦为引串联起挑灯看剑、麾下分炙、沙场点兵等一系列画面,并塑造出独特的英雄人物形象。
其次是语言上的雅俗兼用。遣词造句的用雅用俗往往与词人的创作主张与审美情趣密切相关,同样也和作者所描写的内容与题材有关,当稼轩将词作的主题界定为身边的琐碎世情时,语言往往具有用今用俗的特征。稼轩词中的用俗是指以俗语、口语或者谚语来写景状物或表情达意。而这种俗语的使用往往使词作的感情变得细腻,风格变得清新。如小学阶段的《清平乐》,全词以白描的方式描绘出农村的和谐生活,下片化用乐府民歌中的句子,通俗易懂又不落于浅白。而到了中学阶段,辛词的主题深化,语言往往也呈现出雅的特色。不论是咏史抒怀的《永遇乐》和《南乡子》,还是题赠友人同僚的《破阵子》,多用典故或引经史子集中的句子,妥帖恰当又含蓄蕴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不同阶段所学的辛词进行对比学习,引导学生自己发现辛词在不同学段所表现出来的特色,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并进一步提升学生在写作中熟练地运用口语与书面语的能力。
(二)手法的角度
首先是比兴兼用,比兴的手法滥觞于《诗经》,比是譬喻,即形象的比喻;兴是触物起情或托物寄情,即将客观物象所引发的主观情怀通过客观物象构成主客观统一的诗歌艺术形象。这种手法往往出现在咏怀、咏史与怀古等题材的词作中。如《太常引》借神话传说强烈地表达了词人反对投降、立主恢复的政治理想。学生在掌握了古典诗词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时,解读诗词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意象本身,而是能够从梅兰竹菊想到人的志向高洁,从外部自然界的风雨蹉跎想到人生的一路坎坷。教师在讲解过程中也需要注意,所谓“不愤不启”,教师应在学生疑问的关节阶段予以提示,尽可能地让学生自己去思索与体会,避免牵强附会的解释引发的种种谬误。
其次是善于用典,“典”是指典故,包括事典和语典,事典是引用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语典是对前人警句妙语的援引。典故往往能以不多的字数表现复杂的情感,教材中的辛词,典故运用之最当属高中阶段所学的《永遇乐》。《永遇乐》全篇只有“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三句没有用典,其他处处用典。前人对于辛词中的用典,褒贬不一。陈廷绰认为稼轩词用典“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刘克庄则认为辛词“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对于典故的运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首先需要让学生明确的是:典故的运用不在于其多少,而在于所用典故是否能准确地传递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其次,教师需要让学生了解教材中典故的含义,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积累常用的典故。学生如果不了解词中的典故,对于词作的理解也就无从谈起。学生在学习或阅读过程中遇到典故也要细心揣摩,尽量在了解典故含义后解读文本。
三、辛弃疾“雄深雅健”词风的教学方法
读者对于辛弃疾词风的理解有深有浅,有难有易,更随着年龄的增长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因此从教学角度来看,在不同学段的教学应有不同的教学策略。总体上看,小学阶段的辛词浅显易懂,词风清新淡雅;中学阶段的辛词意蕴丰富,词风深婉典雅。教师应该遵循学生认知的特点与规律,尽量做到删繁就简、循序渐进、逐步深入。以下将提出两种教学路径以供参考。
首先,“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方式是启发学生领悟辛弃疾词风的有效路径。在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孟子的“知人论世”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解读方式之一,“知人”即介绍作家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变化,“论世”则强调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这种方式遵循“修辞立其诚”的文学创作传统,要求在阅读欣赏某位作家的作品时,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解读文本。“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辅相成,读者需要在联系作者的生平及其时代的基础上,从作品的实际内容去推测作者的创作意图,这就是“以意逆志”。而对于不同学段的学生来说,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又有所侧重。
对于小学阶段的辛词教学,教师应该把握“知人论世”的尺度,避免对于文本的过度阐释,在把握尺度的同时要求学生“以意逆志”。《古诗词教学须用对用好背景知识——从一则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教学实录说起》[4]中记录了一则课例,课例中的教师在解释《清平乐·村居》中的“醉里吴音相媚好”的“醉”字时,过于强调辛弃疾的爱国情绪,将“醉”理解为不能保家卫国的“悲和愁”,把“最喜小儿无赖”的“无赖”解释为“无所事事”,实在是穿凿附会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由于教师过于强调“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而忽略了文本自身的“意”,过度解读文本而不考虑学生的理解能力。在中学阶段,学生的理解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提高,教师需要丰富“知人论世”的内容并更强调学生能够“以意逆志”。如在讲解《丑奴儿》时,既要详细介绍辛弃疾闲居带湖时的复杂心境,也要让学生以文本为根揣摩文意:一方面词人沉醉于农家田园之乐的时刻,《清平乐》创作于此阶段,此时需要强调文本之意;另一方面学生在理解《丑奴儿》的深刻意蕴时,更强调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去体会文本所传达的年华已逝、愁苦满怀之意。
其次,“比较阅读”与“专题阅读”的方法是帮助学生理解辛弃疾词风的可行方式。辛弃疾的存词量大且风格多样,这一特点为语文课堂进行比较阅读提供了现实基础。而高中语文课标在“文学阅读与写作”这一任务群中要求:“运用专题阅读、比较阅读等方式,创设阅读情境,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引导学生阅读、鉴赏、探究与写作。”[5]教师可从教材所提及的七首词出发进行比较阅读与专题阅读方法的实践。比较阅读指的是将内容或形式上相似的两篇或多篇诗词放在一起进行阅读教学,学生需要从多篇词作中找到相同点与不同点。高中阶段的教师可以将《永遇乐》与《南乡子》进行对比阅读,两篇词作同为稼轩京口时期的怀古词,表达的手法与情感也大同小异。比较阅读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也可以是不同作者的同主题作品。如在讲授《破阵子》时,可以将其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进行对比阅读,让学生体会苏词与辛词的同与异。专题阅读与比较阅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比较阅读突出的是同中之异,专题阅读更加强调在同类词作中找到共性,强调词作之间的联系。在高中语文课标“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这一任务群中强调“多角度、多层面组织主题单元学习”[5]21,在中学阶段教授稼轩词使用专题阅读的方式进行教学,可以使学生更加有针对性地学习古典诗词。
面对辛弃疾的词作风格教学,教师需在认清所教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方法的组织安排。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循循善诱,以使其从经典诗词中获取人生智慧。
[参 考 文 献]
[1]巩本栋.辛弃疾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23:216.
[2]俞汝捷.中国古典文艺实用辞典[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67.
[3]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2.
[4]詹丹.古诗词教学须用对用好背景知识——从一则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教学实录说起[J].语文建设,2018(22).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18.
[作者简介]季鸣(2000),男,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学科教学(语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