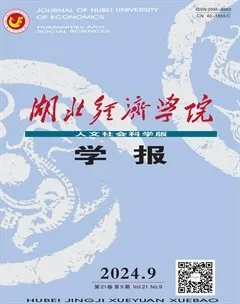区块链智能合约中版权合理使用的机制完善
摘 要: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强技术保护模式正在逐步侵蚀版权法领域所确立的利益平衡立法宗旨。合理使用作为平衡版权利益的重要基础,在技术层面上因智能合约代码对法律价值的损抑使其难以转化为代码规范,在立法层面上因著作权法未设置对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合理规避而使其呈现利益失衡态势,造成了应用在版权领域的区块链智能合约治理需求达到了既有法律规范所不能及的程度。为此,需基于技术与法律的双重视角,在依托技术规则的基础上,剖析其所体现的法律治理规则的建构范式,对区块链智能合约执行的前、中、后的全流程布局,并在立法层面加强对技术保护措施的合理规避情形,共同推进版权合理使用机制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的有效落实。
关键词:区块链;智能合约;合理使用;版权保护;立法完善
一、引言
《著作权法》以版权保护和文化繁荣的双重目标为立法宗旨,维护版权领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面对版权数字化新型业态形式的兴起,《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开发运用”,使近年来“区块链+智能合约”被频繁应用于版权领域中,以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版权安全的强化保护。但需注意的是,区块链智能合约作为版权领域的一种强技术保护措施,虽作为版权人保护版权的必要方式之一而具有正当性,但在技术保护措施的复杂授权程序中,公众及非营利机构对版权的合理使用也将会受到不当限缩,故而版权技术保护措施在理论上仍应受到相应的限制,以维持版权法领域的利益平衡立法宗旨。
学界对区块链智能合约在版权领域的应用主要从版权保护和版权限制两个维度展开研究。一方面,从版权保护视角出发,主要研究区块链智能合约的不可篡改性可对数字版权侵权乱象的遏制[1],去中心化模式对版权人经济利益的分配保障[2]以及自动执行机制对版权流转效率的促进[3],强调通过技术手段以强化对版权人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从版权限制视角出发,主要研究区块链智能合约强制自动执行机制对合理使用的冲击[4],主张以算法推进版权合理使用决策[5],强调应对版权人的专有权利进行适当限制,避免严格技术保护措施下版权人权利的过度扩张挤压合理使用空间,但更多仅聚焦于对图书馆合理使用规则的挑战[6]。
可见,当前学界研究对区块链智能合约在版权交易领域中的应用更多倾向于探讨其对版权人权利的强化保护,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版权限制与例外则关注不足。同时受限于技术与法律之间的专业壁垒,学界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底层技术构造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未能挖掘合理使用制度难以融入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本质原因,使当前版权合理使用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的治理范式缺位。加之以《著作权法》修改后对技术措施的倾向性保护,使法律层面上对技术措施的合理规避情形设置不足,导致了当前版权领域所呈现的“超级版权保护”现象,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使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的悬置风险进一步加剧。
二、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概念与法律性质
(一)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概念
智能合约技术被我国工信部定义为一种数字程序,可通过计算机代码的自动运行实现无需第三方介入的自动确认和合约执行[7]。“以太坊”的诞生使智能合约与区块链技术实现完美融合,开启了“区块链2.0”时代。在各分布节点全链条保护的技术加持下,版权人可实现在统一储存节点上记录版权作品的数据和信息,并依靠哈希值的严格对应关系,确保各节点之间的数据和信息无法篡改,以实现对数字时代版权侵权乱象的遏制。赖于智能合约和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二者在概念内涵和技术特征上保持了一致性,具有去中心化、自动执行、不可撤销等特点,可在版权确权、交易和维权三个方面对版权进行保护,大幅提高数字时代版权保护力度与交易安全。
(二)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
关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法律定义与属性,学界尚未形成定论,目前存在计算机程序说、合同说、要约说、担保说等观点。从数字技术角度切入的计算机程序说观点认为,区块链智能合约本质上是一种计算机程序,基于代码或指令序列设定,在其自动执行的过程中并未涉及任何法律,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现象,无需为其赋予特定的法律含义[8]。从合同法理论角度切入的合同说观点认为无论是从成立过程还是生效规则来看,其与传统的合同存在较多一致之处,传统合同的缔约目的与执行结果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了实现,并且其缔约方式与履行内容均符合民法典合同编的有关规定[9],因此可将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执行纳入合同领域并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除此之外还有担保说,认为区块链智能合约是在传统的合同之上附加了以技术形式表现的担保机制,以辅助缔约目的的实现[10];起源于自动贩卖机的要约说观点认为自动贩卖机属于要约,购买投币行为属于承诺,因此区块链智能合约执行过程可视为要约的成立[11]。
其中占据主流的观点为合同说,此观点可最大限度对区块链智能合约进行法律规制,以有效回应当下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实质上,随着区块链智能合约在各个交易领域的应用,其在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上已具备了和传统合同的一致性[12],是符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合同形态,已被司法实务和美国立法所采纳。
三、技术与法律双重向度下的合理使用风险解析
(一)合理使用制度难以转化为计算机代码规范
数字程序的计算机代码语言与法律语言之间的隔阂给区块链智能合约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植入造成了严重障碍,进而使版权合理使用制度被悬置。本质上,区块链智能合约与版权合理使用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代码与法律之争,即代码在法律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与既有法律规范之间的摩擦与冲突,版权合理使用制度作为一种具有事前不确定性的法律标准,在传统法律规制框架下具有其所蕴含的特定利益,难以通过简单的计算机程序语言进行规范适用。
智能合约是与区块链交互以执行的if-then语句,即通过计算机代码的形式,在授权之前进行程序编码,一旦触发相应指令,便可通过代码的运行进行执行。对版权领域的智能合约执行过程来说,智能合约的代码语句所呈现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一旦对方需要使用某种作品(if),便可通过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获得相应的版权许可(then),实现了版权使用过程的自动化,并直接将权利分配给版权使用者,收益分配给版权人。在此过程中代码语言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在预设条件设置上相较于法律能更为精密,无需考虑文化、政策等外部因素对合约内容的影响。但“绝对客观”的代码却无法解决一切事物的价值评价问题。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了规定,其中该条规定的“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等目的可以免费使用他人作品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尚属于高度抽象的判断情形,对于代码化的区块链智能合约系统来说更难以简化为规范的计算机语言,导致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规定的例外情形被计算机程序架空,严重阻碍了合理使用制度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的有效落实。
(二)《著作权法》对技术措施合理规避的立法失衡
技术的发展与变化不断影响着法律的修订与调整,为应对网络环境的变化和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数字技术的出现,我国《著作权法》在2020年迎来了第三次修订,对涉及技术措施的含义与类别、禁止对技术措施实施规避的行为以及允许合理规避技术措施的例外情形均作出了规定,逐步构成了保护技术措施的完整体系[13]。但对于实践中与合理使用制度密切关联的技术措施合理规避情形的空间却显得过于窄化,使版权人在强技术保护措施下阻止公众合理使用作品,版权保护利益呈现出日益扩张的失衡趋势。
当前我国《著作权法》中存在技术措施保护水平过高、合理规避技术措施例外不足和防止技术措施的滥用机制的缺乏等弊端。根据《著作权法》第49条可知,我国的禁止规避行为既包括直接规避也包括间接规避,其保护强度明显高于仅禁止间接规避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对于合理规避技术措施的例外我国《著作权法》仅规定了5种情形,对图书馆等特别适用主体的例外情形和开放性条款的规定明显不足,阻止了公众依据版权例外规则合法使用作品的途径,使公共利益的保护机制难以运行;此外,我国《著作权法》中缺少针对技术措施的滥用机制,使得如今的版权保护呈现出技术和法律的双重护航。而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体系不同,我国知识产权体系正处于发展阶段,公共利益的保护应放在首位以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如何在我国《著作权法》所呈现出的强技术保护措施体系下确保合理使用等公共利益不会削弱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商榷。
四、区块链智能合约中版权合理使用的机制完善
(一)构建执行过程前的内部自动干涉机制
囿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机制对版权合理使用存在不可控的技术风险因素,应提前构建执行前的内部自动干涉机制予以预防。虽然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运行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但在其设计和运行的过程中仍需要一些中心化节点的存在来辅助运作,因此可在这些中心化节点设置政府、平台等监管介入的“阻塞点”,实现智能合约由“去中心化”向“弱中心化”的转变。
具体而言,区块链智能合约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纠偏,最便捷的方式便是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引入相对柔性的调整机制,构建执行过程前的规范性评价自动干涉执行机制。对此可采取两种路径:一是中止条款的设计,二是智慧仲裁的设计。对于中止条款,可将图书馆大规模合理使用版权的特定事实以代码的形式写入智能合约监测系统,当智能合约监测到时便自动终止执行。对于智慧仲裁,可在智能合约中写入智慧仲裁条款,若相对方因确实存在《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为个人学习等目的的合理使用情形则可提议终止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执行,并以数字签名的形式向智能合约系统提交仲裁申请。相对而言,终止条款的设计更为高效便捷,可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本身化解纠纷,但合理使用情形过于繁杂且情景化程度较高,仅适用于图书馆这类较为清晰、明确的合理使用规则,此种方案较为欠缺灵活性。第二种智慧仲裁的方式较为灵活,可实现区块链智能合约由“去中心化”向“弱中心化”的转变,但仲裁成本较高,且缺乏普适性。由此可见二者之间各有优劣,需同时构建外部风险防控机制予以完善配合。
(二)嵌入执行过程中的外部风险防控机制
对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外部干预者角色,法院、版权管理平台和网络服务供应商最适宜充当,应分别建构相对应的风险防控机制。首先,法院可在版权领域的区块链智能合约中预留权限节点接口,允许在区块链智能合约执行过程中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有关判决终止智能合约的执行,权限接口成DX7oX4J34ARB7nGcxBFgZrbC7Q02W8yZc9evEqbQrW0=为规范性评价的介入执行渠道;其次,可以强化平台责任以实现间接纾解智能合约的执行风险,要求平台设置填充框,提示当事人在智能合约中重申版权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一旦实际作品使用情形与之相悖,且当事人又拒绝对此中作品使用情形进行回复,平台将对此行为进行公示,并对当事人平台信息进行公开,以提醒其他版权人回避风险,落实平台“避风港规则”的规定,要求平台承担相应的责任以降低版权人在智能合约中遭受侵害的风险。
除此之外,智能合约在版权领域的运用尚处于成长和试验阶段,智能合约为版权领域带来的潜能和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与释放。因此在构建智能合约执行前的外部风险防控机制时,应采取相对温和的监管模式,防止刚性监管模式对智能合约技术创新和应用的遏制。可采取金融领域的“监管沙盒”理念对智能合约在版权领域的执行进行适当监管。所谓“监管沙盒”,是指主体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空间”内对其新产品、交付机制等进行实验,而无需承担在正常从事相关活动中的监管后果。可将监管沙盒引入到版权智能合约之中,平衡智能合约的应用风险与鼓励智能合约的应用创新,建立“中国式监管沙盒”的智能合约监管模式[14]。
(三)改进不当执行发生后的法律救济方案
鉴于区块链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后的无法撤销性,需对符合版权合理使用却仍遭智能合约不当执行的情形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方案。依前所述,关于区块链智能合约法律属性的主流观点是将其认定为合同的形式之一,因此应在《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的规范内容与程序框架内对不当执行的智能合约提供法律救济,以最大限度发挥我国既有法律制度的救济功能。
需注意的是,区块链智能合约并未出现在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和合同编的调整范围之内,因此智能合约的合同属性在我国尚未获得立法层面的支持。但通过前述对区块链智能合约底层架构的技术性执行过程解读可知,在理论层面可论证区块链智能合约具有合同属性的合理性。区块链智能合约执行过程所采用的if-then语句的共识机制,一旦触发执行便体现为当事人合意的真实体现,也即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执行过程具备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是缔约主体合意的真实表达与体现。
当事人一方若出于对作品的合理使用需求而进行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签订,并非出于其他非合理使用的情形而实施签订智能合约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因受限于版权法的利益平衡立法宗旨,此种民事法律行为对版权人过分有利而对作品使用人过分不利,在区块链智能合约执行时利益关系明显失衡,故而可通过显失公平来进行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撤销。据此,对于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而受到区块链智能合约的不当执行情形,可认定为因显失公平而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来寻求法律救济。
(四)完善价值平衡的版权立法模式
法的价值在实现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现实矛盾,当矛盾所引发的失衡局面发生时,就需要对各种价值进行评价、选择和协调,以扭转失衡局面达到平衡状态。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技术保护措施代表的是版权人的利益,是一种私人利益,而合理使用则代表的是社会公众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二者背后蕴含的是不同价值主体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但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对版权人技术措施的保护具有明显倾向,由合理使用制度衍生出的对技术保护措施的合理规避例外情形偏少。为促进社会公共文化繁荣,合理使用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必须在著作权法中占有重要席位,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以扭转当前法律层面的利益失衡局面。
但囿于法律的稳定性,且法律修订需照顾多方利益,履行较为复杂的立法程序,平定各方主体在订立过程中的立法争议,耗时耗力,因此《著作权法》不宜做频率过高的修订。但根据现行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兜底条款,对与版权相关的行政法规,如《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规中的合理使用规则进行修订,并根据技术的发展进行更新,在技术保护措施扩张的同时也不断扩大合理规避的范围,及时回应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使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无限趋近于真正的开放式一般条款。
为协调技术保护措施与合理使用之间的失衡关系,可在行政法规中新增避开技术措施的合理使用类型。溯源至《WIPO版权条约》可知,WIPO将技术措施纳入条约保护范围的同时,也设置了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例外来实现作者激励价值和社会公共价值之间的微妙平衡,故而当前网络技术环境的变化、数字版权侵权问题的加剧并不是版权人以强技术保护措施及有限规避豁免等方式来无序扩张版权保护的理由并不具有合理性。为此可对《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进行修改,引入专门的避开技术保护措施的合理规避例外,对《著作权法》中仅限于教学或科研的合理规避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图书馆用户等教学或科研人员以外的社会公众提供基于个人学习、介绍评论以及文本与数据挖掘等目的的合理规避情形,以有效降低当前立法体系所呈现出的技术措施规避例外的保护强度,扩大技术措施合理规避的适用范围。
五、结论
为维护版权法中的固有利益平衡宗旨,在以区块链智能合约为代表的强技术保护措施的应用趋势下,需格外关注版权合理使用机制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的有效落实。面对技术层面上版权合理使用制度无法转换为代码规范的固有弊端,可通过对区块链智能合约执行过程的前、中、后进行全流程治理布局。首先构建执行过程前的内部自动干涉机制,根据不同的执行情景选择终止条款或智慧仲裁的提前介入;其次嵌入执行过程中的外部风险防控机制,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预留权限接口,并利用监管沙盒进行相对温和的监管治理;最后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不当执行后的法律救济方案中,应将智能合约认定为合同的形式之一,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执行过程视为订立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对符合合理使用情形仍被自动执行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应将其认定为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对区块链智能合约予以撤销。通过对区块链智能合约执行过程的全流程布局,全面落实区块链智能合约中的版权合理使用机制。同时,在立法层面上面对技术保护措施的合理规避情形的缺失,可通过《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引入专门的技术保护措施的合理规避情形,使强技术保护模式下的合理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以维护区块链智能合约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 张辉,王柳.区块链下网络文学版权保护问题研究[J].法学论坛,2021,36(6):114-120.
[2] 舒晓庆.区块链技术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中的应用[J].知识产权,2020(8):68-76.
[3] 梅术文,曹文豪帅.我国统一化数字版权交易平台的构建[J].科技与法律,2020(6):9-15.
[4] 刘桢,马治国.利用区块链开展版权保护的局限与应用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2019(9):48-52.
[5] 华劼.自动版权执法下算法合理使用的必要性及推进[J].知识产权,2021(4):34-44.
[6] 赵力.智能合约下版权合理使用及图书馆因应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8):5-10.
[7] 肖君拥.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法理审思及法律规制[J].学术交流,2023(8):32-47.
[8] 张力.智能合约嵌入合同的功能主义阐释[J].社会科学辑刊,2023(5):46-56+238+2.
[9] 夏庆锋.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分析[J].东方法学,2022(6):33-43.
[10] 倪蕴帷.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的民法分析、应用与启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3):170-181.
[11] 王泽鉴.债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56-157.
[12] 陈飏.关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合同属性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23(5):91-99.
[13] 王迁.立法修改视角下的技术措施保护范围[J].中外法学,2022,34(3):643-662.
[14] 陈志峰,钱如锦.我国区块链金融监管机制探究——以构建“中国式沙箱监管”机制为制度进路[J].上海金融,2018(1):60-68.
作者简介:刘学荣(1999- ),女,河北唐山人,吉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