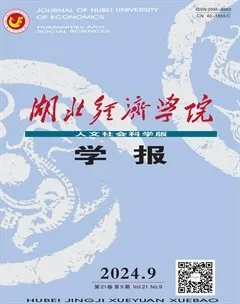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
摘 要: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土地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国家生产力”等概念,马克思对这些“生产力”概念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生产力理论。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生产力概念创造性提升到哲学维度,从矛盾视角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新时代条件下不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养与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生动地体现了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历史延续和生成逻辑,对实现历史向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突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高质量发展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和生产方式发展状况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并推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目前,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凸显为三个方面:首先主要集中在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概要。张林和蒲清平认为,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是在科技创新资源的转化与融合过程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孕育出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高效能、高质量利用上,更在于对自然环境的深度改造与和谐共生[2]。徐政、郑霖豪和程梦瑶则从运动的角度出发,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在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下,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优化升级[3]。其次,探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对于这方面研究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重维度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一方面认为新质生产力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一方面指出其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趋势[5]。最后,阐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有学者以体制变革为重点,提出应以建设新型举国体制为重点发展新型生产力[6]。有学者认为应以数字新质生产力为引导推动构建新型产业体系[7]。有的学者则通过梳理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环境和战略定位,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条件的变化对症下药[8]。总的来说,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有益成果,但从概念源头来看,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多从总体、宏观把握,而较少把其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生产力”概念进行细致地对比探析,对生产力内在的要素分析也较为零散,同时对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更深层次的内生关系研究较少。从学理层面研究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对丰富和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更好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产力”概念的历史梳理及理论回顾
“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一直以来都是学界所讨论的关键概念。从词源学来看,这一概念源自“produce”,更早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producere”,意为引导、拉出,可以认为,该词与创新、创造等词不属于同一意味,更加强调对已有事物的某种转换和发展。从理论渊源考察,该概念的正式使用肇始于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François Quesnay),他提出“农业是财富的来源”的观点,使得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重要的一次转折。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赞扬魁奈道:“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从本质上来说是重农学派的功绩。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9]15马克思在此肯定了魁奈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马克思认为魁奈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魁奈的贡献在于“重农思想”。“没有人不知道,财富是发展农业的大原动力,要进行良好的耕作,必须有很多的财富。”[10]15,魁奈指出:“问题在于这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以十分之一税,给耕作者以利润。”[10]65在此魁奈认为只有通过农业生产才能满足君主、土地所有者、僧侣和耕作者的经济需求和财富增加,也就是农业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只有农业劳动。他在1757年在《谷物论》中指出:“正和土地所有者在为农地经营的必要而挖掘沟渠时很爱惜土地一样;真正的政治家在把人用于战争时,也是很爱惜的。和庞大的军队会把土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10]69在此魁奈把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局限在土地,并把生产力这个有一般性的概念局限在农业之上。但是,尽管他把社会生产力简单地与土地生产力等同起来,仍可以证明此时的国民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对物质生产内部的要素进行了分析。
在魁奈研究基础之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围绕分工理论提出了“劳动生产力”,将“生产力”概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斯密对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始终以增加国民财富为主旨,从其对劳动生产力问题的研究逻辑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步:首先,分工的进化是劳动生产力发展重要的推动力。斯密从国民财富的源泉中抽象出了劳动,而分工则是使劳动专业化和固定化的重要步骤。在斯密的例证中,一个包揽全流程扣针制作的工人在一天内制针的数量远远不能及将制针专门化为各个部门这一模式在一天内所制针的数量。他在《国富论》中指出:“生产力的最大改进,及其任何生产活动,所显现的技能与熟练程度,究其原因似乎均源于分工结果。”[11]6其次,劳动生产力本身的进步实际是劳动工具发展的结果。斯密认为,正是这种劳动的专业化和固定化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力,推动了机器的发明创造,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为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斯密仅从机器技术来探讨生产力未免有些肤浅,其对分工的过度褒扬也使他只能局限于市场规模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不能看到这种“劳动生产力”发展可能带来的劳动异化现象。同时,他对劳动主体的把握也较为孤立,并没有把劳动生产力的提升置于劳动集体之内,而是分离、分散地把主体拆分成一个个劳动个体。
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扬弃了斯密的理论,提出了“国家生产力”这一概念。在1841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系统地发展了生产力理论,从劳动主体层面来看,他认为推动劳动力的是“各种智力和资源为了同一生产过程而进行的联合或协作。”[12]这就突破了斯密个人劳动的狭隘界限,将集体联合纳入劳动过程中。从劳动力的内容来看,他认为劳动力是“获致物质财富的力量”[13]12,其并不受单一生产要素影响,而有赖于社会发展的状况。他指出:“国家生产力的来源是个人的身心力量,是个人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是国家所掌握的自然资源,或者是国家所拥有的作为个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即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物质资本)[13]193-193”,即认为生产力是一种物质、精神和政治的“合力”,一种涵盖多层社会因素的综合国力。虽然李斯特较之斯密在对生产力的认识上有所进步,但从他们的理论要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斯密还是李斯特,都没有突破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为了掩盖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最终目的,他们把一种浅薄的唯心主义包裹在剥削的内核之上。正如马克思所说,“他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主义的东西,然后才敢去猎取它。”[14]240
与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同,莫泽斯·赫斯以哲学思想为基础构建了一种“主体交往中的生产力”。他在《论货币的本质》中集中论述了相关生产力思想,认为货币是人与人关系的中间桥梁,其作为交换手段,已经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在交往过程中演化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成为“外化人的产物”。另一方面,他写道:“生命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15]137,也就是说,赫斯是从人的类本质这一哲学思辨角度考察生产力概念的,他认为个体共同的交换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激发起本质力量,而“只有这种共同活动才能实现生产力”[15]139。由此可见,赫斯已经突破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边界,开始在历史向度上考察生产力,并认为交往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人的本质在交往活动中被凸显,生产力也在这种交往活动中被激发出来。故而,只有实现一种真正的交往联合,即共产主义,才能真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魁奈的生产力概念只限定在土地生产中,始终困于重农主义的藩篱之内;斯密的生产力概念强调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他将理论的重心放在劳动过程上,并没有对生产力范畴作出科学界定;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虽具有一定综合性,但唯心主义倾向明显,且由于并没有在当时形成重要影响,只成为“没有解决问题的标签”;赫斯的生产力概念强调主体交往活动的重要性,且在后来坚持非经济因素在生产中决定作用,偏离了正确的理论发展,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总的来说,对“生产力”这一概念的阐述存在着一个以财富生产为尺度到走出经济学范畴的思维范式的转换,其理论也从为资本家服务发展为论证某种革命的、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实践因素。但是,不论是“劳动生产力”、“国家生产力”还是“主体交往中的生产力”,都没有真正触及生产力概念的本质,生产力概念的形而上学色彩浓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突破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力”概念的局限性,提出科学的生产力概念成为一种可能。
二、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形成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的继承与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问题在于把“生产力”概念局限在单一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与此不同的是,赫斯把“生产力”仅仅放在主体活动加以考察。马克思生产力概念既要突破领域的桎梏又要摈弃理论的狭隘化,真正地上升到哲学层面考察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生产力概念,就要回归到经典文本中加以探讨。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此时他对生产力的阐释主要是为了达到两方面的目的。其一,为了引用其他政治经济学家涉及的生产力问题观点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主要借用了斯密的“劳动生产力”这一概念,比如,他就曾引用斯密的“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来思考生产过剩问题;其二,马克思认为“分工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但最终目的是得出劳动异化这一结论。由此看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生产力问题的原初思考沿用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范式,没有对其进行原创性的阐发,也没有在哲学层面上对其进行理论加工。另外,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受到德国国民经济学李斯特的影响。李斯特指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13]46-47李斯特认为个人生产力和国家生产力、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不同。马克思对李斯特的批判道:“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14]242。他是从理论层面对李斯特的经济学展开批判,证明了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理论根本不是研究现实社会运动的结果,而只是编造出来的体系而已。马克思通过《神圣家族》以及《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逐渐超越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因此,由于马克思刚刚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的理论水平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相应地,他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只能借助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来加以认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矛盾的角度阐释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在哲学意义上实现了对过往经济学家们的生产力概念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使用“生产力”一词多达九十余次,实现了生产力的理论框架的初步搭建。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6]532-533在此马克思部分地吸收了赫斯的生产力思想,从经验层面系统分析了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人的交往所形成的力量构成了生产力的总和,并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尽管马克思此时已经能够从矛盾视角探究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了,但社会历史的发生学过程由于缺少生产关系的维度尚未被清晰地揭示出来。这一理论工作就在《哲学的贫困》中得以完成。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6]602马克思这一思路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形成的理论思路的一种延续。《哲学的贫困》主要是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从理论上说,这一批判对象促使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何以构成矛盾。因此,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形成和理论搭建,而在《哲学的贫困》里真正实现了从矛盾角度考察科学的生产力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力”概念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将其定义为“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17]291”,标志着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概念走向成熟。马克思从运动的视角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不可避免的灭亡结局,在推动这一历史逻辑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因素挖掘出来,他认为生产力是人们通过具体的劳动来生产出有用商品的能力,通过生产力的更迭,生产关系也相对地实现变革,世界历史在这两种要素的矛盾运动下不断向前推进。可以看到,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过往经济学家们在理论、思想史上作出的贡献,“生产力”概念就是在对这些理论的扬弃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着重批判了过往经济学家们理论的缺点,他看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显著的主观性,认为即使是像斯密、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作为永恒不变的公式,没有意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一般动力是具有历史性、阶段性的。同时,马克思扫除了过往经济学家们运用看似精妙的理论对无产阶级的欺骗,他在《资本论》中指出,麦克库洛赫、尤尔、西尼耳等经济学家们认为工人应该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其结果看似是使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得到缩短,不过是缩短了工人为自己工作的劳动时间,让资本家得到了更多利益而已。至此,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生产力概念的糅合,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重要的原动力,成为推动实现共产主义基础性的指向标。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第一,社会历史性。不同于经济学家们把“生产力”概念看作是一种简单抽象、一种超乎于世界之外的非历史的东西,马克思始终强调历史这一内在尺度,并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矛盾运动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基础。以此为依据,马克思扬弃了以往的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导的生产力理论,从社会生活的本质看待生产力活动,并认识到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化发展。第二,物质实践性。马克思从生活中找到了“生产力”概念的现实基础,并从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来解释生产关系。在他看来,任何生产力的进步都是实践的结果,通过实践活动,人们可以推动其自身的发展,最终达到人类解放这一宗旨。事实表明,只有立足实践、立足现实,才有可能掌握规律、利用规律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解放。第三,开放发展性。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所说,马克思的理论从来没有“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18]26。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概念,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是其他经济学家们所创造的那样死板的教条,它始终与时俱进,为后人根据条件、环境的变化继承发展留下可能。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所独有的特质为指向,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历史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凸显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核心要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2023年对黑龙江的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养与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生动地体现了与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深刻结合当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生产力概念“新质”的突破。
首先,新质生产力“新”在对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创新上。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7]592可以看到,生产力的内涵中除了包括工人主体、生产资料之一对象以及生产工具这些基本的要素之外,还包含了自然、科技以及管理等诸多要素,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看到了科技等新的要素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并通过一系列的例证分析了新的方法要素结合在劳动过程中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自21世纪初以来,随着数据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人们已经看得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以数据为导向的发展形式突破了传统产业的生产界限,使得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核心技术的研发逐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围绕着这一竞争场域,各国相继出台多个政策来打压、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企图在关键技术领域围堵中国、拖慢我国的科技迭代进程。因此,我国必须从自立自强、自主研发出发,以内源生长的优势突破外围制约,不断缩小在重要领域上与他国的距离。正如马克思所说,科技的发展能有效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消耗。想要解决现实难题,就必须积蓄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9]4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过去的实践成果,延续了对生产力理论地位的重视,强调发1mV9+mcNQTjagJJtiyQXVQ==展生产力、激活社会动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方面。在这个基点上,党坚持以创新驱动生产力的转型升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为生产力在新时代的发展道路增添新特质。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新”在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拓展上。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展现着我国在新时代对规律的新认识,也显示了其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能力的不断增强。从“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内涵要素来看,它从三个角度体现了其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生产主体来看,“新质”体现了高素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在技能的掌握上,劳动者作为劳动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已经不再是机械地进行简单劳动,随着AI同人的竞争加强,机器已经可以从事多种简单工作,劳动者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加强其数据处理、信息整合、创新研发等专业技能,决策、学习、研究等脑力活动在劳动过程中的需求程度逐渐提高;而从主体结构来看,劳动者也不再只是单纯的个体劳作或作为流水线的某个环节,而是逐渐形成跨学科的专业化团队或以技术型企业等为核心的新模式,从而实现了多学科知识的有效整合和专门学科领域的深耕研究。从生产对象来看,“新质”体现了互联网背景下客体要素的变革。一方面,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自然界物质。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对宇宙、海洋深处、新合成物质等未解之谜的解释不再遥遥无期;另一方面,以抽象数据为主的信息要素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劳动对象之一,这一客体要素的更新大大改善了生产力的发展轨道,内在地拓宽了生产力的前进道路,搜集、处理、分析数据信息已经成为引领生产发展的重要途径,围绕这一生产要素的领域也已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领域。从生产工具来看,“新质”体现了数据驱动下CPS形式的更新趋势。CPS即从现实活动中收集数据、在大数据空间利用人工智能对这些数据进行解析和处理,并将分析到的结果通过自动化控制等方式回归于现实世界,以这种更新趋势的发展为表征,展示出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显著增强。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的生产工具,其在生产过程中以人的脑力的外化为特点取代了大量的中间环节工作,因此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掌握并不断发掘人工智能的新可能,更好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现实问题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必然趋势。
最后,新质生产力在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质”上突破。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经济场域的新概念,尽管在本质上延续了生产力的基本意涵,但在特质上与传统生产力理论有着根本的变革。其旨在通过生产要素与科学技术的融合实现一种跃迁,超越了传统产业的弊病,使低碳、绿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形式;同时,“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条件,极大地发挥了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了个人需求、社会需求与产业发展的耦合。在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新质生产力”既囊括了新环境下生产力的变化因子,体现其时代性、创新性特征,区别了以往传统生产力理论,又坚持了生产力科学理论一脉相传的连续性、联系性,展现了党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一以贯之的重视和思考。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是以当代社会表征的内生变更为逻辑起点,以立足实现人民群众的最终利益为旨归,与时俱进地分析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现实情况,使其综合地包含了与现实需要相结合的基础条件。“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16]544-545”因此,新质生产力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说,而是体现本真现实结果、反映经济发展新质态、展现经济质量标准新要求的新思考、新表达。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顺应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开放发展的特质,它是一个现实的、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定义,代表着一种更高效、更和谐的生产力形态,昭示出新时代我国对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形势的现实回答。
四、总结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没有止境。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质生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质生产力既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真正实现了生产力的“新”与“旧”、“质”与“量”辩证关系,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表现和最新成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具有巨大的内生发掘空间,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发掘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从主体、客体和中介条件三方面进一步认识推进生产力的有效方法,是把握新质生产力概念、推动经济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要求。
参考文献:
[1]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001).
[2] 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9(6):137-148.
[3]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51-58.
[4] 周文,何雨晴.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24(3):1-15.
[5] 李政,廖晓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14(6):146-159.
[6] 曾立,谢鹏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J].经济纵横,2023(12):29-37.
[7] 任保平,王子月.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6):23-30.
[8] 魏崇辉.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理论与改革,2023(6):25-3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人民出版社,2004.
[10] [法]弗朗斯瓦·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商务印书馆,1997.
[1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杨敬年译.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12] 杨春学.李斯特与斯密:一种比较分析[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9):25-2.
[13]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德]莫泽斯·赫斯著,邓析议编译.赫斯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元叙事研究”(23XKS008);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省社科研究基地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历史政治文献’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QN202103);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资助“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视域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批判性研究”(KC-23235412)
作者简介:张小龙(1989- ),男,甘肃通渭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刘诗涵(1999- ),女,湖南益阳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