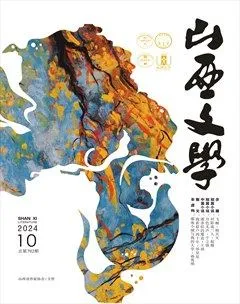那座小城与我的大学
其实,在山西师范大学的八年,我始终以一个学生身份生活在临汾那座小城里。这八年的学习,使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不自弃的力量。
——题记
本以为,退休后在家闲居,与山西南部那座叫做临汾的小城以及被舍弃的校区,早已渐行渐远。谁知,大学同学召集毕业四十周年聚会。连日来,同学老陈号召大家写文章,并询问进度。同学纷纷响应,太原、榆次的同学还提出了活动初步方案,令我怦然心动,引发了我对那所大学和小城的回忆和怀想,由此情不自禁而泪眼迷离——顿时醒悟到,原来我与那所大学早已血脉相连,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能阻断情感的纽带。毕竟,我最好的年华是在那里度过的,山西师范学院和临汾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一
1980年参加高考,我被山西师范学院地理系录取。9月初,大哥送我去学校,从我家门口乘长途公共车到阳方口(宁武)换乘火车经太原去临汾。这是我与吕梁山之外世界的第一次接触。
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感觉新奇又欣喜。从阳方口到临汾,坐了十多个小时晃荡的绿皮火车,到校后一连几天,脑仁都在晃荡,但这些丝毫未减少我对上学的向往与兴奋。
入学后,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一号教学楼、五号学生宿舍楼。开学典礼也是在一号楼南面刚刚建好、还未铺设草坪的操场上举行的。地理系的迎新晚会由77级仇锦学长主持。至今还记得77级学长演唱的小合唱《美丽的塞纳河》和79级学长吴体刚、佘可文表演的相声。当第一学期的课程表发下来时,才知道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理科生,我们这些文科生要学数理化。已经入学了,学好学不好反正就是埋头学呗,就这样懵懵懂懂开始了我的大学之旅。
对我来说,上大学最重要的是身份改变,至于在本省上哪一所学校没有选择的必要,只是觉得到临汾比去太原多坐七个多小时火车。
按部就班的大学生活,波澜不惊。来来往往的人群穿梭在宿舍、教室、食堂之间,我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匆忙地对视,彼此检阅着。如此几年。
二
说实话,我在地理系上学的四年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同时也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在诸多课程中,认真学过的就是《数学》《地质学基础》《地球概论》《地貌学》《气象与气候学》《经济地理学导论》。现在看来,能把上述几门课学好了,地理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掌握了大半。对于我来说,即使认真学了,也是浅尝辄止。
我喜欢上数学课,也是因为遇到了两个好老师:上微积分的吴诗咏老师,上数理统计的张国础老师。我们班都是文科考生,很大的原因是数理化不是强项。我选择文科,是因为天生长了个学文科的脑袋,但我的数学并不差,高考84分。当大家对数学畏难时,我可得学好。于是从图书馆借来相关的讲义、请教数学系的同学,登门向张国础老师求教。有一回数理统计单元测试我得过100分。毕业留校后,听过一次周作胥老师的量子力学课,正是通过和数学、物理两个系同学的接触,我渐渐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认识到世界上的确存在一些不可确知的东西。
我们上土壤学和土壤地理学,却是我最不愿意学习的,我是农民出身,带着与生俱来的土味,最熟悉的不就是地里刨食,我出来上大学,不就是要离土远一点吗?以致上土壤课几乎都在看小说,我可能是全班这门课得分最低的,也感谢赵修齐老师没让我补考。每个人在年轻时都会因无知而有偏激的表现,当明白了这种无知时,已经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尽管不喜欢花花草草的植物学,老师的讲课对我如催眠,还是从普通植物学上到植物地理学,从科属到植物分布、生态环境,认识到自然界看似自然生成,也是有高级、低级,尊卑、强弱之分的。我们上心理学,学习如何从个体推断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看见一些人的外在表现,就会联想到其人的心理。总结四年的学习,有意或无意,总会有所收获,有所茫然。
最可炫耀的是,我们每一学期有一次野外实习的机会,让别的专业的同学羡慕不已。带着罗盘、地质锤、卷尺、相机,还有草帽,近处坐学校的卡车,外地则坐公共车、火车,同学们都学过摄影,还能咔嚓咔嚓地拍照留影。回想起来,挺恨那些持相机的同学,比如陈国栋,怎么就没给我拍个照片?
野外实习的时候,估计其他男同学和我一样,总想着创造机会与女同学搭讪,但由于我天生笨拙,注定不会走近女生。而女生们也似乎从来不想搭理我这类男生。我曾心想,即使我从山顶上滚下去跌死,她们都不会过来看我一眼。
三
在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突然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将来,即再回到吕梁山中的一个县城中学任地理教师。因为贫困山区更缺乏地理老师。即便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从来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因此,我经常神情恍惚,独自游荡在城墙上、与学校相邻的公园里。
年少时莫名的青春躁动,是接近本能的意识,是欲望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迷惘,无理由的颠覆,无所谓的表情。我庆幸在这个时候突然萌生了画画、学书法的想法。
在考上高中之前,我执过羊鞭、牧马割草,再没指望上学的时候,想做一个民间艺人。当时放牲口是有时间看书、画画的,看书、画画、写字,是我的全部业余生活。那时,看完电影后在家里的煤油灯下,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画出来,临摹所能见到的书刊中的画及插图。我画过装进死人的棺材、殷实人家的炕围和四扇柜门,画过街头宣传画、刷写过比我高的标语,画过大批判墙报报头,用毛笔抄过公社和村里的批判文章。然而,命运却又给了我考高中的机会。
也就在那时,仇锦学长发起美术学社,我成了骨干成员。三年级时认识了语文报社美术编辑王伯俊老师,有过那两年刷标语、出黑板报的训练,我写美术字的水平是过关的。在没有电脑打字的时代,写美术字是报刊美术编辑的必备之功。当时语文报社仅王老师一个美术编辑,根本忙不过来,因此我有机会给王老师帮忙,画一些栏图和题图,而且还有稿费拿。
写到这里,想起西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四
1984年8月中旬,我以待分配名义来语文报社做美术编辑,在没有正式分配之前,每月可向报社借40元生活费,俟指标下来正式报到后补足。上班后,我买的第一本书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盖因毕业之际,中文系的同学在传阅此书,在当时温饱尚不能保证,买书无疑是件奢侈的事。
买到《美的历程》后,我读了无数遍。这本书以审美的视角将中国文学、艺术画龙点睛般展示出来。阅读此书,当领略到作者将凝聚了中国五千年的或狞厉、或温情、或奔放、或浪漫的文化,以这样一种娓娓道来的形式从作者笔下汩汩流出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听到那其中工匠攻玉勒石的铿锵与诗人吟咏和曲的悠扬。阅读这类著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从内容到语言的美的享受。从此,我便猝不及防地喜欢上了哲学、美学。并与中文系83级同学鲁顺民、吴焕棠他们班一起学了林清奇老师的《美学原理》课。
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不单单是一个学术现象,它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种表现。就像一条河被封堵多年,一旦解封便向各处冲泻。卸去桎梏的人们,表现出对美的强烈诉求。继《美的历程》之后,我又读了李泽厚评述康德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因此又对照李泽厚此书,硬着头皮,忍受着味同嚼蜡的痛苦看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哲学:《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学了康德哲学,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逻辑和价值判断,使我获益终生。
在语文报社的四年,年轻的我没什么负担,因报社举办的全国性活动多,经常去京、沪、苏、杭、榕、渝等地出差。虽然身居小城,眼界却没有局限。
有一段时间,我的阅读完全是自由放任的,我不以知识的积累为快乐,而是以自由放任和随心所欲地阅读为生活乐趣。我纯粹地经历一种自由而没有约束的思想生活。因为,我虽然可以选择性地在学校文科专业听课,但又不愿意融入学院化或学术化的那种学习与写作。那时语文报社给大家发了很多新思潮中有代表性的书。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观察丛书”、三十多册的“走向未来丛书”。这个时期,语文报社的学长蔡智敏和南开大学分配来的刘阶耳对我的影响最大。蔡兄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在他的引导下,我读了许多汉译经典名著,如雷·韦勒克、奥·沃伦的《文学理论》,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引论》等。在诗人刘阶耳的影响下,我开始学写诗,大量阅读当代文艺思潮的文章。是他们拉近了我与文学的距离。
多年以后,我能通过写作而找到饭碗,全仗于那几年的读书。而那个年代的读书,不仅仅是获得功利性的满足,更是思想的寻求。尽管是肤浅的,甚至是迷惑的,但通过阅读认识世界,尽可能给自己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路径。
读书杂而不精。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学术中人,而是一个问题中人。
五
我总想,我是幸运的。来语文报社工作后,新建的校图书馆在10月开馆,能在宽敞的教工阅览室学习了。紧接着山西师范学院更名为山西师范大学,学校又决定筹备建校26周年庆祝活动。陶本一校长提议学校应该有个校徽,当时校内还没有艺术系,能设计图案的也就只有语文报社的两个美术编辑。于是校庆筹建办的高国顺老师找到王伯俊老师和我,让我们在半个月之内设计数个校徽图案,供校领导班子选用。结果我设计的校徽方案被选中!一直沿用到现在。
四十年来,我不止一次想过,终有一天,校徽会被高水准的设计图案取代。但刚刚从地理专业毕业的我,成为山西师大校徽的第一个设计者,何其幸哉!
六
真正熟悉临汾,是工作以后的四年。
再说一遍,我是幸运的。一个出生在吕梁山里的农村孩子能徜徉在晋南比邻汾河的花果小城,那不是上天的眷顾?那时年轻的我,肆意地留着长发,早上起来绕着鼓楼跑一圈,下午下班后先打一小时羽毛球,或者踢足球,再去鼓楼南吃吴家熏鸡。饭后,或去图书馆学习,或去找楼门口住的大胡子诗人聊聊文学,大家说CITY不CITY?
你能想象吗,我在临汾工作四年没有骑过自行车。那时电话还没有走进家庭,向临汾的画家组稿、约稿,全靠两条腿。因此,这座朴素而散漫的小城,在我的记忆中更加深刻。
我来语文报社最初负责《中文自学考试辅导》(月刊)、《语文报》(其中一部分)、《语文教学通讯》(月刊)的美术编辑,1986年开始,成为语文报的专职美术编辑。除了完成编辑室安排的具体任务外,还要处理大量的作者来稿,工作量不小,又免不了对外约稿。没有时效的画作,可向太原及省外的画家约稿,短时间内的插图、装饰图案都在临汾完成了。因此,临汾市内的知名美术人士我都有往来。如临汾地区展览馆的油画家张德录,一中的漫画家李洪泽,师范的美术老师陶福尔,地区印刷厂的美工刘沙、常小龙,三中的美术老师郑吉平等,通过他们各自擅长的创作,丰富了我的艺术鉴赏能力,同时也提高了我的画画水平。
在临汾的这些年里,我切身感受到了晋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当年我要买本书,得步行半个多小时,赶到解放路新华书店。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出版后,师大书亭数量少而售罄。我一大早赶到解放路书店时,门口已排起了长长的购书队伍。每逢春节后,走在临汾的大街小巷,喜欢书法的我,会格外关注家家户户门口的对联,总会看到功力深厚的行书、隶书,这在我熟悉的吕梁、朔州是难以看到的。
虽然我在临汾只待了八年,却对它有着乡愁般的眷恋。每逢凄风苦雨之时,总会想到在临汾、师大有我无话不谈的师友。小城所散发出的那种自在且温柔敦厚的民风,它像化学反应里的催化剂,使一切发生了激烈的反应。它于我,是生命里的刻痕,烙印颇深。
自1988年7月离开临汾,也有无数次回过临汾和师大。校门上的题字也几经变更。校门口的那条路也不再是马尾巷,不管它叫什么,都与我们没关系了。
有时候会想,假如我当年上了别的大学,这四十年的生命历程会不会比已有经历顺利而平静?虽然很难有答案,但有一点却是必须有的:年轻时的我,自知才情不足,会向平庸妥协。但不可以没有激昂、心惊肉跳的过程。
七
四十年后,我们听到了梦破碎的声音。
但我从未忘记梦开始的地方。
多年以后,我追忆过去,才发现师大八年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四年,尽管年年如一日,岁月蹉跎,但是我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再学习经历。
一个人一旦把自己的某一段人生岁月交付给一个地方,就如同打上了一个相伴终身的烙印。每个人的烙印有不同的呈现方式,而我的烙印,最主要的呈现方式就是我后来的成长经历。不论我走到哪里,这些经历和回忆都会如影随形。我珍视它们,并借此机缘写下它们而与有荣焉。
我不知道能否参加这次毕业四十周年聚会,更不可弥补的是曾经的班聚,我一次也没参加。但我记得你们,记得当年那些事,在不知不觉中,这一切都已成了生命的刻痕,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
只是,你们也还记得我吗?
【作者简介】 孙隽明,山西兴县人。1963年出生。现居深圳。1984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系。自九十年代写作散文随笔、抗战史追寻等文章,散见于各类报刊。闲时写字、画画以自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