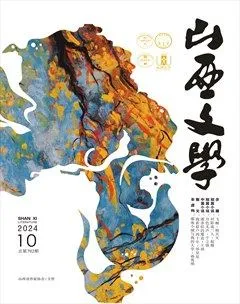两老虎
记录历史,展示人性,存放真情,再现不可复制的人生。
——题记
秋天的一个中午,村里人正在大十字老槐树下吃午饭,边吃边侃大山。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进了村子。到了大十字老槐树下,骑头一辆自行车的人先下了车,自我介绍说:“我是县武装部的副部长,叫王大兴,后面这位是县民政局的孙科长,找村支书。”村支书郑庵正好就在饭场,从蹲着的半截石磙上跳下来说:“我就是,啥事?”王大兴副部长掏出介绍信和几张材料递给郑庵。人们这才发现,两辆自行车的后座上,还驮着两个人。一看,是村里的两个老虎,路老虎和鲁老虎。路老虎哭丧着脸,垂头丧气的,一声不吭,像一只被任人宰割的羔羊;鲁老虎脸上挂着一层不自然的笑,不停地向父老乡亲们拱手,嘴里直说:“爷儿们好!正吃呢?吃吧吃吧!”
突然进村的两个老虎,弄得村里人一头雾水。
村老农会老主席郑同向更是一脸的诧异,一手拿筷子一手端着半碗面条,不停地问县里来的人:“这,该不是弄错了?弄错了吧,你们?”
王大兴:“弄错啥?”
郑同向:“这路老虎,当年是我手拉手把他交给八路军武工队长老焦的,现在咋会成了国民党兵?这鲁老虎,46年秋天被国民党兵抓走,村里人都清楚,这才几年光景,两个老虎咋就……反了?”
“反了?没反。路老虎确实是国民党兵,是被解放军俘虏的,往后村里要监督他,改造他,不能让他乱说乱动。”王大兴态度很明确,“鲁老虎是解放军,他的腿部受过伤,是三等伤残荣退军人,走路不方便,不易干重活儿,村里要多照顾他。”
饭场人端着饭碗,不再吃饭,不再吭声,心里都犯着疑惑:这两个老虎,到底谁是谁的人?
当年,路老虎参加了八路军,那是绝对没错的,村里人都知道。1938年2月初,日军进犯豫北地区。3月中旬,黄河以北全部沦陷。豫西北平原村村建立了维持会,皇协军、杂牌队、大韩义勇军遍地跑。路老虎家几代贫穷,一圈干树枝围成的院子,三间破草房,天天吃了上顿没有下顿。13岁那年,他爹被日本人抓去,在县城南门外修炮楼,一脚踩空从炮楼上掉下来摔死了。那年冬天,娘大病一场,也去世了。路老虎成了孤儿,无依无靠的。15岁那年,太行山的一支八路军武工队到这一带打日本,经常是夜里打白天撤,来有影去无踪。村农会主席郑同向拉着路老虎,亲手交给了武工队队长焦茂成。郑同向说老焦,这孩子苦,带他走吧,让他帮你跑跑腿,打小日本出点力,他也能有碗饭吃。就这样,路老虎走了。路老虎这一走,便杳无音讯,是死是活村里没人知道。时间一长,村里几乎没人再提起他。兵荒马乱年月,村子里很多出去的人都再也没有回来,房倒屋塌院里长满了荒草小树。鲁老虎当兵,是日本投降没多长时间,当的是国民党兵。那年,国民党军队来村里抓壮丁,鲁老虎是独子,没有跑。他爹鲁大头当保长,尽心尽力给国民党部队筹款纳粮送壮丁,就是把全村的青年送光了,也轮不到他鲁老虎,跑啥?没料到,国民党部队战事吃紧,前方急需要兵,毫无商量带走了鲁老虎。他爹保长鲁大头,一口气憋在肚里,生生给气死了。
眼前这两个老虎,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从此在村里,路老虎和鲁老虎过上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郑庵的儿子郑舟后来接替他爹,当了村支书,他对鲁老虎毕恭毕敬:“老虎叔,你腿不好,来村委会看大门吧,接接电话收发报纸、信件。伤残荣退军人往村委会一坐,全村贫下中农放心。”鲁老虎在村里享受着伤残荣退军人的待遇。每个月邮递员在大街上喊:“鲁老虎,拿手章取钱!”鲁老虎一瘸一拐跑来,咧嘴笑着,盖了手章,从邮递员手里接过8元钱。这是政府发给革命伤残军人的伤残费。村里成立互助组,鲁老虎积极参加,每月拿出2块钱,支持互助组。村里成立初级社,一条腿瘸的鲁老虎,把自家的一头瘸腿驴入了社,在乡里声名鹊起,被誉为三条腿驴社。村里人夸赞说:到底是伤残荣退军人,思想觉悟高,和一般老百姓就是不一样。1958年8月,全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湨梁村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辖7个生产小队。鲁老虎每月拿出2块钱交到大队,当上了村治保主任。一个壮劳力一天剜地拉车挑粪干重体力活儿,挣10个工分,才合5分钱。一个月8块钱,顶多少壮劳力啊?鲁老虎不干重活儿,会扎风筝玩风筝。秋天天高气爽,鲁老虎躺在在村北的枯井坑里放龙头风筝。那龙头上安着风哨,风筝飞到了云彩眼里,天上响起欢快的风哨声。鲁老虎四个儿子长大了,沾他们爹是革命伤残军人的光,一个一个都跳出了农门,到县机械厂、县拖拉机站、焦作火车站、新乡造纸厂,都当了工人,吃上了商品粮。有人开玩笑说:鲁老虎家的日子,像他放那风筝。
路老虎后来也娶妻生子,过的则是另一种生活。郑舟给路老虎分派任务:“去,和张磨油一起扫大街吧。村北那条街,张磨油一个人扫,天天磨洋工,从早上扫到中午,扫得尘土飞扬,你两一起干,你负责担水泼路,张磨油还负责扫地。”村东一个大水坑,一年四季有水。每天灰灰明鸡叫头遍,路老虎就挑着水桶,到坑里挑水,吭哧吭哧挑到村北街,一瓢一瓢泼到土路上。离他十步开外是张磨油,杵着大扫把盯着他看,一脸不怀好意的笑。那笑,像是在鉴赏着什么,也像是思索着什么。路老虎一瓢水朝他抛洒过去,嘴里骂着很难听的话。张磨油这才收起了笑,哗啦一扫帚哗啦一扫帚地扫地。
“反右”开始不长时间,县上送来一个右派分子,也加入了扫村北街的行列。路老虎见到那人心中一惊,这不是那个武装部王副部长吗?当年就是他把自己送到村里来的。一问,果然是王大兴。这世间事咋弄颠倒了?不过,这世间弄颠倒了的事还少吗?让人细想起来,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后来,和王大兴接触多了,路老虎才知道,王大兴是天津人,1943年参加了八路军,在晋冀鲁豫一带打日本。日本投降后,随军南下解放了这个县,也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县城一解放,就转业到县武装部当了副部长。“反右”运动开始,他二十六七岁,正属年轻气盛斗志昂扬不吝死活的年纪。路老虎问:
“王部长,恁这走的是哪条路,咋也走到这儿来了?”
“嗨,提意见,过了。”
“啥意见?”
“说现在的驴,脊背瘦得能当刀用,手一摸指头就拉掉半截。那驴头,瘦得一根玉米秆就能把它挑起来。”
“提过了!驴再瘦,也没像你说得恁瘦。”
“还有一句,更过。”
“啥?”
“驴哭了,猪笑了,饲养员偷料了。”
“就这,哪里过?俺村就有。”
“饲养员是谁?村大队支书他爹。”
“哦……这听起来,咋像是个笑话?”
“是的。我当时也是说笑话,后来人们把笑话当真了,被打成了这个。”王大兴抬起右手,甩了甩,一脸无可奈何地苦笑,“还有,我弟弟在台湾,和你一样,是国民党兵。”
这个话题太敏感。路老虎咂了咂嘴,吸溜一下口水咽进肚里,没敢再问下去。
路老虎大儿子路冰,小学一毕业,就回家种地了。18岁那年,焦作煤矿救护队来招人,村里没人愿去,路冰找到郑舟说:“舟哥,我想去。”名字报到公社,政审时被拿了下来。郑舟转告他:“敢死队来挑人的说,恁爹是国民党兵,不是一个阶级,你要是到了煤矿救护队,能不把受伤的工人阶级往死里整?”路冰一听,哭了。小儿子路向小学毕业,也回家种地了。最小的是个女儿,叫路娴,聪明伶俐,学习好,一直是年级前几名,初中毕业上高中,正赶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驻校的贫宣队长不同意,说:“社会主义的高中,很多贫下中农孩子都没有机会,她一个国民党兵的女儿,上什么高中?”
儿女大事,老伴想起来就心烦,嘴碎,一天到晚埋怨他:“你看看,咱这几个孩子,个个精眉楚眼,因为你,全都窝在了村里,天天在地里打牛腿,将来咋娶媳妇?闺女咋找婆家?你啊,贻害了我们全家。”老伴心里窝闷,没有几年,就含恨去世了。
路老虎意识到:自己的历史问题,不仅自己受罪,也牵连到了孩子。他接连不断地给政府有关部门写信,说:“我冤枉,天大的冤枉。”元宵节,县剧团下乡演豫剧《窦娥冤》,窦娥在台上哭,路老虎在台下抹眼泪。慢慢年纪大了,路老虎腿不好,腰肌劳损,血压高,房颤,心跳偷停,整天阴沉着脸,唉声叹气,对谁都很少说话。孩子们天天在生产队地里干活儿,忙挣工分,很少顾得了他。路老虎像一只被人遗弃的老狗,孤零零地住在后院的一间旧草房里,整天写申诉材料。他经常拿着申诉材料,跑公社,跑县里,跑地区,跑省里,还跑过一次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情况,要求还自己一个清白。心不悦,嘴要说。村里,路老虎走火入魔一般,逢人就述说自己的冤枉,把自己的冤枉当成故事讲:
“我15岁参加八路军武工队,跟着老焦,在太行山一带打小日本。一次在沁阳城,和小日本相遇,为掩护武工队长老焦,我的胸部中了一枪。攻打西封口一仗,我的两个手指头被打掉。我为此立过战功,受过嘉奖。”
村里人不解:“那你咋混到了这一步?”
“1941年4月12日至20日,日本侵略军第35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及伪军万余人,出动汽车、坦克百余辆,对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濮阳西北、内黄等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在这次‘大扫荡’中,武工队被打散,武工队长焦茂成牺牲,我被小日本俘虏。几天后,被小日本捆着双手,蒙上眼睛装上轮船,经过几天几夜海上颠簸,到了一个岛上的煤窑做劳工。后来才知道,是到了日本。1945年的一天,看管煤窑的日本人突然不见了,有个胆子大的叫刘葫芦,探头探脑地把周围瞭哨一阵,说咱们跑吧!大家齐往外跑。跑到大街上,街上很乱。很多穿着不同军装的外国军人,一队一队地巡逻。大卡车、吉普车、摩托车穿来跑去。有的人在抢商店、抢东西,有的外国军人在拉扯、搂抱日本女人。而那些穿着不同国籍军装巡逻执勤的士兵,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一样。日本人过去的那种骄狂、蛮横的气势全不见了,个个像过街老鼠,灰溜溜地乱跑。一问,原来是日本投降了。”
村里人依然不解:“那你咋又成了国民党兵?”
“几年后,我们又被装上船,运回国来。到了大连港一下船,见岸上站的全是国民党军人,个个全副武装。一个校官对我们讲话:同胞们,欢迎你们回国,欢迎你们参加国军。还是那个刘葫芦,说长官我想回家。校官瞪了他一眼,一挥手叫过来两个兵,说送他回老家。那两个兵架着刘葫芦到了海边,咣地一枪,刘葫芦一头栽倒进了海里。一船人无人敢再吭声。就这样,我们被换上了国民党军装,押上了军舰,沿海南下。我没想到,在国民党的军舰上,遇见了鲁老虎,他是我们连长。”
“什么?”村里人更加不解,“鲁老虎是你们连长?”
“对啊!鲁老虎在舰艇上亲口告诉我,他自从参加国民党军队那天起,就一直和解放军打仗。参加过辽沈战役、徐蚌会战,他的双手沾满了解放军战友的鲜血,最后官至连长。他的伤,就是解放军打的,一投降,咋就又成了解放军的英雄?人民政府为啥每个月还发给他伤残军人补贴?我15岁参加八路军,冒着枪林弹雨打击日本鬼子,身上几个地方有小日本打的伤。八路军太行支队的嘉奖令和医院的出院证明都有。我参加国民党军队,那完全是出于被迫,而且我从来没有向解放军开过一枪。想不通啊,实在是想不通!”
这些话传到了鲁老虎那,鲁老虎也不争辩,只是淡淡一笑:“我当年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的,我爹一口气没上来,人就走了,这全村老少爷们谁不知道?我后来虽说是当了国民党连长,古往今来当兵打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都是身不由己,如言不信,你到部队试试?没有办法。我是被抓走的,我爹是被气死的,我恨国民党,我不愿跟着他们逃往台湾,所以在战场上起了义,参加了解放军,打军舰上往台湾逃跑的国民党部队。路老虎自己跟着营长往台湾跑,我有啥办法!”
这些事,谁能证明?
路老虎整日里闷头写信,不停地向有关部门寄送材料,到各处喊冤叫屈。“九大”要召开了,稳定压倒一切。村支书郑舟打公社回来,直奔路老虎家,进门见到路老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几乎是哭着说:“老虎叔啊老虎叔,恁可千万不敢再乱跑了,再乱跑,恁侄儿头上这顶乌纱帽就要被公社给摘了。”原来,公社牛书记叫去郑舟,狠狠训斥了一顿:“恁村那个路老虎,天天写信上访,胡乱告状,市里、县里都挂了号,是个不稳定人员,要好好做他的工作,你要是管不住路老虎,村支书换人。”
深秋时节,一场霜冻过后,西北风刮了两天,院子里的老榆树老槐树叶子落了一地。路老虎死了。
村里有人说:路老虎临死前告诉儿女们,死后入殓,身上一定要穿着那套国民党军装。几十年来,它给自己带来了一辈子的噩梦,给全家带来了灾难和不幸。现在死了,要把它带进棺材里,也许一切都解脱了。但在胸前,要放着八路军太行支队发的立功、嘉奖令和出院证明,因为那是老子拿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那纯粹是传言。路老虎家人,从来没出来说过一句话。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又是一个春天,迎春花盛开,金灿灿的。早已平反回到县城的王大兴,突然来到村里,还带来一个人,七十多岁。见到村支书郑舟,王大兴说:
“这是个国民党老兵,我亲弟弟,叫王长兴,打台北来。两岸施行三通,他来到大陆寻找路老虎。”
郑舟听说来人是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有些意外:“你说的,是我们村的路老虎,还是鲁老虎?我们村两个老虎,口音不清的常弄错。”
“路老虎,大路的路。抗日战争时期,我和他是战友,都在八路军豫西北武工队,我给队长焦茂成当警卫员,他是通信员,我们在这一带打日本。1941年春天,日本大‘扫荡’,队长焦茂成牺牲,我和路老虎被日军俘虏,送到了日本煤窑当劳工。日本投降后我们被送回到大连,国民党强迫我们穿上国民党军装,上了军舰向厦门撤退。鲁老虎我也认识。”王长兴有些激动起来,“鲁老虎是我们连长,他俩是一个村的,没错。我们在军舰上航行,我和路老虎商量想跳海逃跑,被鲁老虎听见了,他命人把我捆起来,关在军舰底舱,说是到了台湾要送我上军事法庭。军舰离开了厦门往金门岛跑,岸上用大炮轰。已经快到金门岛了,看见国民党旗在岛上飘扬,不料一发炮弹打来,落在甲板上,军舰上开始乱了起来。路老虎乘人不备,到底舱砸开锁救下我,我俩跳进大海逃生。他掉转身往大陆游。我一直游到了金门岛。我俩大海里分手,是生死弟兄。”
“哦!”郑舟听了,长叹一声说:“路老虎不在了。”
“哪去了?”王长兴睁大了眼睛。
“村北地。”郑舟说。
“还在村北扫地?”王大兴年纪大了,耳有点背。
“村北坟地,公坟,早变成土了。”郑舟说。
王大兴:“他孩子们呢?”
郑舟:“一改革开放,就都离开湨梁村,飞外地去了。”
王大兴很是遗憾:“有新政策了,他走了。”
听说路老虎早已死了,王长兴老泪纵横,哭了起来。
看着哭泣的王长兴,郑舟一时不知所措。他想了想,派人去找来了鲁老虎。鲁老虎还活着,虽说是年纪大了,多年来衣食无忧,精神状态也还可以。鲁老虎一瘸一拐地来到大队部,听了郑舟介绍,看着王长兴,愣怔半天没有吭声。
王长兴已不再哭泣,他擦了擦眼睛,看着鲁老虎说:“鲁连长,我是王长兴,还记得吗?”
鲁老虎嗫嚅半天,说:“时间太长,记不得了。”
王长兴说:“你左耳朵下面长个大猴子,上面有几根黑毛。现在猴子还在,只是毛变白了。肯定是你,不会错。”
鲁老虎眼睛里含着泪花,拉着王长兴的手,说:“中午到我家吃饭,不管咋说,咱两年轻时一口锅里吃过饭,一个连的弟兄。多年不见,老情分还在。”
王大兴也去了。饭间,鲁老虎喝了几口酒,脸色涨红,加上见到几十年前的老战友,话也多:“这世事难料啊,人这一辈太难啦!哪一步迈出,前面是坑是路,是黑是白,谁都弄不清楚。咱们到厦门下了军舰,构筑工事,准备抵抗解放军。营长就命令我,带一个迫击炮班和机枪班留在岸上,掩护全营上舰后再撤。我带领两个班开始枪击炮轰,对解放军进行阻击。一阵激烈的枪炮声中,我腿上一热,血洇湿了裤子,我挂彩了。回头一看,见你们上了军舰,起锚开航了。妈的,我知道上当了,命令弟兄们调转枪炮口,向军舰射击。长兴,你们坐的军舰,就是被我带领的兄弟用炮火击沉的。解放军冲上来了,说欢迎国军弟兄战场起义,弃暗投明。路老虎跳海后被俘,战俘营里我看见了他。”
总之,到了这时,路老虎的一生算是画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
王大兴和王长兴走后C0uSw2dTlKpglArkDJlHNw==,郑舟把这一消息打电话告诉路冰。路冰在广州一家外企当副总,听了电话半天没有说话,电话里传来抽泣声。郑舟的眼睛里也湿漉漉的。路冰放下电话,立刻给老二路向通话说:“清明节前回村里一趟,给爹妈立碑,要把这事刻在碑上。”路冰又打电话告诉妹妹路娴。路娴在成都,是写小说的,听后哭了。路娴说:“爹憋屈了这么多年,立碑那天,要在村里唱三天大戏,让全村人都和爹一样,高兴高兴。前些年,我以爹为原型,写了一中篇小说《谁的人》,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把小说改成电影,正在拍。”
清明节前夕,兄妹仨都回来了。自从爹死后,兄妹三人再也没有回来过。然而,当他们回到村里,找不到爹妈了。曾经千把口人的湨梁村,变成了湨梁镇,居住了好几万人。兄妹三人懵了。兄妹三人忍了多年,现在哭爹妈,竟然找不到坟头。泪水只能往肚子里流。他们在湨梁镇大十字路口,当年曾是湨梁村的饭场,摆上了纸人纸马、金山银山、摇钱树等祭品,点燃花圈锡箔。路冰把给路老虎平反的材料也扔进了火里。一阵微风吹来,灰烬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飘飘摇摇地满世界飞去。兄妹三人对着埋葬爹妈的那群高楼跪下,低声哭泣:
“爹啊,弄清楚了,您是抗日军人……”
【作者简介】 冯俊科,河南温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获得过第三届老舍散文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北京文学奖。出版有长篇小说《尘灰满街》《疑兵》,中篇小说集《老戏台》,中篇小说精选《何处安放》《冯俊科中短篇小说集》《乌蒙响杜鹃》《江河日月》《千山碧透》等文学作品集和《西方幸福论》等专著。多篇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作家》《芙蓉》《长江文艺》等刊,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转载和《作家文摘报》连载。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阿拉伯语等在国外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