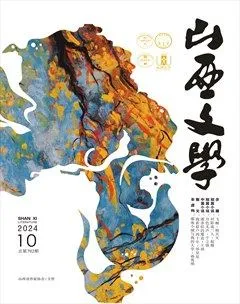羞愧的DNA
今天是给娘烧“五七”的日子。我和的士司机在小镇餐馆里吃了顿饭,然后找旅店开了两间房,天终于被磨蹭黑了,才让司机启动小车往乡下开。
照说,回老家给娘烧“五七”,是堂堂正正的事,但只有我心里清楚,给娘烧袱包后,我还要找借口带品瑞叔去旅店住一晚。所以选择晚上,是不想让村里人看见我回来了。
的士沿着乡村公路行驶,半个多小时便到了村口。我让司机把车停在一边等候,便独自提了礼物和祭品,趁着夜色的掩护向村子里走去。
如我期望的,一路没有遇见人。其实,村子里不是老就是小,天一黑,家家的门都关严实了,一般是遇不到人的。不一会,我来到我家的老屋前,门是锁着的,进不去,只得又往前走,走出几十米,一间熟悉的低矮的砖瓦房出现在我眼前。瓦房里有光亮,细听有说话声,时断时续。我贴近大门足足听了几分钟,确信屋里只有一个人,才举起手,敲了敲门。
门随即开了,门后站着品瑞叔。我不等品瑞叔开口说话,将提着的东西交给他,然后反身关上门。
“这孩子,怎么又带礼物来,上次带来的还剩那么多呢。”很难说品瑞叔说话的语气是嗔怪还是高兴。
我正想说什么,抬头瞥见房间里的桌子上燃着一枝蜡烛和三炷香,蜡烛前,靠墙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正是我娘的遗像。我走上前,对着相框作了三个揖,侧过身,问品瑞叔:“叔,我娘这相框?”
他连忙解释说:“叔不糊涂,只有晚上,我才把它供在桌上,给你娘敬香,然后陪她说说话……”
难怪刚才屋里有说话声,我不禁问:“叔刚才是和我娘说话吧?”
品瑞叔点了点头。我不怀疑品瑞叔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但还是装作不经意地问:“叔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品瑞叔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对你娘说,今天是你‘五七’的祭日,林茂肯定记得,他一准是单位上忙抽不开身,到晚上会回来看你的——这不,正说着,你就来了。”
我移开目光,说:“叔,我也不是很忙,车开到村口时出了点故障,给耽搁了,司机还在修呢……”
品瑞叔“哦”了一声,随即去一旁取出大小两摞袱包,对我说:“叔都给你准备好了,这大的一摞,是烧给你娘的,小的是烧给你爹的。今天是你娘的‘五七’,顺带也给你爹添点财。”
爹对我只是一个伦理上的概念。爹是在我三岁那年去世的,有关做爹的义务是品瑞叔暗地里完成的,比如他无数次以邻居的身份去我的学校给我送米送钱,连保安都认识他了,可是他从不让保安去叫我。品瑞叔为我和我娘付出了多少,这在村子里恐怕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我是在村里人挤眉弄眼的议论声中长大的。从议论的碎片里,我知晓了爹是在集体的一次炸山中受伤的,好像伤到了要害部位,是同时在现场的品瑞叔把我爹背到医院去的,而爹受伤两年后娘生下了我……
“林茂他娘,我们这就去给你烧袱包……”品瑞叔说着,去开门,我赶紧跟了出去。
两摞袱包在我家老屋门前烧了起来。跪在燃烧的袱包前,看着渐渐化为灰烬的袱包,我意识到娘已离我越来越远了。
娘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村子,就是在患病期间也不肯随我进城,直到去世前一天,她才让品瑞叔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她是离不开品瑞叔,还是不愿拖累我,但我更相信是前者。我爹未受伤时,品瑞叔因家庭成分不好而娶不上亲,爹受伤后,他就以潜在的方式参与到我的家庭中来了,甚至让我的身世也成了一个谜团。娘弥留时,拽着我的手不放,嘴唇微微颤动着,却欲说又止,我猜想娘要向我解开谜团了,便俯下身去,催她说,她睁大眼睛看了一遍房间,对我说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茂儿,我走了,你要好好待品瑞叔……”那一刻,品瑞叔正站在我家老屋门前,他是在我哭喊着叫娘时才跌跌撞撞跑进房间的,而我的娘已经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烧完袱包,再次回到品瑞叔家,我正思忖着如何开口,品瑞叔却说:“林茂,你走吧,别让司机等久了。”
看来品瑞叔根本不相信的士出了故障。我想了想,对他说:“叔,您今晚跟我去镇上住一夜吧,房间我都开了的,我想跟您喝喝茶说说话……”
“不用说的,林茂,叔永远只是你的叔,我还能下地,也不用你惦记,有工夫,好好做你的官奔你的前途……”品瑞叔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
“不……”我打断品瑞叔的话,“我想接您进城去。”
“傻孩子,你凭什么要接我去?”品瑞叔呵呵一笑,指着娘的相框对我说,“你要是觉得这样不好,就把你娘的像带走,叔哪里也不去,有一天真不得动了,我就去找村主任,让他把我送到政府的养老院去。”
我忽然为我所谓精心的设计感到羞愧。为了弄清楚我的身世之谜,我想不露痕迹地得到品瑞叔刷牙后的一把牙刷,再将这把牙刷送往省城医院一个老同学那里去做DNA鉴定。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司机的电话:“今晚你一个人去旅店住,明天一早再开车来接我们。”
【作者简介】 王生文,湖北省作协会员。在《芳草》《短篇小说》《百花园》《辽河》《岁月》《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羊城晚报》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四百多篇。出版有长篇小说 《早春》。曾获《奔流》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