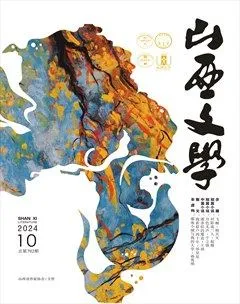月色无声
我相信,第一个发现宋月光退群的一定是田慧。我们的班级微信群早已半死不活,平时难得有人冒个泡,鸡汤文、图片、小视频也早就没人转发了,都知道发也是白发,还会让人生厌。在这种情形下,谁还关心退群不退群这样的屁事呢?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涉及感情的事儿,我暗恋过张倩,这些年就时不时查看一下群成员,看张倩还在不在,看她发了什么朋友圈,即使她的圈里毫无动静,我也能从中得到一种安慰。感情这东西就是奇妙,所以,我相信田慧这些年一定会关注着宋月光。
那天,田慧给我发微信说,宋月光退群了,你发现没?
我回复说,没注意,他为什么退群?
田慧说,我不知道啊,所以才问你的。
毕业后和我互加微信的同学不多,田慧是其一,而且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这不仅因为我们是老乡关系,更主要的是当年我在她和宋月光中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宋月光第一次向田慧表白,就是通过我转达的,其后我充当了他们交往的纽带。他们最终也没能修成正果,田慧有时在微信中和我聊起宋月光,似乎还耿耿于怀。
我问,难道你们这么多年就没联系过?
田慧说,偶尔,就是问个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说,哦。
田慧又说,你知道的,宋月光是个怪胎。
我哑然失笑。田慧说宋月光怪,我完全同意。宋月光的确有点让人难以捉摸,我们同宿舍人都把他归于另类,敬而远之。一位后来成为作家的同学这样写过他:“刚进大学校门时,人们都兴奋地上蹿下跳,只有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墙角里,穿一件看起来大一码的深色西装,人极瘦长,手如鸡爪,看我们的眼神就像看食肉生番。”描述得形象生动,很到位。
宋月光睡在我的上铺,每天上上下下的,却难得和我说句话,他和宿舍里的每个人都很少说话。他虽不排斥参加宿舍的某些集体活动,但感觉总是游离于我们之外。我们打扑克,他有时也当吃瓜群众,我们群情激昂大呼小叫,他却始终保持冷静,面无表情。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打扑克,他一个人高高地盘腿坐在上铺,用一副扑克牌算命。他嘴里叼根烟,熟练地把扑克一张张排开再收起,收起再排开,翻来覆去,不厌其烦。中间不忘把烟灰及时弹到一个空罐头瓶里。那个时候学校里流行一种扑克牌算命的游戏,宋月光乐此不疲,我们都叫他宋半仙。我问他算得怎么样,他不屑回答。再问,他就说娱乐而已。
我发现宋月光很多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夜里睡觉不算,白天也好像被粘到床单上了。除了拿扑克牌算命,他还在床上看书,听音乐,甚至吃饭。他曾不止一次让我帮他从食堂打饭。有时我不想帮他,表现出不耐烦,他就郑重地说整个学校他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如果连我都不帮他,那他就真没一个朋友了。这话像是在激我,又像在恭维我,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便不好意思再拒绝他。在校时我算是和他打交道最多的同学,毕业后却几乎没有联系,我到底算不算他的朋友,直至今天我也没弄清楚。
我认为宋月光不仅是个怪胎,还是个怪才。有一次见他在校门口和几个老头下象棋,老头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但最后还是他赢了。让我惊奇的是,平时就没见他下过棋,真不知道他的棋艺是怎么得来的。我们都认为宋月光不是个勤奋好学的人,但他每次考试都能顺利过关,有几门课的成绩甚至在全班全年级都名列前茅,这尤其让我们心理不平衡。按照惯例,我们都在考前搞突击,经常是熄灯后再点蜡继续学,辛辛苦苦还难免挂科补考。而宋月光呢,每晚十点前必按时入睡,不管我们如何灯火辉煌,他只顾打自己的呼噜。那时我就想,难道这小子梦里也能学习?难道他脑子里装了考试程序?直到后来我帮他成全了和田慧的事,他才肯向我泄露了一点“天机”。他说,只要平时留意老师讲课时特别强调的内容就行了。他又说,还可以干点别的。什么是“别的”?他没有直说,而是亲身给我做示范,在考“马概”前带着我去了马老师家里。马老师爱下象棋,宋月光见面不说别的,就说马老师棋艺高超,今天特来领教。于是两人摆开棋局,一下大半天。我发现,宋月光的棋艺好像突然下降了,总共下了五盘,只勉强赢了一盘。这时,宋月光从兜里掏出一盒烟说,马老师,我甘拜下风,用这盒烟表达我的敬佩之情。马老师一愣,然后哈哈一笑,也不客气,当即拆盒抽起来,也给我和宋月光每人发了一根。宋月光又说,我棋艺比不上马老师,马概水平当然更比不上,我们今天也顺便向马老师领教。马老师又是哈哈一笑说,你不要说了,我明白了,这样吧,我给你们划一下重点。那次我沾宋月光的光,经马老师这么一划,免去了我几夜熬油之苦,“马概”非但没挂,还前所未有地考了个高分。这以后,我对宋月光佩服有加,尤其佩服的是,宋月光针对不同的老师,采用不同的办法。对喜欢抽烟的老师,他带烟上门领教“烟艺”;对喜欢喝茶的老师,他带茶上门领教“茶艺”;对喜欢喝酒的老师,他就约到校外某个小酒馆领教“酒艺”。
宋月光表面冷淡沉闷,给人的感觉是薄情寡义,实际上他属于闷骚型。有一天,他说他喜欢上了田慧,让我帮他传话。我说传话不好,不郑重,应该写情书。那时候虽已有手机、QQ等现代化交流工具,但手写的情书仍具有特殊的杀伤力。于是,宋月光就写了一封厚厚的情书,我在老乡聚会时转交给了田慧。没多久,我们看见宋月光和田慧真就搞到一起了,我们都有点嫉妒,真不知道田慧看上了宋月光什么。如我们所预测,两人最终还是像大多数校园情侣那样选择了分手,但我毫不怀疑宋月光对田慧的真情,我知道毕业前夕宋月光提着礼物去见了田慧的父母,这充分说明他为爱情是付出过努力的。
后来,我只是在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时见过宋月光,他胖了一些,但总体上还是原来那副形象和气质,感觉似乎更加沉闷了。酒酣耳热之际,我们其他人三五成群聊得热火朝天,只有宋月光独坐角落,冷眼旁观我们这些浮躁浅薄的世俗之人。直到曲终人散,我们仍对宋月光毕业后的状况一无所知。真不知道他来参加同学聚会有何意义,难道就是为了来看我们喝酒聊天的吗?那次聚会田慧没有参加,后来我听田慧说,宋月光当时还没有结婚,在县里的一所中学任教,在我们同学中应该算是混得不好不坏的那一类。
时间经不住一晃,眼看快毕业二十年了,我们有意再搞一次聚会,没想到这个时候,宋月光失踪了。对,失踪!田慧先是说宋月光退群了,后来就用了“失踪”这个词。她说,宋月光的退群不是一般的退群,很可能是一起“失踪案”。据她推断,宋月光退群至少有半年时间了,半年来宋月光的朋友圈就像死了一样。田慧说,宋月光发朋友圈很少,但以前每个月总会发上那么一条两条的,但这半年一条也没发。
我感觉像是出事了,田慧又说,我在微信上和他打招呼,他都没回复,打他手机,提示是空号。
能出什么事?我不以为然,我没觉得这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虽然几年前就听说同年级已有人心梗离世,但毕竟是个例,宋月光的血管总不会也那么脆弱吧。
田慧说,说不定是抑郁呢?
哦,我有点犹疑了,这些年网传抑郁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发生在宋月光这种性格的人身上还真不是不可能。
田慧让我留意打听宋月光的情况,说我是距离宋月光最近的同学,找个时间去宋月光所在的县城,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田慧还强调说,花销都算她的。
田慧是个重感情的人,说实话,我有点被她打动了。事实上,我作为班长,理应关心同学,爱护同学,但我觉得马上跑去找宋月光,还是有点突兀。我决定先托宋月光那边的熟人打听打听。打了几个电话,没有得到确切消息。有的说几年前在一个表彰会上见过宋月光,宋月光上台领过奖。有的说宋月光已经不当老师了,但不知道换了什么工作。还有人说宋月光早就辞职创业了,曾在手机里刷到他直播带货。不管这些信息是否可靠,反正最后也没联系上宋月光。
田慧转天干脆给我打来电话,说还是想请我亲自跑一趟。我仍然犹豫着,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我提议发动全班同学,田慧担心弄得满城风雨。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以组织二十周年聚会的名义在微信群里发出一条通知,说为了聚会顺利,要弄个同学通讯录,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联系那些一直联系不上的同学,确保每一位同学都能回归温暖的班级大家庭。通知发出后还真找到了几个毕业后就杳无音讯的同学,但关于宋月光的消息仍毫无进展。到最后,全班同学就只剩宋月光一人处于失联状态。
这个时候,我也开始担心了。我在群里提醒大家要高度重视,想方设法打听宋月光的消息。大多数人似乎都不以为然,有的说“此事古难全”,聚会缺个宋月光也没什么大不了。也有人认为宋月光可能是不想参加聚会,有意自我屏蔽了。我一时没控制住,说出了宋月光“失踪”的可能性,大家一下子都沉默了。到了晚上,群里突然热闹起来,围绕宋月光的“失踪”展开了热烈讨论。各种猜测,各种假设,各种推理,各种解释,各种反驳,各种回忆,各种感叹,加上各种表情,各种图片,各种视频。他接你的话,你驳我的观点,聊着聊着,话题跑远了,再由某个人拉回来,如此反复数次。不知道为什么,那晚大家的热情那么高涨。参与的同学越来越多,一些入群以来从没说过半句话的同学也加入讨论,由此掀起了群史上第一个群聊热潮,好像提前举办了一次同学大聚会。那是一个很热闹很奇妙的晚上,后来每每回想起来,我都不由自主地心生感慨。是啊,所谓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到底还是同学最亲啊!那晚同学们的担忧、关心、怅惘、痛惜之情溢满屏幕,仿佛宋月光真的失踪了,仿佛我们从此要痛失一位亲爱的同学,成为永久的遗憾。
群里只热闹了一晚上,之后便复归冷清。看来,通过同学找到宋月光已不太可能,只有我亲自去跑一趟了,否则就可能永远联系不上宋月光同学。田慧好几次也在微信里有意无意地提醒我,鼓动我,但我没接她的话。说我懒惰也好,说我无情也罢,我确实有点不情愿为了这个说不准的事浪费时间和金钱,我宁愿相信宋月光安然无恙,大家相安无事。对,无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最欣赏的两个字就是,无事。无事小神仙,无事真好啊!我甚至有点怪田慧多事了,不就是一个前男友吗,都时过境迁了,都各自成家了,还念念不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我不就是当过班长吗,不就是和宋月光同过宿舍吗,至于非要把我也扯进来吗?
我提不起去找宋月光的兴致,就一直拖着。直到有一天,单位派我出差,目的地竟然就是宋月光所在的县城,我想这大概就是天意,必须见宋月光一面了。我给田慧发微信说,我要去找宋月光。田慧很高兴,发了一长串鼓掌的表情,又发了一长串玫瑰花,并再次说一切开销都算她的。我说,笑话,我怎么能收老同学的钱。
我从没到过这个叫安宁的小县城,据说曾是个国家级贫困县,现在看起来却呈现出一种生机,目光所及,正有几片高楼拔地而起,街道也在努力地拓宽延伸,街边店铺林林总总,顾客进进出出,确是一派安宁的气象。不过毕竟是小县城,烟火气犹存,繁华度有限。我知道,宋月光当年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考上大学,又在县城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这在他的乡亲们眼里已经是高不可攀了。不知道这么多年,偏居于此的宋月光有何感想,他是不是也心有不甘呢,像他那样聪明多才的人,或许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吧。
没费多大劲儿我就找到了田慧说的那所学校,田慧说宋月光是学校政教处的主任。果然,我在传达室一提宋月光,那个嘴有点歪的看门老头就说,哦,你找宋主任啊,来晚了。我一惊,什么?老头嘴一咧说,他早就不在这里了,调到县委宣传部了。我说,吓我一跳,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呢。老头的嘴更歪了,说宋主任调宣传部去了,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同学。老头说,你同学厉害啊。我说,什么厉害?老头说,什么都厉害,他经常来和我下棋,不是我吹,不要说在这个学校,就在这个县我都算得上是棋王,宋主任呢,能和我不相上下,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老头有点得意,又说,你同学教书也厉害,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孩子弄到他的班里去。还有,他特别会组织活动,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全靠他,很多活动在县里市里得过奖。
我还真不了解宋月光原来是个全才,是个积极分子。上大学时,宿舍或者班里搞活动,宋月光偶尔也表演个小节目,看不出他有多么出色,难道他的才能都是参加工作后开发出来的?我原以为像宋月光这样的人,不做逍遥派,也是个躺平的角色,现在看来我好像错了。
老头说,能调到宣传部的,就不是一般人,你是他同学,你说实话,他是不是有硬关系?
我说,我同学还靠关系吗,你不是刚才还说他很厉害吗,这么厉害的人,不靠关系照样会提拔。
你说得也对,老头说,你大概不知道,宋主任提拔前被人举报了,说他欺负了一个女学生。
什么?这回我真的是大吃一惊,不会吧,我同学应该不是那样的人。
老头说,还是你了解同学,确实不是那回事儿,上级来调查,派出所的人也来了,最后才弄清楚是一个老师和宋主任过不去,看他要提拔,就利用女学生陷害他。不过,最后没把宋主任搞下去,反而替宋主任扬了名,原来调查发现,宋主任多年来一直偷偷资助着一个贫困生呢。这样的好人,不提拔还真说不过去。
听老头这么一说,我好像觉得自己脸上瞬间也有了光。我问,我同学结婚了吗?在哪住?
老头说,早就结了,这么有本事的人能不结婚?在哪住不清楚,没问过他。
我走出传达室,午后的阳光炙烤着校园,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青草这里一丛那里一丛,微微摇曳着,像在等待学生们开学归来。开学后学生们做的第一件事,应该就是清除这些疯长的青草。
县委在城东,我打了个车赶过去。其实,学校离县委不远,我只是为节省时间,想尽快找到宋月光,见上一面,没特殊情况我就马上赶火车回家。
县委大楼位于一个人工湖的旁边,看上去新建不久,符合我心目中对这类楼房的印象,高大巍峨,庄重威严。如果现在的宋月光真像看门老头说的那么优秀,而不是我心目中大学时的宋月光的话,他是完全有资格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的,甚至可以说,只有宋月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这里的气场。我已经想象到宋月光在这座大楼里踌躇满志、如鱼得水地为事业奋斗的情景。
我在大楼里找到了县委宣传部,正赶上他们开会,办公室都关着门,楼道里有几个像是等着办事的人。我百无聊赖,在楼道里走来走去。楼道的墙壁经过精心设计,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墙,图文并茂。中间一栏是宣传部现任领导,只有一个副部长的照片和名字,另外两个空白,显得有点突兀。
会议结束后,我跟一个小年轻进了他的办公室,听说我找宋月光,小年轻警惕地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才说,你不知道吗?宋月光被抓了。
这是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脑海里凌乱得像塞满了烂渔网。小年轻问我是谁,找宋月光干什么,我竟一时愣在那里忘记了回答。在确认我不是记者一类的人后,小年轻告诉我,宋月光被牵扯进了一起安全事故引发的案件中,犯了行贿罪,很可能会被判刑。我想知道具体情况,小年轻说,前段时间我们这里出了个水污染事故,宋月光和这事有关系,你自己上网查查看。小年轻有点不耐烦,说他还有工作要做,委婉地把我请了出来。我不死心,又尝试着到其他办公室去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听说、不知道,个别知道的也不比小年轻知道得多。
从小年轻的嘴里,我知道宋月光之前担任的就是宣传部副部长。我准备下楼,走过文化墙的时候,又盯着那个领导栏看了一会儿,觉得那块空白不仅突兀,还有点刺眼。
我在网上搜到了那个水污染事故,说是县里好不容易通过招商引资建起来的一家化工厂,把污水排放到河里,污染了水资源。在处理事故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部门企图隐瞒谎报事实,被人捅到网上,造成了恶劣影响,最终一大批人被严肃追责,其中有几名县乡干部。我看得一头雾水,不明白这事和宋月光有什么关联,不明白宋月光怎么会在其中犯行贿罪。
我临时决定今天不回家了,明天到宋月光担任第一书记的那个村里去看看。我在县委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晚饭后出来散步,不知不觉又走回到县委大楼。我在时明时暗的路灯下绕着大楼转了一圈,好像这样一转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似的。大楼、广场、草坪,都还是白天看到的那些,但现在的它们都变了样子,白天因为宋月光的存在,它们让我不由地产生一种亲切和豪迈之感,现在它们随着宋月光“离去”,在我心头只剩一种陌生和怅然。
今晚月色朦胧缥缈,让我第一次联想到宋月光的名字。我知道,月光,这来自遥远月球的神秘光线,实际上源于太阳,是月球像镜子一样反射到地球的阳光。但它没有阳光的热烈,更多的是静幽清冷。月光,古人称之为“皎”,在历代诗文和传说中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意象,被赋予了种种神奇而美妙的象征意义,令人浮想联翩。此刻,月光无声无息洒下来,我的思绪也随之飞向了遥远的天空。
第二天一大早,我乘小公交直奔西茂峪。宣传部小年轻说宋月光当初主动提出到这个村担任第一书记。车出县城不久便爬山越岭,我盯着窗外绿油油的树木和庄稼地,感受着乡野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心情也舒展开了。令我难忘的是,中途经过一段盘山路,九曲十八弯,路边悬崖峭壁,飞瀑松风,不愧是一处网红打卡地。司机开车很猛,致使小公交左摇右摆,起起伏伏,真有过山车的感觉。我忽然有点矫情起来,觉得这段行程就好比人生。是的,人生之路总是这样曲曲折折,弯弯绕绕,有时感觉是在走回头路,但走过后才发现,这路其实是一直向上的,是一直向前的,是一直通向远方的,除非你不谨慎驾驶,出了事故,否则终有登顶的那一天。宋月光应该没少走过这段路,但他大概不会像我这样矫情吧,我倒觉得他的人生有那么点过山车的味道。
西茂峪藏在一个山谷中,车在谷口把我吐出来,我又步行一段路才到了村里。村委会门前有个不大不小的广场,四周被杨柳环绕着,阴凉处坐着几个老年人,有的在下棋,有的在闲聊。他们对我的到来没多大反应,我说找村里的领导,一个老太太便把我领到了村南一大片洼地,村支书正带着一帮人挖鱼塘。
村支书姓郝,曾在深圳打工,见过世面,几年前回村当了支书,立志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听说我是宋月光的同学,郝支书说养鱼就是月光书记出的主意,各种关系疏通了,各种手续办齐了,资金也到位了,月光书记却……可惜啊。郝支书欲言又止,我也不想绕弯子了,开门见山问宋月光到底是因为什么受到牵连。郝支书却卖起关子,说带我去看几个地方。
先是到村东看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大棚,棚内种植的全是空心菜,长势喜人。郝支书说,这是我们的空心菜生产基地,月光书记给我们算过账,空心菜亩产六千公斤左右,四个月内可种植两茬,以这个季节最低收购价每斤四毛钱卖,我们的八十亩大棚总共能营收三十二万元,刨去投入、交税等各种开支,保守估计每户每亩地能收入五千元,月光书记说好好干脱贫致富指日可待。郝支书接着说,这是月光书记的得意之作,他去山东考察,喝酒吐了好几回,还和人家比下棋,为的就是请到一个好师傅作指导,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郝支书说的这些数字让我云里雾里,但我知道他是感激宋月光帮助村里找到了一个脱贫致富的好门路,他在夸宋月光精明能干,我这个宋月光的同学也顿感脸上有光,不禁下意识地挺了挺胸。
我们沿水泥路向村后山坡上爬,远远便见层层梯田如雕如塑,错落有致,地里长满了一种黄褐色的灌木,灌木枝上结有一串串珍珠般的绿色果实。我好奇,说从没见过这种植物。郝支书说,这叫连翘,是一种中药材,能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我说,想起来了,常在一些药的说明书里看到这个名字,原来就是这东西啊,还是头一回见。郝支书笑着说,这可是宝贝啊,种连翘,也是月光书记经过多方考察确定的重点项目。月光书记说先试种连翘,后续还要种黄芪、杜仲等中药材,把西茂峪打造成全省特色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他还有更大的规划,说要探索一条农林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主要是围绕中药材种植、蔬菜大棚、水产养殖等产业,打造农业研学采摘、园艺观光、滨水休闲、民俗体验、生态康养为一体的联动新格局。我觉得月光书记的这些想法太好了,我们这里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院、有田,月光书记这些想法都符合我们村的实际情况。我附和说,想法确实不错。郝支书又说,他不光有想法,还确实干了不少实事,修公路,改供水管网,搞“煤改电”,整治村容村貌,他来了还不到三年,我们村就大变样了,不用我多说,你都看到了,一些在外面打工的人也都回来了。听了郝支书的这些话,我不只是作为宋月光的同学感到自豪,内心也生出了更多对宋月光的赞叹。
一路返回村里,郝支书边说边把村子的新变化新气象指给我看,末了又叹息一声说,可惜啊!我理解他说的可惜,既是为宋月光,也是为村里,宋月光一出事,村里的这些项目能不能继续推进还是个问题。我又追问宋月光“落马”的原因,郝支书这次不再回避,回答说,月光书记也是碰巧了,碰上县里出了个工业污染事故。这事看上去和他八竿子也打不着,但问题是县委书记因为这个事被查了,宣传部长跟着也被查了,月光书记就跟着出事了,一环扣一环,传说是月光书记给宣传部长送了钱。其实大家都觉得,凭月光书记的能力和作为,提拔是迟早的事,怎么还要行贿呢?这么聪明的人怎么突然就糊涂了呢?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唉,不说了,可惜啊!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郝支书转了话题说,我还记得月光书记刚来村里的情形,你大概想不到,他一个人开着辆皮卡来了,车是借的,货箱里堆着被褥、衣服、书本和锅碗瓢盆,感觉像是移民。他说西茂峪不穷,我不来;西茂峪不富,我不走。让他住村委办公室,他不住,到村里转了一圈,看上了废弃的小学,就收拾出当年老师的一间办公室住了进去。噢,我想起来了,他桌子上有张照片,里面好像就有你,我说怎么觉得你有点面熟呢。
听郝支书这么说,我突然增了兴致,说能不能去看一下宋月光住的地方。郝支书说,我领你去看看,现在那里面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月光书记突然出事,没来得及收拾,联系他老婆,他老婆说顾不上,让我们看着办。我考虑,扔了不好,留着也不太合适,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旧小学在村西头,孤零零的一个大院,四周是已经有点损毁的石头围墙。看得出,院子里被宋月光整修得挺整洁,但现在有些地方长起了杂草,挂起了蛛网。郝支书说,月光书记原本想改造改造,弄个乡村展览馆什么的,但一直也没弄下资金来。
宋月光住的屋子在大院的一个角落,门上残留着春联,大约是“争当致富领头雁,愿做扶贫孺子牛”之类,字应该是宋月光写的,我大致还记得他的笔体。等郝支书开了房门,进到屋内,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展现在面前的不是一般的那种家居陈设,更像是一个学生宿舍。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两张上下层的铁架子床,分别靠墙置于一张简易办公桌的两侧。其中一张床是用来摆放物品的,另一张床则上下两层铺盖齐全,下铺收拾得比较干净利落,上铺的情形则让我顿时联想到了当年宿舍里宋月光的床铺。那床头一侧的小书架,书架上的书、折扇、耳机,还有扑克牌,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熟悉,有的分明就是当年的原物。我还发现,上铺的被褥正是宋月光上学时所用,被面上印着的学校名称已经被水洗得若隐若现。宋月光分明是把大学宿舍拷贝到这儿来了啊!真的,我眨眨眼,再眨眨眼,仿佛看到宋月光正高高地坐在上铺,拿一副扑克牌在算命呢。
郝支书说,月光书记这人也挺奇怪,把住的地方搞成这样,村委有好床他不用,非要用这种铁架子床,这还是他从网上买回来的。我听他说过,有这两张床,一旦有同学和朋友来,就派上用场了。不过我从没见过有同学和朋友来找他,倒是他老婆孩子来过几次,晚上都是在这里住。
我见床头搭着几件衣物,虽然还算干净,但明显是旧衣物,款式也不新,不应该是宋月光穿的,就好奇地问,这是干什么用的?郝支书说,是月光书记穿的啊,他说在村里就应该穿这样的衣服,容易和村民打成一片。他经常穿着这些衣服和村民们一起聊家常,抽烟,喝酒,下棋什么的。
郝支书把桌子上的照片指给我看,那是一张放大了的合影,是我们宿舍毕业前照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我们八个人姿态各异,或金鸡独立,或双手合十,或弓步单手上举,或手搭凉棚学孙悟空,只有宋月光笔直地站立在右后侧,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和表情。
我的眼窝一热,使劲忍了又忍。我举起手机把房内的情景尽收入镜头中,出来又拍了一张整个大院的照片。郝支书热情地要给我留个影,我想了想说,算了。
回来后,我把宋月光的情况原原本本都告诉了田慧。田慧自始至终没说几句话,最后也是在沉默中挂断了电话。我长舒一口气,觉得总算是给了田慧一个交代。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想到宋月光,我的内心都是五味杂陈。
我们的毕业二十周年聚会如期举行,比十周年聚会来的人多了不少。田慧没来,我能理解。宋月光当然更是来不了,聚会期间也没有一个同学问起他说起他,似乎他不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似乎他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在我们班存在过。同学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声谈论,无所顾忌地搂肩搭背,嬉笑怒骂,又回到了当年同学之间才有的那种氛围中。这次聚会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聚会,但我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和大家碰杯的时候,我的目光总下意识地扫向某个角落,每次我都看到宋月光孤独地坐在那里,冷冷注视着热闹得有点忘乎所以的同学们。
【作者简介】 于立强,文学硕士,现居大同。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出版长篇传记文学《高僧昙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