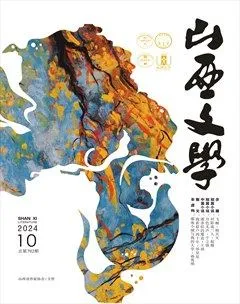夜宿一位养猫的朋友家中
张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张生。没在普救寺遇见崔莺莺,也并非放下架子为妻子画眉的京兆尹。风流佳话以外的这个张生年纪不大,毛病不少。他踽踽独行,从南走到北,从天亮走到天黑。随着行路渐长,他的许多毛病竟不医而愈。像是晕船,像是择席。
择席之症由来已久。少时他离家求学,上榻同窗略有辗转,他便疑心床板断裂,地陷天崩,霎时殒命,苦苦经年方才适应群居生活。学业初成,他客赁别处,纵然拂拭家什千百回,他仍感到前者气味流连不去,闭眼便觉枕畔卧人,细听甚至鼻息幽微,如同奈河潺潺。
此后他游历山河,远涉海外,遍睡世间。虽然山腰木屋漏风,也客舍似家,尽管王谢旧邸轩阔,却人生如寄。不能,也就不再计较床笫。每处异地,常常眠至天明,难得遇见梧桐叶上三更细雨。
此时此夜,他正借宿于一位朋友家中。
朋友家楼高百丈,触手摘星。推开窗闼,不远千里而来的野风是故人生猛的拥抱。它吹动着帘帷,巾栉,木叶……挂在墙上的小忽雷因此铮铮作响,一桌子带着墨迹的宣纸像驱傩的巫觋披头散发漫天而舞。
不管这个改为卧室的储藏间从前是谷仓还是酒窖,风的作业都改善了它沉闷的面目。颗粒或液滴次第还魂,填充着衰老带给它的褶皱与缝隙。张生这时已经有了预感。这种预感所带来的激情不亚于他提篮负箧地跋涉,邂逅沿途所见的日月山川。
他躺下去,闭上眼,择席旧疾悄然复发。
他只好幻想自己是高原上的牧人,背倚朔气,清点暮色中归圈的羊群。他又追忆起推门跌入茫茫雪野的苍冬,万物似无用句点被删去,天地回归未被书写的史前。
全部失效。
他的脉搏比刻漏更精确地计算着长夜的流逝,吐纳的每一缕元气都在默默积聚缔造终将到来的黎明。他以为彻夜不寐的苦茶已经沏好,脑海中却偶然泛起童年纸鸢画样如一缕回甘,不知不觉悠悠入睡,直至一声滑腻猫叫重新将他叼出梦境。
夜深似渊,人沉如溺,张生说不上来声源何处,只知方寸间必有猫的存在。他下了床,蹲下身,伸出没有鱼干空空荡荡的双手,像唤全天下所有猫那样唤着咪咪。得不到回应,他就持续地唤着,并在自己的声线中听出一种忠贞,为之动容。
吵死了。猫说。它陡然跳过来,掌灯似的点亮了两只祖母绿的眼睛。这光力透云霄,不仅屋内生辉若昼,连对面华厦的琉璃翠瓦也在它的注视下鳞次栉比丝丝分明。只是猫自身亦被光晕笼罩,一派清虚,像仙子面目不轻易示人。
张生问它从哪来。猫说你管我,我还没问你呢。
我从南方来。
我问你了吗,我又没问你。
周遭霎时黯淡枯静。猫察觉到了他的低落。带着对老实人的轻微歉疚,它踱到张生身边,拿尾巴扫了扫他的小腿,像成人抚摸另一个成人的脊背。
我是本地猫——再说明白点,我是本家猫。
朋友从没向张生谈起过养猫的事。猫猜到了这一点,它跳到床上,说主人养花,养鱼,养来路不明的女人。它从来不是主人的唯一,不必被隆重提及。
但你不是一只寻常的猫。
猫跳上桌,盘坐在那一堆破烂书法上,说第一百天的猫镇纸绝对没有第一天的猫镇纸可爱。转眼间它又敏捷地攀上墙壁,学着佛窟彩画上的伎乐天那般反弹小忽雷。琴声没传递出丝毫庄严吉祥,只是一阵一阵凛冽地剥开良夜初结的伤痂。没等张生从余音中清醒过来,猫已跃入他的怀抱,毛茸茸地挠着他的胳膊,索取深情的摩挲。
就这样,他顺着它的毛,它回答他的话。
纵然我们带着九条命,活了近千年,每只猫也都只是寻常的猫而已。就像我在外能得到各不相同的投喂和形形色色的爱抚,最后也会回家,回到这里。
张生想到他逗留过的客栈与馆驿,想到遥遥无期的归期。再一睁眼,那笼罩着猫的朦柔光晕骤然溃散,东方既白,尘寰显形。他拈起袖子上的一根毛嗅了嗅,不错,是猫腥气。
朋友带他下楼吃早餐。张生四下环顾,诧异万分——草坪上,石径间,池塘边,几乎处处是猫,反而人不多见,一时分不清是人养猫还是猫养人。行到蔷薇架下,朋友顺手逗了一只通体雪白的猫。它原本在舔舐草茎间的露水,受到拨弄,便仰翻在地,曲承其欢。
走上街衢,张生问他那猫如何一点也不畏惧。
他说,那只就是我养的猫啊。
蓦然回首,天昏地暗,猫已无影无踪。随着一道皎洁闪电反反复复凌空劈过,张生才确认,那是飞檐走壁的猫在义无反顾地奔向属于它的窗口。
【作者简介】张秋寒,1991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 《铅华》《仲夏发廊》《长此以忘》《白昼昙花》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