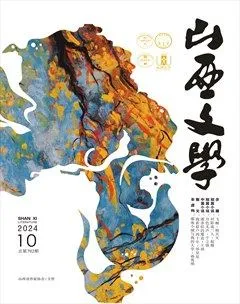长发公主与外婆桥(创作谈)
小时候看完童话《长发公主》总是在想,如果那天经过高塔的不是年轻强壮的王子,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即使公主放下了她的长发,他也没有足够的力气能爬上高塔。又或者如果公主没有惊人的美貌,王子也不会下决心带她离开,更不会向她求婚。时间久了,公主的长发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得稀疏,直到不能支撑别人爬上高塔将她解救出来,她只能永远被困在塔中,看不到一直向往的邻国的星光,直至衰老和死亡。
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困在塔里的公主,遇见王子的,被解救,遇不见王子的,死在塔里。假使长发公主在塔里老去,她在塔里的生活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每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总会是我的外婆。外公在我母亲高中时过世,外婆艰难地撑起这个家,把子女拉扯大,一直到他们全都离开家读书、工作,她自己却永远留了下来。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一个小时车程的位于市区的六女儿家,后来因为中风,腿脚不便,连女儿家也不怎么去了。我和外婆并不算特别亲近,她有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相应地,也有不少外孙和外孙女,她似乎也没有特别偏爱哪个小孩。我们很少去看她,除非是家族有什么重大的聚会。外婆家在村子里面,要经过一条不算长的小路,每次去远远地都会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门前的藤椅上等我们。吃完饭,大人们围成几桌打牌聊天,小孩在外面疯跑,外婆依旧一个人安静坐在那儿,眯着眼睛看我们。到了分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朝她挥手告别,她带着笑意朝我们点点头,目送我们每个人离开。一年又一年,像一株顽强生长的植物,永远矗立在那里,一直到她去世。
写《飞蛾》的时候我总是在想,那时外婆坐在藤椅上,安静地眯着眼睛看我们时在想些什么。是不是在想我们从她家里离开后,各自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会不会也希望我们能多带她出去看一看,哪怕是多和她聊聊,和她分享那些她永远都不曾有机会参与的人生。
飞蛾扑火的意象深入人心,人们总想学飞蛾,目标明确,存有信念,坚定勇敢地去追逐想要的生活。殊不知飞蛾之所以扑火,恰恰是因为它不知道该飞向何处。飞蛾在成为飞蛾之前,是蛹,长久地被包裹在茧中。在破茧而出成为飞蛾之后,因为搞不清楚飞行的方向而只盲目地围绕明亮的物体盘旋。它的一生远没有人们认为的那样灿烂,唯一精彩的时刻,或许是临死前冲向火光的一刹那。
钟希兰也好,小娟也好,她们都逐光而活。钟希兰的光,是儿子和丈夫,小娟的光,是来自家庭的爱和温暖。当她们失去这些时,彼此的处境暗合,前者在地理和生理概念上被困住,后者在心理上被困住,最终相继成为一座孤岛。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情节,是钟希兰独居的第一年,在儿子忌日那天习惯性地做了一大桌菜,然后独自坐在桌边发呆,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后来,她等来了小娟,一个同样无处可去的女人。她们如同两个被砍去长发的公主,没有王子降临,她们彼此拯救,共享一片孤独的光。
我还算年轻,对生老病死的感悟算不上透彻,写作很多时候于我而言是提前感知生活的一种方式。我在钟希兰身上感知到的,是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恐惧却又逃脱不了的东西,我为这种宿命感着迷。纳博科夫说,“万事万物都是先有形再有实的。”在写《飞蛾》之前,我脑海中有无数个钟希兰,当我开始写的时候,钟希兰只有一个,她是我的回忆,也是我的将来。
在这里我要感谢给这篇小说提供建议的师友。当然,我也要对我笔下的钟希兰说一声抱歉,不仅没能让她以相对体面的方式离场,而且还刻意将与她长久相伴的孤独不断放大和延长了。小说里的这一天,只是她周而复始的平凡日子里的其中一天,却也是她漫长人生中的最后一天。倘若她能拥有自由的意志,预知这一天的到来,又将会如何反应。或许一切还是会照旧,因为她并没有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