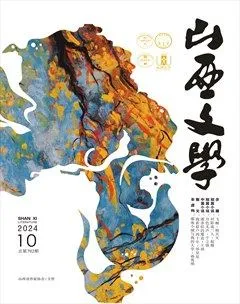母亲
1
母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已侵占洪赵。母亲说,日本人来了,全村人就钻沟,叫“跑反”。跑反的时候,不要说人,连狗都不叫,夹着尾巴,跟在后面;抱着的母鸡,一声也不鸣;拉着的黄牛,低头默默前行。人畜都是惶恐不安,静悄悄地逃命。
母亲的记忆里,比日本人可怕的是“二鬼子”(伪军)。他们头捂毛巾,打扮成百姓模样,吼着嗓音叫唤,“日本人走喽,日本人走喽!快回来吧,快回来呀!”上当回村的人,轻者失财,重者丧命。
有一年年关将至,姥爷在亲戚家借了二十来斤麦子。怕收捐的协助员发现,不敢在村里石磨上磨。借了邻家磨豆腐的小石磨,就着油灯,用手扳着石磨,偷偷磨了大半夜,才把那点麦子磨成白面,想着过年时能稍微做点改善。不料想,还是走漏风声。第二天,收税的人来到母亲家,翻箱倒柜,搜出那点少得可怜的白面,要强行拿走。十来岁的母亲急了,大叫:“这是我家的面,你们放下!”说着就扑上前去,要抢回面袋。那个毫无人性的办事员把母亲一把推倒在地上。母亲顾不上疼痛,顺势抱住协助员的大腿,不让他走。协助员恼羞成怒,劈头盖脸,对母亲一顿暴打。母亲喊着:“放下我家的面!”就是不松手。
母亲念过书。不过,没念几天就辍学了。
说起来,母亲的失学缘由也不复杂。她天资聪慧,过目成诵,先生本来十分喜欢。可先生的做法,却让母亲十分厌恶。那个年代兴体罚。学生娃娃学不会或犯了错误,要打手板。先生打手板分三六九等。有钱人的孩子免打或象征性打几下。穷人家的孩子呢,下手绝不留情,直打得哭爸喊妈,眼泪汪汪。母亲看不惯先生的这套做法,鼓动学生反抗,把手板藏了。或者,让同学在先生手板还没落下时,就“吱儿哇吱”乱叫,让先生手忙脚乱,下不了台。先生发现始作俑者是母亲,恼羞成怒,把母亲一顿毒打。母亲的手又肿又疼,不能端碗,无法拿筷子,吃饭时躲着姥爷姥姥。可是手又烫又胀,十分难受,忍不住时只好在青石板和铁门环上冰一冰。
班里有一同学,家境富裕,爱拿着油饼或者白馍在别人面前炫耀。这对平时吃糠咽菜的母亲来说,是极大的刺激。有一天,他又拿着一个大白馍在母亲面前大嚼。母亲气不打一处来,说了句:“走开!别在我跟前。”那位同学也不服气:“怎么啦,我又没惹你。”说着话,“吧唧吧唧”,馍嚼得更出声了。母亲火了,上前一巴掌把馍打在地上。然后,捡起来,塞进嘴里大口吃了起来。那个同学傻傻地愣了半晌,“哇”地哭了,跑去报告先生。先生对母亲是旧怨未消,又添新气。这次,除了打手板,又增添了惩罚的新招数:让母亲跪在地上,头顶一块砖,砖上放一碗,碗里倒满水,跪够一个时辰。若碗里水洒了,重新计时。自知理亏,母亲忍气吞声,接受处罚。不料想,先生来了客人,吃烟喝茶加排哒,把体罚母亲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两个时辰过去了,也没叫母亲起来。母亲忍无可忍,用手一拨拉,砖碗落地,站起身来,扬长而去。从此,再没有踏进校门半步。
母亲虽然没念几天书,但识字却不少。母亲后来还当过村里的幼儿教师,我的启蒙教育,也来自母亲的这点儿学问。
2
兵荒马乱年月,母亲见过各种各样的部队。晋绥军部队,母亲叫“顽固兵”。母亲说,顽固兵纪律严,当官的说话,没人敢不听,可是缺少生气,总是死气沉沉的。有个老兵,快四十了,整日愁眉苦脸,逢人就说他是河南人,上有老,下有小,常年当兵在外,不知一家人如何过活。有一天,那个河南兵开小差,让抓回来了。那个打呀,让人提起就落泪!马鞭抽得遍体鳞伤。之后是上刑,压杆子,把大腿用杆子压住,往小腿下垫砖。一块,两块,一直往上加。腿不一会就折了,那惨叫声,在村外都能听见。
八路军队伍好,和和气气,笑声不断,整日乐呵呵的,逢人叫大爷、大娘,给村里人挑水劈柴是常事。母亲喜欢八路军。一天,一个八路军战士扛着枪,边走边唱着歌,“军队和老百姓,嗨,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哪,才能打得赢呀嗨!”母亲欢欢喜喜地跟在后面学唱。忽然,从一堵短墙后面,伸出一支枪来,传出短促的声音:“缴枪!缴枪不偿命!”那战士怔了一下,停住脚步,把枪慢慢递了过去,说道:“缴哩咯。”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战士拔腿向前飞逃。母亲不知所措,也跟着跑,只听得身后一声枪响,热乎乎的子弹从耳边擦了过去……姥姥听说了这件事,对母亲一顿好骂。姥爷却说,别吵了,不是没伤没碰么,以后注意就是了。
我们那里大约是1947年解放的。
我姥爷早逝,还不到四十岁就离开了人世。姥姥、舅舅、母亲一家三口,艰难过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母亲才十几岁,就自觉担当起一家之主的使命。村里有什么事,姥姥不用出头,母亲一马当先。
姥姥家分了地。春耕下种姥姥正愁没有牲口用呢,母亲已经把邻居家的大黄牛借来了。那时,舅舅才九岁,小小的身板扶着犁,还不及犁高呢。
3
母亲有个口头禅。一遇不顺心的事,特别是与父亲发生口角之后,总会冲我来一句:“你姥姥把我害了咯!”
这话从何说起呢?却是与学唱戏有关了。
母亲酷爱唱戏。年轻时算是当地红极一时的“角儿”。出演的《梁秋燕》《刘巧儿》《梁山伯与祝英台》 红了河西半边天。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的一出戏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特别是《十八相送》那一段。母亲连说带唱,叙说起来,十分动情。
母亲唱的《十八相送》属洪洞道情,具有原生态的韵味。那唱词与我后来听过的都不相同:“太阳出来红皑皑,一对学生下山来,头里走的是梁山伯,后面紧跟着祝英台。过了一山又一山,碰见樵夫把柴砍。樵夫砍柴为了谁?为了贤妻把柴担。过了一坡又一坡,坡坡碰着圪刺窝,圪子窝里圪刺多,叫声哥哥你疼疼我。走了一里又一里,碰着个大嫂纳鞋底。问声大嫂你为谁纳,我为情哥哥纳鞋哩。走一洼来又一洼,洼洼前头种西瓜。大哥种瓜为了谁?盼着孩子叫爸爸。走一河来又一河,河里游着一对鹅,公鹅就在头前走,母鹅后面叫哥哥。”
晋南有个蒲剧团,听到母亲的名声后,专程派人到樊村,找到母亲家里,想把母亲挖走。没想到遭到了姥姥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当时母亲与父亲已订婚,若跟剧团走了,婚事就吹了,在世上落不起,咱不做那丢人败兴的事!剧团里的人好说歹说,姥姥就是不松口。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村村都有文艺宣传队,已经四十多岁的母亲加入宣传队,再次走上舞台,又过了一把戏瘾。那时她常演的是一个小戏,叫《推荐之后》,说的是推荐学生上学的事。
舞台上的母亲容光焕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回到了年轻时代。
4
母亲嫁给父亲是在1954年,那年,她虚岁十八,刚进婆家,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奶奶腿脚不灵便,常年体弱多病,在母亲过门之前就已瘫痪在床。母亲嫁过来后,还不到两年,就去世了。父亲在外地读书。而父亲的弟弟和妹妹,也就是我的叔叔和姑姑,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爷爷在地里干活,家务重担就全落到了母亲身上。
爷爷脾气暴躁,爱发火骂人,对这个刚过门的媳妇也不当外人,说骂就骂,甚至还想打呢。据说有一次,爷爷在地里干活,嘱咐母亲往地里送饭。母亲干完家务,赶紧做饭。做好后,就往地里送去。紧赶慢赶,还是有些迟了。爷爷又累又饿,看到母亲提着饭篮子姗姗来迟,气不打一处来,怒道:“你看看都什么时分了,这才送过饭来?你就不怕把我饿死呀?”说着话,举着鞭子就要打母亲。母亲赶紧放下饭篮,一边躲,一边说着好话:“爸,我知道你不是嫌我送的饭迟,你是饿得发躁哩!你先吃上几口吧?我今天腌的黄瓜,还炒了两个鸡蛋呢,吃上几口,骂我才有劲,打我也有力气呀!”母亲边说边退,离爷爷越来越远。看见爷爷消了气,蹲下身子收拾碗筷,才往家里赶。我叔叔和姑姑马上就要放学了,还要张罗着给他俩做饭。而且,瘫痪在床的奶奶还等着母亲伺候呢。
母亲娘家樊村当时是乡政府所在地,属孔庄区。母亲又是村里的积极分子,经常参与社会活动,说话、办事,都比较自由。可到了这婆家西昌呢,这样的氛围却没有了。
我们这个家族,在村里虽不是什么大户,可也算是赫赫有名。曾祖父是村里的绅士,主持村事四十余年,在村里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曾祖父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喜爱的是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而不是像母亲这样接受过革命熏陶的新潮青年。
母亲的做派与曾祖父的期望大相径庭。为此,曾祖父对母亲颇有微词。而母亲呢,对曾祖父那一套也看不惯,私下称之为封建礼教,把这个家称之为封建家庭。
上世纪六十年代,搞“四清”运动,我一个本家叔叔因在村里担任生产队长,在一次次过关,一次次检查中,坦白曾经私下拿过队里二斤油。工作队长上纲上线,把这二斤油的事,说得比把天捅了窟窿还大。二斤油不多,可他问我本家叔叔哪年当的干部、一共当了多少年、一年等于多少天?每天拿二斤油,这样算下了,无异于天文数字了。让资产阶级腐蚀了的干部多么可怕呀,一个人要侵吞国家多少财产呀……
我的这个叔叔实在是吓坏了,一直嚷嚷,没活路了,没活路了。家里人劝,怕个啥呀,不就是二斤油吗。我爸爸无奈地说,二斤?二千、二万也不够呀,还不知道要赔多少亿呢。当时的形势,真的有点吓人。
这时,我母亲主动要求去找这个工作队长。母亲到了工作队驻地,一推门进去,先声夺人:“哪个是工作队长?”
“我是。”正与人闲聊的队长一愣神,不由站起身来。
“坐坐。”母亲反客为主,摆摆手,示意工作队长先坐下。接着说:“我过来,谈谈政策上的事……”
母亲对工作队长说,共产党的政策一贯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我们的政策是拉一把,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对吧?队长!
工作队长有点懵了:“对!对!你……你是谁?”
“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也是XX的嫂嫂。”回答完,母亲扬长而去。
母亲其实心里也没底,她只是先让全家人吃了个定心丸。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母亲心里也是有底的。因为,我的父亲那时在河东一个叫李堡的村里搞“四清”运动,也是工作队长。通过父亲,了解了不少政策,她的那一番话,也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来由的。
果然,母亲这虎穴一闯,我那个本家叔叔再写了份检查,就过关了。
5
父亲洪洞一中毕业后,回村当了两年社主任,又被县里安排当了刘家垣中学的老师。父亲教数学,还是红旗班的班主任。课教得好,班级管理也好,让县教育局的领导看上了,提拔父亲到河东苏堡中学当校长。回来和母亲商量,母亲坚决不让去。她对父亲说,隔山不算远,隔河不算近,你到了河东,家里有事咋办?前些日子,过汾河,船翻了,还伤了人。
父亲本就犹犹豫豫,听母亲一说,也就作出了不去的决定。教育局领导做了几次工作,父亲就是不听从分配。当时的局长姓李,很恼火,还有这样的人?给官都不要?撂下话来:“不服从分配,啥也别干了!”
“不干就不干,大不了回家种地!”父亲竟真的卷起铺盖,回到村里种地了。
大约半个月以后的一天,早上刚起床,母亲对父亲说:“今天有什么好事吧,你看这喜鹊子,在咱门前叫个不停。”父亲不以为然,应了一声,抗着铁锨,又到东沟里翻地了。
还不到晌午,家里来了客人,是县文教局的,姓辛。走了几十里地,来到我家,带来文教局领导的最新指示,让父亲上班。
母亲打发人到东沟里去叫父亲回来。在等父亲回来时,母亲忙前忙后,热情招待辛同志,不露痕迹地套些话,看文教局对父亲如何安排。
母亲先是数落了父亲的一番不是,说他不该不服从分配,不该赌气回家云云;又夸了一番领导的大度,是个有本事的好领导等等;又谈了一番党的政策“治病救人”之类。最后,还夸了一番局长的好,说大领导不会和普通教师一般见识。
那位辛同志话本来就少,在母亲的滔滔不绝里,几乎插不上话,只能以点点头,或微微一笑应之。
父亲从地里回来了。他认识辛同志,简单寒暄,不卑不亢。还问母亲,饭做好了吗?老辛从县里来,好几十里地,不容易,挺辛苦呢,做点好吃的。
辛同志以自家人的口气对父亲说,你看你,不声不响就回家了?你不找领导,领导让找你呢。接着哈哈一笑,我说老贾呀,你家里人的认识水平比你还高呢!
父亲能沉住气,也不插话,静听下文。
辛同志见我父母两人都不说话,毫不在意地自顾说了下去:“李局长说了,是人才就不能埋没。有些同志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岗,可以做些调整。老贾呀,李局长给你重新安排了一下……”
“到哪里?”母亲沉不住气,问话了。
“左木公社,当联合校长。”
“呵呵,局领导也挺有意思,你不是不想过河吗,那好,你就上山吧!”
父亲沉吟片刻,回了一句,好吧。
辛同志如释重负,不再提工作的事,不见外地喊上了:“吃饭,吃饭,我是真的饿了!”
母亲怕自己做饭把式不好,还请了邻居桃花婶子,烙了软面饽馍馍,炒了鸡蛋,熬了小米粥。
6
左木公社书记姓郭,叫郭洪星。农工干部出身,穿着朴素,说话风趣,就是眼神不大好。这个郭书记很有意思,批斗他的时候,众人喊口号:“打倒郭XX!”他插话:“不是打倒的,是按倒的。”喊“打倒郭瞎子”时,他又嘟囔一句:“没瞎,还能看见哩。”
母亲见到郭书记时,他的背上粘着一团又一团的糨糊。母亲说,郭书记,你看你衣服脏的,脱下来让我洗洗吧。郭书记摆摆手,不用洗,不用洗。都是贴大字报贴的。今天洗干净了,他们明天又要贴哩。
母亲来到左木的时候,那些造反派们,正让父亲交出公章呢。父亲软磨硬抗,就是不交。郭书记私下对父亲有过交代,那几个人不地道,印章给了他们,会出大乱子。
母亲说家里有急事,要让父亲回家处理。郭书记就坡下驴,立即准假了。
母亲动员父亲回家时,撺掇着让父亲把公章也带上了。回到家里,母亲用布把公章包好,藏到麦瓮里。母亲对父亲说,这下好了,谁找也找不到公章了。
爷爷在队里看西瓜,西瓜地里搭了个庵子。怕人找到家里来,父亲吃住就在西瓜庵子里。母亲天天给父亲送饭。
公社的郭书记关心父亲安危,从左木下山,到我家看望父亲。
进到村里,打听我家住处时,正好问到我家的一个邻居。那邻居看到一个穿着破旧衣服,拄着木棍,斜眼看人的人,还以为是个说书的呢。听说是找我家,也很热心,将人往我家引。可心里一直嘀咕着,这个说书的,不去大队里找支书主任,到老贾家干什么呢?
邻居比郭书记走路快几步,先到我家。见到母亲,低声说,来了个说书的,找你家呢。
母亲感到奇怪,说书的?找我家干啥呢?出门一看,笑得直不起腰来。哈哈,原来是郭书记!
母亲到西瓜地里把父亲叫了回来。见到郭书记,父亲很高兴。两人很能谈得来,对批斗什么的也看得开。
父亲在左木公社没待多久,调到了县城文教局。
7
有了四清桥,进城方便多了。过汾河,不再担心船大船小,风急浪大。也不用费心寻找合适的渡口和撑船的把式了。安全问题全无。还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四清桥,盖得niao,路儿油得真赶照。和城里走,是一股,走起路里不沾土。
农闲时节,母亲会到城里父亲的宿舍住些日子。在城里住的那些日子,母亲的大胆有时让父亲很是头疼,甚至恼火。母亲的一些做法,甚至“干扰”到了父亲的工作。
当时的洪洞,师资力量缺乏,不少老师是外地人。从心里说,这些外地教师真不容易。常年两地分居,夫妻双双孔雀东南飞,牛郎织女般隔河相望,不能团聚。
那些老师变着法子想调回老家,可这个问题又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当时有个土政策,叫对调。走可以,你找一个人来洪洞教书,与你对调,保证洪洞学校里岗位上不缺人。
父亲是人事股长,主管此事,他办事认真,严格把关,进一出一,决不含糊。这些优点,在母亲的眼里,全无是处。用母亲的话说,叫死心眼,担茅子的不偷吃。
有个老师,是外地人,一心想离开洪洞,调回老家。父亲的答复很简单:“行,你找个愿意来洪洞的人,对调就是。”
不知那个老师是不愿找呢,还是找不下。总之是,没有对调的人,却时时来文教局纠缠,要调回老家。
有一天,父亲不在单位。那个人到文教局遇到了母亲。见到母亲,那人像遇到五百年前的知音一样,一条鼻涕两颗泪,诉说自己的不易和不幸。
想来,他是想得到母亲的帮助,以求母亲向父亲求情,达到自己回乡的目的吧。
没想到,母亲从父亲抽屉里拿出公章,说,你的调动表呢,我给你盖章!
那人有点懵:“你……你盖章?”
“我盖!”
母亲大手一挥,啪,大红公章盖上了。
那人愣了半晌,才连连道谢,临走时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从此,那人再无音讯。
父亲回来,对母亲一阵数落,但人已经放走了,这件事终归不了了之。其实,母亲和父亲吵架从来都占上风,但这次挨骂,母亲没有反驳一句。她自是知道理亏,但明知不对还做了,想来,是真心不忍看到别人家的困境吧——骂我挨,福你享,未尝不可!
父亲心脏病突发,在部队75医院住了大半年院。病还没有好利索,又飞来一纸调令,要让父亲到刘家垣中学当校长。
听说才来了一个管文教的副县长,工作认真严厉,要求所有人员不得提条件、讲价钱,立即走马上任。
母亲才不管他什么新来的、旧来的呢。到政府大院找到那位副县长,当面申述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出城到山区工作的理由。说一时有个三灾病荒,在城里就医方便。
那位副县长以理说理,用大帽子唬人:“家里的是共产党员吧?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要有牺牲精神嘛。”
母亲马上把他的话怼了回去:“你这话就不对了。如果是战争年代,我家老贾堵枪眼,踩地雷,二话不说。可这是和平年代。再说了,我们家少了老贾,那就塌了天了。我们这一家怎么活呀!”
整个气氛骤然沉重起来。慷慨激昂即刻转为悲悲切切。
那个副县长不再讲什么大道理,沉吟半晌说,好吧,我们再考虑考虑。
母亲把该说的话说了,也听出副县长的话音,知道该走了。母亲也不会说谢谢之类的话,站起身就走。
刚走了几步,又听那领导问:“你……你什么毕业?”
母亲连头也没转,回了一句,农业大学!
出门了还听到那领导自言自语,喃喃着:“农业大学?太谷吗?”
那次调整的结果,父亲担任了县教育工会主席。
8
据母亲自己说,她在县里接受过培训,受过专门的接生训练,不过无从考证。
不管怎么说,村里的妇女怀上娃娃,总是要找母亲的。母亲不无自豪地说过,咱这村里多一半的人是我接生的。村里有个娃和母亲吵架,母亲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你是个什么东西?和我吵!你回去问问你爸,他敢不敢说我半个不字!你,还有你哥,你姐,是谁把你们从你妈肚子里拽出来的?”那娃一听,再不敢吵了,露出笑脸赔不是,说好话。
说起接生来,母亲一套一套的。“酸儿辣女”“勤厮儿懒女子”,怀胎大肚笨笨的生什么、怀上几个月都不显的生什么、肚子偏左生什么、肚子偏右生什么肚皮圆圆生什么。甚至从孕妇走路的姿势,都能判断出生男生女,十有八九灵验。让人惊奇,信服。可当人们惊奇于她预测准时,母亲又说,女人生娃娃人命关天,是在鬼门关走一遭,可不敢马马虎虎,要当事哩。
母亲接生是无偿的,不收任何费用。用母亲的话说,只能赚几圪垯油馍馍。这是指婴儿满月或百日时,当地习俗要闹一闹,即亲戚朋友前去看望,都拿油炸的面食。主家会拿着油饼给左邻右舍送一块半块,称“花馍馍”,以图吉利。这自然少不了母亲这个大功臣的一份。
对那些怀娃娃的妇女,母亲再三嘱咐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些小媳妇儿们唯唯诺诺,点头不已,心存感激,甚至面红耳赤。有个媳妇听了母亲说的话偷偷地笑,母亲一本正经地责备,笑什么,这可是正事!要造成流产,再也怀不上了,让你后悔一辈子!过几天,我再过来看看,看胎位正不a9Xhbj9pYBEO1V7shj9eXKqHNSgfPLEDjh1ePKX7/QU=正。这一下可就显示出母亲的水平了。若胎位不正,母亲凭一双手,几次捏揣按摩,就将胎位扶正,真是神了。
接生的趣事也不少呢。有一家也是难产,孩子生了一天还生不下。打发男人到公社医院里买催生的针。十几二十里的路呢,还是步行。等他气喘吁吁把针买回来时,老婆已经生了。他舍不得这两支花钱买回来的催生针,就说,可惜了的,不敢糟蹋了,我把它喝了吧。他老婆听见了,不顾产后虚弱,使劲骂他。死人,你可不敢喝了,你喝上,把你的屎肚子也催下来了。
有个媳妇,家里光景不是太好。怀孕后,母亲发现她胎位不正,矫正了几次,效果不明显。母亲就对那家人说,胎位不正,怕是有麻烦。快生了就赶紧去医院。那家人也答应了。
没想到,临产时,却又找上母亲了。母亲有些犹豫,胎位不正,注定难产,我若接产不成,不是耽误人家吗。可那家人也着急了。嫂嫂,你老人家还是去一趟吧,她疼得打滚呢,现在去医院也来不及了!救救她吧!救救我们一家吧!母亲心软又胆大,牙一咬,走吧!
路上埋怨,让你们去医院生,怎么不去?那个人说,寻思着还得几天才生呢。再说,再说……说不下去,眼里落泪了。唉,别说了,赶紧走吧。
有什么好说的呢?就一个字,穷!这个字,让老百姓如此轻贱,生死无门啊。
母亲也算艺高人胆大吧。那个孕妇,生孩子先生的腿,头卡住生不出来。母亲一横心,用手把头硬拽出来!孕妇昏死过去,孩子也没哭声。母亲一边大叫快化红糖水,一边拍打婴儿背,做推拿按摩。“哇”的一声,婴儿哭出声来。那孕妇,心有灵犀般,也醒了。母亲如释重负,拿手巾过来,擦擦汗。母亲全身湿透了,几近虚脱。
母子平安,一家人欢欢喜喜。
后来,那个叫偏头的孩子,对母亲一直很好。
9
除了接生,母亲还喜欢给人做媒。
媒人全凭一张嘴。母亲的口才自然没得说。若男家光景差些,母亲就夸小伙好;那娃娃聪明能干,吃苦耐劳,将来你们就和牛郎织女一样,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夫妻双双把家还,那光景还不好到天上去呀;若小伙差些呢,母亲就夸光景好,这家人是方圆有名的好光景,小伙实实在在多好呀,你一去就是一品掌柜的,穿金戴银,说话一锤定音,真是掉到富窝子里了;姑娘漂亮,母亲会说,咱摘的是一朵花,又不是搬园子;姑娘容貌差些呢,夸姑娘老实本分能吃苦,是过光景的好手。一好搭一丑,能活九十九。有时还会没大没小地开个玩笑,幽一默。吹了灯,还不都一样,想成谁就是谁。这些话都是就事论事,因时因人而不同,别人其实是学不成的。母亲做媒,成功率居高不下。
母亲做媒也走过麦城。就是给uNCfvhR38CBnJvffggpP0TudVdWam3iVjt5s7rvDeok=我舅舅的女儿,她的亲侄女那一回。俗话说,姑姑做媒,只是一回。意思是说姑姑做媒保成。可母亲这一回却是败了。村里有户人家光景好,娃娃好,母亲看上了,赶紧地去说合。舅舅没啥说的,姐,我听你的。在我表妹那里,母亲碰了钉子。表妹问,姑姑,他什么学校毕业的呢?这,这……我回去问问再说吧。其实姑姑侄女二人心里跟明镜似的。表妹嫌对方文化程度低,婉拒了。母亲也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说回去问问了。那个娃娃小学毕业,就跟兄长学做买卖,钱有了,可少文化,是个短板。
有句俗语,宁拆十座庙不拆一门亲。是说夫妻闹了矛盾,劝和不劝散。母亲则说,不得成,咱裂了,别气得没命了。母亲唱戏唱的是《刘巧儿》《梁秋燕》,唱歌唱过《兰花花》,接受的是婚姻自由思想,反对捆绑夫妻和不幸福的婚姻。
我有个本家姑姑,嫁到邻村。婚后好几年不开怀,没生个一男半女。公婆不给好脸色,说姑姑是不下蛋的母鸡。姑姑受了委屈,回到娘家诉冤枉,哭哭啼啼。本家奶奶知道母亲是说事了事的人,就找到母亲,让母亲送姑姑回去,也是息事宁人的意思。母亲说,行。我先去妹子婆家看看再说。没料想,母亲去了根本不是说好话劝和,而是找上门去讨说法。我家妹子在你家,多干少吃,落了个不下蛋的母鸡?你们家祖坟不冒烟,怨你们没积下德!屙不下的怨臭瓮哩,瞎了你的眼窝!三只眼的马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出了一口恶气,回来就带着姑姑去公社办离婚手续。三下五除二,又在河东里给姑姑找了个殷实人家,夫妻恩爱,三年生了两个娃。
父亲在城里上班。母亲跟着父亲在城里住。有个邻居媳妇愁眉不展,不见笑脸。原来是她那个在企业当个小头头的男人,在外面有了相好的,闹腾着要跟她离婚呢。别人劝这个叫什么英的媳妇,忍一忍,咱是正宫,别计较了。男人有地位,有钱财,就凑合着过吧。母亲却另有一番说辞,离!他要离婚咱跟他离!人家心在别处,家里再有,山珍海味吃着也不香。再说了,他的福分也许就是你带的,这样好的妻命不珍惜,让他后悔去吧。不幸,让母亲言中了。这个媳妇离婚不久,那家企业破产,那个男人下岗,相好的自然是好处安生,也离他而去。那个人落得个里外不是人,自作自受,自讨苦吃的下场。母亲说,这人呀,可不敢坏了良心,老天爷照着哩。
10
母亲一天天衰老,病倒了。
那天,我回家接母亲到城里看病。不知谁透露风声,村里人知道了。扶母亲出院门,路两旁站着那么多的左邻右舍,父老乡亲。母亲甩开我的手,不让扶,也不坐进车内。一步一步,坚持走到村外才上车。有人问话,母亲回答,我得了癌症,去城里看病。那份坦然,永生难忘!
2016年11月4日凌晨,母亲离开人世。
丧葬一应事宜,是要请风水先生的。我家请的是村里的长辈越有爷。我问过越有爷,人去世后,为什么要赶紧撕破窗户,四门大开呢。他说是给魂留路呢。人死了,魂也是要走的。他还说,有的人魂不走门和窗子,从烟筒里走。我听了,有点不信。
母亲过世,停枢四天。请了理事会,招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理事会有个小锅炉,与炒菜的炉子连体。做饭师傅正在炒菜。突然,炒瓢里冒烟冒火,那锅炉的烟筒里也冒出数仗的火苗子!人们都慌了,有人大叫,快救火!只几秒钟,烟消火散,没事了。好像没发生过一样。我想起了越有爷的话。
我知道,这一回,母亲是真的走了——她的肉体,连同她的灵魂。
【作者简介】贾小建,笔名晓剑。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已出版诗集《梧桐雨》,长篇小说《魔子努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