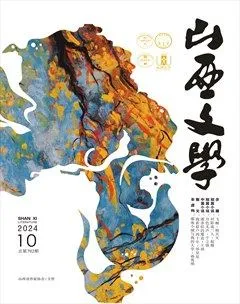酒事杂忆
初夏,我去三联书店,买了一册夏晓虹和杨早编选的《酒人酒事》。谈酒的文章真是车载斗量,这本书也是弱水一瓢罢了。还有一册《茶人茶事》,由陈平原与凌云岚合作编选。据说夏晓虹善饮,陈平原好茶,而杨早与凌云岚是陈、夏两位的高足,也是一对夫妻,可谓书林佳话。由此也想谈谈酒事,可是我不善饮,本是不该作文的,但读了《酒人酒事》中的几篇文章,觉得颇有些人生三味,也勾起了几许的思绪来。或许饮酒是有家族遗传的,我的祖父信佛,他不饮酒,也反对我们晚辈喝酒。父亲倒是饮酒,但酒量很小,有时醉了,也从不说酒话,而是默默躺下休息。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和父亲一起闹酒,但并不会猜酒拳,便用最笨的“老虎杠子”来比划,输了的,则是要罚上一小杯的。那时候家里也无好酒,我曾尝过一小杯,苦辣极了,故而我只是闹,但几乎不喝的。家乡人喝酒只喝白酒,从不饮啤酒,乡人戏称啤酒为“马尿”,认为啤酒味道不好,最多只能算饮料。当然,这是一种偏见。但乡人喝酒却是很有古风的,每每将酒倒入一个酒盅,再有两三个小酒杯,然后轮流敬酒,或互相对饮,那种仪式感,体现了对酒事的尊重。
我的第一次醉酒,却是因为啤酒。记得是上初中的时候,有天与同学们谈起酒事,乃是好不热闹。我虽然未曾喝过酒,但也谈得起兴,便按照家乡人的说法,认为啤酒没有什么酒劲,就像马尿一般。有位好事的同学估计喝过啤酒,当场反对,并问我可否喝掉两瓶啤酒,话已至此,我当然不能退缩,也以为他不过说说罢了。不料,这位同学很快从学校旁的商店购来两瓶啤酒,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在同学们的起哄中喝下去。当时是怎么喝完两瓶啤酒,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喝完之后,头脑尚为清醒,也证明了我的“马尿”之说。但过了不久,我就醉了,且醉得晕晕乎乎,还在教室里吐得满地都是。于是便趴在教室里的桌子上睡着了。按说这是学校里一次非常恶劣的事件,但我记得当时的女老师到教室里来上课,闻到教室里的酒气,走到我的旁边,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并未责怪,对旁边的同学说,让他睡吧。下课后,我在教室里睡到傍晚,才酒醒了,但我记得同学们并未再议论此事,而是将我护送回学校附近租住的宿舍。此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从此不再饮酒,而对于啤酒,也有了认识,它并不是乡人所说的“马尿”。
我的另一次记忆深刻的醉酒,则是刚刚工作时的事情了。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太行山下的一个单位,工作很不如意,心境颇是懊丧。有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辈到我所在单位来代职,他偶然看了我的一篇文章,确系为我所作之后,将我调到了一个认为可能合适的地方。那个职位其实我并不喜欢,再三衡量,还是同意了。他还常到我的办公室来聊天,说说大学读书的往事,也说说文学上的事情。有次,他竟在一本受众面不太大的刊物上读到我的文章,那本杂志也是有意思,刊出了文章,还在文章末尾留了作者地址,这位前辈看了文章,说他感觉很熟悉,读到末尾的地址,才认定一定是我的文章。于是专门找我来谈这篇文章,流露着兴奋,但又说那文章有着迷茫的伤感,似不必要的。我听了很是感动,真有他乡遇知己的感受。不久,前辈代职结束,要返回了。我们为他送行,自然是要喝酒的。从不饮酒的我,那天也数次向这位前辈敬酒,结果酒席还没结束,我就完全醉了,且醉得不省人事。后来,同事们将我送回了宿舍。半夜醒来,头疼欲裂,人像飘浮在半空中一样,半真半幻之中,想起只身他乡的际遇,真是无限惆怅。
后来去京城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又回到过去的单位,但早已物是人非。我之从不饮酒亦不擅酒,已成众人皆知的事情了。每每有酒场,我都以茶代酒,不熟悉的人若劝酒,也有同事立即救场解释,才得以逃脱。而我也是最不喜欢所谓的酒场文化的。但终于发生了一件不快的事情。有次,有位主事者的好友来讲课,自然要请酒的,我作为具体承办者,除了张罗喝酒,还要陪酒。但我实在不乐意在这样的场合表达感情,于是便起身向这位来讲课的人敬了一小杯酒,结果主事者很不高兴,马上要求我必须喝下一大杯酒,我立即反对,表示自己不擅此事,他脸露愠色,结果自己喝掉了一大杯。这件事情之后,有同事提醒我,其实是这位主事者为我解了难堪。如此逢场作戏,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令我对所谓的酒场,更是嗤之以鼻,乃是能躲就躲。还有次,我陪另一位上峰去视察一个单位,结果这位喝得兴起,要求在场的一位优雅女士饮酒,没想到女士推辞不过,竟与其斗酒并豪饮了起来,场面一时更为热闹。后来那位上峰也醉了,而女士竟然无事,我心中颇有些五味杂陈,既为这位女中豪杰叫好,又隐隐有种特别的难过。
在我看来,饮酒恐会失态,进而失礼。故而酒场酒事,常让我感到惶恐。有次到文虎师家中,谈到其中苦闷,老师将这些人斥之为酒囊饭袋,完全没有必要理会。文虎师曾是文学编辑,后来从政多年,宦海三十余年,余时他却痴心学问。文虎师从不饮酒,更显其特立独行。我十分好奇他何以能在如此环境下生存下来,偶尔谈起此事,他说自己不善饮,无论是什么人在场,乃是绝对不会喝上一杯的,后来所有人都知道了,他是绝不饮酒的。而他对于那些用公款狂喝滥饮者,乃是极为反感的。他的这种态度,是一种自好的坚守,更是一种坚定的自信。在我的印象中,亦见过他饮酒,虽然也都是浅尝辄止。一次是他的首位博士生开题,邀请了京城的几位学者,也都是多年好友。中午,在魏公村的刘家香饭店设宴。那天特意准备了茅台酒,我记得他是喝过几杯的,或许这事情他看得很重,便破例喝了几杯。还有几次,乃是在他退休之后了。我们几位学生偶尔相约聚会,他总带好酒来,但自己却是不饮的。有年春节,我也准备了好酒,便请他饮一杯,或许是我屡屡相劝,拗不过我的诚意,他便喝了很少的一点。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事后我却颇为自责。
虽然我对酒场退避三舍,但不知何时,也能略略饮上几杯,有时是独自遣兴,有时则是借酒消愁。若是二三知己,乘兴对饮,倾谈心曲,则堪为雅事矣。妻子Min也能饮,酒量却在我之上,但她只饮啤酒,从不喝白酒。记得我回京城工作,她也辗转一圈重回旧地,我们终于再次团聚。那天中午,同事们请酒,喝的是一坛花雕老酒,这本是很温和的酒。但或许是兴致很好,我们几人竟然将一大坛的花雕全部喝掉了,Min也是乘兴喝了不少,结果那天中午,她就大醉了,导致新上班的第一天,便请了假。有段时间,每到周末,我们做几个小菜,她喝啤酒,我则小酌几杯白酒,也是其乐融融。有次,我和Min一起到郊外青龙湖春游,赏景之余,便将带来的啤酒一人一罐,享受着湖景与微风,对饮了起来,忽然感觉啤酒也有种难得的美妙,且饮后有种微醺的爽快。从此之后,我也开始喝点啤酒,且亦能感受到啤酒的滋味。有种黑啤,价格很便宜,但尤为我们所喜。Min的酒量是远高于我的。几年前,我和她到青岛一游,我们早就知道青岛啤酒是出名的,自然去之前,就想好了喝上几杯。到青岛的当天中午,喝了几杯,晚上是友人接风,也许是兴致太高,那晚几位文友频频相敬,我和Min都喝醉了。现在想来,真是太难为情。
过去酒风盛行,令我苦不堪言,后来一道命令,工作日不得饮酒。我并不贪杯,有时却很想独自饮上一杯,想想禁令在前,也就作罢了。这些对我倒是不算一件过于难受的事情,只是不知那些此前贪杯的同事们,究竟是如何解决难题的。某年上海书展,我初见苏州的王稼句先生,早闻其交游遍天下,果然顿顿有酒,次次有醉。不由感叹,稼句先生真是文苑酒中仙也。去年冬天,稼句先生来京,到西单图书大厦举办由他编选的《北平往事》发布会,并约见几位友人。抵京的那天晚上,书友设宴,稼句好酒,我却只能以茶代酒,颇为遗憾。后来发短信给他,表示歉意,他说暇时来苏州,茶酒两便。稼句先生潇洒风神,望尘莫及矣。其实,对于限酒之事,我本是心中叫好的,不过倒是由此又想起一桩往事来。某年,我在过去工作的一个学校,当时正在调动,有次被安排陪一位上司去看望正在郊县训练的学员,我问他带点什么慰问品,答复带酒吧。于是买了一卡车的燕京啤酒,到了那里,当场宣布午饭加餐,每人两罐啤酒,现场欢呼声一片。回程路上,我和他都有些醉意,于是敞开心扉,谈古说今,针砭时弊,如在昨昔矣。
2024年6月30日
【作者简介】朱航满,1979年生,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文集 《书与画像》《读抄》《立春随笔》《杖藜集》《雨窗书话》等。编选《中国随笔年选》(2012—2020),策划并主编“松下文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