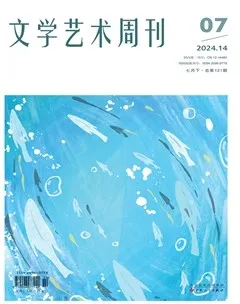网络数字时代的艺术与复制技术的关系探究
一、“复制”的含义及时代演变
究其本源,“复制”是十分复杂的概念,英文中,duplicate、copy、imitate、simulate等单词都具有“复制”的含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复制的含义往往被理解为“模仿”。“复制”的概念即便在古代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于艺术而言。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中就提出过著名的模仿论,而艺术正是作为一种模仿的技艺而存在的,被称为“模仿的模仿”。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其老师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比真实世界更为真实,因为其把握了事物的内在本质与规律。
复制是人类艺术发展和延续的重要技术手段,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承方式,经历了手工复制、机械复制再到今天的数字复制三个阶段。古代复制技术虽然十分落后,但这种临摹与模仿对文化发展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相较于之后的机械复制以及数字复制,制作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在原作的基础上创造了作品,还通过亲身参与真正学习了创作手段及方法,使得 其融入之后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当中。例如我们熟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艺术,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征,古罗马的雕塑受古希腊影响很 大,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雕塑造型上,还在于古罗马人对古希腊雕塑的模仿与复制,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量古希腊时期的雕塑作品,实际上是古罗马人的复制品,米隆的《掷铁饼者》、波利克利特斯的《持矛者》等,都是古希腊雕塑经典作品。古罗马人通过对古希腊作品的复制,在学习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雕塑作品,如果说古希腊人的雕塑着重呈现人体的理想美,那么古罗马人则在这种风格的基础上,着重表现真实而有个性的人。
但是,传统的“复制”作为技术的定义实质上并未改变,它转变和发展了自己的形态,但并未改变自己的本质,即作为一种技艺而存在。
二、从传统复制到机械复制的流变
“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总是可复制的,人所制作的东西总是可被仿造的。学生们在艺术实践中进行仿制,大师们为传播他们的作品而从事复制,最终甚至还由追求盈利的第三种人造出复制品来。”这段文字是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机械复制”一章的开头。本雅明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复制的发展及定义,艺术的产生及发展在本雅明看来总是与复制相伴,同时复制的过程是不断发展的,这在本雅明看来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在历史进程中断断续续地被接受,且要间隔一段时间才有一些创新,但一次比一次强烈”。本雅明认为复制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并且总是带来十分深刻的影响,而机械复制无疑是复制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尤为重要的转折点。19世纪,法国人达盖尔首次成功发明了实用摄影术,这无疑给艺术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这种表面的写实并不是艺术的本质所追求的,转而追求艺术的表现力及事物在心中留下的“印象”,因而印象派诞生了。摄影术的影响除了加速了艺术的转型之外,还使其自身成为艺术门类之一,并且意义深远。这也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理论所要强调的一点,摄影术首先经历的是与艺术的紧密融合。
正是由于时代的机遇以及艺术发展的转变,复制在某种程度上真正被大众所正视和接受。人们需要复制性的内容获得知识,而对于创作者而言,也急切需要大量复制以获得广泛传播,因此在这个时代,复制的定义及地位已经逐渐改变了。复制不仅成为流行、成功、消费的代名词,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它的实质性的改变正是源于创作者和消费者的狂热。对于艺术而言,复制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作为一种令人避讳的技艺,相反,它已然成为20世纪大众消费艺术的主要创作手段,例如著名的波普艺术家理查德 ·汉密尔顿、安迪 ·沃霍尔的许多代表作品就展现了这种流行性和可复制性。例如理查德 ·汉密尔顿的作品《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魅力?》,艺术家运用当时大量流行的广泛复制的海报进行拼贴,反思并体现了时代的流行因素;而安迪·沃霍尔则更是将这种可复制性发挥到了极致,对流行形象和商品进行大量的复制是安迪 ·沃霍尔一贯的创作手法。
复制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法经历了19—20世纪的发展演变,这种以复制为特征的艺术创作手法集中体现了“拿来主义”的特征,达达艺术的拼贴手法、工艺和装置艺术对物体的挪用(以杜尚《泉》为代表),以及波普艺术,都体现了这种特征,这种特征又让我们自然地 联想到本雅明书中所探讨的摄影术、电影艺术,对于事物瞬间的截取和选取,对影视演员瞬间动作的捕捉,其目的都在于复制事物的瞬间,从而为其所用。这种特征及上述艺术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正是本雅明机械复制理论中“光晕的消逝”所引起的现象,艺术通过大量机械复制而走向大众。在这个过程中,艺术 作品的本真性、唯一性正不断流失,而复制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使得传统的艺术原则被打破,无疑加深了流失的速度。因此,本雅明所处的时代以及理论对于接下来所要探讨的网络复制艺术是十分重要的,它为接下来复制技术 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光晕”的彻底丧失埋下了伏笔。
三、从机械复制到网络数字复制
机械复制时代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和改变,对于艺术而言,机械艺术的可复制性为数字复制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主要有两点,一是机械复制时代对观众和艺术家而言最大的改变莫过于本雅明所强调的艺术的“光晕”的消失,艺术的唯一性、本真性的消失,为数字艺术和大量的数字交互埋下了伏笔,并且从过去强调模仿中的现实性,转向在虚拟空间中对心理的预示;二是机械复制的复制规模和手段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对具体的模仿对象而言,依然存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的阻碍,这为数字复制沉浸式体验、交互式体验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能。
相较于机械复制,数字复制在当下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特性,并且衍生出了许多新的特征。比如复制方式的转变,除了媒介的转变之外,复制的形式也发生了转变,成为拟像的形式。拟像也称“类像”,是法国著名哲学家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拟像是指通过对现实或原本的模拟复制而产生的没有本源、没有所指之像,它不再与任何客观实在产生联系,它即它自身的纯粹拟像。拟像的产生源于大量的数字复制,通过复制把自己置换为客观世界的替代者和存在者。
通过与机械复制的对比以及对其实际特征的考证,笔者认为大体可以将数字复制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数字复制在数量、规模上的改变以及传播媒介的改变。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网络时代,对于图像、信息复制的规模是过去无法比拟的,我们可以下载和浏览各种软件、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的内容,媒介传播途径也从过去的书籍报刊转变为网络,大幅提升了音视频、图像和文本信息的传播效率。
第二个特征是数字复制技术使艺术作品与观者的距离发生改变。这个过程是从凝视到刺入,再到嵌入的过程,这个说法来源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的比喻,本雅明在画家与摄影师的章节中,比较分析了传统画家与摄影师的区别,传统画家的作品由于具有“光晕”,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具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这种说不清但又神秘的力量被本雅明概括为一种凝视关系,它是有距离且带有崇拜的。摄影术正如外科医生那般,用科学理性的机械器具“刺入”对象,这个比喻生动地概括了当下数字艺术的现状,也精练地表达了数字复制的特征。网络数字艺术的创作不再需要依赖传统的绘画用具,由于技术的发展,平板电脑和台式电脑上的绘画用具越来越接近传统绘画用具的模式和手感。同样的,通过新形式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转变为各种图像格式,这些图像在网络上最终转化为数据被复制于各种领域,不再被局限在画布上。但这还不足以体现其可复制的特征,这些作品在艺术家之间分享的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互 动作用,原因在于作品不仅只属于第一作者,这些作品无论是否是第一次被复制,本质是可被复制粘贴的代码,而这些一模一样的代码被无限次地复制的过程中,作品的原真性已经彻底消失了,对于唯一作者的含义也在不断的复制当中被忽视了。不仅如此,接收者还能够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新的作品,他 们可以运用电脑绘图软件按照自己的喜好对原有作品进行修改,这正体现了交互性的特征。我们可以充分与作品进行互动,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复制。
第三个特征是数字复制使得重塑时间与空间的连接成为可能,并由此生成了虚拟空间,消弭了观者与对象之间的屏障,营造出一个“虚拟的剧场”。正如前文所言,数字复制不仅产生了新的规模和特征,而且还克服了过去存在的局限,这一局限的突破就在于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数字复制与机械复制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一点就在于机械复制需要一个拍摄的对象,并且这个对象通常是连续而唯一的,而数字复 制(如拟像复制),不需要依赖客观对象,且复制对象也并不唯一,因此数字复制完全可以参照现实中的诸多对象,iRccPmg8wKY/Fh/J1m7DyZRis4725vCbsyj5xDd+0Bc=来创造一个新的形象和空间。如“数字敦煌”通过拍摄大量石窟形成一个整体的数据库,并通过技术手段生成一个虚拟的三维全景导览空间,游客可以按照指示任意穿梭于洞窟之间,形成一种“虚拟的游览”。本雅明在书中还详细探讨了电影艺术的特点,以电影演员的视角来说,电影艺术的观看者从过去的剧场观众变为导演和摄影机,电影的接收者不是观众,而是摄影机,这在对演员的审美要求上与过去是有差异的。在电影放映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电影演员不同于戏剧演员,从整体上来看,还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在时间上,戏剧演员与观众是同时存在的,在空间上也是互相 交融的,是能够产生互动的。但反观电影,由于隔着摄影机,演员与观众是有空间距离的,并且这种距离还带有时间上的迟滞,因为电影是电影演员在完成拍摄之后剪辑而成的影像记录。这种时间与空间的隔阂,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否被克服呢?答案是肯定的,数字复制时代的诸多媒介之中,网络直播正是时间与空间隔 阂的突破口,因为在网络直播中,表演对象能够即时与观众产生交互,并且网络直播传播广 泛,它使得空间上的物理间隔得以消解,演员与观众在充分形成互动关系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虚拟的剧场舞台”。
第四个特征是数字复制技术使受众对艺术作品的现实性和唯一性的关注,转向对个人情感体验、私人占有欲和虚拟体验的关注,加速了艺术作品“光晕”的消逝。我们逐渐不再关注艺术的原真性,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复制的图像,也是在复制的过程当中不断进行修改的图像,我们思考更多的是图像能带给我们什么,是否有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能否在这些图像当中插入个性元素,这等于变相宣示自身对这幅图像的所有权。人们外出旅游 时习惯性地拍摄图片并分享到朋友圈,这种行 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个人的分享欲和消遣, 而不在于传播图片信息。
数字复制技术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巨大的 改变,也解决了本雅明在分析机械复制艺术时 提出的一些问题,但数字复制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绝对美好的,它的发展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给接收者带来的审美方式上的改变以及作品本真性的流逝等问题。通过对于复制发展历 史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复制的变化过程,从过去作为一门技术、一种创作手段,再到今天数字复制技术改变了我们对于事物和世界的理解。数字复制是当下艺术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其特征的把握,往往需要借助一个具体的对象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复制为线索,通过与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相关理论的比较,让我们能更加具体且准确地把握当下数字复制的形势变化。数字复制的时代充满变化,需要我们以更加客观谨慎的态度去看待数字复制技术的发展。
基金项目:2023 年度重庆市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人工智能对摄影艺术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3YB04。
[作者简介]丁昶煜,男,仡佬族,贵州贵阳人,四川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美术学(美术史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