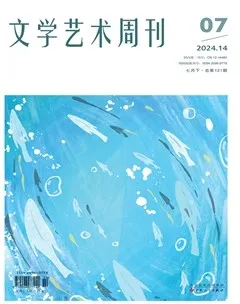《周恩来回延安》中的蒙太奇技巧分析
一、电影艺术的发展研究
电影诞生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光影成像。1829年6月,“电影的祖父”约瑟夫 ·普拉托于提出了著名的“视觉滞留原理”,也被称为“视觉滞留效应”,指的是人的肉眼所看到的影像在其消失后,仍然会在人的大脑中停留1/24秒的时间,如以大于24帧每秒的速度快速播放单个的画面,会给人造成一种画面连续运动的视觉效果,依托这个原理便形成了动 态的电影。
1894年,爱迪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影 播放机器,这意味着电影在技术上逐步走向了成熟。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咖啡馆公开放映了《火车进站》《婴 儿的午餐》等一系列纪录短片,这是电影第一次以动态画面的形式出现在大屏幕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电影艺术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1896年,乔治 ·梅里爱拍摄了《恐怖的一夜》等一系列具有较长篇幅,同时影片内容有一定的情节设计的电影。1915年,大卫 ·格里菲斯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故事片《一个国家的诞生》,从此时起,电影艺术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娱乐属性,成为人类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
电影是一门艺术,它用有限的时空做无限的表达。电影是集视觉和听觉因素为一体的一门综合性艺术创造活动,对电影的理解是一个基于已有的知识储备的审美感受开展的再创造过程,因此电影被制作出来仅仅是电影艺术的第一步,电影本身不具有意义,随着时代的更 迭、环境的变化以及观影主体的不同,受众对于影片的多样理解赋予了它真正的意义。
二、蒙太奇的概念研究
“蒙太奇”一词源自于意大利建筑学术语,其原意有“组接”“排列组合”之意,而后在电影学中发展为一种剪辑的逻辑思维,大意是创作者通过把单个的画面素材排列组接,达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某种叙事或抒情表意的目的,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电影学中,蒙太奇可划分为两大类,叙事蒙太奇和象征蒙太奇,叙事蒙太奇通过镜头的建构完成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倒叙或插叙都需要通过镜头与镜头的衔接逻辑来完成;象征蒙太奇则承担了烘托主题、教育警示、象征隐喻的功能。
电影又被称为“蒙太奇的艺术”,影片通过蒙太奇调度所有视觉元素与非视觉元素,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电影中的视觉元素。
三、《周恩来回延安》的蒙太奇技巧分析
《周恩来回延安》是2019年上映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影片背景为 1973年,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再次回到延安,回忆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革命战争的艰辛历史,提醒人们要时刻铭记在延安发生的这一段光荣的革命奋斗史,以及为中国革命英勇奉献的延安人民的故事。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周恩来回延安》等一系列红色电影的上映,呼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背景,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一)镜头是“电影用来书写艺术的语言”
单个的电影镜头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将影片的客观视觉元素与自身观看的直观感受联系起来,共同形成对影片内容的理解,就像是阅读一样,镜头画面就是作品的“文字”。创作者的叙事思维通过镜头的运动方式、角度、景别等一系列蒙太奇技巧得到体现,所有的表达方式相互作用、相互支撑,最终形成电影,从而实现电影在叙事与表意上的统一性,如果用写作来比喻电影创作,那么镜头就是创作者的“笔触”。
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方位关系就是影片中拍摄镜头的运动方式,可划分为推、拉、摇、移、跟、升、降、甩、固定等运动方式。影片节奏和画面布局依赖于镜头拍摄时所使用的拍摄方式,受众与创作者也通过电影镜头这个纽带传达情感和价值共识。例如纪录片经常运用“一镜到底”的方式营造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悬疑片经常用快速的镜头剪辑和频繁的镜 头切换塑造紧张感。在电影中,镜头的拍摄角度也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场面调度方式,在刻画人物形象时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刻画伟人时,通常用仰角拍摄,塑造出人物伟岸、被人仰视的人物形象;刻画负面人物形象时,通常用近景俯拍,刻画出丑恶的小丑形象。
1.拍摄角度的运用
在创作电影的过程中,创作者对所有视觉元素进行合理布局,场面调度不仅仅包含对拍摄者的调度,也包含了对被拍摄者也就是电影中人物角色的调度,拍摄角度和拍摄方法的变换隐含了创作者想要传达的创作初衷。但与写作有所不同的是,叙述者的角度在电影中并不 仅仅体现为讲故事的口吻和人称变化。我们在分析电影时强调的视角常常是指摄像机的方位与被拍摄者的方位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客观的而非抽象的位置布局,即正、侧、背、平、俯、仰六种拍摄角度。
拍摄者位于摄像机正面的拍摄角度会塑造出严肃、庄重之感,将被拍摄者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将被拍摄者的整体状态和特征完全地展现出来。侧面角度拍摄时,被拍摄者位于拍摄者的正侧面,这样的角度能够将被拍摄者的肢体语言展现出来,通过表现被拍摄者的整体状态,将当下人物角色的情绪外放出来感染观众,这是能够让受众理解角色情绪变化从而产生共鸣的一种方式,其能将人物情感外化为角色行为,同时又能够清楚交代被拍摄者所处的环境。这里的叙事不直接表现为台词叙述,甚至可以通过角色的动作、神态细节为推动剧情发展奠定基础。与正面拍摄不同的是,它无法及时捕捉被拍摄者细微的表情与神态变化,只能够通过人物动作的外化去分析人物情绪,这需要受众投入充分的精力,还需要受众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单一的拍摄角度并不能承担叙事或表意的功能,同一事物的表达可能同时需要不同拍摄角度的相互配合、相互印证。背面角度的拍摄可以塑造神秘的人物形象,也可作为叙述主体把受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事件本身上去,不被过多的拍摄技巧所干扰。因为背面拍摄时,被拍摄者并不直面受众的审 视,该拍摄角度不仅使影片调动了受众的窥探欲,同时还使电影画面具有了神秘感,受众的情绪和思路充分受影片内容主导。因此角度的组合使用能够达到充分的叙事与表意目的。平角拍摄时,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处于同一高度,这样的拍摄角度在使受众与人物角色的交流更加平等、冷静、客观,同时还能够打通受众与人物角色之间的那堵墙,让受众与人物站在同一角度、同一维度去思考和审视问题。仰角拍摄时,由于拍摄者一直低于被拍摄者,使被拍摄者占据画面的大部分比例,这样的构图能够使画面更加有层次感,主次分明,繁而不杂。仰角拍摄需要拍摄者有一定的审美修养和丰富的拍摄经验,被拍摄主体的呈现比例和仰角的大小关乎镜头美感,同时还需要引导观众捕捉镜头重点。例如用仰角拍摄建筑物能够烘托出雄伟、压迫、不容置疑的影片氛围;用仰角拍摄人物则可以塑造出伟岸、高大、强势的人物形象。俯角拍摄指被拍摄者低于拍摄者,人物视角呈向下俯视的姿态,俯角拍摄涵括的视野范围很广,一般情况下用来交代故事背景环境,例如在战争片中,常常用来拍摄两军交战的宏大场面。
2.景别在人物塑造中的运用
电影叙事景别和剪辑思维的变化决定了电影叙事节奏的快慢。景别指的是被拍摄者在画面中占据比例的大小,摄像机与被拍摄者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被拍摄者在电影画面中占据比例的大小。景别的划分标准是成年人的身高,根据成年人的身高在画面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可以划分为五种,分别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影片中景别的变化不仅影响叙事节奏的快慢、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受众对影片内容的理解,还直观地影响受众观看范围的大小。
《周恩来回延安》中38分22秒至39分35秒这一片段,特写镜头和近景镜头出现的次数较多,景别的节奏变化也很慢,对人物的刻画多以正面的近景拍摄为主,把人物情绪和感情的变化充分展现在银幕上,刻画出一个心系人民的总理形象。这一片段主要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革命老区,在这里摆宴席请父老乡亲吃饭,但是乡亲们在饭桌上表述自己不习惯坐在凳子上吃饭,想蹲在地上吃,周恩来总理同意了乡亲们的请求,并脱下外套也端着饭碗陪着乡亲们蹲在地上吃饭,周恩来总理凝视着乡亲们吃得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眼里闪动着泪花,陷入沉思。
该电影片段通过对拍摄镜头的调度来完成对影片主题的强调以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把 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细腻的情感氛围里,再加上背景音乐的烘托以及受众本身对影片时代背景的了解,进而实现对主流价值观念的传达。
(二)画面造型技巧
光线也是蒙太奇手法中重要的视觉元素,影片在拍摄过程中需要通过光线来表现场景的变化、岁月的变迁以及人物命运的隐喻。拍摄者往往需要通过取光或补光,来实现对光线的利用,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例如王家卫的电影,就通过对光线的调度和特殊处理形成其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补光原本最大的作用是补充由于成像和设备问题导致的光线不足,但引 申在电影美学中,光线常常被用来呼应影片主题和构建情感基调,同时这样的表现手法能够引发观众的剖析,这时候光线就具有了一定的美学价值。光线在影片中具有表意的功能,从不同角度补光能够造成不一样的画面观感,光线的明暗对比也具有象征意义,对刻画人物、表达人物情绪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影片《周恩来回延安》以暗调的光线为影片的基调,高调光和明度较大的光出现得较少。这样的光线调度是创作者为了实现对影片主题的呼应而对光线做出的处理,这样的光线运用不仅能够凸显影片的风格,还能够奠定影片的调性,让受众更准确地把握影片的思想内涵。当影调光线偏低时,整个影片给人以沉重、压抑、严肃的感受,这种影调多用在题材沉重、主题严肃的影片中。《周恩来回延安》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为了凸显革命和历史的厚重感,全片的基调以暗调为主,不仅凸显了影片的“革命”主题,也是为了缅怀周恩来总理。
光线不仅能够勾勒影片氛围,还能剖析人物心理,例如影片中已经生病的周恩来总理再次回到延安,经过一路的跋涉身体已经不堪重负、疲惫不堪,但周恩来总理不想让大EmETYlrHaopeamWokutMCw==家知晓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他勉强支撑摇晃的身体和乡亲们握手说话。镜头转到房间里,周恩来总理独自瘫坐在椅子上,这里影片为了强调此时此刻周恩来总理艰难的身体状况和他复杂的心理状态,用了一束强烈的正面光突出周恩来总理的位置和状态,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明暗对比强烈的光影镜头里只有人物的“明”与周围环境的“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个镜头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意味着人物正处于一个无奈的处境,人物即将被黑暗吞噬,此时此刻人物平静地坐在椅子上,没有做任何的挣扎逃避,而是静静地等待黑暗的到来,隐喻了影片人物的处境,运用了象征蒙太奇的手法。这里的光影调度与影片主题紧密贴合,不仅交代了剧情发展的理由,还通过对光影的艺术处理实现了抽象的表意功能。
《周恩来回延安》通过对不同光线的使用完成了对画面造型的设置,光线成为营造影片氛围的手段,通过这样的表达调动受众的情绪,使之产生对影片内容的共鸣。通过光线的明暗对比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出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为后续故事情节的发生奠定基础。
四、结语
电影艺术是一种调动视觉和知觉感受的综合性艺术,也被称为第七艺术,它的叙事和表意主要通过蒙太奇手法来完成。蒙太奇手法通过对单个影片素材的选择,实现对影片主要内容的强调,次要内容则成为表达影片主题的辅助手段;它通过对镜头的组接,引导受众关注影片想要表达的主题,以达到教育和心理疏导的目的;蒙太奇手法还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例如其在历史题材影片中的运用,能够让受众站在当下去审视历史问题或事件,实现了对时空的再造。
[作者简介]刘洪琴,女,汉族,陕西安康人,西北政法大学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