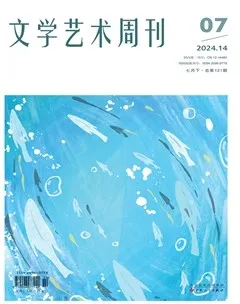建安文学神女辞赋论
东汉建安时期(196—220)是人神之恋母题创作的兴盛时期,神女辞赋寄寓着建安文人的文化观念和人格理想。高雅神女内外兼修、礼情兼备,象征着士人的高洁品格,折射出乱世文人的生命意识;艳情神女热情妩媚、放荡不羁,走向世俗化分支。远古的神话色彩、建安时期的文化观、邺下文人的集体创作是建安 神女辞赋走向鼎盛的重要原因。后人继承了建安神女的形象特质,并发扬出天地之道、世俗艳女、政治隐喻等多种意蕴,逐渐开辟出“江畔遇神”的东方浪漫史。
一、建安神女基本特征及文化内涵
建安文学创造的神女形象主要有两种类型,即高雅化的神女与艳情化的神女,两类神女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形象气质,并分别朝着理想化和世俗化的不同方向发展。
(一)高雅化的神女
建安时期的神女既非先前纯粹作为道德象征的神女,又非放荡不羁的凡俗女子,而是兼有神女之高洁与凡女之真情,神光离合、动人可亲,呈现出一种“爱在神人之间”的浑然天成之美,不断向理想化、高雅化发展。
建安文人汲取诗骚精华,以绮丽华辞塑造出惊为天人的神女形象。《诗经》开美人描写先声,《卫风 ·硕人》[1] 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建安文人继承其强调自然之美的审美传统,对神女的“巧笑”“美目”“皓齿”“玉颈”等方面加以描摹,并多以柔荑等自然景物为喻。应玚《正情赋》有“拢娥眉以掩目兮,启皓齿而含唇。琢白玉以立颈兮,翻墨浪而随风。举素手以摄衣兮,指纤纤如柔荑”[2]。此外建安神女赋与楚辞传统一脉相承。宋玉《神女赋》: “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3] 曹植《洛神赋》亦有“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4] 之语。
建安神女继承了诗骚传统,寄托着文人的高洁精神,表现出“重礼”的道德追求。《诗经》中的神女已步入“礼”的自觉时代,具备道德象征意义,《毛诗序》中有“《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楚辞 中的神女面对君王始终以礼自持,“怀贞亮之洁清”“薄怒以自持”(宋玉《神女赋》) 。神女作为礼教道德的象征得到升华,不仅身具温雅贤淑之美,而且彰显出情操高尚的神性光辉,“体兰茂而琼洁”(应玚《正情赋》),“志高尚乎贞姜”(阮瑀《止欲赋》)。
建安神女赋不仅“重礼”,更奏响了“言情”的新声。建安文人将神女面对人神殊途的“以礼自持”发展为“发情止义”,读来有缠绵悱恻、柔肠百转之感。如曹植的《洛神赋》描写洛神受真情感动而渴望与君王长相厮守,“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人神殊途无奈诀别时“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相比于宋玉《神女赋》史官颂述的体式,《洛神赋》在自陈体式中更加突出了个人情感,达到了心神相通、感发动人的境界。
建安神女融合了汉女之“礼”及高唐之“情”,实现了对诗骚传统文化基因的改造和发扬,塑造出华夏文明史上经典的美神形象。《洛神赋》开篇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洛水与汉水处于同一流域,洛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汉江游女在后世的变体,此为承诗三百之先风。曹植数次易藩、辗转南北,“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曹植《杂诗七首》),笔下神女亦兼采楚辞灵感,调动巫山神女的传说,融入高扬的浪漫情感与沧桑 的身世之慨,用尽了奇高骨气和华茂词笔,塑造出集诗骚之美于一身的洛神。“感《汉广》兮羡游女,扬《激楚》兮咏湘娥。”(曹植《九咏》) 曹植“把两个典故并列起来,创制出‘巫山洛浦’或‘巫山洛水’这样以地喻人的双重换喻,用来夸饰和描绘一种无以复加的女性美”[1]。后人创作神女辞赋时亦常兼备汉水游女与云梦神女之美。如“陪湘妃于雕辂,列汉女以后乘。”(陆机《感逝》) 建安之后,诗之游女与骚之神女万流合一,成为美善之至的化身。
(二)高雅神女的文化内涵
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和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神女形象也表现出建安时代的独特文化内涵。
首先,建安神女的缥缈无踪寄寓着文人对理想境界求而不得的现实感怀。“灵若道言,贻尔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蹰。”[2](曹丕《秋胡行》)文人欲以兰英、桂枝遥寄佳人,而神女缥缈无踪,文人只好徘徊踟蹰、苦苦等待,隐含了曹丕对于前路未卜的隐忧,流露出“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曹丕《杂诗 ·漫漫秋夜长》)的无奈。《正情赋》有“昼彷徨于路侧,宵耿耿而达晨”;《止欲赋》有“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纵使文人苦苦 追求,神女依旧可望而不可即,空留哀伤怅惘。
其次,神女幻梦象征着文人渴望摆脱现实的自我救赎。曹植朝觐京师而归,伤感于同根相煎,又对遥不可及的帝王幻梦心存眷恋,途经洛水之时,通过辞赋发泄内心郁结,彷徨之中洛神悄然而至。“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曹植《洛神赋》),表面是表达对洛神爱而不得的感伤,隐含的却是人生抱负化为泡影的怅然。无常的命运使他与洛神只能隔川相望,而少时的凌云壮志也如洛神般湮灭无踪,纵然心怀“长寄心于君王”的眷恋、“怅神宵而蔽光”的愤懑,也只能化作“揽马非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的悠悠长恨。
再次,建安神女是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缩影,承载着知识分子对文艺修养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士人独立高洁的品格,寓于香草美人的意象之中。建安神女常常表现出飘逸若神、灵 动翩然的仪态美,象征着建安文人浪漫不羁的自由精神和心中追寻的理想归宿。建安时期是久经动乱而将治未治的年代,士人多怀有昂扬振奋的热情,普遍追求治世太平的宏伟政治理想;在思想解放、文学觉醒的影响下,建安时 期的文人士子既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意识,又呈现出浪漫不羁、向往自由的崭新精神风貌。王粲《杂诗》有“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渚间”,表达了作者渴望如神女一般逍遥自在、摆脱世俗尘埃的侵染;曹植《洛神赋》将洛神用“惊鸿”与“游龙”来形容,又如蔽月轻云、流风回雪一般漫舞游弋,寄托着曹植现实中的苦闷心境,希望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在理想国度,不受羁勒地实现人生抱负。
从次,建安神女困于神人之间,进退两难,充满着“将飞未翔”的悲剧色彩。神女翩然翱翔,体现其悠然自在的神性,又受到世俗礼教的牵绊,且怀有对人间的深刻眷恋,无法不受羁勒地飞向理想的云端。曹植《洛神赋》中的神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欲翔而不得,呈现出努力冲破尘网束缚的情态,象征着曹植现实理想的破灭和他欲翱翔而不得的心境。尽管如此,灵动飞翔的神女仍是建安文学浪漫精神的典型体现,彰显出亘古不衰的鲜活生命精神。
最后,神女形象折射出建安文人感逝忧生的生命意识。建安文人身处战乱时代,多有忧生之嗟,反映在辞赋中,尽管神女不愿屈心抑志、随波逐流,却仍流露出对韶华易逝的感伤。如应玚《正情赋》云:“君之来兮何其迟,日将夕兮华色衰。”神女感伤于年华将逝,带有文人士子怀才不遇的心理投射。曹植《杂诗七首》云: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诗句塑造了色若朱丹、志向高洁却遭构陷的神女形象,折射出对浮云蔽日的幽怨和孤芳自赏的寂寞,是壮志难酬的建安士人的真情流露。
(三)艳情化的神女
与高雅化的神女不同,建安文学中的另一类神女呈现出热情妩媚、放荡不羁的特点,是世俗化的分支。在建安七子同题的《神女赋》中,艳情化的神女继承了高唐神话“愿荐枕席”的情节。“顺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辞。”(陈琳《神女赋》)“探怀授心,发露幽情。”(王粲《神女赋》)“微讽说而宣谕,色欢怿而我从。”[1](杨修《神女赋》)神女超越礼教、心神荡漾, 即使篇末保留“欢情未接,将辞而去”(宋玉《神女赋》)的传统,却是曲终奏雅,为文造情。此类神女辞赋丧失了诗骚传统中的文化理想这类有深度内容,因此湮灭了光芒。总而言之,美神既是根植于文人心中永生不灭的,又是不可求思的,作为理想中美神形象的神女也在建安时期完成定型。
二、建安神女辞赋的创作渊源与时代成因
(一)神女母题的远古魅力
神女是以流水为代表的自然力的人格化象征,是自然之道的化身,“惟天地之普化,何产气之淑真。陶阴阳之休液,育夭丽之神人”(王粲《神女赋》) 。一方面,先民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尚且有限,受到人定胜天传统思想的影响,倾向于选择带有征服色彩的 “男人-女神”创作模式,表面是对文人与神女婚恋历程的描摹,实质为人与自然之相和相 争;另一方面,变幻莫测的自然使人感到由衷的崇敬与恐惧,天道无常为文人对神女的追求笼罩上一层悲剧色彩,最终呈现为“人神道殊”的凄凉结局,隐喻着古人与自然依存又对立的 辩证关系。
神女寄托着古人带有原始巫觋色彩的祖先崇拜,楚国因多山川河泽、云气缭绕而盛行巫风祭祀,宋玉《高唐赋》中有“进纯牺,祷璇 室,醮诸神,礼太一”;《墨子 ·明鬼》有“燕之有祖,当齐之社樱,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1] 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指出,高唐神女有可能就是涂山氏,代表着古人对繁衍的重视。这与上巳节水畔幽会的传统类似,后代将对女性始祖的崇拜延伸为原始的生殖崇拜,早期以婚恋为中心的神女辞赋创作便应运而生了。
神女作为亘古不灭的江河之人格化身,常常成为朝代兴衰的见证者,寄寓着士人四海清平的家国理想。《华阳国志 ·汉中志》云:“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2] 汉水乃汉家兴盛之地,因而被视作天赐灵水,而求得汉水神女也成了君王承天受命、开辟盛世的象征,宋玉《高唐赋》有“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延年益寿千万岁”。后代君主也保留着祭水仪式, 给古时“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国风 ·蒹葭》)的浪漫歌咏注入了求贤纳士的时代内涵,神女寄寓着建安文人兼济天下的愿景,象征着他们对明君贤臣理想社会的孜孜追求。
(二)建安文化观念的影响
建安时期的神女发扬了汉水游女可望而不可即的主题,从神人相遇到殊途陌路的整个篇章都弥漫着凄凉的氛围,这与建安时期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及文人独特的创作动机密不可分。严格的门第观念和封建礼教渗透神女辞赋,动荡年代要求士人远离风花雪月而肩负社会使命,因此神女辞赋中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悲剧意识。
建安神女是文人士子阿尼玛原型的心理投射。荣格认为,阿尼玛是潜藏在男子身上的女性意识,像女巫一样千变万化,极具独立意志,令人难以捉摸和把握。神女幻梦根源于男性的阴性特质,是自上古起便累积于男性经验中的女性意象。作为阿尼玛意象的神女冰清玉洁,与文人有仙凡之隔,来去无踪、不可求思,乃有“人神道殊”之惆怅。文人与神女的婚恋也呈现出典型的阴性文化气质,多与夜晚、水畔、幻梦等因素融合。建安文人的阿尼玛意象多附着于求而不得的文化理想之上,塑造出了虚无缥缈而魅力无穷的神女幻梦。
神女想象蕴含着文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其形象细腻多变且极富yyQXDnH7xQcbXaGSxMyrdw==人性之美。建安文学精神的苏醒使得注重个性的抒情传统回归,文学逐渐以表达人的自觉为旨归。文人未竟的理想抱 负构成了缺乏性动机,神女幻梦则成为精神寄 托和情感慰藉。建安七子一生追求建功立业和致世太平,屡屡以“佩花戴草”的潇湘神女抒发情志,又感怀于功名不就、世道多变,故笔下神女有美人迟暮、孤芳自赏之叹;曹丕多愁善感,常有忧生之嗟,笔下神女则脉脉含愁、无以忘忧;曹植渴望“流金石之功”,又一生跌宕,笔下神女隐含心寄帝王的惆怅。
(三)催生创作的历史契机
神女辞赋创作在建安时期之所以走向鼎盛,与曹魏文学集团的推动密不可分。北方汉水、洛水等流域在曹魏政权统治之下免于战火兵戈之苦,加之邺下文学集团对神女母题的钟爱,建安神女辞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迷人光彩。《三国志》载,建安十四年(209),赤壁归来的曹操“置酒汉滨”,宴请群臣,命随军征战的曹丕以及建安七子等文士共同作赋颂扬汉江神女,书写神女华光之下君臣遇合的治世与至美的人生境界,神女的文学创作自此走向巅峰。
[作者简介]陈晓蕾,女,汉族,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1] 出自马瑞辰撰《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
[2] 出自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卷六,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
[3] 出自袁梅译注《屈原宋玉辞赋译注》,齐鲁书社2008年出版。
[4] 出自曹植著《曹植集校注》卷二,赵幼文校注, 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
[1]出自叶舒宪《中国文学中的美人幻梦原型》, 《文艺争鸣》1995年第5期。
[2]出自张可礼、宿美丽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 凤凰出版社2014年出版。
[1] 出自陈延嘉、王同策、左振坤等校点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1]出自方勇译注《墨子》,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
[2] 出自常璩撰《华阳国志》卷二,齐鲁书社2010年年出版。